我们知道,对于蜀汉的灭亡,目前主流史学家对其中源自蜀汉政权内部的原因主要总结出以下四点,即刘禅昏庸、陈祗乱政、黄皓误国和谯周劝降。对于前三点,相关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也无需做过多解释。但对于最后一点,人们在认识上恐怕有相当的不足。似乎谯周的作为,只是在邓艾率魏军兵临城下时那一番慷慨激昂的说辞,令后主不做抵抗便开城投降。然而实际上,“谯周劝降”远不是只有一番说辞那么简单。可以说,正是由于此人的“骚操作”,从根本上否定了蜀汉的立国之基,甚至于在蜀汉亡后千余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于这个国家乃至其主要领导者的评价!
那么,谯周究竟做了什么?他又是如何从根本上动摇了蜀汉的统治基础呢?

“谯周劝降”的渊薮,或者说其理论基础,便是由谯周于延熙十四年(251年)之后主笔所撰写的《仇国论》一文。
文中虚构了“高贤卿”这一人物,以代表支持北伐曹魏者,作者自己则化名“伏愚子”,两人以小国能否战胜大国为题展开辩论。高贤卿以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胜项羽为例,证明小国面对大国并非无法获胜。伏愚子却反驳道,刘氏胜项氏的例子,只能发生在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之时。而如今汉、魏各安天命,蜀汉已传两代,曹魏已传四代,“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指望着在这个时候以小博大是不可能的。高贤卿又以大国内部变乱频仍、外部强敌虎视眈眈,说明小国仍有取胜之机。伏愚子则认为立国之道在于“周文养民,构建恤众”,如此才能“以少取多,以弱毙强”。出兵征伐,则是穷兵黩武,不但不能如愿,还会萌生变乱,导致土崩瓦解。最终在谯周笔下,经过双方的激烈辩论,伏愚子高举“养民恤众”的论调,逐一驳倒了高贤卿的观点,反讽的意味非常强烈。
众所周知,北伐作为一种军事行动,其战略、动机、步骤等均可以商榷。但对于蜀汉来说,北伐却不是简单地向曹魏开战,它是支撑蜀汉立国的重要法理基础。当曹魏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一谶语及“当途(涂与途在当时的古汉语中同音同意,可互用)而高大者为魏,魏当代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法理依据,“受天命代汉”。故蜀汉在建国伊始便鲜明地指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蜀汉承太祖(即刘邦,刘邦为汉太祖高皇帝,习惯上称高祖)、世祖(即刘秀)之血脉,将“恭行天罚”,征讨“窃居神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曹魏,以延续大汉的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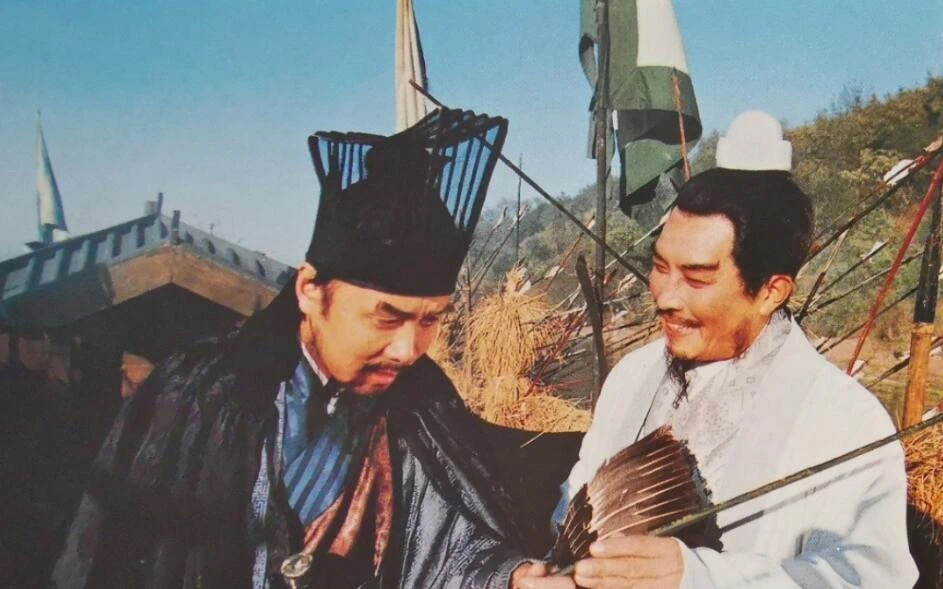
所以,蜀汉本以“恭行天罚”,即讨灭曹魏作为自己立国合法性的基础。尤其在后主即位时,诸葛亮为稳定国内形势、争取支持,从刘邦为义帝发丧从而占据了讨伐项羽的舆论制高点这一政治高招入手,说明高帝代表天下意愿诛灭项羽,以巴蜀为根基创立大汉,证明了巴蜀就是汉朝龙兴之地,“高祖因之以为帝业”。同时,进一步高举“恭行天罚”的北伐旗帜,并终其一生致力于此,以此坚定蜀汉上下复兴汉室的信念,并呼应先主刘备提出的“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从而得到了广大蜀地百姓的支持。所以《仇国论》中高贤卿所言刘氏胜项氏,正是孔明北伐的理论基础。孔明死后,先后主政的蒋琬、费祎虽不再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仍不放弃趁曹魏内部动荡时伺机出兵,姜维利用司马氏与曹氏争权之机,屡出洮西、狄道,便是忠实执行这一战略——这也就是高贤卿所述趁大国内乱而伐之的取胜之道。
然而谯周却以儒家所谓的“施仁政”为由,抛出“养民恤众”的论调,从道德层面上抢占制高点,掀翻了孔明以来蜀汉所秉持的北伐大业的理论基础。他将以小博大说成是穷兵黩武,将伺机而动看作是萌生变乱的前奏,由此完全否定了蜀汉的北伐政策,这无疑让以“恭行天罚”为立国之基的蜀汉被抽空了支柱。

谯周在作《仇国论》后,迅速以其为当时蜀中学者翘楚的身份,将否定蜀汉立国的论调大肆传播。其实早在谯周之前,蜀中已有周舒、杜琼等人以所谓“代汉者当涂高”来宣扬蜀汉必被曹魏取代,但诸葛亮在主政时作《正议》一篇,以刘邦弱而破项羽、刘秀弱而灭王莽,证明“王者之兴,在德不在力”,蜀汉是“据正道而临有罪”,在蜀地引发强烈反响,如此有效对冲掉了“代汉者当涂高”等负面舆论的影响,赢得了广大臣民的政治认同。
但孔明死后,师从杜琼的谯周立即重新捡起“刘氏祚尽”的大旗,公然称“先主讳备,其训具也”(《三国志·蜀书·杜琼传》),即备字有“具”的含义,乃完全、完尽之意,意思是刘氏到这里就到头了。景耀五年(262年),宫中有大树无故折倒,谯周对此解释为“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三国志·蜀书·杜琼传》)大乃魏的意思,大树象征大魏,倒音同到,大魏将到,蜀汉又如何继续长久下去呢?

在谯周的大肆鼓吹之下,蜀地间迅速弥漫起了悲凉的亡国氛围。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因毌丘俭、文钦起兵讨伐司马氏,决定趁机响应、谋划北伐,身为汉军大将的张翼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三国志·蜀书·张翼传》)其反对北伐之理由,竟与《仇国论》中“养民恤众”的观点如出一辙,可见谯周的主张竟渗透到了汉军高层。不仅如此,“瞻、厥以维好战无功”,从而上奏后主罢姜维兵权,“以阎宇代维”(《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诸葛瞻》)。诸葛瞻是孔明之子,董厥则被孔明誉为“良士”,连这二人也站在了北伐的对立面上,甚至想用黄皓的同党阎宇来代替姜维,可见此时蜀汉的舆论已经完全倒向了谯周否定北伐的论调。
身为谯周学生的陈寿,在日后写《蜀书》时,更是全盘继承了老师的观点,批判蒋琬、费祎“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批判姜维“翫众黩旅,明断不周”,总之凡是高举孔明北伐旗帜的,都被视为庸臣,以此间接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来对这个国家主要领导者的评价!

曾经的蜀汉在孔明的带领下,全国皆以复兴汉室为念团结一致,故虽然在三国之中国力最弱,却能够通过高举北伐旗帜有效调动、运用全国的资源,不仅大大促进了蜀地的经济发展,更使得蜀汉成为三国之中最具积极性和进取精神、同时也是民变最少的国家。
可随着北伐大旗被放倒、亡国言论充斥其间后,蜀汉完全失去了孔明乃至蒋琬、费祎主政时期的活力,所有人都开始醉生梦死,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姜维在决策层中屡受排挤,最终变成了“孤家寡人”。身为丞相的继承人他,在蜀汉灭亡的前一年,抱定决心进行了最后的抗争。然而,整个朝堂之上,他竟找不到一个战友。无奈之下,孤军出征的姜维只能率轻军出侯和,终因力量不济无功而返——到这个时候,蜀汉就算不会马上灭亡,也只能是苟延残喘了。

想当年,姜维归降蜀汉时,曹魏遣人持其母书信劝其反正。姜维则被孔明复兴汉室的信念所感召,回书答其母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三国志·蜀书·姜维传》)暗誓他将以光复中原、还于旧都作为自己的志向而奋斗到底。在孔明之后,他接过丞相的衣钵,依然为复兴汉室不懈努力,然而他奋斗了大半生、一心念之的汉室,却已然因为《仇国论》的风靡而视它为敌人。当“恭行天罚”的号角不再响起,当“据正道而临有罪”的壮志飘逝消散,汉室也就无所依托,就算没有邓艾、钟会,它也只能寿终正寝。或许正因如此,数百年后的罗隐在读史至此时,才不得不发出“两朝冠剑恨谯周”的慨叹!
1《三国志》《华阳国志》《汉晋春秋》
2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
3张明扬《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
4若虚《大谋小计五十年:诸葛亮传》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