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4所985高校约2000名学生进行追踪调查。
在学校、考场和格子间里不停地“卷”。
才能长久地解决内心的困扰。”
以下是他的讲述。
责编:倪楚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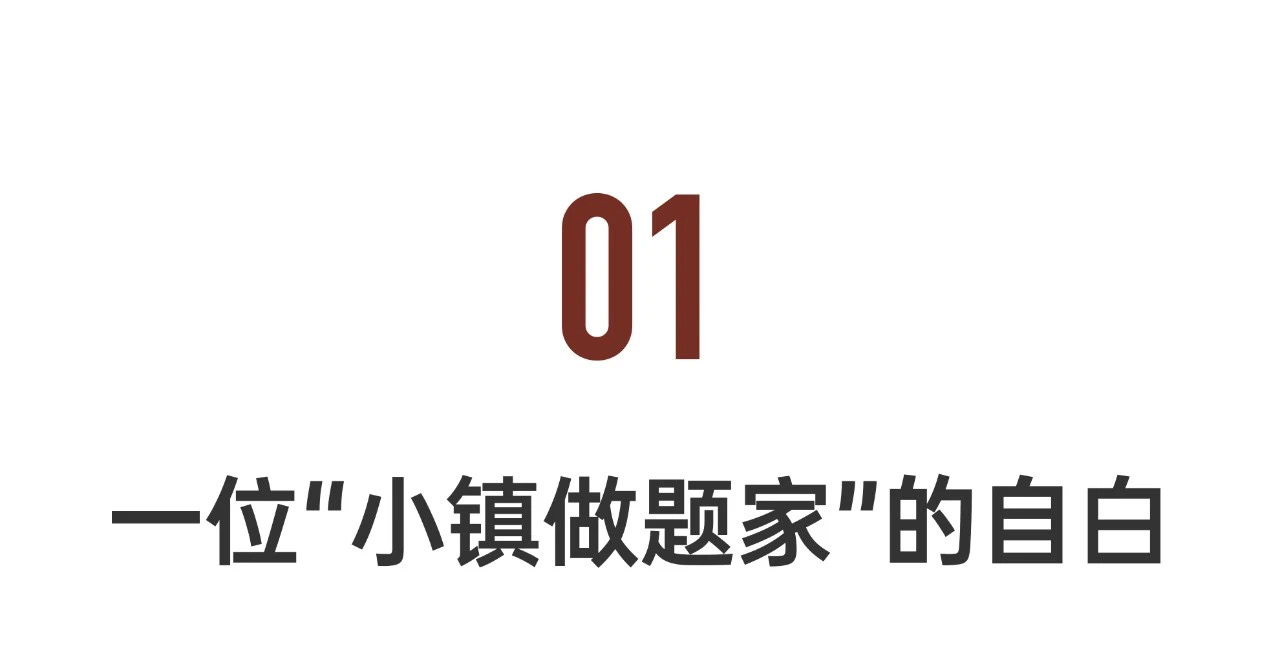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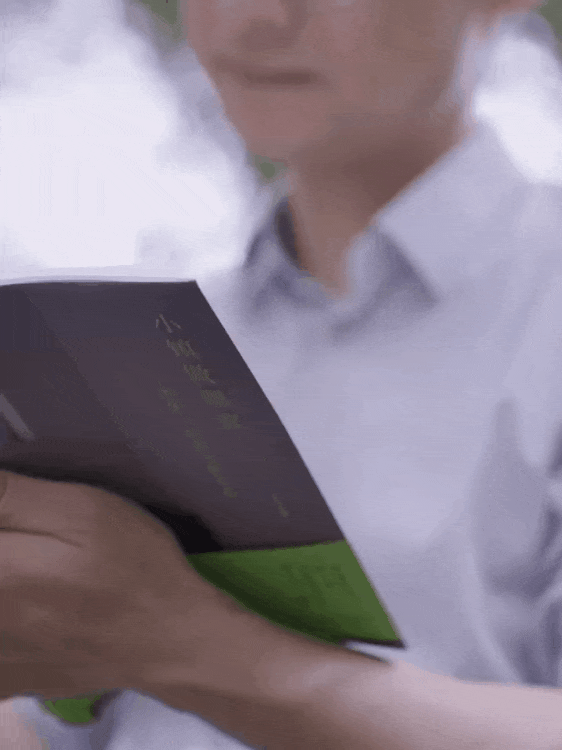
2020年的时候,“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在线上火起来了。有三条标准:1、出身农村或者小镇;2、擅长做题,通过高考,进入一流大学;3、缺乏视野和资源。每一条都特别的客观,好像是摁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一样。
包括出现了一些污名化的现象,说他们“视野狭隘”、“综合素质不高”、“没出过什么远门”、“格局小”、“只会做题”等等。还有人会说你们为什么读书的时候只会死读书,现在就会抱怨,自艾自怜。
不是的。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所谓“小镇做题家”。我在安徽农村长大的,那时候还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

小学是在村里上的,条件很艰苦,一下大雨,老师就不让我们上学,怕建筑塌了。也没有课桌,只有桌面,底下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普通话,都用方言带我们读课文。从小学到初中,我从来没有讲过普通话。高中到了市里面,情况一下子变了,有课桌,有很专业的老师,大家都讲普通话,我一下傻眼了。因为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不敢讲,我的同学很多人觉得我是哑巴。慢慢地摸爬滚打,好不容易适应到毕业的时候。高考考得很好,是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我们还是个省重点。但是填志愿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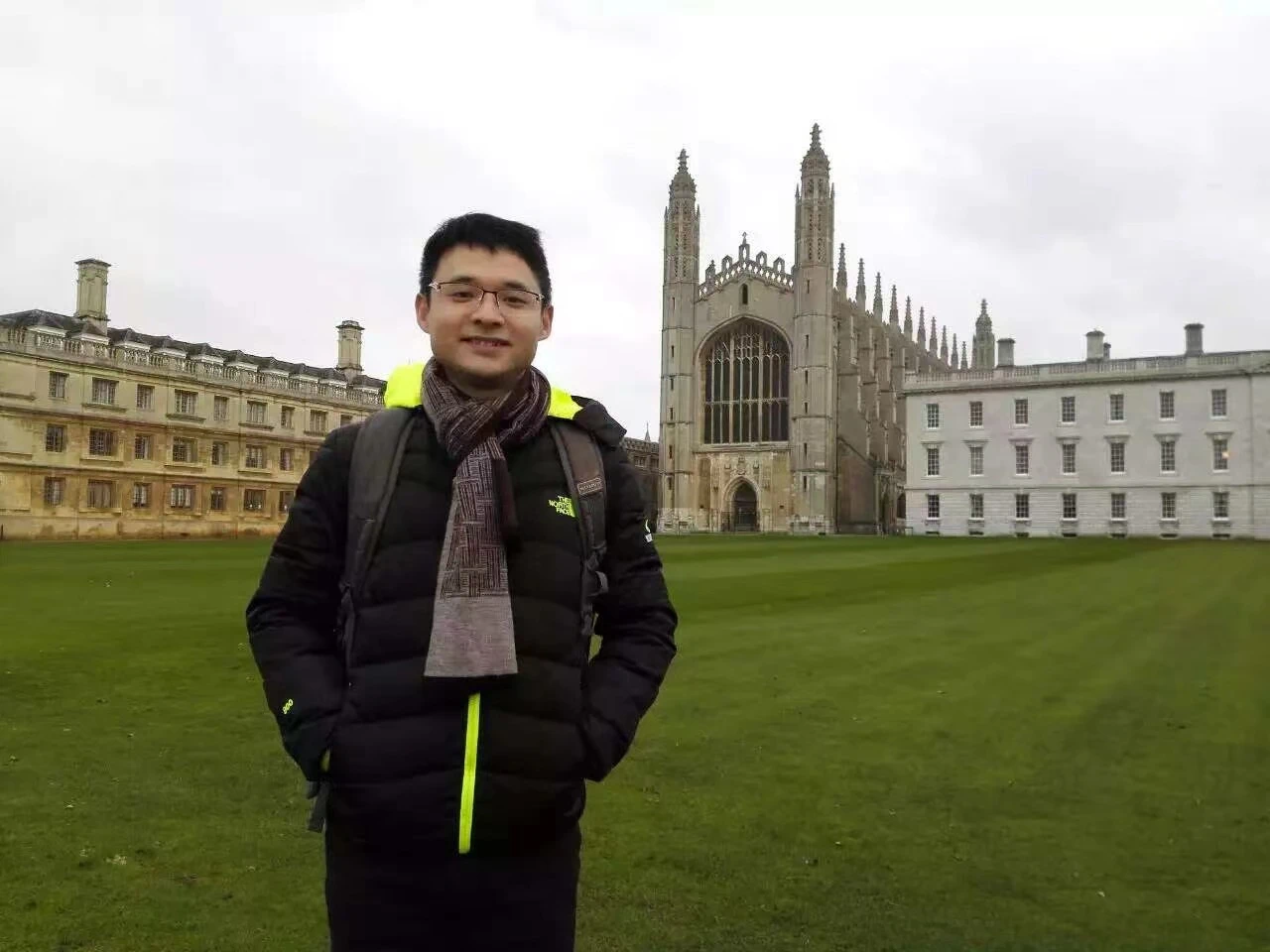
像我这样出身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天花板,玻璃天花板,你看不见的。我们小村子里面就没有谁上过特别好的大学,最好的是安徽大学,你就会觉得好像那是自己的人生顶点。想着综合类大学学费比较高,我要去一个师范类学校,可能会有学费补贴,最后就填了华东师大的英语专业。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北大是可以上的,比复旦的分数线也高了二三十分。我访谈的很多学生都是这样,我记得有一个学生跟我讲,填志愿的时候爸爸妈妈觉得保险一点,做个医生,做个老师。他自己觉得这样太局限了,想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到了大学以后,我的室友特别好,会拽着我出去玩,参加一些party。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那些社交场合,party开到一半我就跑出来。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会跟我们讲戏剧,朗诵莎士比亚,和我们分享他们在美国、法国的留学生活。我就觉得那些离我的生活实在是太远。因为这样的经历,我可能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早期的教育经历和家庭的生活经历对于个人的影响。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老家,我就在我们家老屋的大厅里面,把大桌子摆开,然后去跟隔壁的孩子说,你们到我家来,我给你们辅导功课,我不要钱。
我跟他们讲上海的摩天大楼,讲金茂大厦,我说城市里面可好玩了,如果你能够到城市里工作的话,就不用像爸爸妈妈那么辛苦了。但是讲完以后,发现没有用。放假的时候给他们辅导一下,过段时间再回家,他们的成绩好像又回去了。那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我想把这些困扰表达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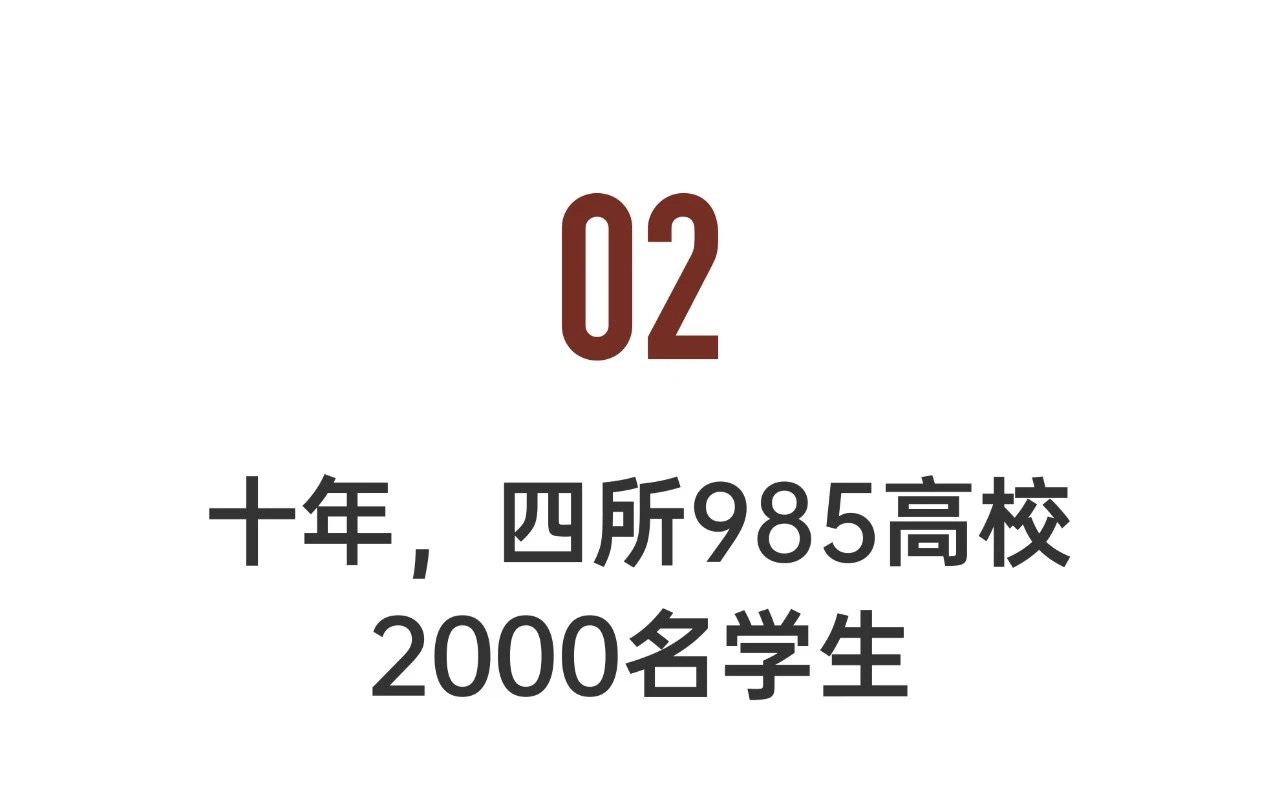
2013年,我在4个985学校,每个学校找500个学生,分别在他们大一结束、大二结束和毕业半年后的三个阶段,先进行问卷调查,紧接着做访谈。我其实一直不太愿意把我研究的学生群体叫做“小镇做题家”。我最初的研究想法很简单,就是精英高校里面的农村籍(包括农村和乡镇)学生。因为我跟学生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他们说,“这个类型说的好像就是我”,“我觉得好无力、好悲哀”。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要给人力量的,而不是把人框在一个架构里面,让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从而失去了向前的动力。最后同意《小镇做题家》这个书名,也是因为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努力,推动大家对这个群体的学生有更多的了解,也对“小镇做题家”这个词语有一个新的理解。

▲
纪录片《高考》,一名高中女生在晨读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一些共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整个高中生活就是“培养做题机器人”。早上6:30起床早读,上午四五节课,下午四五节课,中间吃饭吃个5分钟,晚上10:00回宿舍以后还得学习。很多同学都因此出现了健康问题,甚至延续到大学以后。这种高度竞争性的教育模式,让他们对于自己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完全没有想法,因为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到了大学以后,面对突然的空闲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我的一位受访者叫作小毅,高中老师告诉他:“成绩是最重要的,现在苦一点,到了大学就不苦了。”但是到了大学,他才发现还有很多成绩以外的东西,但他却不知道怎么把时间花在学习之外的其他地方。小毅回忆说,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教室、图书馆。每次经过游泳中心、学生活动中心,都没有推进门进去看一看。到了毕业的时候,他说,“当初应当推开门进去看看的,也许这四年会过得不太一样。”
纪录片《出路》拍摄了不同阶层孩子的命运
左:来自甘肃马百娟在做完农活后读书
右:北京女孩袁晗寒辍学后在父母资助下,在游历欧洲
很多人会讲,农村的孩子很“自卑”,这么说好像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而忽视了背后的社会原因,其实这就是一种“谴责受害者”。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自我低估”,这和两个社会阶层的价值认知是有关系的。社会流动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生活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个不那么值得肯定。那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童年其实也挺美好的,下雨天在稻田里面玩,会放鞭炮,会恶作剧什么的。

▲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贫寒的陈孝正
但是一到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当中,得到肯定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会才艺,会跳舞、会唱歌,会弹钢琴。农村孩子不擅长这些,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社会能力不如别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做一些探索的时候,就会发怵。比如说我访谈过的一个学生刘心,大一想报名院学生会,但是文艺部需要才艺,她不擅长;宣传部要会电脑,她高中很少接触电脑;组织部需要一定的口才,她口才不行……一系列的否定,框定了她尝试的范围,也框定了她尝试的深度。最后她进了生活部,负责一些“幕后工作”。到了大二访谈的时候,她觉得在生活部锻炼机会不多,就退出了学生会,最后她的生活又只剩下了学习。我们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可能不像父辈那一代,有个大学文凭可能意味着很多。尤其是现在,你还要做很多的事情,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探索,积累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资本……这些用刷题的经历是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处于竞争的劣势了。

但是不是年轻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思考,他真的就不会赋予自己生活意义?我想可能低估了我们年轻人。“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思考的方式,是所有人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以后,都可能会有的一种独特的生存心态和人生探索。包含了他们对于过往的生活经历的反思,他在思考自己是谁,自己的生活经历,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性。我访谈的所有学生,其实每个人都会反思,都尝试去改变。当他们在用“小镇做题家”这个词自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做反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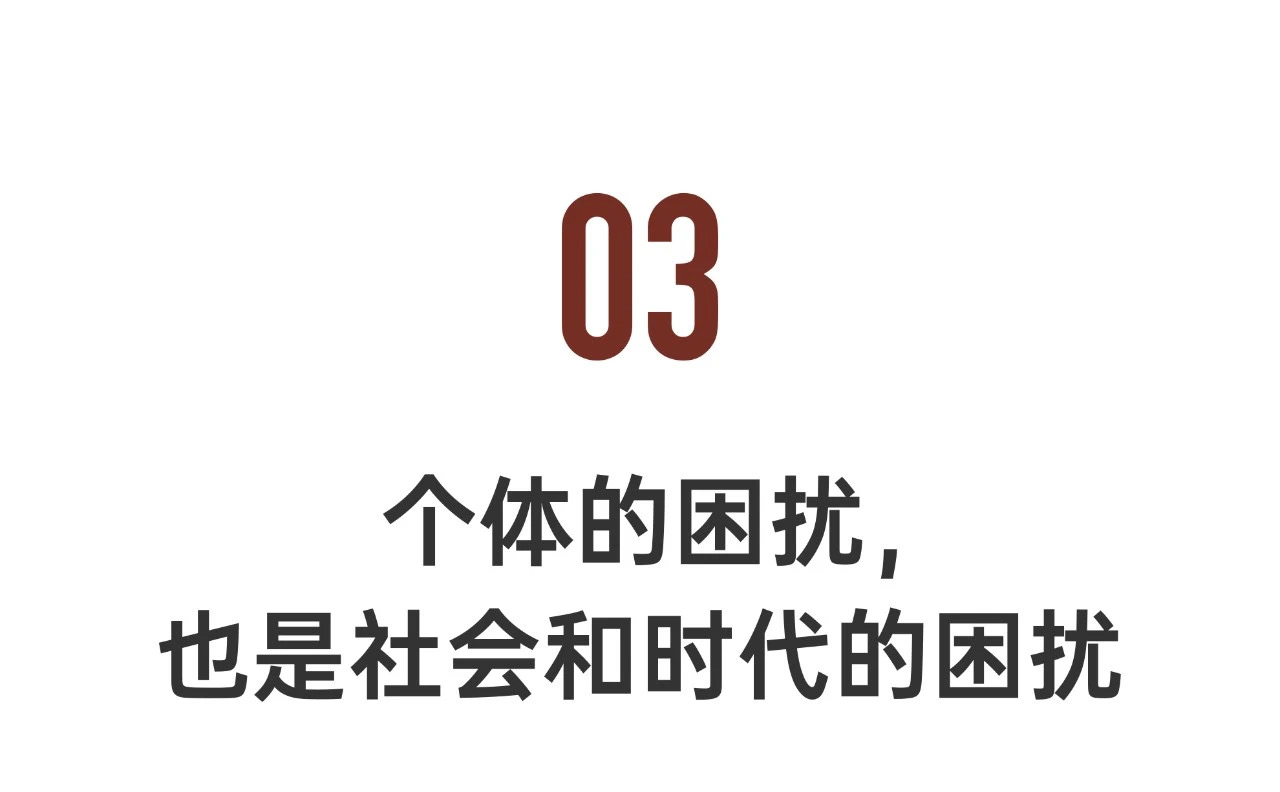

研究生的时候,我转向了教育专业,关注农村教育,希望为更多农村学生做一些事情。现在我是教育科学学院的,我的学生将来大部分是会做老师的。我会尽量培养他们的社会学思维,让学生看到社会阶层方面的教育不平等。而不是单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是不是智商不够,是不是努力不够。这样的话也许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可以共情。比如小时候我的学业还行,不是因为我特别聪明。很多孩子其实比我聪明得多,但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只能出去打工。同一个群体内部,有些人能上大学,有些人不能上大学,就是努力不够或者智商不够。这是“贤能主义”与“优绩主义”给我们的故事版本。我想驳斥这个版本。


前几年我开始带一个公费定向师范班,大部分学生来自粤东西北的农村,毕业之后会回到家乡工作,服务的对象就是农村的孩子。
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农村来的孩子不太善于向上社交,这样会错过很多机会。我就带着他们跟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一个个吃饭,院长、副院长、系主任还有教授都吃过了。
我自己也坚持跟学生定期聊天,他们会跟我吐槽学校生活,我也会跟他们聊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特别鼓励他们出去,在周边旅游,我还会送一些票给学生,让他们去听听音乐会,看看展。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将来就是你们要教的那些孩子的眼睛。
如果思考得再深一点,大学到底肯定什么?我们的教育内容要不要做一些调整?我们教育社会学的人经常讲的一句话,个体的困扰,往往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困扰。这些认识和思考,不是中国独有的,全球范围内的年轻人都是有共识的。早在10多年前,英国就开始做相关的研究,有一篇论文标题就起得特别的直白:credential is not enough,文凭还不够。“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的确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所面对的社会结构性困境。在教育系统里就要拼命做题,出了校门以后,又面临一个分秒必争的竞争环境。

现在网上还经常说“大厂做题家”,就是到了大厂以后,还只会按照做题的模式使劲地卷。人生好像一直被困在学校、考场,还有工作场所的格子间里面,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中国人还是比较信奉教育改变命运的。但是假如我们的教育只剩下标准答案和高分数,只剩下优胜劣汰和成王败寇,那么它就注定只能制造“小镇做题家”、“大厂做题家”,而不能使我们的学生看见更加丰富的选择,拥有更加丰满的人生。
在我看来,教育不是让他们看到另外一种生活高大上的地方,而是重新去肯定自己原来生活的一些价值。当他们走出村子,走出原来的生活以后,他能够从过往的经历中找到价值,是原来的生活给了自己现在的生活。这个可能是教育更加终极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长久地解决一些内心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