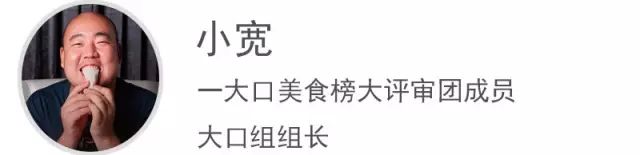
1910年春节,宣统二年,末代皇帝溥仪那年四岁。按照惯例,皇室会在太和殿举行国宴,招待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皇帝只会出于礼节亲临,而不进食。宴会菜品极尽奢靡,据记载: “太和殿大宴原设宴桌210席,用羊百只、酒百瓶。”事实上,四岁的溥仪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因为他还太小。

旧时宴请,场面宏大,礼节讲究颇多。
那一年的上海,已经流露出关于春节的某些洋派气质。春节当天(2月10日)出版的《申报》上有一篇杂谈:“新年各处同也,而上海之新年特别者:门上悬松柏,西例也;贺岁穿貂褂,京式也; 体面商人元旦必手笼箭袖,仿宫派也; 地方绅董初三日穿补褂拜年,忘忌辰也。”
春节之食,即便在动荡的帝国之末,也未曾改变其面貌。阖家、祭祖、团圆、互道新禧,都是必然的路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食是奢望,能够吃一顿饱饭已经是安慰。

放鞭炮是人们童年记忆里,对于春节深刻的印象。
两年后的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改用公历。那也是一个一切求新的年代,旧的、传统的,皆要废除,包括旧历中的新年。原指农历岁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来指公历1月1日,农历岁首则叫“春节”。政府发出告示:“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 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
1935年,一位作家写下一段关于中国人与食物的文字。他说:“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 ‘吃’。”这个人是林语堂。同样是在1935年,林语堂写下了一篇文章——《记元旦》:“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因而想到春联、红烛、鞭炮、灯笼、走马灯等。在阳历新年,我想买,然而春联走马灯之类是买不到的。我有使小孩失了这种快乐的权利吗? 我于是决定到城隍庙一走,我对理智说,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不过要买春联及走马灯而已。”

春联,沿用旧时对于春节的礼仪。
还是1935年,鲁迅也写了一篇文章——《过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从1912年开始,鲁迅就没有过过旧历年,过年对他来说,无所谓节日,更无所谓年夜饭,只是年纪大了,喜欢和孩子们一起放鞭炮。在之后的1936年春节,那也是鲁迅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他在日记里写道:“阴历丙子元旦。雨。无事。晚雨雪。”
鲁迅不是一个喜欢过年的人,但他的著名小说《祝福》是以过年为开头的: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 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

一锅炖肉,被搭配各类食材再制菜肴。
在某种程度上,春节属于童年。梁实秋写过一篇章——《北平年景》: “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肉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 一一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 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现今饺子里放银币的传统仍在,不过是放了更常见的硬币。
饺子也是必需品,梁实秋写道:“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做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胀。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的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作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

“一品锅”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摆放各类食材。
那时的年饭标配是暖锅,就是梁实秋说的一锅炖肉,加上蘑菇、粉丝、山药, 一碗又一碗的,上海称作“全家福”, 到了安徽,则是胡适家的“一品锅”, 据梁实秋撰文回忆:“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地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一层油豆腐,点缀着一些蛋饺,紧底下是萝卜青菜,味道好极。”到了广东的客家,则是盆菜,各种食材分门别类,层层堆积,里面的内容没有一定之规,一般会有萝卜、猪皮、鱿鱼、冬菇、鸡肉、炆猪肉,上层总会是精贵的食材,下面是吸收汤汁最佳的食材,一层层地团圆着吃。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沿用公元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农历新年定为“春节”。
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是在苏联莫斯科度过的,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异国他乡度过春节。毛泽东对过春节也不太在意,他的厨师程汝明回忆,有一年的年夜饭,他做的是不放酱油的红烧肉、腊肉苦瓜、辣椒圈、鱼头豆腐、盐水鸡、扒双菜和一小盆三鲜馅饺子,加上中午的剩菜……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私人宴请溥仪,还请了章士钊等作陪,桌上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唯一能撑点场面的是有瓶葡萄酒。

毛泽东私人宴请溥仪,唯一撑场面的就是葡萄酒。
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饥饿和物资匮乏。这是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的普遍记忆。
1957年2月3日出版的《北京日报》 上的一篇报道记录了一户普通人家的年夜饭:“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然而到了1958年的春节,国家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 粉丝、糕点等种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每月每人供应猪肉六两,牛羊肉五两。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棕子,供应时间在三天至七天以内,售完为止。到了1959年,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糕点、糖块也按人口分配,采取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

1955——1957年的粮票,每月每人供量有限,凭票购买。
能吃到白面已经足够叫人羡慕了,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李锦是江苏射阳人,他写了一系列回忆饥饿年代的文章:“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凭票购物年代,人们抢购的场面。
1959年春节, 李锦家里吃的是一锅胡萝卜:“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吃的是胡萝卜饭, 很少很少的米,也没有菜,是切碎的胡萝卜里撒上一把盐。”
年年难过年年过,即便物资如此紧张,吃一顿年夜饭也是家家户户的渴望。60年代的上海条件要比大多数地区好很多,上海厨师李兴福回忆60年代的上海人如何精打细算过春节:“那时买鱼要鱼票,买蛋要蛋票,买豆制品要豆制品票,为了一顿年夜饭,每户人家往往要在年前的两个月开始省吃俭用,囤积票子用于过年大采购。每年年前,小菜场里半夜三点钟开始排队。要买到些禽类过节,大致得花6~8个小时,冬天脚也要冻僵,为的就是饭桌上的一碗蒸带鱼、一锅老母鸡汤。”

人们在百货店刚开了一条门缝,就迫不及待的蜂拥进去。
到了1970年,年夜饭上可以选择的食物要多一些了,那年春节期间的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

70年代上海,用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招待客人十分体面。
上海美食作家沈嘉禄回忆70年代的上海春节食俗,年糕是家家户户都要吃的,“买年糕也要排队,还要凭户口簿,小户多少,大户多少,还煞有介事地盖个章,防止有人多买。有些人家连年糕也买不起,户口簿就借给邻居买,邻居烧了汤年糕,盛一碗相赠,也是情意暖暖的。门槛紧的上海人不买刚从厂里做出来的年糕,因为此时的年糕含水量大,称分量显然吃亏。过一夜,甚至等年糕开裂,分量就轻了。此时用同样的粮票钞票买,年糕能多出一两条来。平常上海人吃青菜汤年糕,加一勺熟猪油,又香又鲜,可以吃一碗。过年时则吃黄芽菜肉丝炒年糕,上品点儿的,做一盆韭黄肉丝炒年糕,招待客人体面过人噢。”
待到1979年,北京的市民们终于不再为年夜饭发愁了,尽管那时候还是凭票供应。当时的报纸上记载: “春节市场上有金浆、西泉、潞泉白酒投放市场,大核桃巧克力、话梅糖等恢复生产,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新产品安排生产供应。”

西单菜市场旧貌街景。
1992年,西单菜市场推出五种家庭套餐,每套50~70元,回家简单一加工就是丰盛的年夜饭。1994年,人们开始外出吃年夜饭。1996年,餐馆里的年夜饭也开始需要提前预订了......

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王景愚小品《吃鸡》。
一场变革开始了,而变革的细节总是从一餐一饭中体现出来。80年代,人们的年夜饭上添了一道“大餐”, 那就是从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一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 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曲。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 一曲《我的中国 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 大年三十,一家人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饭,一边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中国百姓渐渐约定俗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过节方式。
同样是80年代,我出生了,对于年夜饭,我拥有了个人记忆。
我的老家在河北的一个小镇,小时候过年前要杀猪,我和爸爸去赶集买年货。我记得爸爸当年锃新的黑色二八自行车,永久牌,我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

很多地方都有杀年猪的习俗。
那是80年代的末期,空气中似乎有 “年味儿”: 鞭炮屑的火药味、熏肉味、大白菜味、冰冻的带鱼味、葱花炝锅的味、蒸年糕味、油坊的芝麻香油味、刚写好的春联未干的墨汁味、澡堂子里的蒸汽味...... 种种味道散漫在镇上,似乎刚下过一场雪,踩上去有咯吱咯吱的声音,过年的味道就从路边的积雪里冒出来。爸爸会买许多年货,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慢慢地骑回家。

巧手的主妇会在过年的时候动手做一些别致的面食。
此时妈妈已经在家准备过年的馒头,蒸上几笼,屋子里都是蒸汽。奶奶手巧,会在过年的时候动手做一些别致的面食: 剪出几个刺猬; 用红小豆点缀作眼睛做几个兔子; 还会费心地做几个面老虎——会做别出心裁的面食,也是考验一个主妇能干的标准。
妈妈每到过年才会熏一次肉,锅底放糖,肉煮好了,放在铁质的烙子上,上糖色,最后放到陶制的坛子里腌制。这是我小时候美味的极致,我经常忍不住诱惑,偷偷掰一块迅速放到嘴里,自以为不会被大人发觉,似乎是我自己的秘密。

2009年春节,物质丰富不再因新衣吃食而期待过年。
年夜饭是最隆重的一顿饭。我要给长辈拜年,穿上之前觊觎已久的新衣服,吃饭之前先要在院子里放一挂鞭炮。煮饺子,妈妈做鱼,鱼一定是有头有尾的,还有红烧肉,少不了年糕; 家里所有的灯全部打开; 即便在这天失手打碎一个盘子,大人也会说“岁岁平安”; 爸爸会喝一点儿小酒,我很小就开始陪着他喝酒,不过这是过年才有的特权。
这只是我记忆中的一顿年夜饭,也是华北平原寻常人家的一顿寻常年夜饭,未曾隆重,却也热闹,不擅烹饪,却也美味,一菜一味都融入记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顿年夜饭,上海要吃蛋饺,广州要吃盆菜,湖南少不了腊味,北方是饺子,南方是汤圆,不同地方总有自己过年的方式,不同人家也会有自己的传统。

广东的盆菜,丰富豪华
年夜饭其实是团圆饭,一家人围坐,其乐融融,吃什么反而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准备这顿饭的时光,对这顿饭的期待。一顿饭传承着中国人对于年的认识。
到了90年代,城市里的人们开始在餐厅里吃年夜饭,先是1992年,西单菜市场推出五种家庭套餐,每套50元至70元,回家简单一加工就是丰盛的年夜饭。到了1994年,人们开始外出吃年夜饭,而到了1996年,年夜饭也开始需要提前预订了。
2003年,我入职《新京报》,做了一名美食记者。每年到了春节之前,必选动作是做一个春节美食专题,推荐各家餐厅有意思的年夜饭套餐。从2004年春节到2013年春节,我整整推荐了10年。
这10年也是中国餐饮行业迅猛发展的10年,北京的餐厅越开越多,不同规模,不同菜系,不同风格,人们外出吃一顿年夜饭成了寻常家庭的必选动作,预订年夜饭的时间也越来越提前,有一些生意火爆的餐厅,往往需要提前一个月预定。而餐厅做年夜饭也越来越模式化,有一些餐厅甚至把年夜饭分成上下两场,晚上五点到八点是一场,八点钟之后再开一场。
 新世纪,外出吃一顿年夜饭早已寻常。
新世纪,外出吃一顿年夜饭早已寻常。
2004年春节前,我给报纸写的新闻稿里介绍当年的年夜饭情况:“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各大餐厅就已经开始抢接年夜饭的订单了。与往年相比,今年年夜饭形式突破不大,为了保证菜品的质量和上菜速度,超过八成的餐厅采取由店家统一安排菜式的方法。相对而言,新开餐厅预定量不如老字号多,部分知名餐厅从10月开始接单,如今已订出去五六成。”
而到了2005年,我在推荐餐厅里提到了仿膳的“满汉全席”年夜饭套餐包括:开胃冷盘、豌豆黄芸豆卷、金汤玉肚、翡翠龙钱、鸿运当头、乌龙望春、左宗棠鸡、佛手献宝、福禄双全、连年有鱼……每位价格268元;而四川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是:冷菜有八味围碟,热菜有清汤竹荪蟹肉羹、王府一品鲍、鱼香明虾球、蔬香樟茶鸭(配荷叶饼)、茄鲞、蟹黄娃娃菜、水煮鹿肉、辣味银雪鱼,风味小吃为四样,还有水果拼盘一份,每桌1680元;又一顺推出的800元的“团圆宴”,不仅包括8款凉菜,还有镇店名菜腰果虾球、滑洋四宝、烤羊腿、清真烤鸭等10多款菜肴和面点。
2006年,我推荐的是各种饺子,其中包括百饺园的饺子,年夜饭的菜单上饺子品种包括:“猪肉山野菜 12个 猪肉芹菜 12个 猪肉青椒 12个 西红柿鸡蛋 12个 鲜虾 12个 羊肉香菜 12个 猪肉豆角 12个 猪肉茴香 22个 猪肉胡萝卜 22个 全素馅 22个。”
那一年,北京流行的还有各种餐厅推出的年货礼包:砂锅居饭庄,推出了豌豆黄、小豆糕等近20种小吃糕点,顾客购买20元以上,免费包装精致礼品盒;上海老饭店今年特地准备500套外卖半成品年夜饭,每套售价680元,有“红油焗明虾”、“红焖元蹄”、“黑椒炒牛肉”、“八宝炒辣酱”、“三鲜烩鱼肚”、“香辣羊肉煲”、“糖醋大黄鱼”、“细纱八宝饭”、“黄金麻饼”、“团圆一品锅”共10道,买回家加热即食,十分方便。

中国大饭店今年的年货礼包
2008年,我做的专题是“新潮年夜饭”,讲的是各种新鲜的馆子,有不少餐厅现在都已经关门大吉了。到2009年,我做的选题则是“实惠年夜饭”;2011年,寻常餐厅的年夜饭都已经没得可聊了,于是做了一个选题,外出过年,推荐了郊区的年夜饭,香港的年夜饭,以及国外的年夜饭。
2012年临近过年的时候,我还撰写过一个新闻:“1月12日,豆果网携手旅游卫视‘美味人生’栏目发布《2012龙年春节饮食消费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龙年春节饮食消费选择在酒店餐馆吃年夜饭的比重首次出现下降情况,从去年的14.3%降至今年的14.1%,选择自制年夜饭人群的比重上升;70后、80后自制年夜饭上升明显,酒店定制和自制年夜饭差价大,传统美食仍是春节主打。”
直到如今,互联网也成了改变年夜饭吃法的要素,有了各种外卖、美食O2O项目,用 App 直接就可以请一个厨师回家做年夜饭,想有年夜饭大礼包,也无需去排队购买,手机上下单就可以收到。总之,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年夜饭也不断变身,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年夜饭不断变身,大家依旧期待那顿团圆年饭。
春节,也是一个农业文明的产物。在旧时,农闲了,才有大把的时间为过年做种种细致的准备。在一个工业化的都市里,对过年种种经历的追忆,是一次集体抒情,也是站在此地遥望彼时的感怀。只是越长大,越近乡情怯,明知时间变了,怀旧于事无补,但依然期待一顿团圆的饭桌。坐在桌子边的父母都老了,一年一年地老去。
祝福大家2017年好事多多!好食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