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 [法]让·哈茨菲尔德
编辑丨吴酉仁
1994年4月6日晚,卢旺达共和国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的专机在首都基加利(Kigali)的机场上空爆炸。
这次袭击点燃了卢旺达大屠杀的引信。第二天黎明,屠杀在基加利街上爆发,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国家。在此后的数月时间里,全副武装的胡图族军人大肆屠戮温和派胡图族人、特瓦族人和图西族人。遇害人数约在50万-100万之间。
大屠杀更长远的历史背景,是卢旺达国内的胡图族与图西族长期对立。1962年之前的比利时殖民时代,占人口约18%的图西族是统治民族。比利时人离开后,政权转移到了占人口约80%的胡图族手中,图西族成了被歧视和被压制的对象。卢旺达内战由此而起。1993年,代表胡图族人的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与代表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签订了停火协议。稍后的哈比亚利马纳之死,则打破了来之不易的和平,启动了种族灭绝的阀门。
发生在卢旺达尼亚马塔(Nyamata)的屠杀,是这场大屠杀的一个组成部分。
尼亚马塔坐落于遍布山丘和沼泽的布盖塞拉(Bugesera)。1994年4月11日,大屠杀从这个小镇的主干道上开始。大批图西人仓皇逃命,有的跑到教堂里避难,有的逃进香蕉园、沼泽地和桉树林中躲藏。仅4月14日到16日的三天里,在尼亚马塔和恩塔拉马(N’tarama,位于尼亚马塔20公里开外的另一座小村庄)的教堂中,就分别有5,000名图西人被胡图族民兵、士兵和众多邻居杀害。这片干旱红土地上的大屠杀由此拉开了帷幕。
屠杀一直持续到5月14日。
在这整整一个月里,训练有素的暴徒们带着屠刀、长矛和大棒,在卡云巴(Kayumba)的桉树林和尼扬维扎(Nyamwiza)的纸莎草沼泽地中,一边高声歌唱,一边包围和追捕那些逃跑的人。当地图西族约59,000人口中,有近50,000人死于屠刀之下,也就是六分之五的图西人死于他们之手——在整个卢旺达农村,图西族人口被屠杀的比例也差不多如此。
♦ 卢旺达政府在大屠杀发生地建立了诸多包括遗址、纪念馆在内的地标,引自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官网。
在此后的岁月里,这里的大屠杀幸存者同别处侥幸活下来的人一样,都变得沉默寡言。
他们的沉默和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沉默一样令人费解。一些幸存者解释说,“生活崩溃了”;另一些人说“生活停止了”;还有一些人觉得“生活必须要重新开始”。所以我回到了卢旺达(注:作者在1994年曾以记者的身份前往卢旺达调查和报道大屠杀),回到尼亚马塔,去拜访包括卡修斯(Cassius)、弗朗辛(Francine)、安热莉克(Angélique)、贝尔特(Berthe)在内的那些幸存者,说服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
他们中有很多人表示疑惑,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一个外国人讲述大屠杀,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想要倾听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没有拒绝我。他们解释了自己长久沉默的原因。比如,“感觉自己在大屠杀里陷得太深而被边缘化了”,或是“不敢再信任别人了”,他们感到灰心丧气、孤苦伶仃,“被彻底毁了”。还有人因为自己占据了亲朋好友生存的机会而活下来,或者因为重新开始适应正常的生活而感到不安,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谴责。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不认可历史能给我们以教训。借用一位女性幸存者的话来概括,大屠杀是由人类策划出的反人类事业,它太过疯狂又太过缜密,让人无法理解。
♦ 尼亚马塔屠杀中凶手们使用的武器,包括棍棒、砍刀等,保存于尼亚马塔种族灭绝纪念馆,引自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官网。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关于宽恕的问题。
应该宽恕吗?宽恕有什么用?为了揭示真相?为了缓解幸存者的哀痛,还是为了促进子孙后代的和解?谁有宽恕的资格?我们可以代替别人宽恕吗,比如代替亲属、朋友,尤其是在这个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对于那些并不要求被宽恕的人,或是在这方面毫无真诚行动的人,或是拒绝被宽恕的人,我们还能原谅他们吗?宽恕有很多种方式吗?宽恕分不同程度或不同阶段吗?如果感到自己无法做到宽恕,我们可以要求上帝或者一个比自己更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来代替自己宽恕吗?希望求得宽恕的人和宽恕他人的人分别能做出什么承诺?能够宽恕不承认自己过错的人吗?讲述宽恕的人必须是被伤害过的人吗?能够宽恕自己吗?
这些问题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悠久。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针对平民施暴的历史,还提出了关于宽恕的新问题:我们能够宽恕这些集体犯罪、国家犯罪和反人类罪的始作俑者吗?我们能够共同宽恕犯下这些罪行的活跃群体和同谋、团结支持他们的人民以及大规模犯罪的国家吗?我们能够宽恕那些只请求原谅却不对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的人吗?
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受害者而言,最直接的问题是:种族灭绝过后,能够宽恕那些曾企图消灭你的人吗?
♦ 尼亚马塔教堂祭坛上的桌布,这块布在大屠杀中沾满了血迹。现保存于尼亚马塔种族灭绝纪念馆。
事件发生数年之后,布盖塞拉的幸存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是“不能”。不过,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是否会随时间而变。
在尼亚马塔沼泽地中幸存下来的三个人的回答,有助于理解这种“不能”,她们的回答很好地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弗朗辛曾想象过,杀死她妈妈的邻居主动来请求她的原谅。她不会原谅他,她可以重新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但这一切她都无法原谅。西尔维则认为,问题不在于原谅,而在于和解。那些放纵屠杀的白人和实施屠杀的胡图人,都没什么好原谅的。只有公平正义才能给人带来宽恕;但大屠杀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无法磨灭的缺失感,一切的公平正义都太迟了。还有埃迪特,她是唯一打算宽恕的人,不过她给宽恕赋予了一种宗教色彩。她选择原谅,不是在否认他们的恶行,而是希望获得身心的平静。
尤为重要的是,对于宽恕,幸存者和杀手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可能让宽恕成为不可能的事。
幸存者、杀手、遣返者、政界、人道主义组织和宗教界的见证者......在所有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卢旺达大屠杀的角色中,幸存者是最不关注宽恕的人。即使和解的前景让他们感到焦虑,他们也只在被问及此事时才会谈起。反之,杀手是最常提起宽恕的人,但总是带有一种令人困惑的天真。
种族灭绝罪犯和普通战犯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后者在摧毁、折磨、强奸时同样非常野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常常能够扪心自问:如果想要得到受害者和他们自己的宽恕,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但种族灭绝罪犯不会。基本戈(Kibungo,卢旺达的一个小镇)的那些杀手们大谈特谈宽恕,也希望得到宽恕,但他们的语言中几乎从没有问句。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集体的宽恕还是个人的宽恕,无论宽恕有没有用,无论宽恕的过程是否痛苦,只要他们要求被宽恕,宽恕就是理所当然的。
♦ 一名14岁男孩在尼亚马塔屠杀中幸免于难,他在尸体堆中藏匿了整整两天。图为1994年6月他在尸骨堆旁留影。引自联合国官网。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杀手们可以想象仇恨、愤怒和怀疑对幸存者意味着什么,可以理解幸存者复仇的想法和行为;他们接受这些针对自己的激烈反应,但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宽恕这个行为对于幸存者的意义。一些杀手认为这应该是幸存者的主动行为,另一些人则认为事情很微妙,取决于对方的友好程度和性格。不管怎么说,他们理解的宽恕仅限于幸存者放弃仇恨。
于是,宽恕成了一种对等交易:用供认事实换取同等的宽恕和原谅。或者是走个形式:既然我已经受到惩罚,那我就应该被宽恕,因为我所承受的痛苦应该带来相应的宽恕。又或者这是一个把事情糊弄过去的机会:宽恕意味着忘记,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是回到美好旧时光的最佳方式,让一切重新开始,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杀手们似乎并不清楚对寻求宽恕者的最低要求:说出事情的真相,扔掉策略的算计,让受害者得以纪念和哀悼。
杀手们未曾想过,受害者一旦同意宽恕,就要遭受痛苦,因为这样做不仅是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还抹杀了他们通过报仇而获得慰藉的一切可能性。杀手们不理解,他们要求被宽恕,其实是在要求对方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看不到受害者所处的困境、所受的折磨和给出善心的勇气。杀手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像走程序一样寻求宽恕时,他们对受害者痛苦的漠视会让痛苦加倍。
下面是部分杀手在接受访谈时,针对“宽恕”的讲述。
埃利:杀戮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宽恕同样如此。在沼泽地进行屠杀的那段时间,我们从没有好好地谈论过杀戮;如今一切都已经结束,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否能充分地谈论一下宽恕。我要说的是:一种人是在杀戮结束之前,对自己的悔恨半遮半掩,凭着一己之愿离开沼泽地,留下一堆烂摊子(注:指屠杀尚未完结);还有一种人是真的悔恨,并会由此失去抢掠的收益和同事的尊重,这种人是应该被真心原谅的。但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我们所有的只是对入狱的悔恨,所以换来的也只是人们有限的原谅。无论如何,这也算是原谅,但它是仅存的原谅。如果让我说,这是被剩下的原谅。如果局势变化,它就会变得可有可无。在新的血腥动荡的威胁下,在未来它也不会持久。菲尔让斯:宽恕,就是抹去他人对你的冒犯。但只有听到原原本本的真相,我们才能被宽恕。在审判期间,我曾向受害者的家人请求原谅,我对他们讲述了我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想我会被原谅的。如果不能,那就算了,我会祈祷的。宽恕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它可以减轻惩罚和缓解悔恨,还有助于忘记。对于被宽恕的人来说,这是中奖了。而对于宽恕他人的人,我无法置评,因为我从没拥有过这个机会。我想,对于他们来说,应该要看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吧。阿达尔贝尔:想要求得原谅,首先要对受害者说出有用的真相。然后请求他忘记你对他和他的家人所做的恶行。再然后直截了当地表达你会像以前一样看待他。如果对方一下就接受了你的请求,就太幸运了。如果没有接受,那应该再次请求他的宽恕。承受了这些巨大的痛苦之后,我们不应该灰心丧气。你越想办法求得原谅,就越有机会被原谅,也就能越快获得原谅。尤其是当局会推动鼓励幸存者宽恕的计划。让—巴蒂斯特:狱中的大部分囚犯都放弃了求得宽恕这件事。他们说:我已经请求原谅了,可我还是得坐牢。除了取悦当局之外,这还有什么用?或者是说:看看那个人,庭审的时候他向所有人请求宽恕,然而并没有逃过严厉的刑罚。对于我们来说,今后,求得原谅只是浪费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愿意固守老观念。但是我呢,我非常在意是否得到原谅这件事。而且我确信我会被原谅,因为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我相信是我做了错事,我下定决心要像以前一样好好生活。如果受害者不能一下就原谅我,时间会帮他在合适的契机做到的。虽然两个阵营中的每个人内心深处都隐藏着沉痛的记忆,但宽恕会让我们共同忘记过去。伊尼亚斯:宽恕是上帝的恩赐,让那些被追和挨打的人得以忘记过去。有的人失去了妻子、孩子、房子和所有物品,还有家畜;有的人将痛苦倾吐给上帝。而宽恕可以让他们跨过所经历的不幸和失去的一切。如果幸存者被信仰打动,这就是恩赐,否则就是不幸。我认为,如果换位一下,我会原谅我的错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保有对上帝的信仰。约瑟夫—德西雷:因为我位高权重,所以我的所作所为被更多人看到。我不被原谅,并非因为我更有罪,而是因为我的罪更显眼。利奥波尔:在沼泽地中,很多图西人在遭受致命一刀前求饶。他们乞求怜悯和恩赐,请求逃过一死或挨打的痛苦,是恐惧和痛苦让他们说出了这些话。他们用尽全力哀求,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但我们呢,我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要求甚至乞求。反而这可能会激励我们。他们只是该死的图西人,而我们是毫无怜悯之心的人。所以,在狱中谈论宽恕是很难的。如果出狱之后,我迎来的是暴怒而非宽恕,我也不会表现出任何敌意,我会耐心地处理我的麻烦。我只会对人们说:如今你们拥有宽恕的权利,宽恕属于你们,你们赢得了它,从今往后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它。我可以等待合适的契机。我将重新开始面前的生活,不会悄悄说你们的坏话。阿达尔贝尔:如果我被当局宽恕,被上帝宽恕,那我也将被我的邻居宽恕。这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努力,但这种宽恕是必要的。没有宽恕,可能会再次发生可怕的杀戮。这种宽恕是基加利当局的新政策决定的。对于已经遭受痛苦的邻居来说,和国家的正义与宗教作对,是不堪忍受的重负。潘克拉斯:对经受了苦难的人说出真相,这很冒险但不伤人。而接受一个杀手说出的真相,这很伤人但不危险。这两者各有利弊。所以请求宽恕和宽恕他人都是很折磨人的事情。所以很多囚犯更愿意请求上帝的宽恕而不是邻居的宽恕,于是在祈祷和唱诗之时争先坐到最前排。他们将宽恕托付给上帝,对邻居则没有任何要求。和上帝说的话对未来的危害比较少,而所获安慰比较多。皮奥:我觉得我们在山上很难彼此宽恕。因为漂亮的语言背后会再次生出太多糟糕的记忆,就像种植园中的杂草。那个在某天大发慈悲原谅你的人,谁能保证他不会在另外一天因为酒后的争执一气之下又收回对你的原谅呢?我感觉似乎没有任何宽恕能够风干所有流淌的鲜血。我只看到上帝可能会原谅我,所以我每天都向他祈祷。我向上帝献出我所有的诚意,不隐瞒我的任何恶行。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宽恕我,但我知道我是发自肺腑地请求他的宽恕。
♦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一处村庄的被屠杀者墓地,引自联合国官网。
显而易见,杀手们没有将真相、真诚和宽恕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或多或少说出真相是一种建议行为,目的是多多少少减轻他的过错,进而减轻他的痛苦,甚至是罪行。而请求宽恕也是一件对自己的未来有私利的事情,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实现团聚、恢复地位,对重建旧日的关系也有帮助。
杀手埃利说过一句话:“我曾给认识的一些受害者的家属写信请求原谅,让来探视的人带给他们。”他们寻求宽恕,或是通过这种书面形式,或是通过出庭的人与共同的熟人,来转达他们的请求。在我们访问里利马监狱(注:关押有许多参与大屠杀的罪犯)时,伊诺桑就多次收到囚犯们的求助,希望他代他们向基本戈的幸存者请求宽恕。
埃利和大多数杀手,其实都不是在寻求宽恕,他们只是略微大声地表达歉意,受害者可能听到也可能听不到,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就好比是我们向刚刚在人行道上撞到的人道歉一样。杀手们寻求宽恕时,带着一种笃定:因为这个请求是丢人的、是富于同情心的,所以它本身就应该得到积极的回应。
这是对宽恕的误解。屠杀结束了,杀手们受到了审判,但他们并不理解宽恕的真正涵义。(来源:腾讯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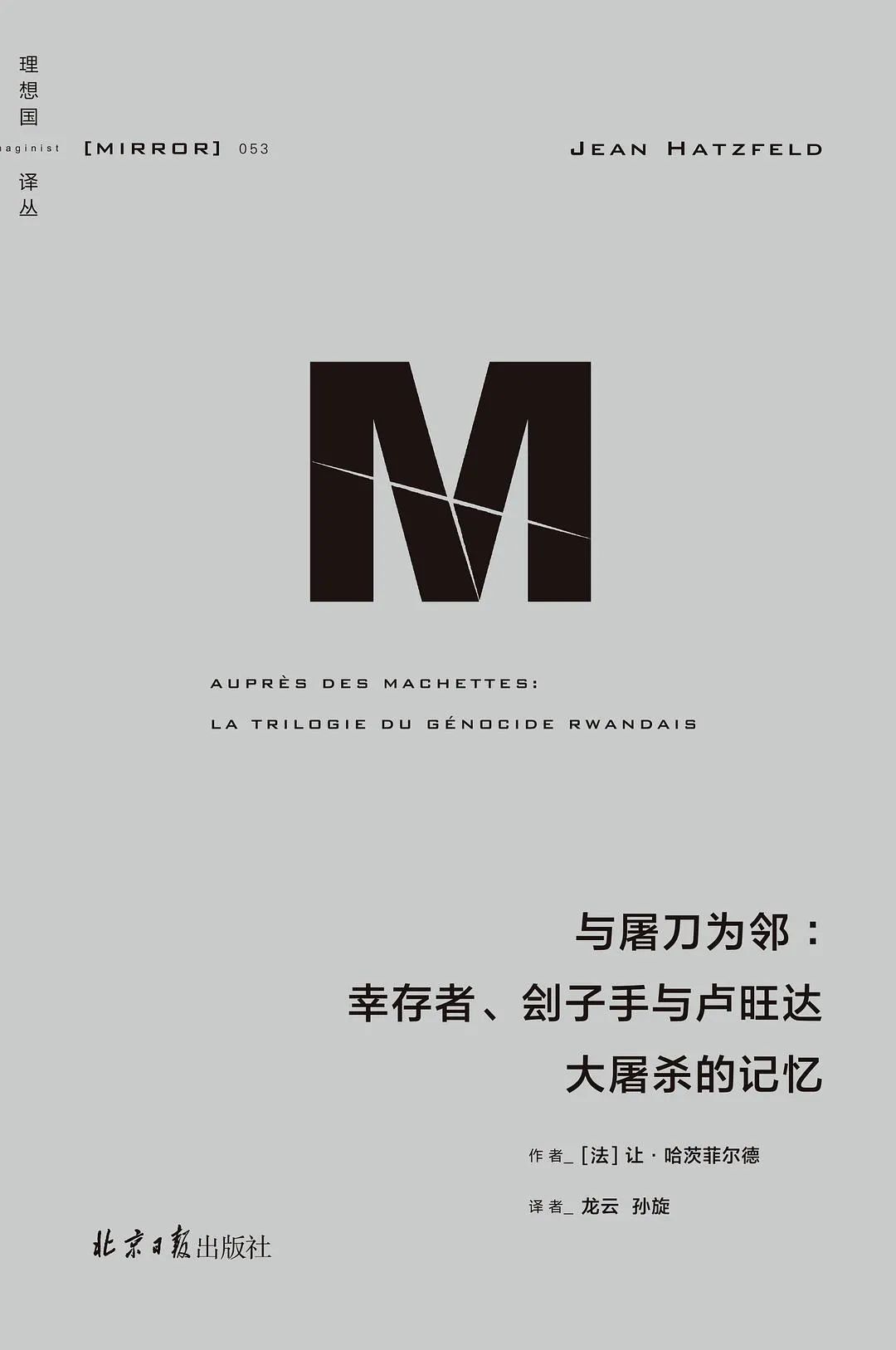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法]让·哈茨菲尔德著, 龙云 / 孙旋翻译。理想国出品,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出版。原文略长,有增删。作者简介:让·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法国作家。曾作为《解放报》战地记者广泛活动于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前往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拉克等国家报道当地战乱;1994年,他前往卢旺达,开始调查和报道大屠杀及其后果,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卢旺达大屠杀三部曲”,陆续获得2001年法国文化奖、2003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以及2007年法国美第奇奖和国际记者联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