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之前《机村史诗》是副标题,《空山》是大标题。《空山》这个标题挺好的,但这六本书的现实性其实很强。而我们中国人说汉语总有些文化影响在里头,一说“空山”大家总想起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可王维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现实的人,他强调禅意,所以这个名字可能对读者形成一种误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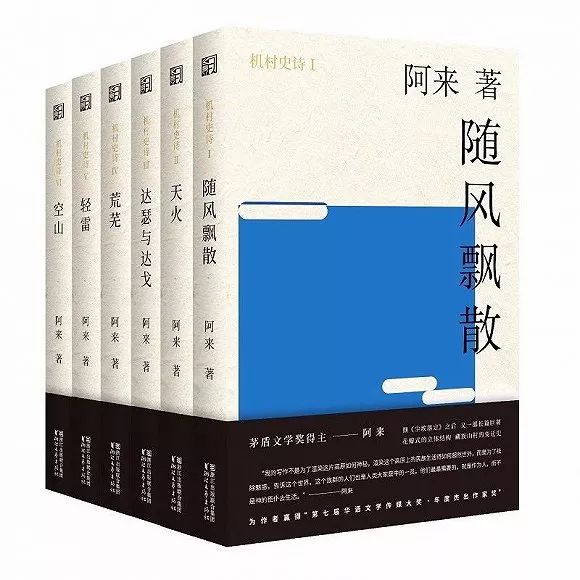
《机村史诗》六部曲
阿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界面文化:在本书最后一篇《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结尾处,你提到了哈罗德·布鲁姆对于“史诗”的定义,对你来说,在中国的语境下该如何理解史诗?如今还存在史诗吗?
阿来:我比较同意布鲁姆的说法。他写过一本《史诗》,在书中评价了二十多部作品,既包括过去最规范的、我们最熟悉的史诗作品《伊利亚特》《奥德赛》,也有后来但丁的《神曲》等诗歌题材的作品。《史诗》同时也收录了一些现代当代小说,比如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布鲁姆对于“史诗”的定义已经把当代小说囊括进去了,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史诗内涵变迁的脉络和过程,所以,当代小说如果写出了历史进程中的某种宏大、壮阔以及对人性的深入,也可以被称为“史诗”。
因此,今天我们在谈汉语文学的时候,也会说很多当代比较好的作品有史诗性,或者说是一部史诗。史诗的意义在发生转化,当代文学中说的“史诗”和古典文学中说的“史诗”是两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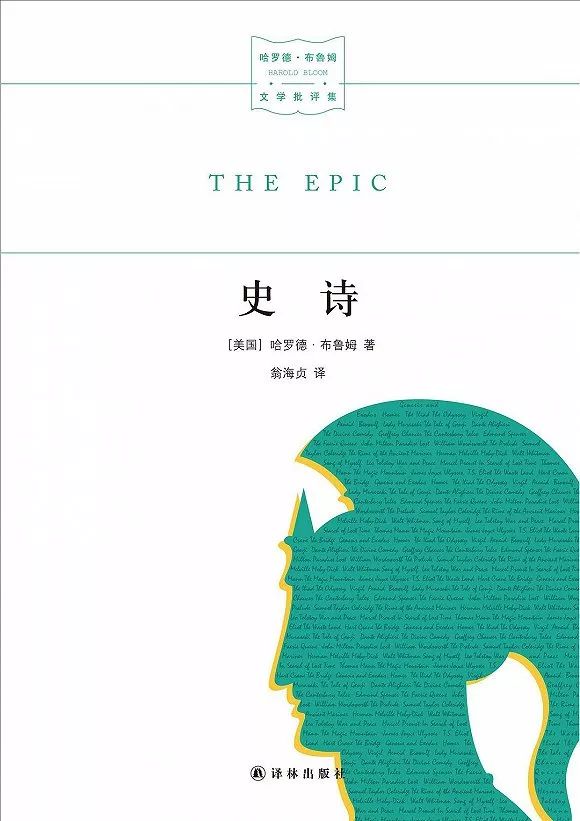
《史诗》
[美]哈罗德·布鲁姆 著 翁海贞 译
译林出版社 2016年5月
回到《机村史诗》,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文学当中还没有聚焦新中国前五十年农村变迁史的作品。上世纪五十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在南方其实是一九五零年——到九十年代及新千年的到来,是今天中国一切变化的基础,中国从过去一个农耕农业国家变迁成为现在这样,这种历史本身就构成了史诗的文化性。
界面文化: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日前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谈到,目前台湾文坛有一种长篇迷思,包括很多文学奖的评选机制也会偏向长篇,导致很多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刻意拉长。你觉得在大陆文坛有这个问题吗?
阿来:我的每一篇小说都非常精炼。《机村史诗》虽然讲了六个大故事,有六个单元,但每一个单元就十多万字,不超过二十万字。有些时候可能东南亚作家有点害怕大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有对长篇的迷思,也许他们反过来也有一种对于长的误解。长篇需要更好的把握,不是为大而大。
我觉得大陆不存在长篇迷思。不是说我们只能写长篇,我自己以及和我同时代的小说写作者都写过很多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没有一个人是专攻一种类型的,没有人说自己一辈子只写长篇或短篇。小说不在于先划定自己,而是依据我们拿到的材料,看我们表达的对象需要什么体量。
短篇小说形式感更强,语言的感觉和修辞发挥得更充分;但长篇有生活洪流一样的、比较粗放的力量。粗细是相对的,各有各的力量,各有各的审美风格。我们做一个小溪一个池塘,就会做得精巧;但如果是一条大河,追求的就是另外的风格。我只写一两个人的一天、一个闪念、情感当中的一个动荡,一个短篇当然够了;但是当我要写五十年,五十年当中上百个人物在大的舞台上交替出现,那五千字确实没法写,写一个梗概都不够。所以,艺术就是当大则大、当小则小。

阿来 吕萌/摄
界面文化:那跳出你自己的创作,你认为,在中国目前文学奖的评选机制中会有对于长篇的青睐吗?
阿来:没有。我们没有一个奖项是把长中短篇放在一起的,长篇就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有专门的短篇、中篇和长篇。这些不同体量是不能放在一起的,比如让一个短篇和一个长篇作比较——论修辞的精巧、形式的完美,可能短篇小说更好;但如果比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以及表达世界的宏观性,那一个短篇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以小见大,也没有办法和长篇比。所以这两个本来就不是可以放在一起等量齐观的东西。
界面文化:说到文学奖,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采取了实名投票制,你的入围作品《瞻对》当年曾被视为获奖热门,但在终选环节以零票落选。这件事你怎么看?
阿来:这是有人操作的。因为我的作品在之前一轮还有很高的票数,最后一轮就变成零票。他们的借口就跟刚我们讨论长篇中篇类似,他们就回到一个体裁问题——这个到底是不是报告文学——在这种东西上做文章。但文学是生长的,每个文体都是不断延展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是不断突破你对它的命名,它要能够成长;如果它可以被控制下来,就不再成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