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发现,如今只要出个电影,恨不得全都用上3D、IMAX技术。美其名曰“提升观影的逼真度”,真不知道做电影的这些人,真的觉得这种用技术造就的“逼真”能让人感动么?
时尚圈里有这样的法则:Less is more。大抵意思是越少些“花哨”的玩意儿,反而会越有味道。我看,这两年流行的“性冷淡风”就挺好。
不过,目前来看电影和戏剧圈儿似乎还没有这种“回归原始”的苗头。
除了动不动就用上IMAX 3D之外、烧钱搞特效、真人CG,连弹幕也搬进了影院,前阵子备受关注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也是不惜超前使用上120帧技术,据说演员须发毛孔都清晰可见。技术在带来更为逼真的观影体验的同时,特效、音效、直往脸上拍的字幕,哪一个没有在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所以,对比之下,我更喜欢“什么都没有”的话剧。
从形式上看,话剧简直“删繁就简”到极致,毕竟,坐在剧场下,演员在台上现场表演,连个字幕都没有,这反倒让人的精神不自觉地高度集中,很快就沉浸到角色的喜怒哀乐里面去。
如同再精美的人形木偶也比不过真人,无论电影技术多么发达,也比不上真人话剧的魅力。
一则,话剧剧本本身的文学性更强。
以中国话剧经典正剧,曹禺先生的《雷雨》为例,角色形象鲜明,个个立得住,语言不仅符合身份背景,只是读台词都能对每个人的年龄有个清楚的判断,不得不佩服曹先生的细致和缜密。

20年前的今天,曹禺先生去世。曹禺原名万家宝,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
而像是廖一梅的剧本,则更有一分“冷淡”的文艺味道,人物性格多了一分偏执,一些台词还有点“诗的韵味”,光是穿雪白色裙子的姑娘在一个追光灯下娓娓地讲“菊花之约”的故事这一幕,心底里突然被激发起哀而不伤的情绪,就足以让人想一辈子呆在剧场。
二来,话剧是充满“变化美”的艺术。
尽管在正式演出前,导演和演员早就做了大量的排练,但面对几百上千人表演,现场什么突发状况都有可能发生。即便是多次配合的团队,也无法保证每一场表演都完美复制。
这不仅对演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意味着会有意外惊喜。
今年夏天我在蜂巢剧场看孟京辉的《枪,谎言和玫瑰》,男主演跑到观众席随即揪起一位观众叫他答话,偏巧观众的回答台上的演员没听清,男主演勾着观众的肩膀,像哥们儿一样,带着角色独有的“放荡不羁”的语气,说:“他没听见,你大点声儿再告诉他一遍!”观众立即对演员的机灵劲儿报以热烈掌声。


《枪,谎言和玫瑰》讲述了主人公想要自杀前一系列的心理状态,到后来精神崩溃的一个过程。
在天桥小剧场看饶晓志的《蠢蛋》,临结束,任素汐脚上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一个趔趄,她也是一边躬身“排除障碍”,一边从容不迫地继续讲着台词。这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小状况,成为话剧不同于电影千篇一律的拷贝版的魅力所在。
第三,话剧演员演得好啊!

濮存昕饰演的李白。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能够演话剧,几乎是对演技最大的肯定。影视圈里好多演技派可都是话剧演员出身,往远了说有陈道明、濮存昕、金士杰,往近了说有郭涛、段奕宏、郝蕾、袁泉。能够接受话剧舞台考验的他们,对于角色的把握和理解也要更深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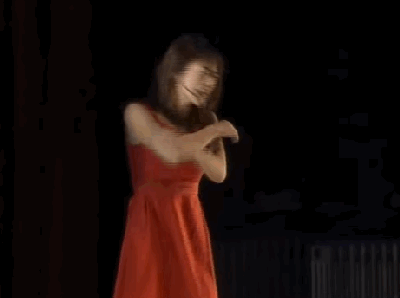

会演话剧的是真女神,看看郝蕾袁泉就知道了。
大剧场话剧场景更宏观、能够借助更多舞台光影技术,可小剧场话剧更有韵味。试想,只有一两百人的小空间里,你和演员的距离最近不足100米,在一个多小时的表演里,幸运的话,你完全能有机会和演员对视。这体验,可不是坐在电影院看3D电影能看得出来的。
总之啊,话剧的语言层次实在太多,坐在剧场的椅子上,你大可以选择自己最想关注的一个点有滋有味地看下去,因为,你总会被这些有血有肉的大活人狠狠感动。
(ps:每次看完剧,我都恨不得在剧场里做一只狗。)

话剧《盗墓笔记》:旁白在黑暗中娓娓道来,有更好的代入感。

话剧《鬼吹灯》:在明与暗的灯光对比下,更能感受到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