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最近在下雨。有时候,奥运会的输赢没有那么了不起。
她是在58岁的年纪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乒乓球选手,在中文互联网里的名字是曾之颖。WTT的官方中文奥运女子单打对阵表里写的也是曾之颖。不过他们都错了。她叫曾志英,只是离开中国太久,没人知道而已。
因为排名靠后,曾志英要在7月27日这天先打67进64的资格赛,结果她1比4输给46岁的黎巴嫩对手玛丽亚娜。这是巴黎奥运会所有项目里年龄最大的一组对决。比赛中途她好几次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气得跺脚,从看台上远看,她在跺脚的时候简直像个少女。但领先后被逆转的比赛进程又提示她老了,两位削球手的对决往往要打很长时间,她的体能跟不上“年轻人”了。
不确定会有多少中国人记得住曾志英。智利人亲切地称她Tia Tania(塔妮娅阿姨)。很多年后,她应该记得自己唯一一场奥运会比赛最后一局时场景:旁边两张球台的比赛已经结束,场地里只剩她和对手聚焦起所有人的目光。她清晰地听到了智利人和中国人用两种语言给她的加油声。
比分定格的瞬间,她神情上倒没有一个落败者该有的失望。塔妮娅已经很开心了。她22岁自我放逐走向远方的人生,比乒乓球台辽阔得多。

7月26日傍晚塞纳河的开幕式上,塔尼亚阿姨感受到了一种好像是专为她设计的幸运——智利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在同一条船上,前后挨着。中国和智利的头两个字母一模一样,这种安排秩序是常规操作。无论如何,塔尼亚在这条船上很开心。她以中国代表团为背景,手里举着智利国旗,找人给自己拍了一张独照。
◎曾志英在中国代表团身后拍照
一种模糊的归属感和距离感,很难言说。
她身后的中国代表团里几乎没有她认识的人,但有一个故交,乒乓球队的李隼。40多年前他俩在铁道兵体工队当过队友。
1989年出国前,曾志英是体制内的专业乒乓球运动员,分别代表河南队和广东队各打过全运会。这个身份很大程度上源于她的家学。
中国乒乓球的辉煌始于“108将”。1960年,为备战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体委从全国选调了108名运动员到北京集训,这批战士般的选手为中国称霸世界乒坛奠定了基础。108人里有庄则栋、徐寅生、容国团等名角,也有一个不那么知名的叫邓惠璋的女选手。邓惠璋是曾志英的母亲。
邓惠璋在广州出生长大,但在河南成为运动员。她和在郑州机械厂工作的广东客家老乡结了婚。
在母亲的引导下,曾志英9岁开始打球,11岁进入省体校,13岁的时候被选到铁道兵体工队。1982年,国家集训队招了一批16岁左右的小孩进队,曾志英在其中。她至今有美好的记忆:“我们在太原封闭打内部教学赛,我才16、17岁,赢了童玲、戴丽丽,只输给了齐宝香,我能赢国家队绝对主力,我当时的信心上来了。”
童玲是那个年代的超级明星,1981年世乒赛的女单冠军。
运动员是一种敏感的群体,信心上来得快,丢掉得更快。
◎曾志英在训练中
曾志英没有代表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她代表河南打了全运会,打了一届还是两届,她现在已经记不清。她只记得从国家队回到省队后越打越没信心,因为国际乒联胶皮改革了。
作为早期国内典型的削球手,曾志英一直打双面防弧的拍子,但1985年世界乒联对胶皮规则进行改革,球拍不能再双面防弧,这个变化影响了很多人。
“我感觉自己没威力了,人的斗志都没了。你本来觉得你的球板很有用的,突然之间没用了。信心就丧失了,全部丧失。”时隔多年,曾志英如此向凤凰网回忆那个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她不是那种跟自己死磕的选手。她才18岁,已不想留在河南队打球。恰巧珠海经济特区当时在广纳人才,用交通警察的编制在全国招募运动员,她去了。她所在的部门是交警大队的秩序实施科,负责红绿灯这类装备,她倒也穿过交警制服,但没正经上过班。珠海市体委总派她打各类比赛,很快广东省队来借调她,让她代表广东征战第六届全国运会。
曾志英说她现在能记住的22岁出国之前的唯一一场正式比赛,就在六运会上。女子双打八进四,她记得自己特别想赢这场球,因为赢了进前四就有奖牌了。她此前在国内没拿过奖牌,单打能打到前16都很难。但这场球还是输了,她终究还是没拿到。
所以很多年后曾志英才会变成“曾之颖”,因为没人记得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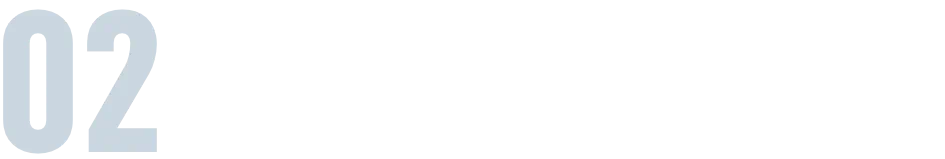
比赛前几天的训练时间,置身巴黎南方竞技场的乒乓球馆,第一个直观感受是:中文在乒乓世界里是通用语言。
葡萄牙队教练谢娟,坐在一旁看曾志英在跟古巴选手练球,她对身边人说,“志英打得还可以的。”斯洛伐克队帅气的削球手汪洋走过来,会先跟谢娟打招呼。训练的时候,汪洋有时会脱口而出中文“卧槽”。加拿大的教练陈宏韬走过来说:“汪洋的弧线是真漂亮啊。”
中国乒乓球太强大了,很多人在国内没有什么机会,所以散落飘零在天涯。曾志英是走得最远的一个。
现在回首40年前人和人之间的联络方式,就像在偷窥另一个平行宇宙。
1987年六运会结束后,智利乒乓球队的教练王晋富在圣地亚哥的中国驻智利大使馆翻看他们订阅的《羊城晚报》,上面有一则六运会“旧闻”,他看到了曾志英的消息。王晋富以前在国内代表山西队打球,他俩是旧相识。王晋富马上给曾志英写信,他不知道具体地址,就把信寄到了珠海体委。王晋富在信里说,智利这边一个省想找一个中国球员过来带队训练。
◎曾志英与巴黎奥运吉祥物
两人通了很久的信,曾志英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决定去智利。听起来这不是一个很随意的选择,但人往往只是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一些决定的分量,而在当时,可能也只是跟着模糊的感觉走而已。
曾志英轻描淡写那次出远门:“运动员从小独立,所以习惯了自己说的算,没那么多顾虑,我都不记得我当时的心态了,可能只是想尝试一下外面的世界。”
曾志英第一次出国,到的就是天涯海角。确实是天涯海角。她从香港飞巴西圣保罗,再转机到圣地亚哥,花了32个小时。在圣地亚哥住了一晚,第二天再沿着狭长的智利国土飞到最北部紧挨着秘鲁的边境城市阿里卡,又花了4个小时。
人生中没有比22岁更冲动的年龄,地球上没有比这更远的路途。
飞到阿里卡,曾志英觉得有点吃惊,跟他想象中的欧美城市生活不一样,是沙漠。这个10万人的城市当时甚至没有几颗树。
曾志英说:“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虽然内向,但胆子大,我还是有点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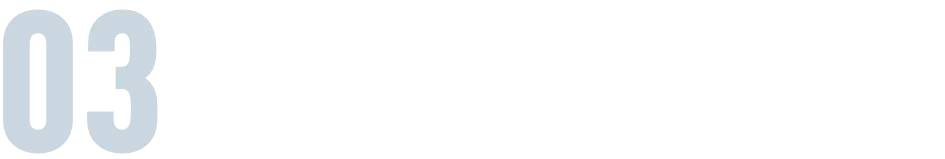
阿里卡最初的生活是单调的。那边不是体工队模式,她在地方乒协旗下的乒乓球俱乐部给孩子们当教练,但队员们晚上才有空,她白天是空闲的。
曾志英会看到一些智利、秘鲁边境做贸易的华人。台湾人居多。还有一些从南边紧挨着的城市伊基克过来的广东人——清末太平军的后裔,他们的祖辈战败后逃亡,流落到智利当矿工。
◎曾志英与粉丝们
能让曾志英融入阿里卡的,还是当地人。塔妮亚(Tania)是当地朋友给她取的西语名字,她自己都说不出含义。最初塔妮亚总往当地乒乓球协会主席家里跑,言语不同,就靠手比划,她感受到自己像个孩子一样被照顾。
“你总会认识到一些人,能以各种方式让你往前走的。”
她慢慢认识了一些朋友。“一个做贸易的大叔跟我说,你既然白天无所事事,去做生意吧,他愿意把货给我,货卖出去了再收货款,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租了个小门面做起生意来。”
她最早卖的货是内衣、内裤。
后来又卖卖季节性产品,卖圣诞礼物,再后来又开了一家五金铺。这不是她最初设想的生活,完全不是。
“我从小在队里,管吃管住发工资,从来没觉得生活会有什么困难,也不觉得生活有很大的一片属于自己的空白要自己去填写。这是我的惯性思维,我以为到了智利,当个教练的生活跟国内也差不了太多吧。”
但她没有想过要往回走。
智利北部365天都不会下雨,所以可能不容易让人太想家。待了一年后,她的选择是放下球拍,俱乐部教练也不做了。“因为生意做起来了,我不想傍晚就关门。我不想请人给我看着,我什么都想一个人干。”
曾志英唯一一次接近回家是1994年。那年圣诞节进货,她进了很多儿童自行车,这些车都要自己安装,她记得自己每天独自从早上9点装到晚上12点,活儿干不完,货又好像卖不出去,她在孤独劳累中有了一种恐惧,她跟自己说如果这个坎儿没过去就一走了之。但后来的结果证实,这只是一次内心的波澜。
她彻底从运动员变成了生意人,没有再摸球拍,直到1997年她要从阿里卡搬到伊基克而收拾行李时,才时隔几年从柜子里重新看到她的熟悉又陌生的球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