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8日,
一架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MH370号航班
在起飞后不久从雷达上消失,
机上载有中国乘客154人。
直至10年后的今日,
飞机失联原因不明、黑匣子仍未找到。
仍有1/4失联乘客家属拒绝“和解赔偿”,
▲
前新闻记者权义,跟拍马航MH370家属十年。家属汪永智在拍摄间隙感叹:“十年前,权义还是一个背着相机的小伙子,跟谁关系都特好,如今也长出白发了。”失联乘客家属十周年肖像(部分)/权义摄
家属程利平,她的丈夫在失联飞机上。事发后,她经常给爱人发短信。这天,一束阳光把她爱人的婚纱照淹没在阴影里/权义摄

家属栗二友,是一位来自河北邯郸的老农民。为了寻找儿子,过去10年,K183、K157次列车他坐了上百次,每次都是过夜的硬座/权义摄责编:陈子文


赶往寺庙,祈祷儿孙三人能早日回家
正月十五清晨,天色未亮,72岁的包兰芳独自骑自行车从两公里外的家赶往后海附近的法华寺,路面的积雪还未消融,寒冷让每一次的呼气化为白雾。
过去十年里,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包兰芳都要到寺庙为飞机上的儿子、儿媳、孙女上香,祈祷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平安归来。包兰芳是权义长期跟拍的家属之一,人们都叫她“包姐”。
2014年3月8日早8点,时任《东方早报》新闻记者的权义看到微博上弹出了一条快讯,“一架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飞机失联”,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失联”这个概念,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十年后,持续缺席的真相,让他对这个词有了残酷的实感。

酒店里,家属彼此拥抱,共同祈祷/权义摄
3月8日当天,家属们被安排到了北京朝阳区的丽都酒店,等待事件的后续通报。一位家属给了权义一张房卡,他因此获得了跟进报道的机会。权义混在家属中,在丽都酒店度过了52个日夜。每一天,走廊里的哭声、悲痛、愤怒不断上演。
这段密集的接触,让权义和一部分家属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舆论的潮水退去后,权义成了唯一没有离开的“外人”。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他看到了“370事件”对他们造成的隐秘伤害。权义长期参与灾难报道,天津爆炸、东方之星沉船、北京大兴火灾……但370的家属们呈现出不一样的特性。一般的灾难事件发生后,家属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接受亲人的死亡、人生的变故,但370事件不同,由于信息公布混乱、迟迟没有定论,它的折磨被无限拉长了,延绵不绝,反反复复。

事发后的两年里,他坚持给儿子发短信/权义摄
来自河北邯郸的栗二友,在事发后的两年里,坚持给失联的儿子发短信,天气转凉,他会提醒儿子添衣保暖,他逢人就会诉说儿子在孤岛上漂流的猜想。
来自北京的胡秀芳,她的儿子、儿媳以及孙女都在航班上,她每周会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为孩子们的回家做好准备。
家属徐京红在手臂上文的飞机,希望自己不要忘记“370”后来她洗了多次,原因是她看到这个图案就会感到刺痛
徐京红的母亲在飞机上,这么多年她一直拒绝去法院申请母亲的“死亡证明”/权义摄家属徐京红,在手臂内侧文了一架飞机,飞向她的心脏,后来她反复清洗。看电影《归来》的时候,巩俐饰演的冯婉瑜数十年如一日地等着丈夫回家,她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等到母亲的归来。
家属群里,权义格外注意自己的用词,飞机是“失联”不是“失事”,亲人是“失踪”不是“遇难”,甚至一段时间,权义不敢提“飞机”二字,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家属们的情绪崩溃。重度抑郁,几乎是每位家属的必经之路,低落、敌对、惊恐、无力,有人长期无法下床,有人把家里的窗户焊上封条。有人出现耳鸣、幻听、眼花,有一位母亲因为长期流泪而双目失明。
心理援助的缺位,让家属们只能独自面对这场灾难。事发后的大半年时间里,马航都没有为家属提供心理支持,错过了心理干预的黄金期。直到2014年12月,马航在北京成立了一个5人的心理应援小组,为上百位的乘客家属提供服务。家住北京的失联乘客姜辉一共只申请到了两次咨询,而在北京之外的家属大多一次都没有申请到。
“后来我跟一些心理医生聊过,他们说心理援助的前提要有一个底,接受家人的死亡,然后在此基础上恢复建设。但370案件没有底,是越来越深的”,由于整日整夜地搜寻飞机相关资料,刚过五十,姜辉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家属张建义在出租屋的墙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他想知道:孩子们到底去哪了?他的女儿一家在MH370上
失去女儿不久后,便患病离世/权义摄
有些人没能熬过漫长的折磨。张丽霞是一位来自齐齐哈尔的单亲妈妈,在权义印象里,她像是《繁花》里的那种姑娘,“干练”“有知识分子气息”,家属们都特别喜欢她。她经常去北京追问女儿的下落,女儿曾在国外读书,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
不久后,张丽霞患癌去世。10年里,亲属中有五六位都因抑郁症及其并发症离世。

等孩子回家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权义摄
“那个年代坐飞机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这些乘客也是他们家里的经济支柱。”十年里,权义看到了原本不同的命运,如何因为同样的死结深陷痛苦的漩涡。
包姐和亲家都是“双独家庭”,儿子、儿媳、孙女都在飞机上。事发以后,两个“独子独孙”的家庭自此陷入了停滞。
包姐家位于北京东城区的胡同里,她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人生晚年,院子一下从热闹变得死寂。去年7月,老伴去世后,包姐成了独居老人。包姐和权义
十年间,家庭的急遽变故摧毁了她的健康和生活,长期失眠让她的面孔憔悴浮肿。孤单的时候,她常对着老伴的遗照说话:一生中最成功的就是我们这儿子了,我一定会等他回来。
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南无阿弥陀佛》的挂字显得醒目。字的前方摆着3只生肖玩偶,象征着 三口之家——包姐的儿子是属羊的,儿媳是属猴的,孙女是属兔的。
包姐只有一个儿子,生于1980年,那一年全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年轻的时候包姐去云南插秧,丈夫被发派至新疆教书,长期分居两地。后来包姐被调回北京,到手表元件厂当女工,干活特别勤快。儿子恰好又很争气,考进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包姐“心里特知足”。
2014年2月底,包姐给孙女盼盼过完3岁生日后,送一家三口去马来西亚旅游。一周后,包姐和丈夫老胡接到了飞机失联的通知。2015年7月,一块“高度疑似MH370的飞机残片”包姐不相信飞机坠海的推断。飞机失联19个月后,一块波音777的襟副翼残骸在法属留尼汪岛被找到,疑似MH370的机翼。家属群有传言,电视台播报的机翼序列号和飞机真正的号码不同。
“就几个数字,它凭什么弄错了?弄一假的机翼你扔到水里边了,能对吗?”包姐用自己在手表厂的工作经验举例,每一块钢材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编号。
面对外界纷繁复杂的推测,包姐的丈夫老胡始终是沉默的。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他的言行特别有分寸,“相信国家”“相信法律”。他唯一表现过的情绪就是“内疚”,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家人,这么多年没能找到孩子。这种内疚感同样笼罩了包姐。几年前,包姐发现丈夫的眼神变得浑浊、呆滞,“老头原来是个挺英俊的人”,她怪自己没有及时注意到老伴的心理变化,一提到这里就泪流满面。包姐回想,丈夫可能早已经抑郁了,后来,医生告诉她,是抑郁症造成了丈夫的癫痫。
丈夫去世后,包姐有两个月吃不进去饭。第一次去菜市场买菜,她一下变得茫然,眼泪簌簌地落下:“原来我总是想着他(丈夫)爱吃什么,他们(孩子们)爱吃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爱吃什么”。
街道工作人员给包姐请过心理医生,但她觉得这种问题是治不好的,一切终归是要靠自己,“没有什么方法。我就是靠我精神上的寄托,就是说,我的孩子肯定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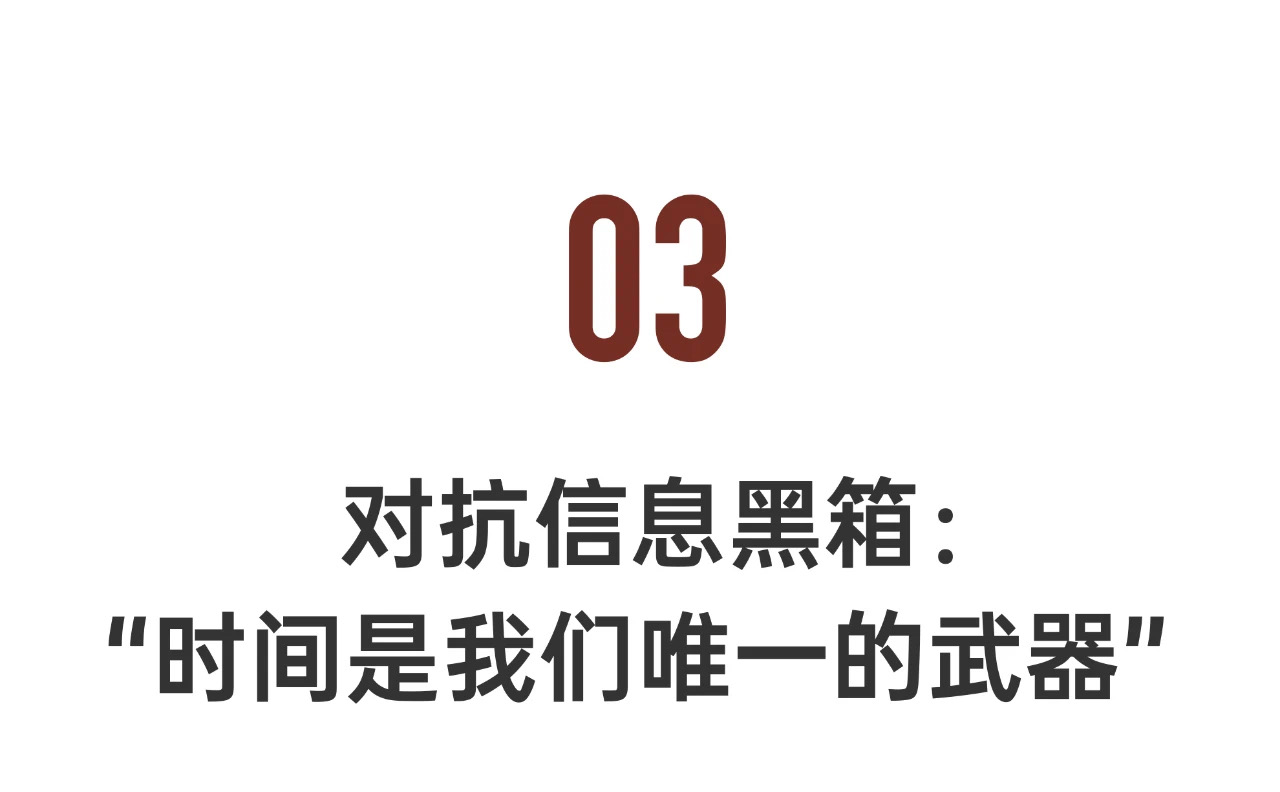
用姜辉的话来说,家属们是在对抗一个“巨人联盟”。
MH370像一个密不透风的信息黑箱,装满了一连串的未解之谜。
客机起飞40多分钟后便与地面控制失去联系,但几小时后当局才发布失踪警报;失联7天后,马来西亚当局才宣告,飞机在飞行途中掉头偏离航线;10个月后,在未能出示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当局就将机上人员状态由“失踪”改为“全数罹难”。官方信息的严重缺失,导致民间的各种猜想、假说开始甚嚣尘上。权义对各种推测倒背如流:有乘客盗用假护照登机,身份可疑;机长曾在家中演练过相同的折返航线,不排除自杀的可能;飞机上还有大量未经扫描的货物、电子通讯设备……
姜辉一开始很喜欢这些假说,至少给了他一线生的希望——母亲有可能还活着。但很快,这些假说被陆续证伪,希望一遍遍坍塌,他受到了更痛的打击。
随着时间推移,姜辉和家属们感受到面对跨国联盟和大资本时,个体“被践踏”的渺小和无助 。抗议马来西亚政府在MH370失联事件中公布的信息混乱/权义摄“它甚至可以利用国家立法的形式,去对付你。”2015年2月,马来西亚政府专门颁布了“765号法案”,宣布重组后的新马航(MAB)将剥离老马航(MAS)的部分债务,其中就包括免除MH370的债务、责任。法案在家属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至今,马航拒绝向家属提供乘客的登机录像。如果家属想要拿到赔偿,必须要签署一份“和解协议”,条款之一是“马航和马政府对370事件免责”,这就意味着家属需自愿放弃飞机搜救与追责。姜辉为我们拿出马来西亚政府于2018年发布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共计822页,他读了好多遍。“官方调查的结论是失踪,不是失事”,有些地方他用荧光笔标记了重点,报告中写着“不能排除第三方干预的可能性”。
与官方的冷漠推诿相比,来自民间的爱和关怀,给了姜辉持续寻找真相的动力——“每去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只要是跟老百姓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到这种爱”。当地一位小老板主动提出,把传单放在他的超市里,因为各个部落都要到他这里进货在留尼汪岛,姜辉与当地土著之间隔着重重的语言障碍。每说一句话,都需要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法文,最后由当地的司机译成土语,“5人一来一回,就10个步骤了”。但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理解和共情,让语言“不厌其烦”地传递下去。
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悉尼大学的海洋学家计算出残片所出现的概率比较高的地方,制作成地图,免费提供给姜辉和其他家属。栗二友躺在沙滩上休息/姜辉摄
英文版的《MH370安全调查报告》发布以后,四川民航学院的老师用了两周时间,自愿帮家属们翻译了这本近600页的报告。
姜辉觉得“370”不会被时间忘记,爱与好奇心是人类发展的两个根本推动力,而这件事恰恰占据了这两点。没有舆论、没有资金、没有向上监督的权力,但他还有时间,他说:“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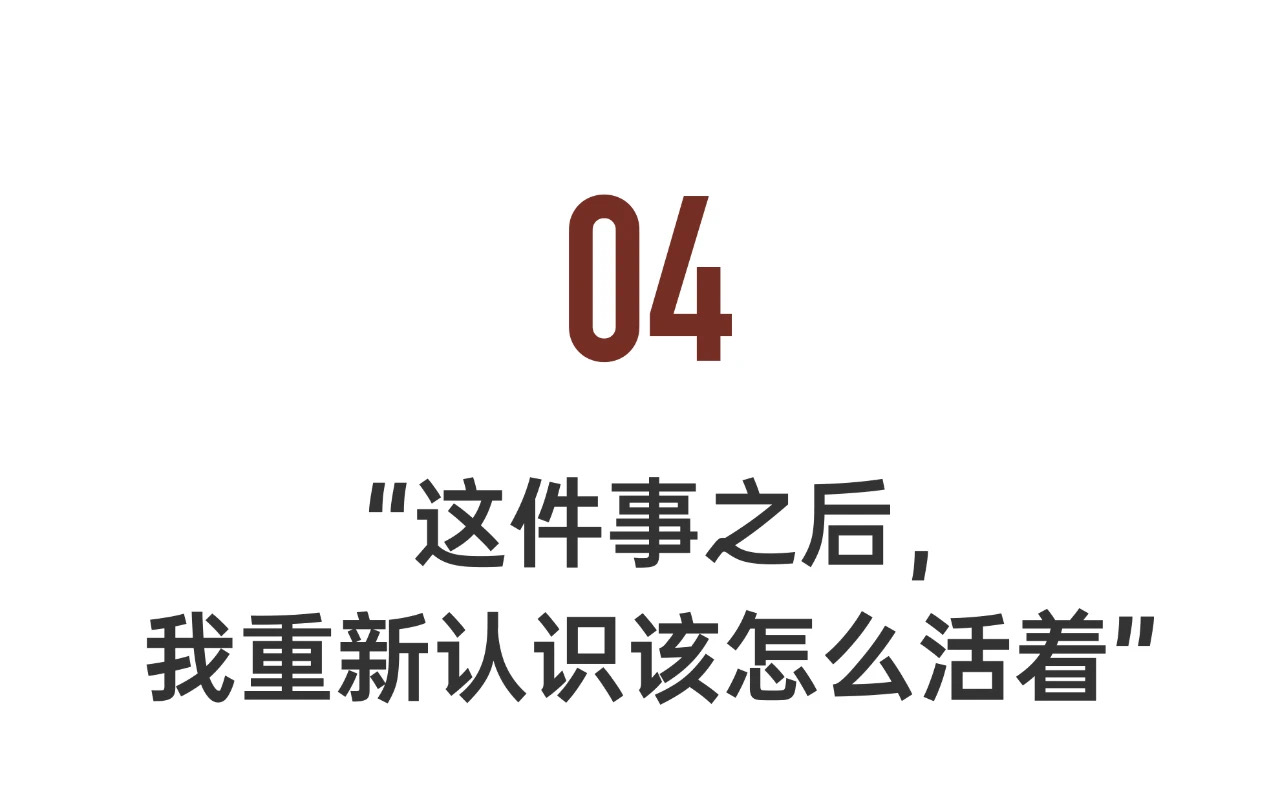
75岁的独居老人汪永智,是家属里极少数“解开死结”的人。我们和权义一起,在北京的家中见到了他。
每天,汪永智都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早上写字、画画,下午练电子琴,吃完晚饭是电影时间,空余时间还会写公众号。电视机旁是一柜子的电影碟片,《野鹅敢死队》《海狼》的台词他几乎全背下来了。
汪永智的爱人在飞机上。MH370失联之后,汪永智生了一场大病,心脏需要支架手术,哮喘激化,从早到晚吃药,“老婆不在了,我还活什么劲的想法都有了”。汪永智年轻的时候在服装公司工作,是北京市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服装企业。他的爱人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两人是大家眼里的东城区模范夫妻。
“出事儿以后,我连我的袜子放哪我都不知道,东西都是我老婆管”,汪永智突然意识到家务也是门大学问。他投入到具体的日常中,洗衣服、打扫卫生,包饺子、擀面条、煮意面,还买了一台烤箱,研究做面包,烤披萨。
这个大半辈子没怎么下过厨房的男人,成了老年料理专家,厨房里堆满了各式各样新奇的西餐调料。差不多两年过后,汪永智觉得缓过来了,“原来只想着找别人,现在能找到自己了”。
汪永智不喜欢“养儿防老”的观念,对“家庭”“亲情”有着不同于传统国人的理解。汪永智只有一个儿子,在上海工作,平时很少回北京,他鼓励儿子首先要过好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奢望、太多的依赖、太多的苛求,这样你的亲人、孩子,他们都是解放的。”
他也因此解放了自己。“既不和解,也不起诉”是他对“370”的态度——拒绝赔偿金,是因为他不希望事故方可以因金钱而被免责;没有起诉,是因为他不愿把余生的精力赌注在漫长的官司之中。370事件让他重新认识了人该怎么活着:“我肯定不是为老伴活着的,她也不是为我活着的。我们俩有的只是一种人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情感。”
“孤独终老,不过是所有人的宿命”,说到这儿的时候,汪永智的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当生活被摧毁之后,继续寻找370的真相成了一些家属活着的意义。
事发一年后,姜辉因为频繁地参与“社会活动”被公司辞退。当时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华北区大区经理。
这些年,姜辉每天都在看资料、研究各种法律条文,全职推动案件调查的发展。他频繁沟通过的律师少说也有快20位,为了找飞机行走过的里程至少可以绕地球4圈。
他已经成了半个法律专家、航空专家。姜辉说:“如果真的能把这架飞机找到,把亲人找到,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公司头20年那种风光的业绩,相比之下,不过是过眼云烟。”
权义发现,近几年不少老年家属都在积极地锻炼身体,跑步、跳绳、做单杠,他们中很多人迈入了古稀之年,寻找亲人是他们现在生活的目标。
失联乘客家属谢修萃是江苏连云港人,唯一的儿子在马来西亚打工/权义摄谢修萃和丈夫都在城里打零工,一天的收入只有百十来块。他们在北京南五环的小沟旁边租了一个工棚,50块钱每月,没水没电,冬天的屋子跟冰窖一样寒冷。唯一的目的就是每天能到顺义的空港,去和马航的工作人员打探孩子的消息/权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