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是钱锺书在《围城》中打过的比喻,流传极广。
不知情的人揣度这是作者本人的血泪史,但恰恰相反,钱锺书的婚姻却是一座他永远不愿意走出去的城。他和杨绛之间的爱情,始于一见倾心,陷于相濡以沫,终于岁月长情。他们执手走过66载春夏秋冬,从少年到白头,同样婚姻美满的冰心都忍不住满怀羡慕:“他们是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和幸福的一对。”
成了家后,他曾对杨绛认真地说了这么一句痴话:“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而在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后,钱锺书坚决反对再生第二胎。在提倡“人多力量大”的时代,在多子多福思想由来已久的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在当时很不常见。
钱锺书他是这么看的:“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钱瑗的小名)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他这是认为父母对孩子也要“用情专一”呀。
倘若钱瑗没有早逝,扛过了恶疾缠身,享有如她双亲一样的福寿,那么本该由她本人参与撰写的《我们仨》上会诉说怎样的故事呢?这一天父亲节,她又会对她最爱的pop(爸爸)说些什么俏皮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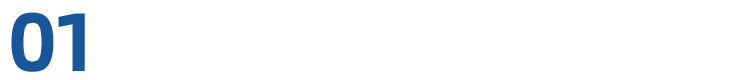
一说起钱锺书,人们大概就会想到《围城》。这一部1946年出版的小说,堪称中国的“新儒林外史”,一经问世,洛阳纸贵。有外国记者曾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亲临万里长城,二是看看《围城》的作者。
慕名而来的人多了,让钱锺书不胜其烦,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故而有了那一句大众耳熟能详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去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在世人面前,钱锺书是刚满20岁就能为父亲捉刀代笔替钱穆的《国学概论》写序的少年天才,是以数学仅仅15分破格录取升入清华的学霸,是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年轻时,钱锺书最引人瞩目的还要数他的狂气,因为很少有人入得了他的法眼。从清华毕业后,他拒绝了留下继续深造,他认为“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据说,他还曾评价“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就是后来与国民女神林徽因做邻居,他也并不感冒。甚是少年轻狂。
而在女儿“圆圆头”的眼里:“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在中国的家庭里,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大多是缺位的,偶尔出席,也大多以“严父”这种高高在上的严肃形象出现,更毋庸谈将对孩子的爱意直白地诉之于口了。譬如,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从小就会严厉要求他,基本不会当着钱锺书的面夸赞他一句。
然而,钱锺书却着实不能算是传统典型的父亲,倒“现代”得让人有三分意外、三分惊喜、余下四分理所当然。
从小到大,他就是女儿阿圆的玩伴儿,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杨绛戏称他们是“老鼠哥哥同年伴”。
他爱带着女儿玩埋地雷的游戏,把女儿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书等通通搁藏在被子里,一个藏,一个找,两个“儿童”玩得不亦乐乎。
在阿圆两三岁的时候,钱锺书不仅会用墨笔在女儿的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被杨绛说了一顿不敢再乱画之后,就开始编顺口溜,给阿圆起绰号。
有一天,看到女儿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蹦去,好不欢快,于是故意出言逗阿圆说:“身上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气得阿圆噘嘴撞头表示抗议,见状他立刻又把她比作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直逼幼稚鬼。
多年以后,小儿童自己也成了白发老人,患病住院在床时,拟定目录提笔准备写《我们仨》,第一篇就是“爸爸逗我玩”,可见这些童年记忆之深刻难忘。

1932年,钱锺书和杨绛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古月堂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面对着怦然心动的命定之人,平日里看谁都看不上的钱锺书当即表态:“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看着这个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的男子,也略带紧张地回应:“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钱锺书曾对杨绛说:“没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结婚这事我没想过和别人。”于是两人次年订婚,1935年,正式结为夫妻。
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一家妇产医院里,随同钱锺书到英国留学的杨绛果然生了个女儿,她的降临让钱锺书喜出望外。钱瑗出生时浑身青紫,被护士用产钳夹出来,无声无息,像一只虚弱的小猫。护士们使劲拍拍拍,钱瑗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响亮地回荡在产房中,于是护士们戏称她是“Miss Sing High”(意为“高歌小姐”,又译为“音海小姐”)。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孩子。
等在病房外的钱锺书看到了护士手中抱着的娃娃,他仔仔细细看了又看,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而杨绛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反倒觉得这个小娃娃“又丑又怪”。
对着这个“又丑又怪”的娃娃,钱锺书有时候会闻闻她的脚丫丫,故意做出恶心呕吐的模样,惹得孩子总是咯咯发笑。
有次因为工作关系,钱锺书和钱瑗两年不见,阿圆似乎已经不认识了她的爸爸。自钱锺书回家后把行李箱放下,堆在杨绛的床边,钱瑗就一直睁着好奇的眼,眼里饱含猜疑,继而有点不高兴了,于是向钱锺书宣布杨绛是她的妈妈,开始赶人:“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钱锺书欲哭无泪地笑问:“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谁料阿圆一番话让这个大学者也直接惊呆了:“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了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对于这个女儿,作为母亲的杨绛,称她为“平生唯一的杰作”,作为父亲的钱锺书更是不吝赞美。他评价他的女儿:“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钱瑗五岁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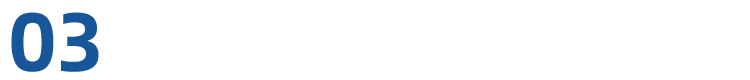
钱瑗和她父母一样,志气不大。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只想日后做个教师的“尖兵。”她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执教36年,为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以来,已经被反复出版了9遍。
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本教材“既是一部出色的专著,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然而,由于钱瑗多年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钱锺书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学者,精通多国语言,当年破格录取入清华的时候,国文和英语都取得了满分,后来留学欧洲,自学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等。后来回到清华任教,任外文系教授。
在钱瑗小时候,钱锺书亲自教她说一些英语单词,短的如牛、猪、猫、狗,最长的是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为她日后的英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钱锺书的学风更是名副其实的传家宝,对钱瑗的影响极大。
和钱瑗曾经多年共事的陈教授,去钱家探望闲谈时,曾见钱瑗翻出一部很厚重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书中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往下翻,几乎每页都是这样,而全书有几千页,这本辞书正是钱锺书的。
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这让陈教授啧啧称奇。
其实,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是钱瑗主审。她同样是逐字逐句认真校对,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只可惜,杨绛和钱锺书最钟爱的女儿病逝在了父母之前,白发人送黑发人。许是女儿的逝世终究给了钱锺书沉重的打击,次年冬天,钱锺书也走了,只剩下杨绛一个人独自回忆着“我们仨”的过往种种。
而《我们仨》这部本该由三个共同完成的人生大书,最后也只能由杨绛一人完成。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有对普通的夫妻,“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一个他们的普通孩子,“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七年前,杨绛去世,这个与世无争、单纯朴素的小家庭最终落幕。而中国仍有无数这样的小家庭,无论身份、财富或者地位,每天在上演着共同的悲欢。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杨绛:《我们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杨绛等:《我们的钱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