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维尔堡是一幢笨重的灰色石头建筑。1830年代,阿道夫·梯也尔为保卫巴黎,下令修建了一圈防御工事,这座堡垒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外墙高10米,桥墩宽17米。其外形构造呈一颗巨大的星星状,中间有片空地,墙壁的样式使它看起来有点像19世纪为法国外籍兵团(Foreign Legion)而修建的前哨堡垒。
纳粹国防军最早在1940年6月占领了罗曼维尔,但它很快成了关押“帝国敌人”的拘留营。到1942年夏天,它成为关押巴黎地区的人质的主要场所。如今,在有关镇压的词语中,“赎罪者”(Sühnepersonen)一词基本取代了“人质”(Geisel)的说法。“赎罪者”指他们对反抗占领军的行动负有集体责任。一旦要报复那些针对德国士兵而发动的袭击,关押在罗曼维尔监狱的“死敌”和“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就随时都可能会被处死。德国人不枪毙女性,至少不把她们当作人质。因此,罗曼维尔也成了关押参与抵抗运动女性的监狱,因为她们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可能意味什么。在法国被占领的四年间,约4000名女性被关在了罗曼维尔。二号人物、突击队长特拉佩(Untersturmführer Trappe)的统治异常冷酷,使人感到恐惧。罗曼维尔也被称为“122拘留营”。
1942年8月1日,第一批230名参与抵抗运动的女性被送到了罗曼维尔,她们最终将前往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她是一名32岁的西班牙护士,名叫玛利亚·阿隆索(Maria Alonso),朋友们都叫她约瑟(Josée)。她曾照看过152抵抗运动中的伤者和病人,还在医院秘密协助一名女医生做小型手术。她因为向一个邮政工作人员网络提供了一台属于她哥哥的油印机,被另一名遭受刑讯逼供的抵抗运动成员告发而被捕,在庭审中,她被判无罪,但她所在组织的男性均被判处死刑。她本可以逃跑的,但她不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与丈夫分开后,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她是个性开朗的、好心肠的女性,迅速成了堡垒中女子监区的领袖。院子中间有一个带刺的铁丝网,将这里与男子监区隔开。约瑟在狱中仍然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自尊。据说,在她当值分发包裹、信件并传达特拉佩的指令时,陪同她的德国士兵仿佛在她的指挥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之间的友谊变得愈发深厚。在女子监区的各处,房间里,楼梯上,空地上,其他人的友谊也在萌芽、生长。女人们按年龄、教育程度、出身和职业,自然地结为小团体,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相似的损失,加深了她们对于彼此的理解和爱意。为被处死的丈夫而悲伤,想念她们的孩子,担心她们的家人——女人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因为也没有太多其他事可做。通过诉说,她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了,更能面对如今的局面。她们已经明白,女性之间亲密的友谊将在今后保护她们,而身处堡垒另一侧的男性,则没能培养出类似的关系。
有些女性的丈夫、爱人参与了抵抗运动,但尚未被捕,她们时刻为他们的安危担心;有些女性的家人已经落入盖世太保手中,一部分人被关押在罗曼维尔院子另一侧的人质牢房,她们终日痛苦不堪:她们很快就会作为袭击德国人的人质而被枪杀?马德莱娜·诺尔芒的丈夫是农夫,她曾卖掉了牲口,为自己的地下活动筹钱。有一天,她在院子里看见了自己的丈夫:他几乎看不清她,因为他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视力。

罗曼维尔拍摄的照片。上:苏珊·马亚尔马伊·波利策玛丽-埃莉萨·诺德曼;中:奥尔加·梅兰伊冯娜·诺泰里安妮特·埃波;下:伊薇特·吉永波利娜·波米耶斯雷蒙德·乔治
也许,对女性之间的凝聚力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在牢房蔓延开来的求知欲和分享欲。为了打发漫长的白天,为了避免回忆过去且担心孩子的未来所带来的恐惧,女人们开设了一系列非正式课程,每名女性都贡献出自己的经验和技能。维瓦·南尼教意大利语;玛丽-克洛德教政治史;马伊记得她和乔治之间的长谈,她会和大家讨论哲学;达妮埃尔讲述每天的新闻;夏洛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并和茹韦相处了多年,她的脑海中充满了话剧的每个场景与茹韦一丝不苟、孜孜不倦的舞台指导,她重现了在剧院的那些夜晚。
9月21日,星期一,清晨7点,罗曼维尔的女人听见靴子踏过地面的声音,男人们唱着《马赛曲》。堡垒外的街道上停着数辆卡车,它们的窗户很暗。女人们仍在尝试说服自己,男人们只是要被送去贡比涅车站,随后会被驱逐到德国,所以她们不用太害怕。
直到现在,女人们才知道46名男性每五人一组爬上陡峭的山坡,被带到了瓦莱里安山的行刑场。没有一人要求戴眼罩。事后,行刑队队员分到了12瓶干邑红酒。尸体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火化,当局下令不准通知家属。从一张被藏在阿司匹林药瓶中偷偷带进堡垒的纸条中,女人们才知道了骨灰的下落。“他们太伟大了,那些倒下的人,”玛丽-克洛德在设法带出堡垒的一封信中写道,“给人的印象是一辈子都愧对他们,也不配为他们的死报仇。”在巴黎和波尔多被处决的116人当中,只有1人因为曾参与袭击德国士兵而被德国法庭定罪。“有些日子,”达妮埃尔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逼近恐惧的极限了。”
如今,罗曼维尔多了14名寡妇。她们的朋友们倾尽所能。女人们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待在她们身边,希望身体的温暖和接触也许能减轻她们的痛苦。贝蒂在给父母的信中悲伤地写道:“这里只剩寡妇了。”许多年后,有名女性形容了她与丈夫共度的最后一刻:“那天早上叫到我时,我身体里的某个部分仿佛停止了,没有什么可以让它再次启动,就像死去的人所佩戴的手表。”尽管她想寻死,但她选择了活下去,反抗德国人,不向任何人屈服。“我必须坚持到最后,向死而生。”
10月14日,另一群寡妇被送到了罗曼维尔。在30名从波尔多来巴黎的女性中,包括玛格丽特·巴利尼亚、伊丽莎白·迪佩龙、伊薇特·吉永和阿米瑟·吉永,9月21日,她们的丈夫在苏热的兵营被枪毙了。同行的还有马德莱娜·扎尼、约朗德和奥萝尔两姐妹以及克洛德的母亲安妮特·埃波。出发前,没有任何女性获准见她们年幼的孩子最后一面。
在被枪毙前数小时,普罗斯珀·吉永和让·吉永拿到了纸和笔,给他们的妻子写告别信。笔头很钝,信潦草地写在粗糙的纸张上。“你啊,我最亲爱的妻子,你必须学会忘记,重新开始你的生活。”让在信中告诉伊薇特,“原谅我,如果我曾让你感到痛苦的话……永别了。我会勇敢地死去,为我曾奋斗过的事业。”普罗斯珀的信更简短。“我会勇敢地死去。”他在给安妮特的信中写道,“无论怎样。尽量让你的每一天过得舒服些。我最后想着的都是你。”但两个男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妻子没能平安地回到农场而是被关到了监狱,他们也不知道彼此会同时死掉。
1942年圣诞节前不久,最后一批即将被驱逐的女性来到了罗曼维尔。她们是波兰人,不是人人都会说法语。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她们受北部就业机会的吸引来到法国,只要情况允许,她们都打算回家。这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团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她们煮波兰餐——香肠和紫甘蓝;在温暖的夏日夜晚,170男人会用口琴吹波尔卡舞曲。但是,战争和纳粹在他们祖国的迫害困住了在法国的波兰人,停战协定签署后,在法波兰人发起了抵抗运动,成立了“波兰独立斗争组织”(Polska Organizacja Walki o Niepodleg os'c',POWN)。该运动的领导人是前波兰总领事亚历山大·拉瓦科斯基(Aleksander Kawalkowski),化名为尤斯廷(Justyn)。1942年夏天,他们发动了一项名为安格莉卡(Angelika)的计划,后改名为莫妮卡(Monika),协助同盟军在一次登陆中使德军的行动瘫痪;与此同时,其成员发起破坏行动,收集情报,还把犹太人偷偷运出法国。
1月中旬,罗曼维尔的女人突然被允许与外界通信。“这里刮起了一阵离别之风,”玛丽-克洛德写道,尽管她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距离获得真正自由的时间,还差好几个月,“但我很有耐心,非常确信一切就快结束了。”有传闻称,同盟军即将攻占的黎波里(Tripoli),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败了。普佩特和玛丽刚得知,她们的母亲因为胃癌去世了。听说这个消息时,玛丽晕了过去。
1942年7月,在贡比涅附近的营地,首批1170名与“夜雾命令”有关的囚犯被送往“未知目的地”。他们均为男性。这批人中有车工、水管工、电工、轨道工人、码头工、裁缝、邮递员和农夫。他们中的90%都是共产党员,因为抵抗活动而被捕。其中之一是贝蒂的叔叔夏尔·帕索(Charles Passot)。在贡比涅时,他们继续学习政治、锻炼、分享食物。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德国人在明白了大规模的死刑无法遏制抵抗者之后,认为驱逐——尤其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们又决定派第二辆列车驶往未知之地,处理掉罗曼维尔监狱里那些麻烦的女人。
1月22日夜晚,女人们正准备回自己的房间睡觉时,她们突然被集中到了一起,其中的222人被点了名。她们接到指示,只准随身携带一只装保暖衣物的小箱子。“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达妮埃尔飞快地给她的父母写信,“但你们在想念我时永远不要灰心……我觉得充满了干劲,年轻的血液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她说她的同伴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刚得知她的兄弟与摩洛哥的内政部长攀上了关系,正在想办法将她转移到南部的监狱,但她拒绝离开,说自己要留下来和大家在一起。她的决心既来自她将自己视为大家的领袖,也因为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她们的处境有多么危险。

玛丽-克洛德从罗曼维尔寄出的最后的信,写于1943年1月21日
玛丽-克洛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她带上了兰波(Rimbaud)的诗歌小册子,除了似乎有更年期早期症状外,她的身体很好,“旅行时它很实用,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的”。贝蒂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同样兴致昂扬。她已经分别在桑特监狱和罗曼维尔熬过了五个月,她相信只要再过五个月,肯定就可以回家了。
1943年1月24日的清晨潮湿又寒冷。空中弥漫着一股雾气,云层压得很低。这是一个星期日。天色渐亮后,230名女性在德国士兵和法国警察的陪同下坐卡车来到火车站,她们先经过了一条“被驱逐者专用通道”,之后,被分配到四辆运牛货车上。在去车站的路上,她们朝附近的几个人大喊,但那些人只是望向别处,匆匆地离开了。火车的前几节车厢已经关闭了,里面有1446名男性,他们是前一天晚上上车的。他们之中包括乔治、格鲁嫩伯格,即西蒙娜在青年武装翼认识的朋友。六七十名女性为一组,被分别带到前三辆运牛货车。剩下的27人爬上了第四辆运牛货车,包括夏洛特、达妮埃尔、玛丽-克洛德、贝蒂、西蒙娜和塞西尔。每辆车上铺了半捆稻草,这让夏洛特想起需要打扫的谷仓的模样。有一个供大家方便的桶。马德莱娜·诺尔芒不知道,而且永远都不会再知道,她们离开贡比涅的时候,她的母亲因为担心女儿而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门被关上后,插上了门闩。车厢非常拥挤,无法让所有女性同时伸展开身体,所以,她们设立了轮换制度,每次让半数人躺着,另外一半坐着。箱子堆在桶的四周,以免火车开动时翻倒。在夏洛特的车厢,有一个五十岁出头的荷兰女人,名叫雅各巴·范德莱(Jakoba van der Lee),她的前夫是阿拉伯酋长。她将一顶黑色帽子放在自己的行李箱上,摊开她的毯子,并把自己裹在一件长及大腿的水獭皮外套里。在车上所有的女人当中,她的存在也许是最荒谬的:她给在荷兰的兄弟写了一封信,满怀期待地预言希特勒肯定会战败。这封信被德国人截了下来。
出发前,玛丽-埃莉萨认为应该写下并记录车上每一名女性的身份。她催促大家留下姓名、年龄、有几个孩子,以及与每人经历相关的重要事实。
230人当中有119人是共产党员,有9人不是法国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法国各地,包括巴黎、波尔多、布列塔尼、诺曼底、阿基坦以及卢瓦尔河的沿岸地区。她们庇护抵抗者,撰写、复印反德的小册子,在购物袋中藏匿武器,协助发起破坏行动。12人曾经是向导——雷蒙德·塞尔让也是其中之一,她们协助人们穿越分界线。37人由于皮肯-达利代-波利策事件而被捕,17人为廷特林网络的印刷工和技工;40人曾活跃在夏朗德省、滨海夏朗德省和吉伦特省附近。车上有超过20人——比如范德莱女士——几乎与抵抗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她们只是对占领者持有负面评价,或者认识抵抗者。还有3名告密者,她们的存在更加诡异,她们明明支持而非反对占领者。
车上有1名医生阿代拉伊德、1名牙医达妮埃尔、1名助产士马伊和4名药剂师,玛丽-埃莉萨是其中之一。她们中有农妇、店主,有在工厂和邮局工作的妇女,还有老师和秘书。有21个裁缝或懂针线活的女性。有几名学生。其中一人是歌手。42人称她们是家庭主妇。半数已婚,51人的丈夫或爱人被德国人处死了。99人诞下了167个孩子,其中最年幼的婴儿出生仅数月。60多岁的寡妇玛格丽特·里希耶(Marguerite Richier)生过七个孩子,她的两个女儿奥黛特(Odette)和阿芒德(Armande)也在车上。
就她们接下来将经历的事而言,最关键的是有54人在44岁或以上,尽管多数人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岁出头。车上最年轻的女孩是罗莎·弗洛克,她刚庆祝完17岁生日。最年长的是来自索恩河畔沙隆(Chaons-sur-Seine)的67岁寡妇玛丽·肖(Marie Chaux),有人告发她在厨房的抽屉里藏了一把儿子的手枪——一战的纪念品;尽管根据后来的发现,她也为抵抗者提供安全屋。
车上还有几个家庭。卢卢和卡门、约朗德和奥萝尔是为数不多的两对姐妹;有六个母亲和她们的女儿,包括埃玛·博洛和埃莱娜·博洛,她们曾想尽一切办法要求分在同一辆运牛货车上,但未能如愿。布拉班德尔一家都在车上,男人在前面的车厢,埃莱娜和索菲在后面的车厢。在前一天,布拉班德尔医生在贡比涅瞥见了妻子和女儿的身影,他恳求获准与她们说几句话,但遭到了拒绝。还有艾梅·多里达(Aimée Doridat)和她的嫂子奥尔加·戈德弗鲁瓦(Olga Godefroy),她们来自南锡的一个共产党员大家庭。艾梅本来也可以逃跑的,一名铁路工人让自己八岁的儿子向她传话,要她最好想办法躲起来,但她不愿意离开她的六个兄弟,而他们则都处于拘留之中。
但最重要的是,尽管这些女性在年龄、背景、教育程度及拥有的财富上不尽相同,不过,她们都是彼此的朋友。她们在罗曼维尔度过了一段非常亲密的时光,车上到处是她们的朋友。她们知道彼此的长处和弱点,会陪伴在陷入可怕的痛苦的人们身边。她们照顾着彼此,共同踏上了未知的前路。阿代拉伊德推测她们将前往一家德国工厂,好奇她们将如何一起工作、关心彼此。
火车穿过法国时,铁轨上的字条火车在贡比涅车站启动时,她们从包裹里拿出了铅笔和纸片写字条。维瓦在最后一行写的是“我会回来的”,还加了下划线。她们在空白处写下了家人的名字和地址,写她们正在火车上,即将前往遥远的某个地方——她们认为可能是德国。她们用指甲刀在木质车厢壁上挖小洞,等火车在车站停下来后,就往外塞纸条,还加上了一点钱,恳求捡到它们的人把纸条送给她们的家人。安妮特·埃波给家人写的是“照顾克洛德”,给儿子写的是“妈妈亲亲最爱的儿子”(Maman t’embrasse, mon cher fils)。在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中,她携带了克洛德的照片和在罗曼维尔收到的他的肖像画。有人在讨论从车上逃跑,但门是从外面锁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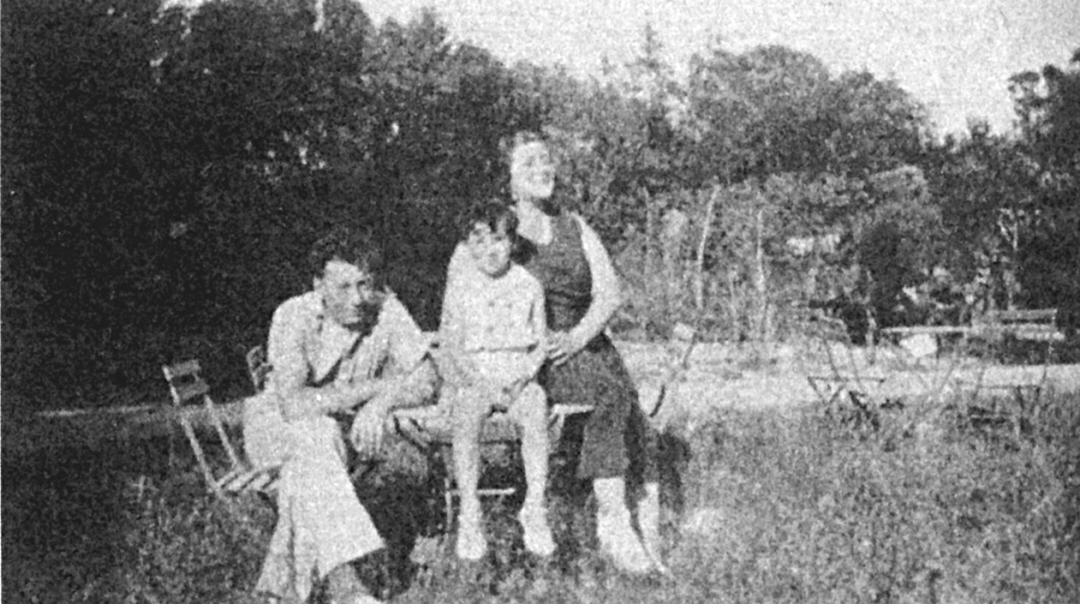
安妮特·埃波与丈夫和儿子

安妮特带在身边的克洛德的画像
第一天,女人们轮流透过车上的缝隙观察,试图弄清楚她们所经过的地方。火车在马恩河畔沙隆停车时,一个铁路工人走到车厢附近低语道:“他们打输了。他们输掉了斯大林格勒。你们很快就会回来。坚强点,女孩们。”在梅斯,法国司机换成了德国人。现在,车上由盖世太保做主。几名女性获准外出为大家打水。一个车站的守卫告诉她们:“充分利用你们的机会。你们将被送去永远无法再回来的集中营。”大家根本不把他不吉利的话放在心上。女人们唱歌,唱那些从童年起便记得的歌谣,以保持精神愉悦。
温度越来越低,在昏暗的、没有窗户的车厢里,女人们紧挨在一起,为对方揉背。尽管她们很快就吃完了面包和香肠,但是,比饥饿更难熬的是口渴,每当火车在车站停靠时,女人们都恳求着要水喝。玛丽-克洛德持续用最大的声音喊道:“给我们水喝,我们很渴。”没人回答她们。很快,她们陷入了沉默,尝试保存唾液。第二天夜晚,火车停在哈勒(Halle),车上的男人从此与她们分道扬镳,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将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尽管当时车上没有人知道。布拉班德尔一家虽然还被蒙在鼓里,但他们还是在此分别了。
1943年1月26日,星期二早晨,火车停在了弗罗茨瓦夫(Breslau),女人们喝上了温水。天越来越冷了,仅剩的面包块都被冻硬了。她们听见波兰人在说话。车再次开动时,负责从缝隙观察外部的女人们发现,这里被漫漫白雪覆盖住了,大地平坦,结了冰,了无人烟。那天夜晚,火车停下了,再也没有启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