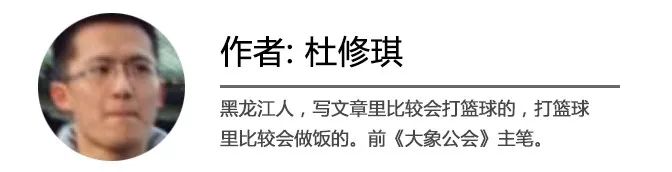作者供图
点击联系人间编辑
一百年前,他来到中国云南宾川州朱古拉的倮倮泼部落,生活四年,写出五篇倮倮族语言笔记、两篇人类学考察。一百年后,他被一些中国人宣传为:“中国咖啡始祖”。
去年初,我搬到云南大理,最初的日子很枯燥,逢人就聊天。
三月底,我跟一位客栈老板聊了一下午,他说自己最近去了一个山村,在宾川县的山里,偏,路难走,但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种着咖啡,接待客人,也会拿铁壶煮自己泡的咖啡。
我顿时被吸引了:即使在大城市,咖啡作为西式饮品,也远没有茶叶普及,在这个边境闭塞的乡村里,怎么会有这样的生活习惯?
“村里现在还有几十棵上百年的咖啡树,说是清末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是个法国人,真不知道当年他是怎么进到村子里!那路太难走了,现在还是土路,我们开越野车进去都很难。”
他只在那待了一天,知道的不多,我记下村子的名称:朱苦拉村。
回家后,我搜索了下朱苦拉村子,发现在2008年,曾有一家叫“后谷”的云南咖啡企业最早宣传过这里。他们召开了一个发布会,宣布这个村子是“中国咖啡的起源地”,拥有着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林,并在村里立了一块石碑。
但是,后继的报道里,和朱苦拉村合作的公司却在不断变化:有一阵子是意大利华人,后来又成了北京来的女商人。朱苦拉的名号也不断增多:“最古老咖啡”、“咖啡活化石”、“中国咖啡发祥地”……
各种商业报道中,关于咖啡具体是哪一年被带入这里的,说法五花八门:“后谷”的发布会上,说是1892年,而在另外一些报道里,有1902年,还有1904年。那位带来咖啡的天主教的神父也面目模糊,只知道他中文名字叫“田德能”,法国人,既没人知道他的法文名字,也没提及他的任何生活细节。
在图书馆,我在《宾川县志》查到了一段相对完整的记载:清末,天主教神父田德能,因帮助彝族村民打赢了与东升“顺江王”的官司,得以入村传教。清光绪三十年(1904),田德能正式受派遣进入宾川,在县城、朱苦拉村、力角镇生活了四年,发展教徒几百人,占到同时期大理地区的一半左右。
县志有记载,随后,田德能在宾川州城(今县城)设置经堂,拉拢官员,欺诈民众,强奸民女,最终被古底村村民告到省城,这就是“宾川教案”。之后,田德能被赶走,宾川知州也因此调离。
县志没有提到咖啡,也没有记载田德能的法文原名。这让我很困惑,也激发了我的好奇——我决定寻找更多关于田德能和朱苦拉的故事。
一位朋友告诉我,丽江有一座“田德能咖啡纪念馆”,墙上挂了很多田德能的照片,生意寥落,不知道是否还在营业。
我到了丽江,地图显示有两个“田德能咖啡纪念馆”,大研古镇的已经停业,束河的还在。我按照导航,沿着束河古镇中和路,到了聚宝街拐过去,走到头,都没看到什么咖啡馆。找出地图看,没有错,又折回去,找了两趟才发现一个小门,普通的木门,大概一米五宽,左侧放着白色牌子:田德能纪念咖啡馆。右侧则是五十厘米长的红色小牌子,大概是商标,线条勾勒的一个人扶着椅子,下面是字母:tiandeneng。
我跨进木门,是条三米长的通道,墙上挂着一幅咖啡的画,一幅标着说是田德能的黑白照片:一个中年白人站在山崖边,拿着烟斗,扶着椅子——这张照片就是门口商标的原图。
院子空无一人,我喊了两声,没人应和。正对着通道的是一个吧台,有菜单,但是没有服务生,吧台靠墙一侧是带着“田德能”商标的马克杯,中间是制作台,咖啡的种类都很常见:卡布奇诺,拿铁,摩卡,美式,意式浓缩,焦糖玛奇朵。
二楼看起来有几张沙发桌,但暂时没开放,像是一个待开业的私密咖啡馆。一面墙上挂着六幅大照片,都是咖啡地或者采摘咖啡的农民。
吧台旁边是一个二层房子,落地窗,透过窗户看进去,一个男人正躺在沙发上,脚蹬在椅背玩手机。我和他打招呼,他站起来,告诉我,他是老板,纪念馆的创办人,武戈。他皮肤黝黑,布满坑洼,上身穿一件黑色的冲锋衣,半敞着怀,露出系了一半扣子的白衬衫,握手时,胳膊上青筋直露。
我们就在玻璃窗旁边坐下,武戈给倒了我一杯水,告诉我,这家院子生意很少,以前有服务员,辞了,之前在丽江古城的店,也关了。若有人来看田德能的资料,就看,没有,他就在这坐着。
我问他怎么关注到田德能的,武戈笑了:“我也是偶然知道这个事情,觉得有意思,没想到越陷越深,就成这样了。”
武戈是新疆人,汉族,四十三岁,年轻时候在北京做音乐,后来又做户外运动,2007年来丽江,开了一家小咖啡店。2012年,他听说了朱苦拉村的故事,觉得是一个商机,于是注册了田德能商标,开了新的咖啡店。武戈同样寻找了所有相关的中文书籍,县志,其中一些摘录贴在了院墙上,但是,都没有超出我在大理州图书馆看到的范围。
院墙中央,有两张大白纸,上面是田德能种咖啡的基本经过,武戈起的标题是:“田德能——中国咖啡始祖”。
下面是一段倡议口号:
“我们与咖啡的美好生活,由他们在百年前开启并传承至今。
他们,是中国西南偏僻大山里种植咖啡的农民。
他们,是被中国咖啡爱好者遗忘的一个群体。
关注他们,从你开始,选择中国咖啡”
武戈又聊了一会儿,激动了起来。他告诉我,做“田德能”的五年,他尝试过卖咖啡豆、开了两次连锁咖啡、商谈入驻新景区,都没有成功。
“去年年底,是我最崩溃的时候,钱,时间,精力,已经折腾地什么都没有了,”他说,“今年开始店里只有我一个人,不再雇人,就卖卖咖啡,当一个宣传展览地点,钱也周转过来了。我想明白了,我只是一个链条的一环,我可以做的,就是宣传和研究田德能,这个中国咖啡的原点。除了我,没人再会接着做这件事了。”
武戈脱去外套,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咖啡,手臂粗壮得像是退役的体操运动员。他指着窗沿摆着的一排铁壶,说,这就是从村子里学来的,田德能教的煮咖啡的法子。
 △一排铁壶,是武戈从村民那里学来的煮咖啡用具 作者供图
△一排铁壶,是武戈从村民那里学来的煮咖啡用具 作者供图
2014年,武戈租了一辆面包车,从悬崖土路上开去了朱苦拉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沿着一百多年前田德能的路线,和朋友去爬老山路。爬到山顶,发现老路已经断掉了,只剩下两米宽的裂缝,下面是万丈悬崖。天色已黑,前行和后退都有危险,最后他们伏在悬崖上,一点一点蹭着边儿过去了。
“我在路上,就想,为什么田德能要来这里?他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当年的路更加不堪,不像现在有半山的公路、土路,他要翻山的呀,很多地方是悬崖……”
武戈忽然问我,知不知道朱苦拉老教堂?我说知道,田德能建的,第一棵咖啡树就种在教堂墙边。
“你知道我站在那里什么感受吗?我就一阵阵地冒冷汗。我想,这就是田德能当年待的地方,他在这里传教,面临的是即将驱逐他的村民,孤立无援。一想到这些,我就脊背发凉。”
我决定去趟朱苦拉村。我和朋友租了车,从大理市区出发,开了七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盘山路上。新修的乡道覆盖到了距离朱苦拉七公里的地方,但这最后一段老路,只有一车宽,布满碎石,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的时候太阳只剩了一点点余晖。
朱苦拉村在半山上,村里的房子白墙黑瓦,峡谷里流淌着的是草灰色的渔泡江,整个山谷都灰蒙蒙的,零星的绿色仿佛放大的像素颗粒。唯一的一大片绿色,就是村子下面的咖啡林了。
 △朱苦拉村半山坡的咖啡林 作者供图
△朱苦拉村半山坡的咖啡林 作者供图
我们把车停在一座废弃的水电站办公楼边,向山上走,下面的咖啡林都是新种植的,低矮,结着樱桃大小的咖啡果。往山上走,咖啡树高了很多,也都有蓝色的“平川镇古树名木保护牌”,写着品种,树龄。
田里躺着一块灰白色的木牌,是朱苦拉古咖啡林简介:
“1904年,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获得一株他的同行从越南老街经河口带入中国的咖啡苗,并亲手栽种下朱苦拉天主教堂后墙下的第一棵咖啡树。”
现存的古树,则分为百年树龄,和七十年树龄两批:
“栽种于1908-1912年间的24株,为百年咖啡古树,栽种于1948年的1110株。”
我们经过田里,有的矮树还开着白色的花,有的树干密集地挂满红绿相间的果子,从浅红到深红。村里一些平地上晾晒着咖啡豆,还有的堆在墙角,牛马经过,踩踏进泥土。
傍晚,我们村民李师傅家吃饭,他的家在村子中间,我们走了十几级石阶,拐过一道岔路,才进了院子。屋子低矮,进门后左手边吊着一盏钨丝灯,一个女人走进走出,正在煮饭。我们右拐进了主屋,李师傅打开电视,坐了一会儿,猛地站起来问:
“你们喝咖啡不喝?”
我立刻点头。他转身,向吊灯照射不到的角落走去,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拎出一个麻袋,掏出一个透明塑料罐,里面满满地装着黑褐色的粉末。他把塑料罐捧到桌上,摆了三个玻璃杯,然后用汤勺各舀了一勺,侧身,又拿出一罐白糖,各舀了一勺。停了停,又拿起糖罐,我连忙摆手:
“够了师傅,一勺就行。”
“不不,这咖啡苦。”他说着又加了一勺糖。
这种咖啡粉就是本地的咖啡,做法还沿用着一百多年前传教士传授的土法:每年十一月到第二年春天,采摘咖啡果,用砖头或者木板磨掉表皮,筛一遍,然后晾晒;半个月后,手工剥掉第二层皮,再次晾晒;晒干的豆子放入铁锅翻炒,最后送到磨房,磨成粉末,存储起来。
师傅用开水冲好咖啡,大颗粒的咖啡沫浮满玻璃杯口,我从桌上拿了一只筷子,拌了一下,杯底的白糖立刻泛上来。晾了两分钟,我喝了一口,粗粝的咖啡沫刮过嗓子,除了甜,嘴里没剩下其他味道。
“苦不苦?再加点?”李师傅又拿起了白糖罐。
“不用了师傅!”我赶紧说。
我问李师傅,平时他自己喝咖啡吗?
他说:“不多,喝茶叶多点儿——这村子每家都种,有的爱喝,有的不爱喝。”
我又聊到教堂的事情,问现在村子还有教徒没?
“现在没有了,原先就老人里有一些是教徒。老教堂还在那里,之前是小学,现在锁起来了,晒咖啡时候才让进。”
晚上,我们借宿在水电站旁边的一排板房里,接待我们的中年女性告诉我,周围也有村子种咖啡,有时候拿到这边来卖,因为可以卖贵一点。现在有人专门来朱苦拉收豆子,偶尔还买手工做的咖啡粉,一百块钱一罐。
她说,之前村子里没人弄咖啡,都是种核桃和玉米,后来不断有人进村来,要发展咖啡,于是,山坡上原来的粮田都改成种咖啡,政府专门发咖啡苗,水渠也是为了咖啡林修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由村长的妻子带着,进到武戈口中那个让他冒冷汗的老教堂里——如果没人领着,我根本认不出这是教堂,一个比篮球场大一点的院子,两栋二层的建筑,像是加宽的民房。主楼木结构的支架还很牢固,但墙皮乌黑,像是被火烧过,上面刻了一些曾经的标语——“学习雷锋精神”、“毛泽东思想万岁!”墙外四处都没有咖啡树的痕迹,转了半小时,我们就离开了。
去和李师傅告别的时候,他还专门去地里取了几株咖啡苗送我,嘱咐多浇水,“养两三年能结果”。
 △朱苦拉正对着的山谷 作者供图
△朱苦拉正对着的山谷 作者供图
1930年代,大理州约有教徒两千人,其中一半是宾川的彝族,也就是田德能最早去传教带起来的。回到大理,我去古城的天主教堂,周日上午的弥撒结束,我向神父询问,他一听到“朱苦拉”,就说,那里也曾经有教会,还有一座教堂,但是现在很难恢复了。我问他是否有田德能时期的档案,他说没有了,之前有一些法文的资料,很少,也和咖啡无关。
就在我一筹莫展时,我在一本书上发现了田德能的名字。书的全名是《倮倮·云南倮倮泼——法国早期对云南彝族的研究》,书的第一部分是倮倮族人类学笔记,作者为维亚尔,第二部为语言学考察,作者阿尔弗雷德·李埃达,中文名字正是田德能。
我给书的译者、中山大学的郭丽娜老师发了邮件。郭老师就任于中大法语系,国内研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少数专家之一。她很快回复了,确认李埃达就是田德能——她写过一篇论文,专门评述田德能,也就是李埃达的彝族语言研究。
她在论文里关于此人的生平是:“李埃达于 187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在法国旧孔岱,后来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1896 年 7 月 29 日被派到中国,1898 年至 1904 年期间在路南滥泥箐阿细部落中传教,也曾在宾川州朱古拉的倮倮泼部落生活过四年,1912 年 7 月 5 日卒于云南昭通。”
除了这本书,郭老师列出的田德能的五篇学术著作,还有三篇倮倮族语言笔记,以及一篇人类学考察。这些作品都是用罗马字母注音,勾勒出了基本的语法,还制作了一部《法倮词典》,给后来法国的彝族语言研究提供了帮助。
郭丽娜说,“李埃达是一位杰出的人种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华期间,他对传教地区的语言和文化均作过研究和比较,并与法国的东方学研究者保持学术往来。”
我再问她,是否还有田德能更详细的资料?她说没有了,资料不多,而且法国部分的档案没有人整理,没法研究。前几年,有一位国内的老师去巴黎,通过一位神父,调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但是档案馆不允许他进资料库,只能在外等候,而档案还堆在一起,尚未分类。没办法,他只好让对方,看到汉字就拿出来,最后拿到的是一批日文、中文、韩文混杂的文件。
郭老师说,本来在学界,李埃达就是法国汉学里西南民族语言研究的先驱之一。这些年,朱苦拉咖啡的宣传多了,她才仔细对比了田德能的足迹,派遣时间,对朱苦拉老村民做过访谈之后,这才确认田德能就是李埃达。
1912年,田德能死在昭通,还不到四十岁。他一直醉心于彝族语言,所有著作,都没有提到咖啡。没人能确定他带去的咖啡苗来自哪里,只能推断,是经越南进入中国时购买的。
我跟郭老师提起了丽江那个“田德能咖啡纪念馆”,拿出手机给她看咖啡馆里那些“田德能”的照片,她看了一会儿,摇摇头:
“这些都不是田德能,肯定不是,田德能的照片,能确定的只有‘一张半’。”
她从手机中找出一张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官方资料,照片中,来中国之前的田德能微胖。另外一张是大理教区天主教神父们的合影——其中肯定有田德能,但是最开始谁也没标识出来,因为神父们来到中国后都变化很大,不少人瘦了,留了胡须。最后仔细对比,推测其中一个很瘦的神父也许是他。
最后,郭老师建议我去找“云南精品咖啡学会”的陈德新,她说,陈是咖啡生意人,但一直在做咖啡文化的研究,马上要出书,其中很细致的考察了咖啡的起源,但他的研究里,似乎中国最早的咖啡并不是朱苦拉的。
“朱苦拉咖啡不是最早的?”
“对,好像有一个边境的景颇族村子,通婚带来几株咖啡苗,更早。”
我通过邮件联系到陈德新,在昆明见到了他。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咖啡生意人,他在1993年就开始生产咖啡浓缩液。1995年,陈德新听说当时德宏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一位老师曾去朱苦拉考察了咖啡林,说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咖啡,但他没有跟进。直到2008年,看到村子的宣传后,他才决定去研究这件事情。
我见到陈德新时,他已经出版了研究成果《中国咖啡史》。书中说,在中国大陆,最早种植咖啡的是云南缅甸交界处的景颇村子“弄贤寨”,时间是1893年。弄贤寨一界之隔的缅甸木巴坝早在1837年就由英国传教士种植咖啡。1950年代,云南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还收集过这批咖啡种,尝试着推广种植。
陈德新去过朱苦拉接近二十次,还出过一本《朱苦拉咖啡之旅》,里面考证过,朱苦拉引入咖啡的准确时间是1904年,由于山区闭塞,加上国外传教士后来的离去,这批咖啡从未没有流出村子,直到2008年才被包装宣传。
他说,这其中,还有一件他特别痛心的事情。他翻到书中一页,指着一幅根雕的图片说,“你看这张,这是什么——这就是田德能亲手种的最早的咖啡树,本来在教堂后墙旁边,自然死亡了。2008年做宣传,‘后谷’把这棵树根挖了出来,做成根雕。”
我仔细看图片,根雕被抛光,打蜡,变成亮黄色,正面刻了几排字,我勉强辨认出最大的几个:“后谷神韵”。
我于是问陈德新:“后来和朱苦拉村村合作的,就不是‘后谷’了吧?”
“对,后来就换人了,先是一个意大利华侨,后来是北京来的女商人万雪君。但是这颗树根是在‘后谷’那里,就在德宏的咖啡会所。”(注1)
● ● ●
半个月后,我去了德宏州,找到了在州府芒市的中心广场旁边的后谷国际商务会所。会所有一座院子,可以做简餐饮品,侧面的铺面售卖咖啡周边商品。服务员递给我菜单,我翻到第二页,就看到“后谷铁皮卡咖啡”,文字简介说,这是来自朱苦拉村的咖啡,历史可追溯到1892年田德能的引入。旁边还有一些咖啡豆的图片,然后标注了价格:特价200元/杯,续杯300元/杯。
“有人买这款咖啡吗?”我问服务员。
“很少,但还是有的。”
“这款咖啡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吗?”
“就是,咖啡豆是老咖啡树的,历史比较悠久吧。做法都差不多。”
会所正在装修,里面的根雕也被转移到大厅的角落放着。我仔细看了这棵百年树根上刻的字,竖着有几排,写着1892年田德能进入朱苦拉的事情,还标注着品种:蒂皮卡(铁皮卡)。
大厅里除了我,没有别的客人,灯光也很暗。树根的两段向两边伸出,模模糊糊中,仿佛一个伸开双臂,正等待拥抱的人。
我从芒市又去了瑞丽,拜访云南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张洪波。我想向他确认,朱苦拉咖啡是否晚于瑞丽弄贤寨,因为这有关田德能还能不能保住“中国咖啡始祖”的身份。
张洪波1984年毕业于华南热作学院,之后一直做咖啡品种研究。见到他时,他才从园圃种苗下来,头发凌乱,讲话时习惯性地扶着眼镜。
“目前看是的,(弄贤寨)那一片挨着缅甸嘛。”他说,“只能说,1893年是一个保底数,是我们能确定的最早的时间。”
“那品种呢?和朱苦拉的一样吗?”
“那边有罗布斯塔种,也就是中粒种,也有铁皮卡,就是小粒种,我们叫老品种。老品种和朱苦拉的一样,但是来源不同。”
张洪波给我讲解了品种的差异:很多人都将“小粒咖啡”作为云南的特产,实际上,人们熟知的蓝山、耶加雪菲、苏门答腊(曼特宁),世界上70%以上的咖啡都是“小粒”,也就是阿拉比卡种。也只有这种咖啡豆能作为单品,加工成有风味的咖啡,这些风味受海拔、降雨、初加工方式影响大,所以,一般都以地名命名,而不是颗粒大小。
小粒的阿拉比卡种发源于东非,直到20世纪中期,仍然是咖啡里的主流,也就是张洪波所说的“老品种”,最典型的就是铁皮卡,以及它的变种波旁。到现在,老品种仍受到咖啡爱好者推崇。朱苦拉、弄贤寨的咖啡,都是老品种铁皮卡。
“朱苦拉主要还是文化价值。”张洪波说,“那里的咖啡林延续一百多年,保存完好,又有着传教士的故事,这是独一无二的。品种上,它对中国咖啡几乎没什么影响,太偏僻了。”
建国后,云南大规模种植的咖啡,是来源于苏联的要求。经过一番试种,云南潞江坝的国营农场开始大规模种植咖啡,品种也是铁皮卡。当时,别的国家已经有新品种出现,“那个年代很闭塞,拿到种子是很困难”,张洪波说,“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去中美洲、非洲考察,人家都很谨慎,绝对不允许种子被带出去。”
潞江坝第一批咖啡成熟后,中苏关系破裂,咖啡改为用于出口赚取外汇。
在潞江坝镇,快七十岁的董祖亮带我开车去了新寨村,这里号称中国咖啡第一村,在半山坡上,种植着一万多亩咖啡。
“我呢,小时候就在农场,那时候粮食不够,饿肚子。我就看到老鼠总跑去咖啡田里,吃那个豆子,我也跟着尝了一下,咖啡豆红了之后,糖分很高,芯是甜的,这就没事儿就去吃,就外面那层果胶。后来留在农场了,就专门研究它。”他说。“那时候我的老师,他就说这玩意是给国外,有钱人喝的,咱们国家还没到喝这个的水平。”
我询问他对朱苦拉咖啡的看法,董祖亮说,那里是老品种,风味不错,但是气候太干燥了,土壤也贫瘠,缺水是个大问题。
“现在潞江坝种咖啡多吗?”我问他。
“没那么多了,这两年收购价不到十五元,很多农民都把咖啡树砍了,改种蔬菜。”他说,“咖啡价格太不稳定了,而且还要三年才能摘果。不像茶叶,种茶的农民都会自己泡茶,但很少有农民喝咖啡。”
回到大理,我拜访了一位咖啡烘焙师张胤,他在大理古城经营着一间烘焙实验室。进到实验室里,地面、桌上摆放着不同来自各个产区的咖啡生豆,桌上留着烘焙的记录表格,上面标注着温度、时间、品种等信息。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培训学员,两人面前摆着三杯咖啡,是昨天烘焙的三锅咖啡豆,每隔几分钟,两人就分别用勺子舀一勺,快速地吸进嘴里,然后吐出,然后评点一番。这是咖啡杯测,一种成熟的咖啡测试方式,小口地吸入咖啡,能快速在口腔内散开,从而辨别其中风味,再根据各项打分。
“中间这杯平衡性好一点”,张胤对学员说,“前面那杯香气没烘出来,后面这杯有涩味,算失败了。再过五分钟测一下,瑕疵会更明显。”
张胤说,刚开始在云南,也主要用进口咖啡豆,后来接触到云南本地的庄园,发现生豆的质量总是差一点,“主要是种植、初加工的精细程度不够。”
两年前,张胤就尝试过朱苦拉咖啡豆,一位朋友骑摩托车进入山村,带了几斤生豆给他。
“品种不错,一些是铁皮卡,还有一些波旁种”,他笑了笑,“但是我不推荐这款豆子。”
“为什么?”我问。
“种植的条件不好,缺水,导致豆形不整齐,农户的初加工太粗糙了,仓储条件也不行,风味损失很大。”
我想起来村里堆放咖啡的墙角,各家零零散散晾晒的豆子,之前一位摄影师,还拍摄过村里老人,按照以前的习惯用牙给咖啡豆去皮。
“而且,现在朱苦拉豆子宣传的厉害,贵,性价比不高”,张胤说,“正常的烘焙思路,是不会选择这种豆子的。”
● ● ●
我又去丽江见了一次武戈。我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发现他把田德能的照片都撤了下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笑了,说后来有人告诉他,照片弄错了,所以都换下来。
“那商标怎么办?”
“那个没办法,都注册了。就那样子吧。”
武戈说,自己的咖啡馆经营状况已经改善不少,现在又振作起来,也许未来会和别人合作,再开出去。他还是惦记田德能的事情,我转述了郭老师的一些研究,他很感兴趣,问我能否向郭老师要到田德能真正的照片。
于是微信上联系郭老师,将田德能的照片发给我后,说即将要去法国做交换学者半年,不出意外会去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馆调一下。
九月,我问郭老师进展如何,她说一个传教士给了一些田德能的照片,但是没有进到档案馆。又过了一个月,她告诉我,档案馆馆长变动,现在不论外国学者还是法国本土研究者,都进不去,可能帮不上忙了。
田德能的故事依旧残缺不全。他在朱苦拉只待了四年,种的咖啡才成熟,第二年就被驱逐了,后来种植大片咖啡林,向村民传播技术的,是新派的神父。
● ● ●
尾声
有一天,朋友告诉我,大理古城床单厂正在办“百年大理”摄影展。我在办公区见到了床单厂艺术总监乔崎,他为了积攒传教士拍摄的大理照片,也去过法国拜访过巴黎外方传教会,但同样没有拿到任何资料。
难得的是,乔崎和同事随后去了法国南部的波城,这里是伯大朗圣心司铎会总部所在地,就是他们修建的大理主教堂,接替了田德能所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
伯大朗圣心会给了乔崎一份回忆录,是大理教区第一任主教叶美璋写的。我翻阅了回忆录,其中有两段和朱苦拉相关:一段是叶美璋听说朱苦拉的传教基础很好,赞美了之前神父的工作,另一段是说朱苦拉的咖啡种满了山坡,当地神父留下一点,其余的都运去了昆明。没有提到李埃达(田德能)的名字。
我依旧在寻找田德能,但是希望渺茫。
寻找过程中,我不断听到类似的故事:云南西北部的茨中教堂,由法国传教士许伍冬带来了葡萄酒技术,变成了现在几千亩的庄园,靠近缅甸的澜沧县,美国传教士永伟里家族建立了糯福教堂,创立了拉丁化的拉祜文、佤文等,并翻译了赞美诗,这些多声部的唱法流传至今。
曾经的传教士们,在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进入的偏僻角落,细致,琐碎,又连续地带来了影响。他们曾经被一笔带过,现在,又被装扮成可以营销的历史。
● ● ●
注1:在2017年6月“首届云南大理宾川朱苦拉咖啡论坛”的新闻报道中,介绍过朱苦拉村咖啡近十年的“开发历史”:1981年,云南省著名热作专家已故的马锡晋教授深入朱苦拉村进行考证研究,认定13亩的朱苦拉咖啡属于云南小粒咖啡最古老、最纯正的波邦铁皮卡品种;2008年7月27日,德宏州宏天实业集团后谷咖啡有限公司组织了十几家中央省市新闻记者突击性造访了朱苦拉古咖啡林,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2010年,侨居国外33年的浙江籍商人吴洪平来到朱苦拉村,投资开发朱苦拉咖啡,并注册了公司;2011年,在北京做照明器材生意的万雪君入股,2012年,吴洪平撤资。
根据2014年《中国妇女》的报道记载:2013年5月,万雪君抢下了“中国虹吸壶咖啡师大赛”的主办权,把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评委请进了朱苦拉村,朱苦拉咖啡是参赛选手规定动作的必选咖啡豆。赛后,国外专家一致认定,百年工艺制作出的朱苦拉咖啡,价值超过100美元/杯,13亩朱苦拉百年古咖啡林年产咖啡豆4.5吨,万雪君部分制作成咖啡礼盒,售价高达1800元/套。
编辑:沈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