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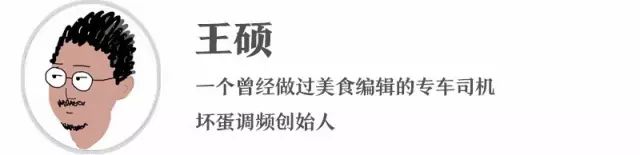
在一大口开专栏,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原来做过几年美食编辑,后来去开了一年的专车,再后来专车合法,我觉得没意思了,于是写了一本和非法专车有关的书,现在重新回来写一些和美食有关的道听途说。
通常写第一篇都比较难,不知道从何入手,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难”字,打算从难吃的东西开始说。
从小到大,我听很多人说过最不喜欢吃某样东西,比如榴莲,比如香菜,比如葱。但榴莲香菜和葱与一碗北京豆汁儿放在一起,这些人可能会重新思考榴莲香菜和葱于他人生的意义。
有一次,我一个高中同学对豆汁儿的形容特别贴切,说这就是一碗洗脚水,碗边残留的豆渣就是混着肥皂泡的脚巴丫泥。虽然我爱喝豆汁儿,不喝洗脚水,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形容特别贴切。只可惜那个同学没有把这句话写进刚才的作文试卷。

豆汁这种饮料,味道实在难以形容,但是爱它的人真心离不了
那次我们三个去中戏赶考,参加笔试,可能是因为后来在地安门路口喝了那碗“洗脚水”,我们三个都没去成中戏。
关于北京地安门那个路口,后来还成了流行文化当中的一个符号。陈升《北京一夜》里提到过“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地安门”。电影《顽主》当中有一段时装走秀,堪称经典,但是这段戏原本的结尾,是一个超级胖的大胖子上台,一人压全场,后来这段戏不知道为什么被减掉了。当时那个大胖子每天就坐在地安门路口的西南角,也就是今天“秋栗香”的门口。关于秋栗香,最近有一个传说,他们家旁边有一个咖啡店,如果你在咖啡店消费,就能买栗子不排队,所以在那样一个和咖啡没有任何关系的路口,那个咖啡店的生意着实不错。

地安门传奇之一直在排队的秋栗香
后来我和许多人讨论,为什么他们觉得豆汁儿难喝,他们说的理由全都成立,我听过那种小公主型的女生跟我说过豆汁儿不够美,还有我一个亲戚跟我说过豆汁儿太酸,而且老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种腐朽的臭,是放坏了的东西。我觉得他们都说的特别有道理,豆汁儿从各个角度来讲,就不应该是人见人爱的东西,我们这种喜欢它的人,纯属意外。
后来我分析过这种意外,没有结论,但是可以用一件事去做比喻。这就好比小时候踢完一场球,回到家,有三种饮料摆在面前,分别是北冰洋、酸梅汤、豆汁儿,我一定选择豆汁儿。北冰洋喝完了打嗝,酸梅汤喝完了觉得涩,就像是杨梅吃多了,牙齿失去知觉。真正解渴的只有豆汁儿,而且没有副作用。
关于豆汁儿,各种微信公众号上有各种推荐,我倾向于北新桥二条里面那家“粉房”。说是粉房,并不是粉色的,这个“粉”,你可以理解成是凉粉儿的“粉”,凉粉儿是北京的另外一种食品,制作工艺和陕西凉皮很像,只是原材料不同。

北新桥二条里的粉房,豆汁一直不错
他们家的豆汁儿我不敢说有多好,只能说确实不一样,酸味没那么重。不过,我倾向的原因和味道没关系,而是一段故事,被作家叶广岑写成《豆汁记》,基本上是豆汁儿最好的文学注解,相当于豆汁的说明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在这里不赘述。
关于豆汁儿,后来还在日本宫城县喝过一种,叫毛豆汁儿。但那个不是豆汁儿,更像是甜豆浆,只不过那个豆浆的颜色有点绿,豆味也比咱们这边早点摊儿上的豆浆更浓。除此之外,我还有过一场邪念:如果有一天妓院合法了,我一定开一个豆汁儿店,让男的给女的做大保健。
除了豆汁儿,我朋友圈里被谈论第二多的难吃食物,就是一种叫哈吉斯的东西了。哈吉斯原名Haggis,是苏格兰传过来的。我去苏格兰之前,别人就对我进行过预防普及教育,告诉我种种关于哈吉斯的可怕。后来我去苏格兰吃了哈吉斯,是挺可怕的,可怕的不是哈吉斯,而是那些随随便便说可怕的人。其实哈吉斯很好吃,到底有多好吃呢?如果你能吃香河肉饼,哈吉斯就是你在苏格兰时期的香河肉饼。

哈吉斯,羊胃做肠衣,羊肝羊心做内馅,被称为苏格兰“国菜”
后来有一次找广州来的鲍汁飞老师做节目,觉得他来自南方,吃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于是就问他吃过最难吃的东西是什么,他说的不是野味,而是有一次去新疆吃到的羊尾油。我听了之后觉得纳闷,羊尾油挺好吃的,无论是拿它涮锅子,还是烤成羊肉串。
他说对,是涮是烤都好吃,但他那个是生吃,羊尾油刺身。
欢迎分享一下你觉得难吃的东西,下周见。
文:王硕
图片源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