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身患肺结核,葛剑雄或许不会成为学者。
1962年5月,正在读高二的葛剑雄,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开放性肺结核,拍片复查,确诊无误。他被迫休学治疗,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他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年高三“试读”。但是到第二年高考报名体检时,他的肺结核还是没有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如果葛剑雄没有患肺结核,他将于1963年高考,大学即将毕业时,会遇到文革的开始。最后,迎接他的会是另外一条路。但是,患上肺结核,迟迟未能“钙化”,他不得不高中毕业就留校工作,以一个中学教师的身份度过文革10年。恢复高考后,他直接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导师是谭其骧先生。他的学术生涯开始得很晚,但是起点很高,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博士,第一批赴海外交流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生涯保持了完整性,没有被文革打断。
肺结核钙化,是一个医学专业术语,网上的解释如下:在机体抵抗力强,或者化疗后,干酪样病灶中的结核杆菌代谢低落,繁殖能力被削弱,病灶失水而干燥,碳酸钙和磷酸钙没着形成“钙化”。在胸部X光片上要想看到病灶钙化,一般需要1—3年以上时间。肺部结构病灶钙化的快慢与年龄关系甚大,儿童、少年在长身体、长骨骼时期,钙磷代谢旺盛,肺结核钙化要快些,彻底些,一般一年到一年半。成人肺结核钙化过程缓慢,往往要数年时间。
我喜欢“钙化”这个词,它让我想起通常所说的“缺钙”。在隐喻的意义上,一个社会也需要“钙化”,比如说,我们至今还没有从文革这场病中形成“钙化”。一个人也需要“钙化”,从病痛中挣扎,结疤,蜕变,新生。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词,我们可以换一个。葛剑雄本人用的是“反思”,他的新书,书名就叫《我们应有的反思》。这本书还有一个副题“葛剑雄编年自选集”,除了第一篇“我的1978年”之外,以后的每一年,都包括作者的简单纪事和自己选出的文章。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做70岁葛剑雄的自我总结,他在“纪事”中所作的挑选,表明他希望自己以这样的姿态进入历史。这不是一个真实而全面的葛剑雄,而是一个他希望展示、希望我们阅读或记住的葛剑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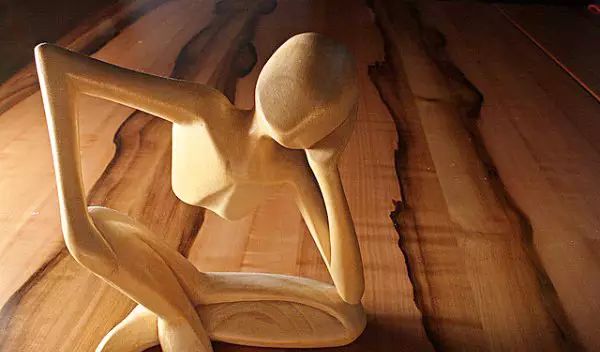
这是一个多声部文本,包括三种类型的文章:个人纪事、学术文章和非学术文章。分别塑造了三种形象:个人史中的自己、学者和知识分子。作为普通读者,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第三种形象。这一部分文章,是未被学术体制侵蚀的,或者虽然被侵蚀但却已“钙化”的他。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1994年葛剑雄就撰文呼吁调整生育政策:“逐步改为‘鼓励一胎,容许二胎’,在推行中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如税收、福利方面的优惠和限制。”(《中国人口:21世纪的忧思和希望》)。葛剑雄的学术研究,是从历史人口地理开始的,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西汉人口的考证,可以说,他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是基于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而提出的,是一个学者进入现实的尝试。
中国从2014年开始放开单独二胎,2015年,上海等地有不少人呼吁全面放开二胎,从这个角度看,葛先生的建议,早了20年。如果从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这一角度入手,葛先生的建议,是不够坚决的,但是这正是他介入现实的特点:从历史和研究出发、从政策的可行性出发进行提问和建议。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即使在历史学中,恐怕也只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分支,葛先生为公众所熟知,多半是因为他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公共发言。他对现实的介入,某种程度上是“政协委员”式的,不求轰动效应,而力求能做现实的改变。
但是,即使是这种“不够坚决”的介入,也会引起不小的反弹。2009年,他在广州“岭南讲坛”做报告,在回答听众提问时,他提到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经媒体报道后,竟然引起一片大哗,甚至有斥为“卖国”、“媚韩”的,网上讥刺和谩骂更不一而足。他不得不写一篇小文《礼失求诸野》发表在《SOHO小报》上,来证明韩国对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他举了一个例子:韩国在1972年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产生于1377年,相当于中国明朝洪武年间。《直指心体要节》显然传自汉传佛教和产生于中国的禅宗,用的是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到目前还没发现更早的同类印刷品,这却是历史事实。
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捍卫,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他进入公共领域发言所秉承的原则。这样的影响,来源于他的导师谭其骧先生的影响。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出了一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版,把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疆域拼凑出一个极盛疆域,以便显示中国从来就拥有辽阔的领土。比如,无论如何,中原王朝的边界都要画在长城之外,至少要比长城更外一些,是为了证明长城绝不是中国的边界;从秦汉时期开始,就要将台湾和大陆画上同一种颜色,是为了突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80年,谭其骧先生起草了一份修改提纲,指出孙权当年去台湾是为了掠夺人口,结果得不偿失。而元朝的澎湖巡检司只是福建同安县的派出机构,显然不可能管辖台湾,文献上也没有找到过任何证据。谭先生的意见是,台湾在清政府设府以前,不应被看做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在历史地图上可以采用中国的基色,但不同于大陆上的政权。谭先生的主张,遭受到重重阻力,经过反复争取,1986年后的《中国历史地图集》(7、8册)才按照这种方案修改、出版。
反对者除了死板的官员,也有不少是有声望的学者。他们认为,画历代的疆域,是越大越好,谁要根据史料进行缩小,都有“卖国之嫌”,而主张尽可能大的,都成了“爱国主义”。有人质问:“画大一点儿有什么不好?”据说,还有著名学者向各级领导上书,指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本自唐代至清代某段边界的画法对国家不利,是“卖国主义”。谭先生的这段故事,葛剑雄1997年就撰文提及(《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我的史学观》),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经常提到,这种“提到”,很明显是故意为之,要传递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甚至是对现实的某种反抗。
在种种“爱国主义”热潮盛行的今天,对历史真实的捍卫与坚持,不仅需要研究得来的知识,有时候还需要勇气。
在“一带一路”成为热门概念的当下,葛先生指出:“当初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命名‘丝绸之路’时,指的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路线,而现在指的地方已经离开了当初李希霍芬命名的路线。我们以前更多只看到中原对今天的新疆、中亚,或者华夏诸族(也就是汉族、农业民族)对这一带的影响,实际不止如此。欧洲对这里的影响早就开始了。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这条路主要不是由汉朝人,而是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建立的,动力来自他们。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是张骞通西域起到的效果。但张骞通西域本身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贸易。”(注:这是他的新文章,《我们应有的反思》没来得及收入)从这个角度进入“历史”,其实所指称的乃是现实。
用作书名的文章《我们应有的反思》写于1995年,那一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葛先生此文的主要主张是重提日本的战争赔款,但是他当年认识存在“失误”,比如沿用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的陈说,在这本书出版时,葛先生在《自序•七十而思》中专门做了更正,能不能思考,不断纠正自己,这才是“应有的反思”。
这些年葛先生逐渐被媒体打造为所谓“明星委员”,在两会期间要对各种热点事件进行回应,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会期间自己是“公共产品”,在我看来,三言两语地回应热点事件,被媒体随便地拿去做个标题,很多时候往往背离了他自己的本意。因此,他在70岁的时候,出这一本“自选集”,收录了很多谈论现实的文章,或许有他的良苦用心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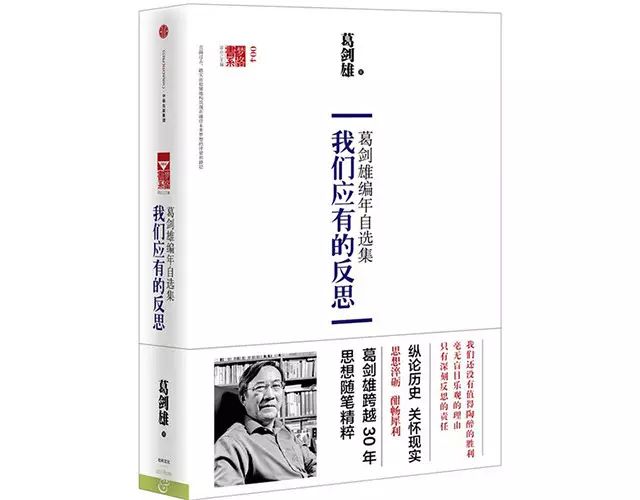
▲《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著,中信出版社
(本文原标题《从对历史真实的捍卫中进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