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是豪放词的代表,更准确地说,苏轼词代表了一种反映士大夫的生活、趣味与学识的新式词,更多地借鉴了文人诗与古文的创作经验,与俗乐性质的本色词有着明显区别。
那么,苏轼是在怎样的文学背景与时代际遇下,开始了这种独具特色的创作呢?
苏轼出身于曾经孕育了《花间集》的蜀地。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评传》中猜测,苏轼对词的爱好,与少年时故乡文化的影响有关。如果是这样,苏轼少年时应该有不少“花间”风格的词作。但事实上,我们今天看不到苏轼出蜀前后的词作,他少有的无法系年的词作,也不似少年轻艳之作。很有可能,他开始填词是比较晚的。
苏轼的座师欧阳修也是重要的词人,苏轼词学受其影响,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苏轼在欧阳修身边时,似乎也没有词作。

▲ 《十二月令图》之九月登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根据龙榆生先生《东坡乐府笺》的编年,苏轼现存最早的词,作于杭州通判任上(本文所引苏词,文字均以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为据。《龙榆生全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个别标点依词牌格律有修订)。我认为这是可信的。杭州是苏轼词的起点。苏轼少年高第,早期的诗文还不无拘执之态。那么,外放杭州期间发生了什么,促使他变得通脱,走向了词这种当时还算是新出的文体呢?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词学前辈张先正在那里。
在苏轼之前的词坛,已经有了柳永。但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还保守着晚唐以来的那种婉约的小令,越写越雅。对于柳永那种节奏繁复的长调,还带着俗乐气息、多有放达之语的新式词,还不能接受。苏轼的豪放词,在调式和语言风格上,多有得力于柳永之处,而在柳永和苏轼之间,还隔着一个张先。
张先使用的很多词牌,都与柳永相同,这在他那一代人中,其实是极为少见的。张先的词,也有像柳永一样的佻达之作,但也有了像《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这样,用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改造新词牌、反映士大夫生活、变俗艳为清越的词作。张先是较早接受柳永词牌体系的士大夫,也是较早改造这个体系的词人。
苏轼在杭州,与张先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宴饮唱和。苏轼在杭州的词作,有很多体现出张先的影响。
如《行香子·丹阳寄述古》:
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消魂。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 寻常行处,题诗千首。绣罗衫、与拂红尘。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
这是苏轼杭州词中较早、较完备的一首,可以算是苏词的压卷之作。苏轼巧妙利用上下阕结尾的三言句,营造出飘逸隽永的效果,下阕更胜于上阕。相较之下,上阕开头数句,仍略显陈熟,流露出一丝尝试新文体的生涩。在此之前,恐怕苏轼真的没有过太多的填词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行香子》这个词牌,不属于晚唐的词牌系统,目前可见最早的使用者就是张先。很有可能,苏轼是在张先处学到这个词牌的。而这首带有尝试色彩的词作,已经是酬赠之作,属于典型的文人诗功能,而非俗乐的功能。苏轼一出手,就是在士人的生活场景下填词,并不曾有过更为本色的情爱旖旎之作。可以揣测,苏轼最初填词,就是为了酬赠,也就是为了适应当时刚刚开始流行的以词酬赠,特别是以新式词牌酬赠的风气。
苏轼在杭州的词多为酬赠词,其中不乏与张先酬赠者,如《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与文人诗一样,这首词是有题目的,题目已经清晰地说明了写作背景。与其索隐莫须有的背景细节,不如首先注意到其士人化的功能、审美,以及可能是学习对象的酬赠对象。词中对山水的专注审美,是俗词所不具备的士大夫情怀。“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更是其中秀句,是对风景很好的观察。如果论缺点,则上阕过于拘执于风景的刻画,下阕则花了过大篇幅化用“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典故。这么做,很像是为了适应词牌要求而疲于奔命的结果,缺乏后来苏词的飞动,显示出初学者的窘迫。
苏轼开始填词,是受张先的影响,而非欧阳修的影响,这意味着,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柳词,而且是已经开始雅化的柳词,而非继承朝中的雅词传统,及其背后的花间词传统。
除了张先的影响,还应考虑到苏轼此时的心境。苏轼离开京城,从杭州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外任时代,虽不能说是贬谪,却也是有很多落寞失意的。
苏轼本是被视为预备宰相的少年英才,但在他成长的路上,却横亘着“拗相公”王安石。当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际,苏轼却没有像同龄的官员一样投入进去。当王安石变法波及到苏轼任职的领域、试图将科举内容由诗赋改为策论时,苏轼还参奏了一本,表示异议。这次参奏表面上胜利了,却也吸引了敌对方的注意。苏轼在这一年出题嘲讽王安石的小事都被记录下来,其实说明了这件事在王安石心底是一个难以化解的芥蒂。
于是,三十二岁正当锐意进取之时的苏轼,中断了他的拜相之路,悄悄离开了京城,前往杭州。我们无法知道,在这次体面的告别之下,有着怎样的暗潮涌动。苏轼这次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但他春风得意的青年时代就此结束了。
也许是放逐的心境更有益于洞悉人生的真谛、开阔接纳新文体的胸怀,也许是宴饮酬唱活动自古就是新文体雅化的催化剂,此时此地,苏轼与词相遇了。
五年后,苏轼从杭州通判转为密州太守,从见习太守转为实职。此时朝廷对苏轼的态度颇为暧昧。一方面绝不肯让他回到京中继续有所作为;一方面又仍然维持着他在地方官序列里的迁转,保留在较高的品级上重新叙用他的可能性。苏轼也继续在这不好不坏的胶着状态中磨练。
离开杭州后,苏轼继续写词。在去往密州的路上,他写下了《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仍然是一首酬赠词,属于行旅中的寄赠。其中,“渐月华”一韵,是一组漂亮的扇面对,显示出长期受到赋与骈文熏染的文人不俗的文字功底。而后文仍然显得生硬,为长调复杂的声律所缚,特别是像“似此区区长鲜欢”这样的句子,仍然显得稚嫩,有“填”的感觉。像“身长健”这样的表达,既是借鉴了俗乐的语言,也不失为此时真实心境的流露。活过挡路的老人,是受到压制的青年人此时唯一的希望,这句祝福的套语,却成了一件非常现实的事。
在密州任上,苏轼的词得到了大发展。比起在杭州时,在密州的苏轼似乎更为孤独,再也找不到以词酬唱的朋友了。一个好的诗学群体,可以带领伟大的诗人见识新的天地,但只有离开这个群体,伟大的诗人才能在孤独中最终成就。苏轼再一次印证了这条规律。苏轼一生经历了很多孤独,而在密州任上,他大概是第一次尝到孤独的滋味。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苏轼此时的词,减少了小群体中的酬唱,而有了更多咏怀式的个体吟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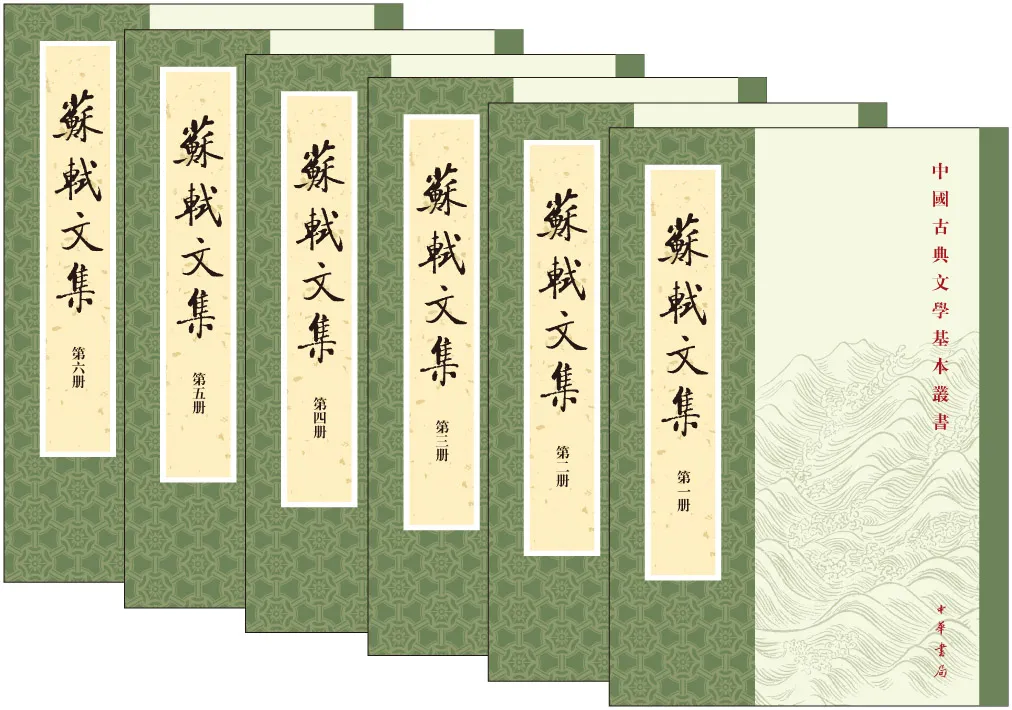
▲ 《苏轼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比如我们熟悉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就是一种个体的低吟: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豪放—婉约”二元对立的思维下,这首词总是被拿来当苏轼婉约词的代表,因而很容易被混同于词的原生状态,即传唱的俗词。但应该注意的是,这是一首悼亡词。与俗词相比,悼亡词虽然同样关涉女性,但关涉的是身份非常特定的一位女性,且这位女性是得到儒家宗法承认的正妻。更不必说,这位女性已经逝去了。因此,悼亡词比那些带有调笑性质的俗词要严肃很多,有了更多的个人性、文人性。
悼亡本是文人诗的典型功能。潘岳的《悼亡诗》被视为悼亡的样板,而潘岳《悼亡诗》见于《昭明文选·诗部》的“哀伤”类。《昭明文选》构建了一个排斥声色伎乐的文人文学世界,进入《文选》的作品,在人们的印象中成为最典型的文人文学。潘岳之后的整个悼亡传统,都是一种对潘岳的追步,亦即对《文选》的追步。因而,直到苏轼之前,很少有人用词来悼亡。苏轼写作悼亡词,是又为词褪下了一层旖旎的颜色,为词这种方兴未艾的文体,向典雅的《文选》又要了一块地盘。
苏轼的这首词,无论是内心对亡妻的诉说,还是所记叙的梦境,都是极为私人化的,是不必像柳词那样,拿到大庭广众下万口传唱的。读者其实都知道,这就是苏轼在怀念王弗,而非一个无名的男人在思念一个无名的女人;这就是苏轼在某一个夜晚的完整梦境,而非一个可以任意移植的语焉不详的话头。
苏轼感叹,“十年生死两茫茫”,在这十年中,苏轼已从少年得意落入了中年失意。让亡妻“纵使相逢应不识”的,不仅是自然的衰老,更多的是四十岁的苏轼,已不再像三十岁的苏轼那样壮志凌云、所向披靡。
苏轼在悬想千里之外的孤坟,孤坟所在的千里之外,也是他的家乡。想念亡妻,也是在想家。人穷反本,在受到打击的时候,人就会渴望故乡的庇佑,想要做回当年那个简单快乐的少年。苏轼在离开京城前往杭州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写下,“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他从那时就已经对官场心生厌倦。或许他在想,再干这一任,攒够了养老的钱,如果还不能回京,就回老家归隐。然而,杭州通判任满,他既没能回京,也没舍得回家,而是仍然恭顺地出任了不尴不尬的密州太守。这时候,他心里大概也会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的理想。
苏轼在梦中还乡,是去会见亡妻,也未尝不是去看看家乡,暂时回到令他感到安全的少年时代。而他为自己营造的“小轩窗,正梳妆”的温馨场景,即使在梦中,也是很容易被打破的,转眼就变成“惟有泪千行”,回归到现实中的“明月夜,短松冈”。
值得一提的是,《江城子》是苏轼与张先酬唱时用过的词牌。在孤独的处境中,苏轼在“记梦”的低吟中,选择了这个词牌,或许也会想起在张先身边的日子。
没过多久,同样用这个词牌,苏轼又写出了最典型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套用《文选》的分类,这首词应该属于“田猎”。在《文选》中,“田猎”是赋的功能,连诗都高攀不上。田猎诗的兴起,要等到盛唐前期王昌龄的时代了。而把这个功能引到词里来,苏轼可能是开天辟地的。与其说苏轼是拓展了词的功能,不如说苏轼是提高了词的地位。
苏轼在这里自称“老夫”,其实,他才虚四十岁,“聊发少年狂”也没什么特别不可以的。他喜欢这么说话,早在壬子年过第三个本命年的时候,他就自称“人老簪花不自羞”(《吉祥寺赏牡丹》)了。大概是他出身太早,虽然人还不老,但是已经觉得过了很久了。这里说的“鬓微霜”,也就是上一首里的“鬓如霜”,看来,苏轼很在意自己有了白头发这件事。其实,颜回、潘岳,都是三十出头就有了白头发了,何况苏轼已经四十了,或许他此时也想到了这些古人。
苏轼很好地利用了《江城子》中三言句的声情,“左牵黄,右擎苍”,几个三言句都写得非常爽利,模拟出了田猎时的果决、快意。他十分得意,他做一点“聊发少年狂”的轻狂事,能做到“倾城随太守”,看来这个太守人缘不错,自有一种“倾国倾城”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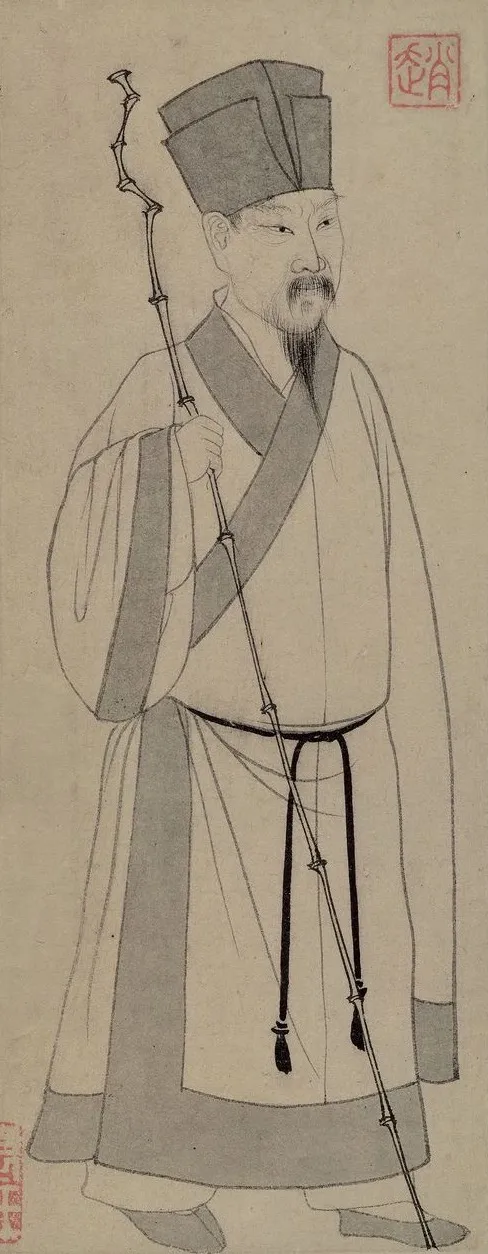
▲ 赵孟頫《赤壁赋 卷首苏东坡像》(局部)
即便如此,苏轼还是会落寞地想到,“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在外任过得很惬意,或者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惬意,但他还是会想,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叙用我,让我回到京城呢?
这里苏轼用了冯唐的典故,他真正产生共情的,恐怕不是那个被冯唐搭救的魏尚,而是冯唐本人。冯唐自己说,汉文帝喜欢文人、汉景帝喜欢美人,他是武人、长得丑;等到汉武帝喜欢武人了,他又老了。这个口吻,和后来苏轼说自己“一肚皮不合时宜”莫名相似。苏轼少年高第,但是当时的大佬说,他太年轻,要历练一下,没有及时给他升到高位;后来就赶上了王安石变法,他没能和同龄人一样攀龙附凤;到了现在,大概已经有更年轻的少年高第出现了。朝廷的荒谬,让幽默的苏轼联想起了冯唐。四十岁的苏轼想,我是不是也得像冯唐一样,等到九十岁去呢?
这首词中,两次提到了“射”的动作,我们不必对此求之过深,与当时的边境形势强行联系。苏轼是个文人,不可能有带兵去边疆打仗的理想。这个“射”的动作,更多的只是一种意象而已。射箭可以让相对的弱者有机会挑战远距离外的强者,人可以射老虎,在地上可以射星星。苏轼此时身处劣势,心头的理想之火却没有熄灭,他还想挑战强大的对手,或许也在默默诅咒朝廷中那些高不可及的存在。一个“射”字,带着微微的杀意,表现出苏轼对成功的信心,也不自觉地透露出了一丝怨愤之情。
转眼来到了“丙辰中秋”,苏轼即将过完他人生中的第四个十年,此时,他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诗是寄给苏辙的,属于酬赠词,因为不是当面递交,是在孤独的处境中写下的,所以比杭州酒席上的酬赠词,带上了更多的忧郁。
此时,苏轼到密州已经两年了,太守的任期是“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西湖留别》),接下来,他要到哪里去呢?是回到京师重新发挥作用,还是继续在各地迁转,做各种各样的太守?苏轼表面上不在意,内心却不可能不忖度。就像他第二年清明在诗中写下的,“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东栏梨花》),这里的风景,我还能看多久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这首《水调歌头》中,读出更多的滋味。
一开头,苏轼继承屈原和李白的姿势,拿着酒杯,问月,问天。但是接下来,他不是像屈原和李白那样纯粹的浪漫,一下子就飘到天上去了,而是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很实在地打听了一下,“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天上现在怎么样了呢?“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不那么好待。苏轼说他还是想回去的,这只是在故作大言,说他本来是天上的人吗?这个“天上”,恐怕是可以坐实到当时的朝廷的。“高处不胜寒”固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此时恐怕还有非常现实的所指。
苏轼想,我在外面漂泊这么久了,朝廷中不喜欢我的新党,互相之间打得怎么样了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贵之争,已经更新到哪个版本了啊?如果更新到了对苏轼有利的版本,苏轼也不是不想回去,可是这种事谁说得准呢?就怕回去以后,要面对险恶的环境。
所以,苏轼想,我要是继续放外任,也不错,可以“起舞弄清影”,落得个逍遥自在,“何似在人间”,这么快乐,哪里看得出我没有在朝廷里呢?
下阕从“无眠”的主题写起,这既是乐府中相思的元素,也是《文选》传统的元素,鉴于这首词的主人公是苏轼自己,所以更多的还是《文选》传统的体现。苏轼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一种俗乐谚语般流利的语调,也是苏轼本人深沉的哲思。最后,他祝福弟弟,也祝福自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其实是前面那首《沁园春》中的“身长健”的升级版。让我们一起好好活着,等待有利于我们的形势。
两年后,苏轼离开密州的时候,还是没能回京城,而是改任徐州太守。又做了一届太守,就看出形势有些紧张了,朝廷没有给苏轼贬官,但也绝不给他升官。此时的苏轼,心里暗暗地没有那么云淡风轻了,他在焦急地等待着尘埃落定。
这时,他登临古迹燕子楼,写下了《永遇乐》: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唐代张愔去世后,他的爱妾关盼盼孤独地住在燕子楼中。有人指责关盼盼不能为张愔殉死,关盼盼听说后就自杀了。苏轼自称,他是留宿在燕子楼中,梦到了盼盼,才写了这首词。其实,他写这首词不是为了记录一个奇异的梦。记梦词往往是与自己的对话,其中是有自己的寄托在的。
从这首词来看,苏轼与关盼盼共情的点,在于无望的等待。苏轼在等着来自朝廷的音讯,而关盼盼最终自杀了,这也反映了苏轼对未来的不良预期。
开头的“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是极好的形容,比起写《沁园春》的时候,苏轼在词中写景的技巧,显得更为成熟了,从华丽而略显板滞的描摹,变成了精炼而独到地提取特征,能够以意气驱使词句。在这美好的良夜里,人们却都睡着了,好的景致也没人看见。“寂寞无人见”,说的是景物,又何尝不是此时的苏轼?他此时远离朝堂,做到第三任外任,仿佛已经被遗忘了。
在这寂寞的夜里,苏轼被惊醒了。是什么惊醒了他呢?是远处三更的鼓声吗?不,苏轼说是窗前落下的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坠落,可以惊醒人吗?词人形容落叶的声音,是“铿然”。一片叶子落下的声音,再怎么也不会是“铿然”,这是极言叶子的干枯,也极言静夜中叶子落下的声音对人的冲击。这是苏轼极具个性的修辞。
相反,更鼓的声音,却是“紞如”,是低沉的,并不那么有穿透力,像是背景音一样。分贝更高的鼓声,反而是背景音;极轻的落叶声,反而穿透了词人的耳膜。这也是有意营造的对比,突出词人独特的感官感受。可以被一片落叶打断梦境,说明四十出头的苏轼,已经神经衰弱了。落叶为什么会惊断词人的梦境呢?因为落叶提示了季节的变易,提示了时间,提醒词人:“你在外面又漂泊了一年了。”令词人惊惶,不能再继续睡下去了。
词人用“梦云”来形容有关盼盼的梦境。写“梦云”被“惊断”,既是梦境被惊断,又让梦境好像夜空中的云一样,有了可以断裂的具象。词人写“梦云”是“黯黯”的,也像是夜云的样子。应该是词人被落叶惊醒后,出神地仰视着夜云,将夜云的形象与无形的梦境叠印在了一起。
醒来后,词人再也睡不着了,就在小园中行走,却再也找不到梦中的关盼盼了。他无眠的姿态,继承了阮籍的“夜中不能寐”;他在暗夜中行走的身影,已经预演了他后来的“谁见幽人独往来”。
换头的地方,苏轼又想家了,想着“有田不归如江水”的可笑誓言,想着上一个梦中“小轩窗,正梳妆”的温馨一刻。如果只是记录一个有点风流色彩的奇异梦境,他这时候完全没有必要想家。这说明,他从关盼盼的处境,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关盼盼在燕子楼中无望地坚守,我何尝不是在徐州太守的任上无望地坚守呢?我难道也要像关盼盼那样,一直等到别人说我怯懦,甚至等到死吗?还是离开这囚牢般的“燕子楼”,回到故乡去呢?或许,一切坚守都是虚妄的,就像这燕子楼中,也终将泯灭佳人的身影,只有应该在不同人家的屋檐下飞来飞去的燕子,暂时地栖居在这里,反倒像是楼中的囚徒。刚才梦到盼盼,是一场梦,但是整个人生,整个历史,何尝不是一场醒不来的大梦呢?盼盼当年的坚守,是可笑的梦;我如今的坚守,也是可笑的梦 —我们都太执着了。这样的执着,是不是没有意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将来也会有人,对着燕子楼的夜景,为我的这份坚守而感叹吧。
苏轼说的是对的,后来的人仍然会对着他这首词,为他感叹。苏轼借关盼盼寄托自己的寂寞情怀,自己却成了比张愔和关盼盼更值得纪念的历史名人。但是,他困守徐州的处境,却不能说是毫无价值的。至少,他开启的新的词风,在这里成熟了。相对于他对词史的贡献,他此时的一切蹉跎与煎熬,都是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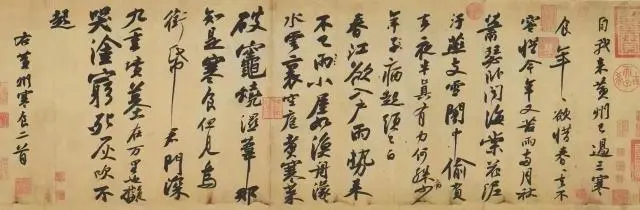
苏轼的豪放词,发生于他的十年外任期间。其中,杭州的酬赠词,是他填词的起点,与张先的启发有关。在密州与徐州的蹉跎与孤独,则成就了他的咏怀词,让他的词艺趋于成熟,更稳定了他独特的词风,在功能上为文人词建立了“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