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腾讯新闻发起了《从她说起》女性分享会,邀请到几个在不同领域都非常出色的女性朋友,她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分享了在成长中的“内有引力”。
复旦大学教授马凌分享了自己上学时的经历。刚上大学时,同为中文系毕业的母亲告诫她,“不要堕落成一个女作家”,而如今,她是网上人气极高的书评人。近年来,越来越多优秀女性创作者活跃在各个领域,马凌说,“好的文学不分性别,女作者应该受到更公平的对待,女性故事应该反映更多的真实处境和心声”。以下是她的分享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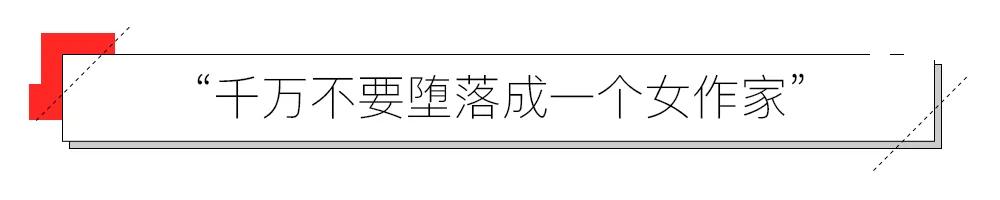
大家好,我叫马凌。我是女儿、妻子、母亲,我也是老师、书评人、艺术爱好者。我来分享我的故事。
当年,我要去中文系报到上学了。我的母亲,她同样毕业于中文系,临行叮嘱我说:“千万不要堕落成一个女作家”。开学典礼后系主任训话,头一句就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惊心动魄。这也说明,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时期,在那个时期,女作家被普遍污名化了。记得当时开始流行一个概念——“身体写作”,好像只要是女性作家,就必然是写自己的隐私、写七情六欲,写得涕泪横流。
女作家,尤其是漂亮的女作家,人们总以别样的目光看待她们,似乎她们是动用了身体资本,才取得了文学成就。在中文系的课本里,尤其是古典文学课本里,女作家寥若晨星,即便四大才女,被津津乐道的却是卓文君私奔、蔡文姬被匈奴劫掠、李清照守寡改嫁离婚、上官婉儿被乱兵所杀这些轶事,而鱼玄机、柳如是这样的女诗人,在文学史上只有寥寥数语,不够一个段落。
明末清初,汪启淑编撰《撷芳集》80卷,将历代女性作者归为八类:节妇、贞女、才媛、姬侍、方外、青楼、无名氏、仙鬼,其中“才媛”独占53卷。上世纪五十年代,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列出历代妇女作品4000余。当代华裔汉学家方秀洁,曾以十年之功在世界各大图书馆的中国古籍部寻找明清两代妇女的散轶著作,写下了《卿本著者》。卿本著者,奈何做了母亲、做了妾妇、做了女伶。在我看来,不考虑阶级的性别叙事皆为虚妄,只有少数上层社会的妇女、或者从事特殊职业的妇女有自主写作的权利,而这少数妇女中又只有极少的人能逃开“男性凝视”。
我的母亲身在集体偏见中,出于母爱,希望我受人尊重、名声清白,她希望我像她一样当大学教授而不是作家。我很听话,自小就是乖乖女,从此在学术之路上日拱一卒。因为成绩优异,我的本科导师把我推荐给我的硕士导师,我的硕士导师把我推荐给我的博士导师,按部就班,每一步都不曾失误。目前,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如我妈妈所愿,我可以在我的简介里写上:“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别人的眼中,这算是一个职业成就吧,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心底里还有别的梦想,我曾有可能走上别的道路。

王尔德有一句名言,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想得到的,得不到;一种是想得到的,得到了。当不了作家,我可以当读者。到今天,我读过的书超过五千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活跃于各个媒体的书评人。必须要说明一下,书评是不算在高校的科研成果里的,写书评是为爱发电,往深里说,写书评也是因为它是写作之一种吧,我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和我的梦想在一起。
在读了这么多书以后,我又是如何看待女性作者、女性故事和女性文学的呢?实话说,我真的不想在作者、故事、文学前面加上“女性”这个定语,我认为好的文学不分性别、种族、阶层、年纪、职业,好就是好。可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就目前的社会观念和运行机制来说,女作者应受到更公平的对待,女性故事应反映更多的真实处境与心声。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言人们耳熟能详:“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经济独立是第一需要,空间——物理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也具有特殊重要性。
我在这里精选了十二位我喜欢的女性作家的传记性作品,或为自传,或是他传,但每一位的成长故事都是那么精彩。
比如法国作家科莱特,她的作品曾被她的丈夫窃取,她离家出走当了一名流浪女演员,后来成长为著名记者、法国国宝级作家。
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在中学时代就向朋友们勇敢宣布,她要当作家。20岁她又决定,不做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顺从女人。她结婚,有女儿,她的婚姻很幸福。她记得曾经有一个时代,女性被告知,只有怀孕和生子才能体现她们的女性气质。她也记得也曾有一段时期,女性被告知她们不应该生孩子。这两种说法她都不喜欢。她一方面反对把女性当作生育机器,反对将女性物化和商品化,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红遍世界,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她又告诉我们,女作家的正确道路不是全力以赴攻破男性设置的壁垒,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不落入任何陈旧观念的陷阱,且绝不自我设限自废武功。
我很安慰地看到,女作家的地位自我上大学的时代以来,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从1901年到1987年,86年间只有6位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从1991年到今天,33年里有了11位。她们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对女作家和女作家作品的偏见,好的文学不是因为作者本身的性别,而是因为它的真、善与美。
我喜欢的作家门罗刚刚离世,她有“当代契诃夫”的美誉,她不愿被加以布尔乔亚式的解读,含情脉脉、泪水涟涟、伪善的同情、明确的教谕,这都是门罗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只因为,真实远比小说残酷,人性远比虚构复杂。而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成功,美满,功利和梦想,也始终在门罗的视野之外,她笔下的人物遍及从中产阶级到无产阶级、从平常女性到性变态的宽频谱系之中,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皆是从日常生活的主流轨道上暂时或永久“逃离”的人物,心怀“秘密”,奋力挣扎,貌似静若止水,实则波澜壮阔。
门罗的精神气质是“冷峻”,她不抒发同情、不表达感慨、也不站在高处批判环境,她只是站在生活内部,不高也不低,沉着而勇敢。需要说明的是,门罗一直都是家庭主妇,在做家务、照顾孩子之余抽空写作,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所以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同样,门罗并没有遵守约定俗成的女作家剧本,她的小说里自传性不多,也没有什么主义,但她就有本领写出心理的真实和社会的真实,给读者胸口重重一击。

我现在愿意使用的一个词是“写作者”。每星期我都要去书店,意识到女性写作者的队伍在扩大、领域在拓展、音量在增强。无论是政治、社会、历史、艺术、还是我所在的新闻学院中的非虚构写作,都在源源不断地产出精彩之作。姐姐妹妹敲起键盘,拿起摄影机,充分表达。记者、编辑、译者、书评人、导演、博主、主理人、学者和教授,都是写作者大军的成员之一,网络上她们也被称为内容创作者。
在我看来,婚恋、爱情、生育、日常生活,这些“茶杯里的风波”已经不是女性写作者的目标范畴,女性写作者也不仅仅是嘶喊:“我爱、我恨、我痛苦”!传统上认为,写作有四方面目的: 一、纯粹的自我中心,二、审美方面的激情,三,历史方面的冲动,四、政治方面的目的。任何一个元素都好,组合起来更好,这就是写作的世界。
就中国的当代文坛来说,王安忆、池莉、迟子建、陈丹燕等老一代作家依然活跃,而新作家们每年也都带来惊喜。我尊敬的北京大学徐泓教授,一年来连续出版《燕东园左邻右舍》、《韩家往事》,将家族史与宏阔的历史相联系,延续的是齐邦媛《巨流河》的传统。受到大众欢迎的杨本芬,花甲之年开始写作,八十岁成名,她的“看见女性四部曲”,“世界看不见我,我看见我”,呈现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与心灵。还有海外华裔女作家的创作、80后女作家的成熟和90后女作家的崛起,数不胜数。
我觉得,昔日的写作,有一种男性化的虚荣和好胜心,包含成名的想象以及鄙视链。而今日的写作,应该更加平等和真诚,更加温和而坚定。
我有三位朋友,她们分别是:
于是,她是作者、译者,她写的和翻译的作品已经有51部。她翻译丹布朗,也翻译托卡尔丘克,她为杂志写稿,也有自己的播客。
黎戈,南京的散文作者,负责的母亲,过着简素的生活,有着敏感的神经,写出8部散文作品,深受文艺青年喜爱。
包慧怡,她是青年学者、译者、作者、也是新妈妈,她已经有24部作品。
她们各美其美,各自精彩。
以她们为镜,我看到自己。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走出“女教授”的标签,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去年,我出版了书评集《多年爱书已成精》,其中有我喜欢的女作家们,张爱玲、弗吉尼亚·伍尔夫、安吉拉·卡特、格温·拉夫洛、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后面的几位不太为广大读者所知,不要紧,我想那反倒是这本小书的意义所在。
我是我,无须是完美妻子、完美母亲、完美女同事、完美女教授。我表达,只是因为我想表达,只是因为自己的声音无可替代。我们是讲故事的人,我们也在别人的故事里受到启发,我们相互启发。
出品|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