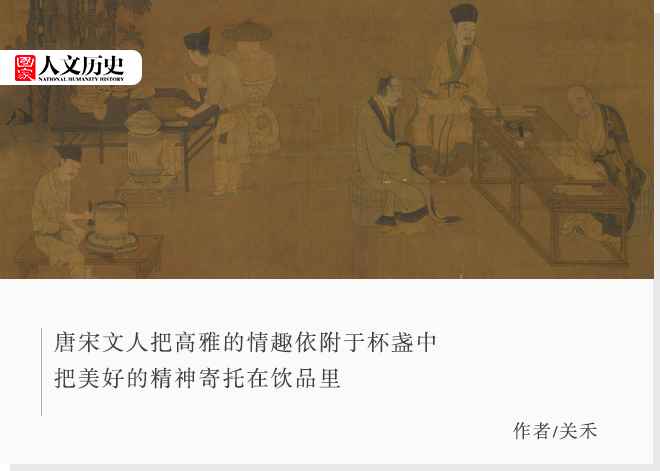
茶和酒是中国人最常饮用的饮品,纵观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也处处弥漫散发着幽幽酒香与茶香。尤其唐诗和宋词,更是与酒和茶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并由此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文化。
在唐代,诗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酒伴随他们吟咏诗文,抒唱心绪,酒助诗兴,诗传酒情,为后人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乐章。从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等觞咏之作中,我们仿佛能嗅出大唐空前绝后的酒香醇厚。
而在宋代,诗词文学的本质则被茶的芬芳所晕染。黄庭坚的《看花回·茶词》,米芾的《满庭芳·咏茶》,苏轼的《西江月·茶词》……宋代词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笔墨之间挥洒浪漫情怀。茶香入词,使宋人笔下的诗词别具一格。
唐人之于酒,充满激昂慷慨、洒脱奔放的胸襟与浪漫的情怀;宋人之于茶,则冷静适意、委婉含蓄,显示出一种闲散自然的格调。唐宋诗词分别以酒文化与茶文化为底色,一个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个含蓄深沉、内向收敛,二者的文化脉络截然相反而又丝丝相系,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的差异。
唐朝诗人究竟有多爱酒?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歌艺术最为辉煌鼎盛的一个时代,流传至今的《全唐诗》900卷中,诗歌达四万三千多首,而与酒有关的诗歌就有六千多首,约占15%,这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饮酒本来是件俗事,但因历代名人尤其是诗人饮酒赋诗,才使酒渐具雅趣。诗使酒化俗为雅,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有了诗的唱和,酒从此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饮料,饮酒也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现象,一跃成为与作诗齐名的文化活动。饮酒与作诗一样,成了文人的风流韵事,这种转变则起源于魏晋名士。《世说新语》说,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竹林七贤无一不是能饮者,嵇康、阮籍还是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也是一个能酒善诗的大家。

《高逸图》(残卷),描绘了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作者/(唐)孙位,来源/上海博物馆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陶渊明、刘伶、嵇康等人的饮酒赋诗、弹琴抚瑟后,诗酒唱和也自然成为后世诗人展示生活情趣和抒发情感的重要传统。
唐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发达,社会文化开放自由,这一时期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最流光溢彩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唐人旷达乐观、潇洒恢弘的气质,唐代饮酒之风的盛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唐代诗人借鉴前人的诗酒风韵,以其开阔的胸襟、宏大的气魄,极力讴歌“盛唐气象”。
唐代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了专业的酒类生产部门——良酿署,许多唐代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高昌国(今属新疆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做成的酒呈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绿酒”在唐诗中多被提及。较为知名的有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皮日休《春夕酒醒》里的“四弦才罢醉蛮奴,酃醁馀香在翠炉”。
唐代不仅民间饮酒,统治者也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特许臣民聚会欢饮。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写的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士女们在曲江边的踏青宴。
可以说,这条曲江就是唐代文人饮宴、游赏、赋诗的乐园。科考每出一批新进士,曲江边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游宴。每到此时,全长安上到皇室贵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倾城出动,而喝酒吟诗正是曲江游宴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刘沧的“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王涯的“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都是描写万人齐集的曲江游宴场景。在这种普天同饮的社会风气的带动下,文人学士更加纵酒酣歌、放荡不羁,曾经魏晋名士的“饮酒啸傲”,演变为唐代文人学士的“长醉高歌”。

《曲江图》(局部)。作者/(唐)李昭道(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唐诗中,我们还能发现一种特别的名称——酒家胡。王绩《题酒店壁》中的“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维《过崔驸马山池》中的“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都有所描写。所谓酒家胡,是唐代在中原开设酒店的西域胡人,特指为在酒店消费的顾客提供西域歌舞音乐助兴的侍酒胡姬。可以想见,在盛世王朝的大都会中,达官贵胄、富豪阔少以及文人名士纷纷来到胡人酒店中,夜夜开怀畅饮,极尽享乐。如花的胡姬们用各种酒器、酒令、歌舞乐器佐酒,难怪客人们会“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二首》)。
唐代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似乎只有饮醉后,诗人所思所虑才可进入“醉乡”。在醉乡之中,大唐盛世色彩斑斓——
李贺在他的《将进酒》里有“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的诗句,他劝大家不妨整天醉倒,连魏晋酒鬼刘伶的坟上都无酒可洒。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了李白、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等八位“酒仙”的形象,最知名的便有那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八个盛唐酒人整天醉得东倒西歪,可见唐朝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

《太白醉酒图》。作者/(清)苏六朋,来源/上海博物馆
再看与“酒中仙”李白相交游的盛唐几位诗人,也无不醉于诗酒,孟浩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赠孟浩然》);王昌龄“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王昌龄《送魏二》);高适“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贾至“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贾至《对酒曲二首》);岑参“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至于杜甫,他不但对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醉态由衷赞美,自叹不及,还连连发出“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感叹。
初唐诗人王绩的《过酒家五首》,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咏酒诗,大都是诗人酒后之作。
唐代以儒治国,同时尊奉老庄,也不排斥佛教。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进入空前的活跃状态,加上酒政松弛,统治者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使得唐代的诗酒文化精神带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自信,杜甫“把臂开尊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的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诗成癖,俱因酒得仙”的欢畅放达,李贺“少年心事当拏云”的雄心壮志,聂夷中“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的豪气洒脱,戴叔伦“且向白云求一醉”的浪漫飘逸,罗隐“酒贳馀杭渌满樽”“人来何处不桃源”的落拓潇洒,无不显示唐人醉酒心态的旷达与大气。
饮茶的普及,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了宋代,整体生活富足,城市的商品经济、货币流通、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内涵都得到全面提升。这样繁荣的社会经济,自然也刺激了茶叶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宋代饮茶之风比唐朝时期更为兴盛,饮茶之习开始全国盛行。《宋史》记载:“茶为人用,与盐铁均。”茶税收入逐年增加,到了徽宗政和年间,已经超过唐代中期茶税的30倍。饮茶作为宋代文人乃至宋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休闲娱乐方式,其饮茶环境和场所的选择促使了宋代茶坊、茶肆的迅猛发展。《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宋人好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

《清明上河图》(局部)右下和对岸两旁有茶坊,屋檐之下,方桌整齐排列,供茶客在席间饮茶闲谈。作者/(北宋)张择端,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茶坊、茶肆的兴盛不仅带动了茶的销售,也扩大了茶的消费群体,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市民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茶坊茶肆成为文人墨客相聚言欢、流连往返之所,咏茶词的出现也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
宋代是理学家引领思想潮流的时期,理学强调士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内省。要自我修养,时刻保持清醒,茶是再好不过的伴侣。因此不同于唐代诗人以饮酒为乐,宋代文人儒者兴起了一种新的“高雅之事”——填词赋诗、以茶入词。茶词,是宋代文人饮茶、斗茶、咏茶之习的产物,表现宋人的闲逸之趣,既有奢华的宫廷茶文化,又有朴素的市井茶文化,品茗的逍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宋代文人各领风骚,著名的词人黄庭坚、苏轼、陈师道、秦观等都有茶词问世。
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现象,它能够在文人笔下熠熠生辉,必有其独特的韵味。陆羽《茶经》中说:“茶为之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言之,饮茶者须具备“精行俭德”的品质。看来,茶与人们的内在修养有莫大关系,陆羽将茶与人们的精神品质联系起来,也暗含着他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唐人好饮千杯,宋人则愿对杯茶。茶所具备的香醇有味的特性与悠然宁静的情愫,正好契合了宋代文人雅士追求的超世清雅和精深透妙的时代心理。

宋建阳窑褐釉碗。建阳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北宋时兴起,这与上层社会饮茶、斗茶的风气紧密相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果说,唐代文人是用浪漫雄豪来书写情怀,那么宋代文人则是鲜明地表现出了高雅精致、心性内敛的时代审美品格。茶词,在宋词中独树一帜,是宋代文人精神风貌和情怀的展现,体现着宋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浪漫情怀。
宋代文人士子几乎在所有能够具化成艺术品佳作的文化样式中,自觉追求这种“雅”的风尚与审美品格。擅长茶事、精于茶艺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数,苏轼就是个嗜茶之人。他对茶有着浓厚兴趣,除了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还曾作一首七律诗《汲江煎茶》,描写了烹茶煮茶的过程:“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面对着一盏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苏轼留下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感叹,可见他品茗尝鲜时的喜悦和畅快。而这杯清淡的茶,也展现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处世心态。
宋代与茶文化、茶学、茶道相关的诗词、书法、绘画不胜枚举,例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作《斗茶歌》,对宋人的斗茶之习进行了生动描写,他说宋人有了茶,“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喝茶能让“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所谓斗茶,就是茶人们将茶饼碾成细末,置于盏中,注入少量沸水用茶筅击拂茶汤,产生泡沫后饮用。茶汤泡沫凝结得越久,则分茶技艺越高,这便是宋词中的“一水试云痕”。斗茶风靡于民间,士大夫们亦热衷于此,斗茶已然成为宋代人们雅致的消遣娱乐形式。
宋徽宗曾亲自注汤击拂,斗茶试茶,并分赐群臣,还写下《大观茶论》,记述宋代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发达。

《文会图》(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作者/(北宋)赵佶,来源/裘纪平著《中国茶画》,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
黄庭坚的《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更是阐述了宋代茶汤制作过程的全貌:
其一
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
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其二
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
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其三
乳粥琼糜雾脚回,色香味触映根来。
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绳床过疾雷。
除了碾、煎、烹的“制茶三部曲”,黄庭坚一生中创作关于茶的诗作几十余首,茶不仅是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他也以茶传情,以茶悟道,在品艺中品味生活。
从这些宋代诗词中,我们能读出两宋日盛的饮茶之风,文人雅士们延续唐代以来的饮茶传统,将文人饮茶的风尚进一步发展。他们品评泉水优劣,赏鉴茶用器具,举办茶会,摆设茶宴,以茶相赠表达情意,以茶会友以表俭德,以茶入诗词以咏志趣,在茶的“精行俭德”的特质中寻找人格升华的精神需求,将茶文化与诗词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千百年来,唐宋文人将喜怒哀乐、悲欢情愁倾注于酒与茶中。不过,尽管唐诗多酒、宋词多茶,但并不代表唐人不喜品茶,也不意味着酒在宋代失去了市场。
茶也是唐诗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唐代茶诗往往以简约的环境衬托诗人淡泊的心情,如白居易的《题施山人野居》:“春泥稻秧暖,夜火焙茶香……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贾岛的《郊居即事》:“住此园林久,其如未是家。叶书传野意,檐溜煮胡茶。”与酒引人入醉乡相反,茶能让人清醒平和,因此与茶相关的唐诗也呈现出平实、理智、真切的特点。就连“酒中仙”李白品茶后,都感叹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还执笔作了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正所谓“一曲新词酒一杯”,宋代词人也爱好乘着酒兴挥毫作词,不过相比唐朝诗人喝酒寻欢,宋词里的酒,品起来往往有股苦涩之意。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辛弃疾等就喜喝酒,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无一不是醉中所作。婉约派词人也同样爱用酒来抒发内心愁情,“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便是在酒中释放哀怨情愁。
在文人雅士眼中,琼浆和香茗,如同气若幽兰、绝世独立之美人,锦簇娇艳、姹紫嫣红之繁花,葱翠欲滴、静谧深远之竹林,能够与眼前幽幽清辉之残月、耳畔呼呼劲吹之疾风、船底涓涓流淌之江水等诗词意象相互唱和。于是,他们把高雅的情趣依附于杯盏中,把美好的精神寄托在饮品里,反复吟咏。酒与茶,已深深融入唐诗宋词的灵魂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参考资料:
[1]黄永健:《从李白的觞咏看唐代的酒文化》,《中国文化研究》,2002。
[2]剑鲲:《酒入豪肠诗自成——浅析唐诗与酒》,《新西部》,2008。
[3]葛景春:《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4]张金贞:《另类唐朝用食物解析历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5]杨海丰,吴中胜:《茶文化与宋词的世俗化及士人生活的雅化》,《湘南学院学报》,2017。
[6]黄光:《宋代茶词中的民俗风尚》,《湖北社会科学》,2013。
[7]岳晓灿:《宋代咏茶诗词的审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2。
[8]王时秀:《探析南北宋时期茶事雅集题材在诗书与绘画作品中的体现》,《新美域》,2022。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