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史知识 Author 陈尚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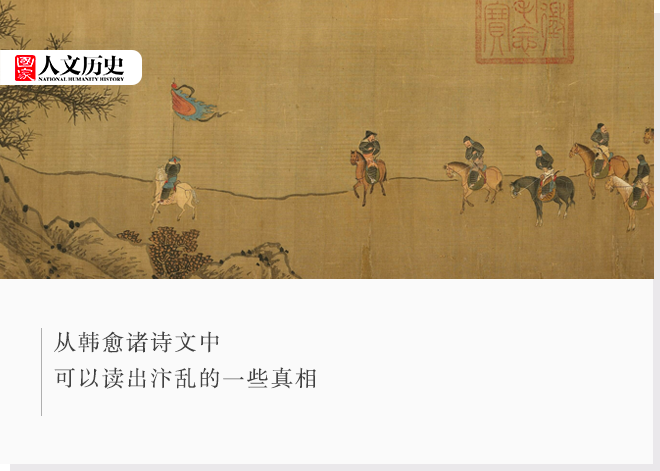 韩愈以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这一榜知举者为名臣陆贽,同榜者后来大多声名显赫,世称龙虎榜。这是后人的说法。韩愈接着连续三年参加制科考试,三年连续下第,不免有挫折感。挫折归挫折,他仍自诩不凡,只是在等待高人,等待机会。《应科目时与人书》认为,自己若得不到机会,“盖寻常尺寸之间耳”,如果得到机会,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这是何等不凡的胸怀。他也说到,官场有力者肯帮助自己,仅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多数有力者,对自己皆“熟视之若无睹也”。就在这期间,真有位大人物决定重用他,这个人是董晋,做过宰相,新任命的宣武节度使,给韩愈的职位是推官,在大镇文职幕僚中大约可以排到五六位。对还没有任何历练的韩愈来说,不算委屈。干吗?干吧!宣武节度使的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是唐王朝在东都以东最重要的节镇之一。如同近代京广线开通前,开封地位高于郑州。唐代的宣武,不仅控扼运河自江南往两京的咽喉,且因其西望京洛,北接相卫、魏博,东连东平、淄青,是四战必据之地,说是唐王朝命脉之所在,也不为过。从贞元初名将刘玄佐帅汴,宣武镇就处于军将自立不受代的半割据状态。玄佐在镇八年,卒,朝廷任命外戚吴凑出镇,凑惧军中拒命,中道而回。朝廷只能任命玄佐子士宁为节度使。一年半后,军乱,军中拥立副使李万荣,朝廷再次接受。十二年,万荣病风将死,其子李迺煽动士兵作乱,为都虞候邓惟恭与监军俱文珍携手平定,将李迺送赴京师。邓惟恭认为自己有功,应该继掌节帅,这时朝廷宣布以旧相董晋为节度使。董晋虽是文官出身,但内外履历完整,有过领军、领镇的经历,曾为宰相四年,有识见,有决断。危急时刻,朝廷起用在洛阳赋闲的他任宣武节度使,是希望他能稳住此一方重镇。七月,董晋受命,几天内组成幕府班底,立即出发。韩愈的具体职务是观察推官,实际兼军事参谋兼掌书记,责任重大。董晋携幕僚赴镇,也就十多人,不自带军兵,立即赴镇。韩愈在《董公行状》中述董晋赴镇之勇决果敢云:“公既受命,遂行。刘宗经、韦弘景、韩愈实从,不以兵卫。及郑州,逆者不至,郑州人为公惧,或劝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于公曰:‘不可入。’公不对,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与诸将至,遂逆以入郛,三军缘道欢声,庶人壮者呼,老者泣,妇人啼,遂入以告。”因为已经有过两次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惧不敢入的先例,董晋遂慷慨成行。其间郑州是邻州,知道汴州军人跋扈,劝董晋暂且坐观进退,若董晋接受了劝告,即是知怯,绝不可能成功。从汴州出来的知情者,也警告不可入。其后三日,经圃田、中牟、八角,已经接近汴州城郭,城中诸军将方出而相迎。可以说两方相逢勇者胜。董晋一往无前的气势,吓退了城中军将的图谋,只能出而迎接。所述“三军缘道欢声,庶人壮者呼,老者泣,妇人啼”,虽然有所夸张,其实就是刘禹锡在闻听平定淮西以后,所写诗中“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三首》其一)的意思。在经历十多年军府自立后,天子任命的节度使终于到任了。董晋此行,颇有乾坤一掷的气概,韩愈是同行者,他也在用生命赌明天。他的叙述,是亲历者的记录。董晋在汴州任上,实际时间是两年半多一点点。史称四年,是就跨及四个年头而言。董晋在汴州的政绩,韩愈《董公行状》及《旧唐书》本传皆有叙述,最重要的记载则是张籍的《董公诗》。此诗作于董晋生前,曾被白居易称许“可诲贪暴臣”(《读张籍古乐府》)。诗很长,不能全录,述其要点。其一,“慈惠安群凶”,即以宽和的态度安抚屡次叛乱的军将:“公谓其党言,汝材甚骁雄。为我帐下士,出入卫我躬。汝息为我子,汝亲我为翁。众皆相顾泣,无不和且恭。”你们在我属下为军将,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使军人们为之感泣。其二,本人节俭,理政也轻刑薄赋。“所忧在万人,人实我宁空”,为州人忧虑,不为自己着想。在他治下,“四郡三十城,不知岁饥凶”。其三,董公得政,天子放心。“天子临朝喜,元老置在东。今闻扬盛德,就安我大邦”,大邦安定,盛德广播海内外。张诗最后说:“昔者此州人,但矜马与弓。今公施德礼,自然威武崇。公与其百年,受禄将无穷。”即汴人崇尚武力,由来已久,董晋以德为政,移风易俗,如果能长久以往,当然可以改变一切。董晋赴任时已经七十三岁,在唐代说来是很老了。百岁当然是人人的理想,可惜人命毕竟难敌金石,这仅是诗人的愿望,所见说不上深刻。从具体措施来说,董晋剪除了军中的潜在威胁。《旧唐书》本传说都虞候邓惟恭“心常怏怏,竟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即削弱军头的势力。又说:“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以陆为辅佐,有以强辅柔之意。陆这时也近七十岁了,大约在十二年夏秋间就任。如果说张籍认为董晋安定地方得法,其中也应包含陆长源的成就。今人谈韩愈在永贞革新期间的立场,常举他的这篇《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并序》为例,认为他求媚于宦官,反对变革。其实这篇序和诗,皆作于贞元十三年春,是应董晋要求而作,其时距离永贞内禅还有八年,韩愈不可能预先知道俱文珍入朝后成为宦官首领,及在朝政剧变时期发挥关键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理解唐代地方州军治理中,文武官任节帅,掌控军政,宦官代表皇帝,监督军政,节帅要有所作为,必须搞好与宦官的关系。对此,韩愈看得很明白。序中首先说到“今之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关涉天下安危,无论节帅与监军,天子皆选最信任者担任。韩愈是就董晋与俱文珍之任职而言,故意不提以往的多次叛乱。称赞俱文珍,则说:“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就当时情况来说,这一评价不算过分。董晋到任前,俱文珍联合邓惟恭平定李迺之乱,使朝廷可以命重臣出镇。董晋到任后,能够贬逐邓惟恭,清除军队内乱的祸根,肯定也得到俱文珍的支持。俱文珍归朝,董晋命幕府群僚皆出饯行,自是人之常情。韩愈受嘱作诗,更是职务行为。诗云:“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芒寒。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其中首二句,肯定俱文珍在建中间吐蕃平凉劫盟事件和汴州平乱中的贡献。然后称赞他的报国业绩,继而转入送别,以人臣难以忠孝两全为结。这是场面上的诗作,不必求之太深。应该说明,此篇诗及序,见于《昌黎先生外集》,是宋人搜罗而得,韩愈本人似乎并未留稿,大约也估计到会引起后人之议论吧!孟郊比韩愈年长十七岁,因韩愈登第在前,两人关系又极其腻密,一直视如兄弟。韩愈随董晋入汴,孟郊有《送韩愈从军》诗宠行,称赞他“坐作群书吟,行为孤剑咏”,从军而不改书生本色。最后几句说:“王师既不战,庙略在无竞。王粲有所依,元瑜初应命。一章喻檄明,百万心气定。今朝旌鼓前,笑别丈夫盛。”引前代以书记从军的诗人王粲、阮瑀相期,祝他随董晋幕府,不战而屈人,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孟郊于韩愈赴汴前不久,刚刚进士登第,对他这样久困科场,年逾四十六岁的诗人来说,高兴得一度失去理智,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表述这种心情。不过冷静下来,才发现从登第到除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归途中,他在汴州,作为比韩愈官高的宣武长史陆长源的客人,住过一段时间。他在几年前,曾到汝州看望过刺史陆长源,留下《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燕》《汝州陆中丞席喜张从事至同赋十韵》等诗。他在汴州,称陆为主人,也有过几次唱和,今存陆诗即赖孟集附录而保存。韩愈与孟郊相识已久,各怀高远的理想。首先是诗歌,他们共同确认前代诗人以李白与杜甫最为伟大,怀有追踪李杜、开拓新境的理想。《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子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因为是醉后所言,不妨有些大言。这时距离杜甫去世还不到三十年。韩愈说昔年曾读二人诗,至晚也是他贞元初到长安应试时,这也是编年史上所见最早将李白、杜甫放在一起议论的记录之一。“长恨二子不相从”,似乎有惜于二人间来往太少。但若与韩愈晚年所作《调张籍》放在一起看,也很遗憾自己与李白、杜甫没有生活在同一时代。所幸有孟郊,有孟郊也就够了。他的诗反复纠缠,说自己如同“青蒿倚长松”,绝不会放过与孟郊共同努力的机会,即便云龙变化,出入六合,也要常与孟郊在一起。这是醉话,也是心声。《答孟郊》也作于同时:“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馀酒肉,子独不能饱。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炒。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弱拒喜张臂,猛挐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当咬。”这里用嬉笑怪嗔的笔法,写出孟郊的生存状态和诗风特点,因为关系好,譬喻怪奇偏激一些也没有问题。这里当然还要讲韩、孟之间的唱和。两人共同癖好,是喜欢写联句诗。在汴州写有《远游联句》,其间李翱也有参与,不过仅写“取之讵灼灼,此去信悠悠”,就被两人甩开了,似乎还不太适应这种类似游戏的文学活动。诗因孟郊将要南行而作,故起句孟郊就说:“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极尽夸张能事。韩愈接:“离思春冰泮,澜漫不可收。”即景取喻,颇为奇妙。诗很长,也很难分析。最后,韩愈说:“名声照四海,淑问无时休。归哉孟夫子,君归无夷犹。”是说孟郊名遍天下,仍不断给自己以关心。最后说到送别,你不必担心,放心地走吧。事实证明,孟郊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汴州乱后,韩愈生死未明之际,他有诗《汴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会合一时哭,别离三断肠。残花不待风,春尽各飞扬。欢去收不得,悲来难自防。孤门清馆夜,独卧明月床。忠直血白刃,道路声苍黄。食恩三千士,一旦为豺狼。海岛士皆直,夷门士非良。人心既不类,天道亦反常。自杀与彼杀,未知何者臧。”这里,他想到分别时的情景,感慨以往的欢悦可能再也没有了,忠直之人死于叛乱,道路的议论则各说各的话。他说的“海岛士”指田横五百士,生死以之,不计得失;“夷门士”从典故说是信陵门下士,这里已经顾不上用典,而是直斥汴州军将之无良,不知食德感恩,为此豺狼之行。孟郊的反应是激烈的,朋友的安危不能不萦系于情怀。孟郊是旧友,张籍则是韩愈在汴州认识的新友。张籍出生之年,至今难以明确,一般估计比韩愈小一两岁。张籍在韩愈卒后,作《祭退之》诗述二人之初识:“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囊。略无相知人,黯如雾中行。北游偶逢公,盛语相称明。名因天下闻,传者入歌声。公领试士司,首荐到上京。一来遂登科,不见苦贡场。观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兹类朋党,骨肉无以当。”张籍是苏州人而居于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自诩诗兼众体,苦于在朝无相知相识者。他北行到汴州,是贞元十三年,也不知什么原因,到第二年方与韩愈相识。恰好韩愈以节度推官的身份主持汴州的进士解送,特别欣赏张籍,置于首荐。这年秋张籍赴京试礼部,第二年就高中进士,也就是“一来遂登科”。是否韩愈的推荐就如此管用,还真无法判断,张籍终生记得韩愈的好,也是事实。韩、张之间在汴州有诗来往。如张籍有《寄韩愈》,首云“野馆非我室,新居未能安。读书避尘杂,方觉此地闲”,估计是韩愈为他安排在远郊的所居,远离尘嚣,可以读书。他再说:“出林望曾城,君子在其间。戎府草章记,阻我此游盘。”可惜韩愈忙于公务,没有时间相约同游,自己只能引颈遥望。韩愈有《病中赠张十八》诗赠张籍,有几句说到对张诗的评价:“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谈舌久不掉,非君亮谁双。”这时张籍还仅是布衣,有能力而无助于国事。诗文嘛,写得再好也只能自娱自乐。韩愈看到了他的诗文的力量与追求,且认为当世与自己可以谈得来的,也只有张籍了。极尽推崇,可以仔细体味。《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一四有张籍《遗公第一书》,提出当今“世俗陵靡,不及古昔”,根本原因在于“圣人之道废弛之所为”。他认为自秦灭学后,“汉重以黄、老之术教人,干惑人听”;汉末以来,“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国”。“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他建议韩愈能够继承孟轲、扬雄的学说,“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为乎”,应该写书以明儒学正道。希望韩愈“绝博塞之好,弃无言之谈,弘广以接天下士,嗣孟轲、扬雄之作,辩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这里,是挚友以天下道义为期的殷切之谈。张籍认为自己的能力与影响都不及韩愈,希望韩愈起而挽回儒学之颓势。韩愈《答张籍书》首先感谢张籍的建议,并说自己关心于此已经多年:“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仆为好辩也,然从而化之者亦有矣,闻而疑之者又有倍焉。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所得矣。为此而止,吾岂有爱于力乎哉?然有一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这时韩愈刚过三十岁,认为自己入世还不深,已经做过许多努力,从而化之者是愿意接受的人,更多是闻而疑之者,即将信将疑的人,至于顽然不入者,你永远也别想改变他们,这是社会的大多数人。韩愈希望到五十以后再著书立说,见解深刻,减少偏失,以传后世。张籍再致第二书,认为“士之壮也,或从事于要剧,或旅游而不安宅,或偶时之丧乱,或不皇有所为,况有疾疚吉凶虞其间哉?是以君子汲汲于所欲为,恐终无所显于后。若皆待五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人生短暂,充满不确定因素,君子第一要义是显名于后,一定要到五六十岁以后方有所论述,难免会有所遗憾。韩愈作第二书回复,感谢张籍“意欲推而纳诸圣贤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谓愈之质有可以至于道者,浚其源,导其所归,溉其根,将食其实”。朋友如此以圣贤、道义相期于自己,心存感激。也说出为难之处:“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譊譊。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即举世迷惑于佛道二教,上自公卿,下及庶民,若公然反对,必遭遇许多不虞之祸。又说二教盛行中国,“盖六百年有馀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又说:“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扬雄,亦未久也。然犹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为之哉!”这里已经提到了道统流传之体系,更认为前代圣贤之有所成立,不仅勤于弘道,更能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方能有所成立。自己有理想,也明白不会轻易地获得成功。彼此的交流,透露韩愈倡导儒学、排诋佛老的心路历程。张籍的敏锐与鼓励,最终造就韩愈成为思想史上的巨人。一般人之印象,张籍仅仅是个诗人,算不上思想家。从以上二信可以理解,虽然他那时只是一位赴考的进士,但心怀改变世道人心的宏愿,并希望韩愈来有以完成。而韩愈最著名的弘道宣言《原道》等文,今人都认为作于贞元后期,当与张籍的督促有关。从汴州相识,到韩愈去世,两人的友谊终身不变,不仅因为诗,更因为文章道义。还有一层,张籍脾气好,对韩愈绝对信任。韩愈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他的喜怒哀谑,一切都可以向张籍倾诉。对张籍来说,随便你怎么喷,我绝对不生气。有这样的朋友,是韩愈的幸运。就在张籍欢庆进士登科,杏园欢会之时,汴州城中因董晋去世,发生血腥政变,韩愈经历了此生最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贞元十五年二月初,董晋在任上去世,得年七十六。仅仅七天后,汴州兵变,杀留后陆长源、判官孟叔度等人。汴军为什么叛乱?《旧唐书·董晋传》认为:“(董)晋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长源好更张云为,数请改易旧事,务从削刻。晋初皆然之,及案牍已成,晋乃命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皆恶之。”是说陆、孟二人因为改易削刻、轻佻慢易而激起兵变,要负一定责任,被杀是咎由自取。从韩愈、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文来看,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韩愈《董公行状》云经过董晋与其幕僚诸人之施治,汴州已经“职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鹊集,苍乌来巢,嘉瓜同蒂联实。四方至者归以告其帅,小大威怀。有所疑,辄使来问;有交恶者,公与平之”,这是四方共同的观感。但在此同时,董晋“累请朝,不许。及有疾,又请之,且曰:‘人心易动,军旅多虞,及臣之生,计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难期。’犹不许”,董晋已经看到军心不稳,自己在世,还压得住,自己身后,实在无法预料。韩愈进一步说:“公之将薨也,命其子三日敛,既敛而行。于行之四日,汴州乱。故君子以公为知人。”即董晋临死前,已经料到兵乱不可避免,让其子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后事,三日成敛后立即启行。是他已知汴兵必叛之势,以他的馀威,仅足维持数日之太平。韩愈因为偶然的原因,送董晋灵柩出城,逃过此劫,纯属幸运。韩愈作《汴州乱二首》:“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这是乱后不久的诗作,大夫、留后皆指陆长源,昨日还风光无限,须臾皆死于兵乱。从房屋连栋被烧,留后及幕官阖家被杀,动乱规模很大。责任在哪里?韩愈一说是“诸侯咫尺不能救”,即邻镇坐见汴兵嚣张,无动于衷;二说是“庙堂不肯用干戈”,即朝廷长期与方镇苟且偷安,使汴军拒绝朝廷命帅,只有军中拥立,方能接受。韩愈更有《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说明自己在兵乱之际的遭际,这是其中相关的一节: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怳难为双。暮宿偃师西,徒展转在床。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傍徨。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骄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东来说,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东去趋彭城。从丧至洛阳,还走不及停。假道经盟津,出入行涧冈。日西入军门,羸马颠且僵。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诗写给张籍,前面讲到许多往事。这里说他护董晋丧车西行,到达偃师以西,即距离洛阳还有一日行程时,先听闻张籍及第,悲喜交集。当晚汴州兵变消息传来,彻夜无法入眠。他离汴时,并没有带上家人。这时跟随他的家人约有三十多人,最惦念的是妻与子,还有未断奶的幼女。他这时负有为董晋护丧的责任,一步也离不开,想到幼女的哭声,真是无从自已。所幸后续消息很快也传来,他的家人没有遭遇屠戮,已经脱祸离开汴梁,乘船沿汴水东下,先避地徐州。可以稍微放些心了,但仍魂不守舍,毕竟家人到徐州如何安顿,还得自己去张罗。诗里透露,韩愈送丧至洛阳,对董家有所交待后,立即假道盟津,入河阳军,然后转奔徐州。因为他与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还有一些交集,此后得以在徐州幕府暂栖。孟郊有《吊国殇》:“徒言人最灵,白刃乱纵横。谁言当春死,不及群草生。尧舜宰乾坤,器农不器兵。秦汉盗山岳,铸杀不铸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起争。”这里用《唐文粹》卷一五下的文本,与孟集所载颇多不同。此诗应该是为陆长源而作,从“白刃乱纵横”“谁言当春死”等句可以明白。孟郊与陆长源交谊最厚,对陆为国死难,身后还遭遇污名,似乎兵乱是因他失政而引起,更感不满。他甚至骂到秦汉以来对暴力得胜者之歌颂,可见怨愤之深。从韩愈诸诗文中,还可以读出汴乱的一些真相。他为董晋子董溪所撰墓志中说:“太师(董晋)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维纲,锄削荒颣,纳之太和而已,其囊箧细碎,无所遗漏,繄公之功。上介尚书左仆射陆公长源,齿差太师,标望绝人,闻其所为,每称举以戒其子。杨凝、孟叔度以材德显名朝廷,及来佐幕府,诣门请交,屏弃所挟为。”颂赞董溪助父理政的同时,对遇害的陆、孟二人评价颇高,皆属助董治汴的关键人物。韩愈《送湖南李正字归湖南序》云,李础之父曾与他同在汴幕,“以侍御史管汴之盐铁”。“军乱,军司马、从事皆死,侍御亦被谗,为民日南”,即汴幕被杀者外,李础父也得罪贬窜到今越南境内。是朝廷无力追究叛乱者的罪责,反让被害者与同幕者承担罪责。韩愈《韩弘碑》载,汴州经过多次反复,“军中皆曰:‘此军司徒所树,必择其骨肉为士卒所慕赖者付之,今见在人莫如韩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司徒指刘玄佐,曾领汴军八年,韩弘是玄佐妹之子,故称韩甥。即汴军只认刘家之宗人,不接受朝廷委派之军帅。汴乱之根本,也即在此。此后韩弘领镇二十一年,平安无事。从贞元十二年七月到十五年二月,韩愈在汴州度过了两年半时间。这是他进入仕途的第一份工作,走的也是中晚唐士人从幕府出发的习惯道路。在这两年半中,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也理解了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与朝廷的苟且无为。当然,他也学到了许多,董晋之公忠体国,一往无前,以及处理政事时的柔软身姿,和对潜在危机的准确预判,他皆有切身体会。他接待了路过暂住的孟郊,增进了友谊,也表达了可以长期合作竞争的愿望。他认识了有才分也很有社会担当的诗人张籍,凭借自己的权力首荐张籍入礼部就试,张籍也很争气,一举高中,彼此友谊维持了一生。更惊心动魄的是,他在护送董晋灵柩归洛时听闻汴州兵变,昔日之同官全家惨遭屠戮,自己家人也几落贼手,更看到事后朝廷之不负责任。陆长源年纪也在七十左右,是旧相之孙,他在遇害当日被任命为节度使,当然是出自董晋的推荐。怎么可以说董晋有所施为,一切都好,陆长源仅接手几天,就铸成大错?其实汴军积恶成习,利欲熏心,毒蜂成窠,无视皇权,有重臣在还能维持,重臣一死就旧态复萌。朝廷知道平叛要依靠实力,国家偏偏不具备这个实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遇害者承担责任,让继任者尽量在叛军与朝廷间保持平衡。这些,韩愈都看到了,有愤懑也无从发声,只留下若干闪烁其词的片段。将这些现象梳理清楚,可以体会他在经历此番剧变后,人生有了更深切的体悟,此后一系列论著中倡导恢复儒家道统,讲求夷夏之分,力求在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现状,汴州的这段经历对他是很重要的。
韩愈以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这一榜知举者为名臣陆贽,同榜者后来大多声名显赫,世称龙虎榜。这是后人的说法。韩愈接着连续三年参加制科考试,三年连续下第,不免有挫折感。挫折归挫折,他仍自诩不凡,只是在等待高人,等待机会。《应科目时与人书》认为,自己若得不到机会,“盖寻常尺寸之间耳”,如果得到机会,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这是何等不凡的胸怀。他也说到,官场有力者肯帮助自己,仅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多数有力者,对自己皆“熟视之若无睹也”。就在这期间,真有位大人物决定重用他,这个人是董晋,做过宰相,新任命的宣武节度使,给韩愈的职位是推官,在大镇文职幕僚中大约可以排到五六位。对还没有任何历练的韩愈来说,不算委屈。干吗?干吧!宣武节度使的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是唐王朝在东都以东最重要的节镇之一。如同近代京广线开通前,开封地位高于郑州。唐代的宣武,不仅控扼运河自江南往两京的咽喉,且因其西望京洛,北接相卫、魏博,东连东平、淄青,是四战必据之地,说是唐王朝命脉之所在,也不为过。从贞元初名将刘玄佐帅汴,宣武镇就处于军将自立不受代的半割据状态。玄佐在镇八年,卒,朝廷任命外戚吴凑出镇,凑惧军中拒命,中道而回。朝廷只能任命玄佐子士宁为节度使。一年半后,军乱,军中拥立副使李万荣,朝廷再次接受。十二年,万荣病风将死,其子李迺煽动士兵作乱,为都虞候邓惟恭与监军俱文珍携手平定,将李迺送赴京师。邓惟恭认为自己有功,应该继掌节帅,这时朝廷宣布以旧相董晋为节度使。董晋虽是文官出身,但内外履历完整,有过领军、领镇的经历,曾为宰相四年,有识见,有决断。危急时刻,朝廷起用在洛阳赋闲的他任宣武节度使,是希望他能稳住此一方重镇。七月,董晋受命,几天内组成幕府班底,立即出发。韩愈的具体职务是观察推官,实际兼军事参谋兼掌书记,责任重大。董晋携幕僚赴镇,也就十多人,不自带军兵,立即赴镇。韩愈在《董公行状》中述董晋赴镇之勇决果敢云:“公既受命,遂行。刘宗经、韦弘景、韩愈实从,不以兵卫。及郑州,逆者不至,郑州人为公惧,或劝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于公曰:‘不可入。’公不对,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与诸将至,遂逆以入郛,三军缘道欢声,庶人壮者呼,老者泣,妇人啼,遂入以告。”因为已经有过两次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惧不敢入的先例,董晋遂慷慨成行。其间郑州是邻州,知道汴州军人跋扈,劝董晋暂且坐观进退,若董晋接受了劝告,即是知怯,绝不可能成功。从汴州出来的知情者,也警告不可入。其后三日,经圃田、中牟、八角,已经接近汴州城郭,城中诸军将方出而相迎。可以说两方相逢勇者胜。董晋一往无前的气势,吓退了城中军将的图谋,只能出而迎接。所述“三军缘道欢声,庶人壮者呼,老者泣,妇人啼”,虽然有所夸张,其实就是刘禹锡在闻听平定淮西以后,所写诗中“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三首》其一)的意思。在经历十多年军府自立后,天子任命的节度使终于到任了。董晋此行,颇有乾坤一掷的气概,韩愈是同行者,他也在用生命赌明天。他的叙述,是亲历者的记录。董晋在汴州任上,实际时间是两年半多一点点。史称四年,是就跨及四个年头而言。董晋在汴州的政绩,韩愈《董公行状》及《旧唐书》本传皆有叙述,最重要的记载则是张籍的《董公诗》。此诗作于董晋生前,曾被白居易称许“可诲贪暴臣”(《读张籍古乐府》)。诗很长,不能全录,述其要点。其一,“慈惠安群凶”,即以宽和的态度安抚屡次叛乱的军将:“公谓其党言,汝材甚骁雄。为我帐下士,出入卫我躬。汝息为我子,汝亲我为翁。众皆相顾泣,无不和且恭。”你们在我属下为军将,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使军人们为之感泣。其二,本人节俭,理政也轻刑薄赋。“所忧在万人,人实我宁空”,为州人忧虑,不为自己着想。在他治下,“四郡三十城,不知岁饥凶”。其三,董公得政,天子放心。“天子临朝喜,元老置在东。今闻扬盛德,就安我大邦”,大邦安定,盛德广播海内外。张诗最后说:“昔者此州人,但矜马与弓。今公施德礼,自然威武崇。公与其百年,受禄将无穷。”即汴人崇尚武力,由来已久,董晋以德为政,移风易俗,如果能长久以往,当然可以改变一切。董晋赴任时已经七十三岁,在唐代说来是很老了。百岁当然是人人的理想,可惜人命毕竟难敌金石,这仅是诗人的愿望,所见说不上深刻。从具体措施来说,董晋剪除了军中的潜在威胁。《旧唐书》本传说都虞候邓惟恭“心常怏怏,竟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即削弱军头的势力。又说:“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以陆为辅佐,有以强辅柔之意。陆这时也近七十岁了,大约在十二年夏秋间就任。如果说张籍认为董晋安定地方得法,其中也应包含陆长源的成就。今人谈韩愈在永贞革新期间的立场,常举他的这篇《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并序》为例,认为他求媚于宦官,反对变革。其实这篇序和诗,皆作于贞元十三年春,是应董晋要求而作,其时距离永贞内禅还有八年,韩愈不可能预先知道俱文珍入朝后成为宦官首领,及在朝政剧变时期发挥关键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理解唐代地方州军治理中,文武官任节帅,掌控军政,宦官代表皇帝,监督军政,节帅要有所作为,必须搞好与宦官的关系。对此,韩愈看得很明白。序中首先说到“今之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关涉天下安危,无论节帅与监军,天子皆选最信任者担任。韩愈是就董晋与俱文珍之任职而言,故意不提以往的多次叛乱。称赞俱文珍,则说:“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就当时情况来说,这一评价不算过分。董晋到任前,俱文珍联合邓惟恭平定李迺之乱,使朝廷可以命重臣出镇。董晋到任后,能够贬逐邓惟恭,清除军队内乱的祸根,肯定也得到俱文珍的支持。俱文珍归朝,董晋命幕府群僚皆出饯行,自是人之常情。韩愈受嘱作诗,更是职务行为。诗云:“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芒寒。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其中首二句,肯定俱文珍在建中间吐蕃平凉劫盟事件和汴州平乱中的贡献。然后称赞他的报国业绩,继而转入送别,以人臣难以忠孝两全为结。这是场面上的诗作,不必求之太深。应该说明,此篇诗及序,见于《昌黎先生外集》,是宋人搜罗而得,韩愈本人似乎并未留稿,大约也估计到会引起后人之议论吧!孟郊比韩愈年长十七岁,因韩愈登第在前,两人关系又极其腻密,一直视如兄弟。韩愈随董晋入汴,孟郊有《送韩愈从军》诗宠行,称赞他“坐作群书吟,行为孤剑咏”,从军而不改书生本色。最后几句说:“王师既不战,庙略在无竞。王粲有所依,元瑜初应命。一章喻檄明,百万心气定。今朝旌鼓前,笑别丈夫盛。”引前代以书记从军的诗人王粲、阮瑀相期,祝他随董晋幕府,不战而屈人,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孟郊于韩愈赴汴前不久,刚刚进士登第,对他这样久困科场,年逾四十六岁的诗人来说,高兴得一度失去理智,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表述这种心情。不过冷静下来,才发现从登第到除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归途中,他在汴州,作为比韩愈官高的宣武长史陆长源的客人,住过一段时间。他在几年前,曾到汝州看望过刺史陆长源,留下《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燕》《汝州陆中丞席喜张从事至同赋十韵》等诗。他在汴州,称陆为主人,也有过几次唱和,今存陆诗即赖孟集附录而保存。韩愈与孟郊相识已久,各怀高远的理想。首先是诗歌,他们共同确认前代诗人以李白与杜甫最为伟大,怀有追踪李杜、开拓新境的理想。《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子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因为是醉后所言,不妨有些大言。这时距离杜甫去世还不到三十年。韩愈说昔年曾读二人诗,至晚也是他贞元初到长安应试时,这也是编年史上所见最早将李白、杜甫放在一起议论的记录之一。“长恨二子不相从”,似乎有惜于二人间来往太少。但若与韩愈晚年所作《调张籍》放在一起看,也很遗憾自己与李白、杜甫没有生活在同一时代。所幸有孟郊,有孟郊也就够了。他的诗反复纠缠,说自己如同“青蒿倚长松”,绝不会放过与孟郊共同努力的机会,即便云龙变化,出入六合,也要常与孟郊在一起。这是醉话,也是心声。《答孟郊》也作于同时:“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馀酒肉,子独不能饱。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炒。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弱拒喜张臂,猛挐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当咬。”这里用嬉笑怪嗔的笔法,写出孟郊的生存状态和诗风特点,因为关系好,譬喻怪奇偏激一些也没有问题。这里当然还要讲韩、孟之间的唱和。两人共同癖好,是喜欢写联句诗。在汴州写有《远游联句》,其间李翱也有参与,不过仅写“取之讵灼灼,此去信悠悠”,就被两人甩开了,似乎还不太适应这种类似游戏的文学活动。诗因孟郊将要南行而作,故起句孟郊就说:“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极尽夸张能事。韩愈接:“离思春冰泮,澜漫不可收。”即景取喻,颇为奇妙。诗很长,也很难分析。最后,韩愈说:“名声照四海,淑问无时休。归哉孟夫子,君归无夷犹。”是说孟郊名遍天下,仍不断给自己以关心。最后说到送别,你不必担心,放心地走吧。事实证明,孟郊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汴州乱后,韩愈生死未明之际,他有诗《汴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会合一时哭,别离三断肠。残花不待风,春尽各飞扬。欢去收不得,悲来难自防。孤门清馆夜,独卧明月床。忠直血白刃,道路声苍黄。食恩三千士,一旦为豺狼。海岛士皆直,夷门士非良。人心既不类,天道亦反常。自杀与彼杀,未知何者臧。”这里,他想到分别时的情景,感慨以往的欢悦可能再也没有了,忠直之人死于叛乱,道路的议论则各说各的话。他说的“海岛士”指田横五百士,生死以之,不计得失;“夷门士”从典故说是信陵门下士,这里已经顾不上用典,而是直斥汴州军将之无良,不知食德感恩,为此豺狼之行。孟郊的反应是激烈的,朋友的安危不能不萦系于情怀。孟郊是旧友,张籍则是韩愈在汴州认识的新友。张籍出生之年,至今难以明确,一般估计比韩愈小一两岁。张籍在韩愈卒后,作《祭退之》诗述二人之初识:“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囊。略无相知人,黯如雾中行。北游偶逢公,盛语相称明。名因天下闻,传者入歌声。公领试士司,首荐到上京。一来遂登科,不见苦贡场。观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兹类朋党,骨肉无以当。”张籍是苏州人而居于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自诩诗兼众体,苦于在朝无相知相识者。他北行到汴州,是贞元十三年,也不知什么原因,到第二年方与韩愈相识。恰好韩愈以节度推官的身份主持汴州的进士解送,特别欣赏张籍,置于首荐。这年秋张籍赴京试礼部,第二年就高中进士,也就是“一来遂登科”。是否韩愈的推荐就如此管用,还真无法判断,张籍终生记得韩愈的好,也是事实。韩、张之间在汴州有诗来往。如张籍有《寄韩愈》,首云“野馆非我室,新居未能安。读书避尘杂,方觉此地闲”,估计是韩愈为他安排在远郊的所居,远离尘嚣,可以读书。他再说:“出林望曾城,君子在其间。戎府草章记,阻我此游盘。”可惜韩愈忙于公务,没有时间相约同游,自己只能引颈遥望。韩愈有《病中赠张十八》诗赠张籍,有几句说到对张诗的评价:“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谈舌久不掉,非君亮谁双。”这时张籍还仅是布衣,有能力而无助于国事。诗文嘛,写得再好也只能自娱自乐。韩愈看到了他的诗文的力量与追求,且认为当世与自己可以谈得来的,也只有张籍了。极尽推崇,可以仔细体味。《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一四有张籍《遗公第一书》,提出当今“世俗陵靡,不及古昔”,根本原因在于“圣人之道废弛之所为”。他认为自秦灭学后,“汉重以黄、老之术教人,干惑人听”;汉末以来,“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国”。“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他建议韩愈能够继承孟轲、扬雄的学说,“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为乎”,应该写书以明儒学正道。希望韩愈“绝博塞之好,弃无言之谈,弘广以接天下士,嗣孟轲、扬雄之作,辩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这里,是挚友以天下道义为期的殷切之谈。张籍认为自己的能力与影响都不及韩愈,希望韩愈起而挽回儒学之颓势。韩愈《答张籍书》首先感谢张籍的建议,并说自己关心于此已经多年:“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仆为好辩也,然从而化之者亦有矣,闻而疑之者又有倍焉。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所得矣。为此而止,吾岂有爱于力乎哉?然有一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这时韩愈刚过三十岁,认为自己入世还不深,已经做过许多努力,从而化之者是愿意接受的人,更多是闻而疑之者,即将信将疑的人,至于顽然不入者,你永远也别想改变他们,这是社会的大多数人。韩愈希望到五十以后再著书立说,见解深刻,减少偏失,以传后世。张籍再致第二书,认为“士之壮也,或从事于要剧,或旅游而不安宅,或偶时之丧乱,或不皇有所为,况有疾疚吉凶虞其间哉?是以君子汲汲于所欲为,恐终无所显于后。若皆待五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人生短暂,充满不确定因素,君子第一要义是显名于后,一定要到五六十岁以后方有所论述,难免会有所遗憾。韩愈作第二书回复,感谢张籍“意欲推而纳诸圣贤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谓愈之质有可以至于道者,浚其源,导其所归,溉其根,将食其实”。朋友如此以圣贤、道义相期于自己,心存感激。也说出为难之处:“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譊譊。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即举世迷惑于佛道二教,上自公卿,下及庶民,若公然反对,必遭遇许多不虞之祸。又说二教盛行中国,“盖六百年有馀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又说:“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扬雄,亦未久也。然犹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为之哉!”这里已经提到了道统流传之体系,更认为前代圣贤之有所成立,不仅勤于弘道,更能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方能有所成立。自己有理想,也明白不会轻易地获得成功。彼此的交流,透露韩愈倡导儒学、排诋佛老的心路历程。张籍的敏锐与鼓励,最终造就韩愈成为思想史上的巨人。一般人之印象,张籍仅仅是个诗人,算不上思想家。从以上二信可以理解,虽然他那时只是一位赴考的进士,但心怀改变世道人心的宏愿,并希望韩愈来有以完成。而韩愈最著名的弘道宣言《原道》等文,今人都认为作于贞元后期,当与张籍的督促有关。从汴州相识,到韩愈去世,两人的友谊终身不变,不仅因为诗,更因为文章道义。还有一层,张籍脾气好,对韩愈绝对信任。韩愈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他的喜怒哀谑,一切都可以向张籍倾诉。对张籍来说,随便你怎么喷,我绝对不生气。有这样的朋友,是韩愈的幸运。就在张籍欢庆进士登科,杏园欢会之时,汴州城中因董晋去世,发生血腥政变,韩愈经历了此生最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贞元十五年二月初,董晋在任上去世,得年七十六。仅仅七天后,汴州兵变,杀留后陆长源、判官孟叔度等人。汴军为什么叛乱?《旧唐书·董晋传》认为:“(董)晋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长源好更张云为,数请改易旧事,务从削刻。晋初皆然之,及案牍已成,晋乃命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皆恶之。”是说陆、孟二人因为改易削刻、轻佻慢易而激起兵变,要负一定责任,被杀是咎由自取。从韩愈、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文来看,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韩愈《董公行状》云经过董晋与其幕僚诸人之施治,汴州已经“职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鹊集,苍乌来巢,嘉瓜同蒂联实。四方至者归以告其帅,小大威怀。有所疑,辄使来问;有交恶者,公与平之”,这是四方共同的观感。但在此同时,董晋“累请朝,不许。及有疾,又请之,且曰:‘人心易动,军旅多虞,及臣之生,计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难期。’犹不许”,董晋已经看到军心不稳,自己在世,还压得住,自己身后,实在无法预料。韩愈进一步说:“公之将薨也,命其子三日敛,既敛而行。于行之四日,汴州乱。故君子以公为知人。”即董晋临死前,已经料到兵乱不可避免,让其子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后事,三日成敛后立即启行。是他已知汴兵必叛之势,以他的馀威,仅足维持数日之太平。韩愈因为偶然的原因,送董晋灵柩出城,逃过此劫,纯属幸运。韩愈作《汴州乱二首》:“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这是乱后不久的诗作,大夫、留后皆指陆长源,昨日还风光无限,须臾皆死于兵乱。从房屋连栋被烧,留后及幕官阖家被杀,动乱规模很大。责任在哪里?韩愈一说是“诸侯咫尺不能救”,即邻镇坐见汴兵嚣张,无动于衷;二说是“庙堂不肯用干戈”,即朝廷长期与方镇苟且偷安,使汴军拒绝朝廷命帅,只有军中拥立,方能接受。韩愈更有《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说明自己在兵乱之际的遭际,这是其中相关的一节: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怳难为双。暮宿偃师西,徒展转在床。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傍徨。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骄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东来说,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东去趋彭城。从丧至洛阳,还走不及停。假道经盟津,出入行涧冈。日西入军门,羸马颠且僵。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诗写给张籍,前面讲到许多往事。这里说他护董晋丧车西行,到达偃师以西,即距离洛阳还有一日行程时,先听闻张籍及第,悲喜交集。当晚汴州兵变消息传来,彻夜无法入眠。他离汴时,并没有带上家人。这时跟随他的家人约有三十多人,最惦念的是妻与子,还有未断奶的幼女。他这时负有为董晋护丧的责任,一步也离不开,想到幼女的哭声,真是无从自已。所幸后续消息很快也传来,他的家人没有遭遇屠戮,已经脱祸离开汴梁,乘船沿汴水东下,先避地徐州。可以稍微放些心了,但仍魂不守舍,毕竟家人到徐州如何安顿,还得自己去张罗。诗里透露,韩愈送丧至洛阳,对董家有所交待后,立即假道盟津,入河阳军,然后转奔徐州。因为他与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还有一些交集,此后得以在徐州幕府暂栖。孟郊有《吊国殇》:“徒言人最灵,白刃乱纵横。谁言当春死,不及群草生。尧舜宰乾坤,器农不器兵。秦汉盗山岳,铸杀不铸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起争。”这里用《唐文粹》卷一五下的文本,与孟集所载颇多不同。此诗应该是为陆长源而作,从“白刃乱纵横”“谁言当春死”等句可以明白。孟郊与陆长源交谊最厚,对陆为国死难,身后还遭遇污名,似乎兵乱是因他失政而引起,更感不满。他甚至骂到秦汉以来对暴力得胜者之歌颂,可见怨愤之深。从韩愈诸诗文中,还可以读出汴乱的一些真相。他为董晋子董溪所撰墓志中说:“太师(董晋)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维纲,锄削荒颣,纳之太和而已,其囊箧细碎,无所遗漏,繄公之功。上介尚书左仆射陆公长源,齿差太师,标望绝人,闻其所为,每称举以戒其子。杨凝、孟叔度以材德显名朝廷,及来佐幕府,诣门请交,屏弃所挟为。”颂赞董溪助父理政的同时,对遇害的陆、孟二人评价颇高,皆属助董治汴的关键人物。韩愈《送湖南李正字归湖南序》云,李础之父曾与他同在汴幕,“以侍御史管汴之盐铁”。“军乱,军司马、从事皆死,侍御亦被谗,为民日南”,即汴幕被杀者外,李础父也得罪贬窜到今越南境内。是朝廷无力追究叛乱者的罪责,反让被害者与同幕者承担罪责。韩愈《韩弘碑》载,汴州经过多次反复,“军中皆曰:‘此军司徒所树,必择其骨肉为士卒所慕赖者付之,今见在人莫如韩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司徒指刘玄佐,曾领汴军八年,韩弘是玄佐妹之子,故称韩甥。即汴军只认刘家之宗人,不接受朝廷委派之军帅。汴乱之根本,也即在此。此后韩弘领镇二十一年,平安无事。从贞元十二年七月到十五年二月,韩愈在汴州度过了两年半时间。这是他进入仕途的第一份工作,走的也是中晚唐士人从幕府出发的习惯道路。在这两年半中,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也理解了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与朝廷的苟且无为。当然,他也学到了许多,董晋之公忠体国,一往无前,以及处理政事时的柔软身姿,和对潜在危机的准确预判,他皆有切身体会。他接待了路过暂住的孟郊,增进了友谊,也表达了可以长期合作竞争的愿望。他认识了有才分也很有社会担当的诗人张籍,凭借自己的权力首荐张籍入礼部就试,张籍也很争气,一举高中,彼此友谊维持了一生。更惊心动魄的是,他在护送董晋灵柩归洛时听闻汴州兵变,昔日之同官全家惨遭屠戮,自己家人也几落贼手,更看到事后朝廷之不负责任。陆长源年纪也在七十左右,是旧相之孙,他在遇害当日被任命为节度使,当然是出自董晋的推荐。怎么可以说董晋有所施为,一切都好,陆长源仅接手几天,就铸成大错?其实汴军积恶成习,利欲熏心,毒蜂成窠,无视皇权,有重臣在还能维持,重臣一死就旧态复萌。朝廷知道平叛要依靠实力,国家偏偏不具备这个实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遇害者承担责任,让继任者尽量在叛军与朝廷间保持平衡。这些,韩愈都看到了,有愤懑也无从发声,只留下若干闪烁其词的片段。将这些现象梳理清楚,可以体会他在经历此番剧变后,人生有了更深切的体悟,此后一系列论著中倡导恢复儒家道统,讲求夷夏之分,力求在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现状,汴州的这段经历对他是很重要的。
 END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