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陷落后,契丹人耶律楚材穿过重重战火,来到成吉思汗面前。
“身长八尺,美髯宏声”的耶律楚材让蒙古征服者眼前一亮,成吉思汗从此十分信任这个帅气的知识分子。耶律楚材则经常劝谏成吉思汗行文治之道,想要让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这是蒙金战争之际,北方士人所见的动荡局面。
蒙古人南下中原,由于缺乏文化素养,只知烧杀掳掠,一度要将中原夷为牧地。北方士人不仅要在国破家亡之中艰难求生,还要饱尝文化沦丧、价值幻灭之苦。
后来,成吉思汗西征,俘获一个善于制造良弓的工匠,为此沾沾自喜。耶律楚材却对他说:“治弓尚须用工匠,治天下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耶律楚材所说的“治天下匠”,是指和他一样致力于考取功名的读书人。
但是,蒙元时期,科举制度陷入至暗时刻,经历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停顿。
一场关于科举行与废的博弈,在帝国的权力中心不断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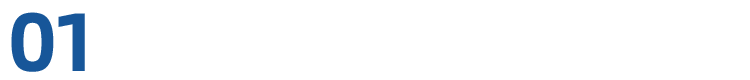
作为辽朝皇室之后,耶律楚材的家族在金朝倍受优待。17岁时,耶律楚材本来要因门荫得官,成为中央部门的干部,但他没有到任,而是放弃到手的官职,跑去参加科举考试。从小学习汉文典籍的耶律楚材靠实力通过皇帝的当场考核,从地方官做起,进入官场。
可见,这是一个不愿意走捷径的学霸。
耶律楚材臣服于蒙古大汗后,依然不改其执拗的性格,在蒙古军疾风迅雷般的征伐之中,苦苦寻找中原衣冠的生存空间。他为蒙古帝国“定税赋,权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为推行汉制殚精竭虑。
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史称元太宗)通过“忽里台”大会,正式接过蒙古汗位,即将对苟延残喘的金王朝发起最后的冲击。
在窝阔台大举进犯前夕,南渡开封的金廷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廷试放榜那日,状元李塘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上街头,开封的老百姓照例群聚围观新晋进士游街,即便在江山风雨飘摇之际,科举考试仍是举国关注的头等大事,仿佛士子的得意春风可以吹散黑云压城般的蒙古大军。
蒙古灭金后,北方科举陷入停滞,儒士的地位急转直下。
历经数十年的征战,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文化已经产生新的认识。
一方面,信奉“长生天”的他们崇敬世间能与神灵“沟通”的宗教人士(蒙古人称为“孛额”),因此形成一种宗教优容政策,善待佛、道两家,尤其尊崇全真教为首的新道教,僧、道可“优免赋役”;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尚未完全接纳中原汉制,对儒家不甚重视,许多儒士在战乱之中四散飘零,甚至被掳为奴,北方士民“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
为此,耶律楚材忧心忡忡,上书建议窝阔台重启选官制度,恢复儒士身份。
1238年(元太宗十年,也是农历戊戌年),在耶律楚材的极力主张下,蒙古大汗窝阔台下达诏令,宣布实行“戊戌选试”。
按耶律楚材的设想,诸路先通过考试,甄选儒士,尤其是“被俘为奴者”,通过考试可免除奴隶身份,免掉征徭杂役,获得与僧、道一样的地位。当时,通过选士的儒生有四分之一曾陷于奴籍。
接着,耶律楚材进一步要求为这些儒生“开辟举场,精选入士”,也就是举行科举考试,授予官职。
元代士人认为,耶律楚材为蒙元做出的贡献之一是“设科举”。但“戊戌选试”没有按照耶律楚材的计划进行,而是在筛选出儒户后就戛然而止(“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因此,只能算是蒙元时期恢复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失败尝试。
不过,由“戊戌选试”确立的儒户制度,成为蒙元一代的定制,至少让很多儒士免于蒙古人的蹂躏,也有利于恢复社会秩序。
耶律楚材救千万儒生于水火之中,晚年却遭到蒙古权贵的猜忌,他恢复科举的宏愿始终无法实现。耶律楚材失势后忧愤而死,天下士子“莫不茹泣相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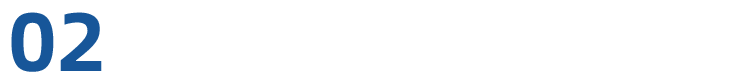
元朝设立儒户,免除儒户的赋役,却没有给儒生提供跨越阶层的好出路。
蒙元一代,朝廷用人最看重“根脚”,也就是出身。
在游牧民族特色的贵族政治下,出自好“跟脚”的蒙古人、色目人无疑是权力核心层的宠儿,但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低,执政能力差,连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务都做不好。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当时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很多不识文字,就连执笔签字都不会,于是在象牙或木头上刻上花押来代替签字。
国家交给这帮人,肯定乱成一锅粥。
科举停废期间,蒙古统治者仍然需要大批掌握掌握文化知识的儒士,来负责各级政府的实际运作,于是有了“岁贡儒吏”的制度,规定各地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儒士,由他们充当各衙门的吏员。这些儒吏成为帝国中底层官员的主要来源,甚至有一部分可以跻身朝廷高官。
但是,贡吏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也没有公正的选拔制度。除了少部分儒生能够以吏入官,更多读书人上进无门,只能一辈子混迹于社会底层,甚至成为社会上最穷困潦倒的阶层。
在没有科举的日子里,元代儒士“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但这些儒生经商比不上商贾,种田比不上农民,干活比不上工匠,好一点的出路就是进官府打杂,真的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
儒生被蔑称为“老九”,正是在元代科举停废时期,所谓“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叠山集》卷二)
这是说,儒生的社会地位列于十等中的第九等,仅比乞丐高一级,比妓女还低一级。
与黄金家族中的长辈和兄长相比,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比较尊崇儒学的帝王。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重用大批熟悉汉法的大臣,如刘秉忠、许衡、郭守敬、王鹗、王恽、董文炳等,并设立翰林国史院,颁布一系列兴学诏令,广泛搜罗前代图籍。
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权。儒生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也许是希望他能进一步尊儒,恢复科举制度。
重新开科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关科举行废的讨论再度展开。赞成者认为,科举为“先朝典故,最为切务”;反对者则以科举为“无用学”,甚至提出“金亡于儒”的不利舆论。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的重要谋士许衡出任国子监祭酒,遭到科举支持者的抨击。
许衡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师承程朱理学,却崇尚“实学”,包括天文、历算、医学、农学、律学等,像这样的实用型人才,一向得到忽必烈器重,而支持科举的儒生大多死守章句,不通实学,对许衡十分不满。
支持科举的大臣想利用忽必烈对佛教“崇教而抑禅”的态度,来弹劾许衡,鼓吹科举,便将儒与佛相提并论,上书说许衡那一套都是歪门邪道的“禅”,科举才是正统的“教”。
殊不知,科举支持者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而不是儒生的空谈,这种诡辩更是惹得他龙颜大怒,当即召集朝廷重臣廷议。
朝臣议论时,忽必烈对汉人大臣董文忠说:“我听说你每日诵读《四书》,也是个道学家啊!”
董文忠是蒙元开国功臣董俊之子,他的哥哥董文炳也是元初猛人,被忽必烈尊称为“董大哥”。
董文忠喜好儒学,却不支持恢复科举,便回复道:“陛下常常说:‘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海内之士这才逐渐知道要从事实学。臣如今每天所诵的是孔孟之言,但不知道什么是道学,只知道俗儒守着亡国的旧习,想要推行他们的学说,以此来迷惑陛下,这不是陛下教人修身治国的本意。”史载,董文忠说完这番话,廷议就被忽必烈叫停。
忽必烈在位时,关于科举的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姚枢、许衡、王恽、杨恭懿等大儒都被卷入其中。师承关学的杨恭懿提出一个折衷的主张,一方面赞成恢复科举,另一方面建议改革考试内容,罢黜词赋,改成考“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
直到忽必烈去世,大臣们多次动议恢复科举,但所拟方案都没有付诸实施,此后的成宗、武宗也曾下诏议行科举,但都不了了之。
科举像是盘旋在帝国上空的幽灵,蒙古统治者自从踏入中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难以摆脱其纠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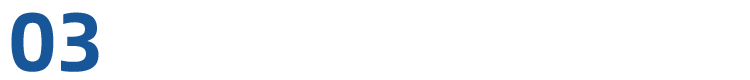
忽必烈攻灭南宋,一统天下后,又吸收了一大批儒生。随着战火平息,蒙古统治者久居汉地,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恢复科举的条件亦逐渐成熟。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生长在汉地,身边有儒臣相伴,早年师从太常少卿李孟,是一位倾心儒家的皇帝。
元仁宗曾问左右,宋朝丞相文天祥是怎样一个人?
左右为了奉承蒙古统治者,都说文天祥拒不降元的行为很愚蠢。没想到,元仁宗立马变了脸色,说:“照你们的道理,冯道岂不是忠臣!”冯道是五代十国的人物,先后仕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官至宰相,但按照理学家的观点,他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小人,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种官僚风气也不值得提倡。
元仁宗更推崇状元出身的文天祥,以及他所代表的孔孟儒学。初登帝位时,元仁宗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生,何以至此。”
元仁宗的老师李孟也经常劝其恢复科举,说:“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
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经过诸多儒臣的筹措,元仁宗正式下诏,恢复科举。
蒙元统治者议论数十年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科举史上历时最长的停废也告一段落。
此时,距离蒙古灭金,已经过去79年,经历过科举的北方儒士早已谢世,距离元灭南宋,已过去34年,南宋遗民听闻这一消息,恍如隔世。
元仁宗恢复科举的诏令下达后,天下士子如久旱逢甘霖,奔走相告,欢呼道:“庶几可以展吾志矣!”
科举停废时,很多读书人为生计所迫,只好混迹于市井,等到重开科举时,他们手头连几本书都没有,却都跃跃欲试,懊悔自己为了眼前的苟且而荒废学业。
有个叫刘将孙的读书人,得知朝廷恢复科举后,在诗中写道:“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刘将孙乃南宋进士刘辰翁之子,却只能与演戏的倡优、算卦的卜祝混在一起,直到有了科举,他才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
元朝的首届科举考试,就在这样一种民心大振的气氛中开场。
元仁宗的老师李孟被任命为主考官(知贡举),此外,还有张养浩等名臣担任考官。
当时,有人主张要用严格考试来考验人才,张养浩却表示反对,说:“科场被废近百年,如今刚刚恢复,能够得到的士子必定不多,如果要求太严,恐怕会打击后来者。”
放榜后,新进士要谒见“座主”,表示感谢,张养浩却拒见考生,写了一张免谢帖:“诸公但思致公竭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
张养浩的高风亮节,一时传为佳话。
这位元代散曲大家,在其代表作《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有一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饱受争议的元朝科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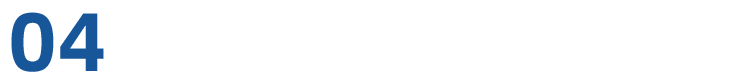
元仁宗恢复科举时,命中书省官员在御前说明考试主旨,其中说道:“四书五经以程氏、朱晦庵批注为主。”
有的学者认为,元朝科举进一步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但根据余英时等学者研究,元代科举考试主要还是以经典本身为本,并没有形成固定、僵化的标准。
真正对儒生形成桎梏的,是元朝令人窒息的民族政策。
元仁宗皇庆二年所订的《考试程式》规定了乡试、会试等各级考试的内容和标准。
其中,会试分为左右榜、四等人分卷录取,规定四等人各选七十五人,共三百人参加,录取人数不过百人。这个人数规模与两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宋朝仅一场会试的人数就多达数千人,而将四等人制强加于科举制中,更是打破了科举的公平原则。
所谓四等人,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统治者占据着第一等级;色目人作为最早被征服的民族(包括中亚、中东、东欧等地的民族和西夏、畏吾儿、吐蕃等),为第二等级;汉人,指金亡后归降蒙元的民族,为第三等级;南人是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人,最晚归附,位居第四等级。
四等人中,南人儒生数量最多,文化水平最高,却只能拥有与蒙古人、色目人同样的名额,而且蒙古、色目人所在的右榜考试科目比南人所在的左榜少,不用考难度较大的经义和古赋。
这种分配方案本就不公,而汉人、南人不仅在科举的过程中受到歧视,还要在仕途中面对新的矛盾。对于蒙古军事贵族和吏员出身的官僚来说,科举士子进入官场,难免会分走原本属于他们的权力蛋糕。
元顺帝在位时,出身怯薛的权臣伯颜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他极度排斥汉文化,反对蒙古人读“汉人书”,也“禁汉、南人演习蒙古、色目文字”,甚至提出要杀尽 “张、王、刘、李、赵”等大姓汉人,着实令人发指。
有一次,伯颜上书皇帝,说:“陛下有太子,千万不要让他读汉人的书,汉人读书就会欺负人。前阵子我的马夫突然失踪了,一问才知道是去应举考试。我不想科举都让这等人得了!”
倒行逆施的伯颜,动了废除科举的念头。
▲《佛郎国献马图》(明代摹本)中的元顺帝形象。图源:网络
元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在伯颜、彻里帖木儿等蒙古大臣的操纵下,科举再度被废。
当时,御史台19人联名弹劾主持此事的彻里帖木儿,引起伯颜震怒。最终,抗议无效,这19人中有18人去职,御史台为之一空。
时任参知政事的许有壬是元仁宗年间进士,作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拥护者,他亲自找伯颜理论,说:“如果罢废科举,天下有才能的人都会怨恨的!”
伯颜不以为然,说:“如果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世上贪赃枉法的人就更多了。”
许有壬反驳道:“就算没有科举,我朝贪官也不少啊,这怎么能怪科举!”
随后,伯颜从吏治、选官等多方面找理由搪塞许有壬,尤其是提到,科举制妨碍了元朝的选官之法。
许有壬一听,更来气了,说:“古人有言,立贤无方。如今通过通事、知印等吏员出身的官员,多达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每一年就有四百五十六人,而科举三年一次,每次只选百人。太师(伯颜)您想想,科举制真的会阻碍我朝的选官之法吗?”
老许据理力争,当场甩出数据对比来怼伯颜,可伯颜不愿跟许有壬多做辩论,还在争辩时讽刺道:“我看中举的人才少之又少,只有参政你一个人可用!”
一旁的彻里帖木儿看着伯颜和许有壬吵得不可开交,就对许有壬说:“参政请坐,不要多说了。”
许有壬一见彻里帖木儿,又开怼了,说:“太师刚刚说弹劾你的御史都是我指使的,你还愿意和我共坐吗?”
彻里帖木儿笑道:“我从未相信这些流言。”
许有壬讽刺道:“还好你不信,如果是我让人弹劾你,可不会这样就善罢甘休。”许有壬虽然斗不过蒙古权贵,嘴巴却很硬。
伯颜当然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停罢科举的诏书下达时,他特意让许有壬位列百官之首听读。众臣散去后,一个御史跑到许有壬身边,悄悄对他说:“参政这样就成过河拆桥的人了。”尽管许有壬没有掺和废科举的事,但他毕竟身在朝堂,难免会被天下士子误解。
许有壬面有愧色,从此借口生病,不来上朝。
解铃还须系铃人。
伯颜掌权时,将侄子脱脱安插到元顺帝身边负责监视。脱脱平日里尊重汉儒,推崇汉制,与他暴虐的伯父截然不同,眼看着伯颜一手遮天,脱脱担心祸及宗族,便与元顺帝的亲信联合,打算大义灭亲,扳倒伯颜。
后至元六年(1340年),伯颜约元顺帝到柳林打猎,元顺帝托疾不去,伯颜便挟持太子同往。敏锐的脱脱察觉到了政变的机会,与其他几名大臣合谋,封锁京城,命亲信率兵列于城下。
等到伯颜的人马回来时,只见城门紧闭,脱脱倨坐于城楼之上。脱脱拿出元顺帝拟好的诏书,宣布罢免伯颜,并告诉城外的人:“跟随伯颜的人一并无罪,可以即刻解散,各自归还本卫,朝廷问罪的只有伯颜一人而已。”树倒猢狲散,孤立无援的伯颜只好束手就擒,不久后于被贬途中病死。
脱脱与伯颜的权斗,表面上是蒙古贵族争夺权力,实际上也是元朝汉化与反汉化两股势力的对抗。最终,排斥汉人、废除科举的伯颜被判处变乱祖宗之法的罪名,遭到驱逐,而脱脱掌权后,为了维护元朝统治、安抚天下士子,很快恢复了科举制。
从脱脱再开科举到元朝灭亡前夕,科举制度依然得到士子的拥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帝国如大厦将倾,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大运河通道阻塞,元朝最后一次科举却如期举行,南方考生为了进京参加会试,纷纷取海道赶赴大都。
即便生逢乱世,科举仍是士子在暗夜之中拼命追逐的微光。
清人秦蕙田对元朝科举有一段评价:“元中书省所定科举条目皆参用宋、金之制,斟酌损益,最为得中,自明以来相承用之,虽有更定,大略不出乎此。”
这是说,元朝科举制度上承宋、金,下启明、清,其历史地位不容抹杀。
但是,元朝科举的落后性同样不容忽视,除了前面所说的民族政策外,元朝对科举入仕者也充满歧视。
有元一代,共开科十六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人数为统一王朝中最少的,而在文治大盛的宋代,单是宋太宗一朝录用的进士就有数千人。
据学者姚大力统计,元朝文官中,通过进士入仕者,所占比例只有区区4.3%,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进士只有二十多人。
故而,姚大力说:“元朝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其数量或地位来说,在官僚构成中都居于绝对劣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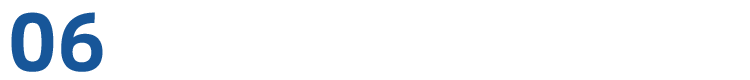
无论科举行与废,元代的读书人都难有出头之日。在这个黑暗时代,儒士即便考中科举,也难以进入权力集团。
因此,除了部分士子仍汲汲于功名利禄,在科举这条希望渺茫的独木桥上奔竞外,还有一些儒士“甘隐山林”,成为游士、隐士。
画家王冕是元代著名的隐士之一,他也曾“应进士举”,考不中后便归隐田园,侍奉老母,也曾乘舟入江,游览名山大川,寻访奇才、侠客。
王冕性情高洁,鄙视权贵,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傻”。
▲[元]王冕:《墨梅图》。图源:网络
年少时在田间放牛,王冕跑去听学生念书,结果,书背下来,牛给放丢了。
有朋友在战乱中不幸去世,留下两个幼女和一个书童,无人抚养,王冕当即前去安葬了朋友,并收养了这三个孤儿。
称霸东南的朱元璋想邀请王冕出来做官,但王冕拒绝了,他以出家为由,跑到寺庙躲起来。
有位当官的朋友要推荐王冕为府吏,改善他窘迫的经济状况。王冕却说:“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给人使唤?”
王冕“状貌魁伟,美须髯”,平日里模仿古时的名士,头戴高帽,身披绿蓑衣,足穿木齿屐。有一次,他前往绍兴,迎回此前安顿在此的母亲。回乡路上,王冕用一头白牛拖着母亲的车,自己穿着那一身衣服跟在车后,乡间的孩童争相围观,对着他笑,王冕也笑了。
王冕不过是元代千千万万的科举失败者之一,但明朝开国功臣宋濂在修《元史》时,专门为其作传。
或许,是因为王冕的故事告诉世人,即便身处昏暗的时代,也要做一个心中有光的人。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联经出版公司,2008
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武玉环,高福顺,都兴智,吴志坚:《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辽金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辑,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