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使臣陆贾第一次来到番禺(今广州)时,南越王赵佗用个性十足的的方式接见了他。
这是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一统中原后,意欲收服割据岭南的赵佗,于是派陆贾南下劝降。
赵佗身居岭南多年,自称“蛮夷大长老”,平日里身穿越人服饰,头发梳成椎髻,见到陆贾时,他双腿向前叉开而坐,没有半点儿中原礼俗的样子。
陆贾当面数落他,赵佗还不服气,说:“假如我当时也在中原逐鹿,哪见得就比不上汉皇呢?”
清代学者屈大均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意思是,广东自古远离中原,受中原声威教化的影响较小。
用王道正统的观点来看,古代岭南的发展史,似乎是一段接受中原教化的历史。从中原进入岭南的移民,历来被描述为传播文明的使者,中央朝廷的每一次变动,都有可能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但是,中原帝王都的声教,并非文明的唯一标准。从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同力量之间长期的博弈与交融。

▲广州陈家祠屋檐的传统雕塑。图源:摄图网
林语堂评价广东人,说其“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这种性格似乎从两千多年前就被刻进了岭南的文化基因。
南越王赵佗本是河北人,早年在秦朝当官,他之所以在岭南割据称雄,还要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的一次远征。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囊括四海的步伐伸向了五岭以南的疆土,命屠睢率领50万大军南征百越。史书记载,此战十分惨烈,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尉屠睢一时轻敌,遭到越人夜袭,当场阵亡,百战百胜的秦军在南征途中狠狠地摔了个跟头。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军吸取教训,先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灵渠,确保后勤补给,并训练精锐的水军“楼船之士”,随后以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再次出兵岭南。
四年后,任囂与赵佗率领的秦军平定岭南。秦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其中任嚣为南海尉,总领岭南全局,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南越。
岭南,包括今广东、广西及海南等地,先秦时聚居于此的越人被称为“南越”。
任嚣对岭南的经营一直持续到了秦末乱世,为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史书将他与当时在北方防御匈奴的蒙恬并称:“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嚣,恩洽扬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
这一时期,来自中原的戍卒、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与谪吏,为岭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并与土著的越人通婚。
任嚣采取宽松政策,“抚绥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复加荒裔”,接受南越习俗,与越人和睦相处。他任职数载,越人皆诚心归附。
公元前208年,秦朝灭亡前夕,任嚣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他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于是,任嚣召赵佗到番禺,临终前将岭南托付给他,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当时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
秦亡之后,赵佗不负任嚣所托,迅速派兵切断通道,严守关口,在番禺自立为王,史称“南越武王”。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为东江、北江、西江三江相汇之地。南岭以南,三江来水分别从博罗田螺峡、清远飞来峡、肇庆羚羊峡倾泻而出,汇入珠江,奔涌向海。
由于古时候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当地人习惯将穿城而过的江河称为“海”,称今黄埔南海神庙一带为“大海”,而“小海”指今荔湾一带。
在古代,广州不仅坐拥浩荡江水,还有三十余峰逐级而下,其中,以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番山、禺山为第三级。
屈大均在《广州新语》中描述广州的山势时说:“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越)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番山、禺山大约在一千年前随着广州城市建设而被夷平,后来逐渐退出历史。
直到南越国灭亡的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仍然觉得依山临水的广州城有“王气”,下令在越秀山修建望海楼(后改称镇海楼,即现在的广州博物馆馆址)。
这座雄伟的五层高楼取“威震海疆”之意,表面上像是一个观景楼台,实际上代表帝国对这片海疆的统治。按照当时统治者的迷信心理,其修建是为了镇压广州的“王气”。
史书记载,赵佗活了一百多岁。
在赵佗统治期间,南越国长期处于承平年代,他继承任嚣的政策,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南越风俗,对南越旧俗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并鼓励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南越土著通婚,此即“和辑百越”。
当年陆贾见赵佗时,指责他“反天性,弃冠带”,整天和越人混在一起,想要以区区南越之地与大汉天子抗衡。
这是因为,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看,赵佗割据自立,身着越服,是落后的表现。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赵佗摆出“椎结箕踞”的姿态,更容易与越人打成一片,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移风易俗,史书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
这种“文理”正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初次融合,在赵佗的领导下,南越国也渐渐学习了来自中原的音律、衣食、人伦、语言文字、政治制度。
赵佗去世后,南越国又存在了二十多年。汉武帝在位时,派五路大军直捣番禺,灭南越国后,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合称“交州九郡”。
南越国灭亡后,汉朝将岭南的政治中心移往苍梧郡广信县,意欲削弱番禺的政治地位,却不经意间唤醒了此地的另一个特性——平民属性。
当时,番禺昔日的王室禁地变成了平民区,大量民众涌来,在王城的城墙下贩卖商品,建起了广州最早的“城中村”。

▲现在的广州:高楼与城中村融为一体。图源:摄图网
据《史记》《汉书》记载,当时的广州已经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北方中原的主角似乎总是赫赫有名的明君贤臣、名将大儒,而远在南方的番禺,却把历史的舞台让给了无数默默无闻的商贩。
三国时期,孙吴统治下的交州划为交、广二州分治,其中广州的州治为南海郡番禺。
广州由此得名。
孙吴大臣步骘南下到广州为官时,登上象岗山,遥望珠江烟波万顷的壮阔景象,才知道当初赵佗为何会选择这里作为王都,赞叹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只因古人常将广州的江河称为“海”,所以步骘说,这里真是海岛上的肥沃之地,是宜于建立都城的地方。
于是,步骘筑立城郭,围绕着曾经的南越国王宫,对番禺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营建。
步骘扩建的广州城在南海之滨焕然一新,直到两晋之际,这里仍是庇护南下移民的世外桃源。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十室九空,远在越秀山下的广州城却是一片平静祥和的乐土。有个南下移民去世后,在墓砖上刻下:“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南朝梁武帝在位时(502年-549年),菩提达摩从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达摩祖师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史迹:一处是今广州上下九步行街旁边的“西来初地”,这里相传是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另一处是光孝寺的“洗钵泉”。
广州光孝寺原是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期孙吴学者虞翻被贬广州后,来到赵建德的故园中讲学,每次前来听课的学生多达数百人。虞翻在园中栽种树木,人们将这个园子称为“虞苑”。到了虞翻去世后,这个园子被捐出作为寺庙,因为其前身为王苑,故俗称“王园寺”。
达摩祖师在广州登岸后,见王园寺的和尚每天都要到外面挑水喝,就告诉和尚们,寺院的地底下有黄金。
因为王园寺曾是南越国王故宅,又是大学者虞翻讲学之地,大家都相信其中确有宝藏,就跟着达摩,挑起锄头往下挖。挖了几丈深后,黄金没找到,却挖出了甘甜的泉水。正当众人失望时,达摩却说,这不是用黄金的斤两可以来计算的。
据《光孝寺志》记载,人们在这里打了一口井,称为“达摩井”或“洗钵泉”,其“味甚甘冽,盖石泉也”。
到了唐代,六祖惠能到广州时,光孝寺(当时名为乾明法性寺)有了“风幡之论”的著名典故。
当时,印宗法师在寺中讲涅槃经,讲了一半,指着飘动的幡说,问大家是幡为何而动。
有人说是幡在动,有人说是幡随风而动。
正当众僧为此争论不休时,惠能来到寺中,插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乃仁者心动。”
菩提达摩在广州登岸,开启中国禅宗的历史,其实蕴含着广州另一个古老的属性——海洋属性。
秦汉时期,广州流传的果布、珠玑、玳瑁等商品多来自于海外。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也是海外舶来品。甚至就连秦始皇发兵征服岭南的原因,一说就是看上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早在先秦时,“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这条从南海出发,通往东南亚等地的航线,即“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珠江“八门入海”示意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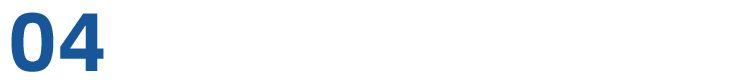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外商船“岁十数至”的繁荣景象。
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这是说,广州的刺史在城门附近转一转,就能收获几千万钱财。
隋朝灭南陈,一统南北后,接管了广州的海外贸易市场,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隋朝加重对商人的盘剥。于是,番禺人王仲宣起兵反隋,以恢复南陈为名,引兵围广州。
隋朝不得不派兵平叛,解广州之围,随后请出本地土著领袖冼夫人安抚民心,才平息了这场动乱。
为此,隋文帝杨坚规定,“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拆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确保海上贸易畅通,禁止广州官吏不得从海外客商身上侵吞牟利。隋代,广州“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隋炀帝时,在锐意经略海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岭南的统治。
自隋炀帝起,朝廷在广州建南海神庙,祭祀南海神祝融,祈求海不扬波,风调雨顺。南海神庙的意义不仅在于祭祀,它也是王朝统治的象征,南海神被朝廷推崇,南海也受帝国管辖,但这种超越人间的力量是王朝统治者赋予的,以此宣称这片山海已被纳入帝国的体系。
到了唐代,从南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乃至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有了一个官方名称——广州通海夷道。
此外,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使院。这一时期,“广人与夷人杂处……日发十余艇……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号称“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六祖惠能在广州留下“风幡之论”典故的时代,除了佛教外,还有无数外来文化在广州争奇斗艳。
从这条伟大航道而来的外国来客,在广州“蕃坊”定居,做生意,购田宅。唐代的蕃坊在广州西城外,大致以今光塔路为中心,始建于唐时的怀圣寺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蕃坊的居民以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为主,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等不同宗教。
商贾骚动之下,广州开放包容。但即便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对广州这种重利的风气还是看不惯的。
农为本,商为末,官府认为商人都是逐利之徒,广州一带“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而商人表面上对官员毕恭毕敬,背地里也与官府若即若离。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广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官商矛盾。
当时,有些商人不堪官吏的任意盘剥,向广州都督路元睿告状。然而,路元睿不顾商人们的说辞,只知官官相护,判定商人有罪。这激起了商人们的愤怒。
那时有钱人家中经常用“昆仑奴”(即东南亚一带的“黑人”)作为仆役。其中一个商人的昆仑奴闯入官署,提刀杀死了路元睿及其十多个亲随,并带走了路元睿的尸首。昆仑奴完成刺杀之后,与商人登船入海,逃之夭夭。路元睿死后,人们从他家拉出了几大车金银珠宝。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广州又发生了所谓“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的事件。
中国史籍中常引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描述,认为这是大食、波斯等国趁乱出兵攻打广州的事件。但在阿拉伯等国的史籍中都找不到相关记载。
有不少人认为,作乱的其实是居住在广州的蕃客,这背后也是官与商、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冲突。
蕃商攻入广州城,“劫仓库,焚庐舍”,其主要目标都是官衙与官仓。由于地方官上报朝廷时不敢名言,而是夸大其词,在史书中就变成了兵众攻城的历史事件。
唐代广州的繁华如梦,后来被黄巢起义军踏碎。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私盐贩子出身的黄巢率领他的军队攻入广州。黄巢看重广州“市舶宝货所聚”的金山银库,却在掠夺之后,将对唐朝的满腔愤恨发泄到广州城上。
史载,广州“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黄巢四面纵火,大肆焚烧,使广州遭受自东汉末年以来最严重的灾祸,同时,大批居住在蕃坊的蕃客也被黄巢屠杀。《中国印度见闻录》说,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徒等,总共有12万人死于这场劫难。
由于黄巢手下大都是北方人,南下后水土不服,疫病大发,黄巢只好放弃广州,再次挥军北上,攻打唐朝都城长安。但就是黄巢在广州短短停留一个月期间,广州至阿拉伯的通航被切断,听说黄巢大肆屠杀蕃客后,直到唐朝灭亡(907年),外国船舶都不敢来广州了。
五代十国时,割据广州的南汉政权在国内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建蕃坊,再度开海,才修补了黄巢起义留下的创伤。
《南汉书》声称,诸国之中当属南汉富甲一方,“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南汉君主虽然暴虐,却支持宽松的营商环境,广州远离北方的军事打击,故而民安物阜,经济繁荣。
在此后以海上贸易闻名世界的宋元时代,广州城再度走向复兴,但也存在一条隐秘的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