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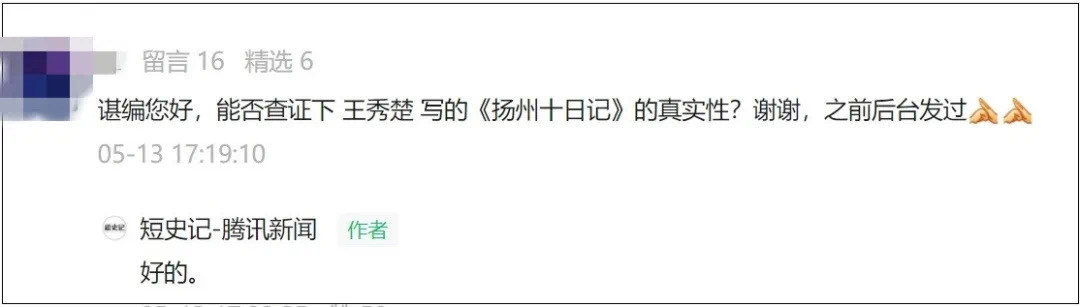
《扬州十日记》记载了清军入关对扬州民众的残酷屠戮。该书全文约八千字。作者王秀楚当时身在扬州(有说法称他是史可法的幕僚),亲身经历了这一惨剧,遂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五的所见所闻。因日记共十天,故名《扬州十日记》。关于大屠杀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日记的前五天。这五天字数约占到了日记字数的八成,主体内容是王秀楚与家人竭尽全力躲避屠刀却徒劳无功的悲惨经历。当大屠杀结束时,王秀楚失去了半数以上的亲人,“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外姨又不复论”。该书在清代属于禁书,相当长一段时期只在民间秘密流传,并无刻本。1998年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是“依据各种四库禁毁书目的著录”来做的一场典籍还原工程,其中就有《扬州十日记》。该《丛刊》收录了一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清钞本,其面貌见下图。为了躲避文字狱,该钞本中没有留下关于抄写者的任何资料,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抄写于哪个年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扬州十日记》自写成后,在民间一直有秘密流传。到了文网略宽的道光、咸丰年间,虽然市面上仍见不到刻本,但部分读书人已敢于在诗词文章中蜻蜓点水式地提及这本书。比如,吴清鹏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科举探花,主要活跃于道光时代,著有《吴氏一家稿 笏庵诗》。该书正式刊刻于咸丰五年(1855年),其中收有诗句“读图我亦为泪下,十日之记同一酸”——这里的“图”指的是“扬州史氏家藏国初鼎革时张孺人殉节画卷”,也就是一幅描写女性在明末清初扬州大屠杀中不愿受辱而自杀的画作。作者在诗后留有注释称:“图与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正合,即一家可知当日之事矣”——画作描述的内容与王秀楚《扬州十日记》的记载完全吻合,由一家人的遭遇可以管窥当日的整个大屠杀。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另一位文人徐鼒,也在其著作《小腆纪年附考》中提到了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徐写道:“予读王氏《扬州十日记》,言可法抑万里长城之黄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杰,至谓坏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此盖书生率意妄语,无足论也。”
意思是说他读到了一本由“王氏”撰写的《扬州十日记》,里面批评南明大臣史可法,说他用人大有问题,说败坏南明天下者正是史可法(史可法字道邻)。徐觉得这是胡说八道,是书生之见。《小腆纪年附考》有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刻本,其写作时间肯定要更早一些。我们之所以能够认定徐鼒读到的《扬州十日记》就是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是因为《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的清钞本《扬州十日记》中,确实有“坏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这样一段话(见下图)。♦ 左: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右:清钞本《扬州十日记》晚清多事,内有太平天国之变,外有列强不断以新秩序冲击清帝国的旧体制,清廷已腾不出手来制造文字狱,《扬州十日记》的传播渐广。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为回答学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这个问题,他特意撰写了一篇《书目问答》,给学生开列了两千余部图书。其中提到“明季稗史十六种”,里面赫然就有《扬州十日记》。当然,我们不能据此便认定张之洞读过这本禁书,毕竟张是一省学政,未必会亲自殚精竭虑去给学生开列书单,这种事有可能会交给幕僚来做。只能说,这份书单显示,张之洞自己或者他身边幕僚当中,必有人读过《扬州十日记》,且希望将该书推荐给四川的学子。《扬州十日记》被正式刊刻并广泛传播,是晚清最后二十年间才发生的事情。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派遣弟子梁启超等人入湘,与湘省知识分子谭嗣同等人合作,谋划以“保中国不保大清”为宗旨的“湘省自立”,便曾“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也很重视这本书的传播。为了扩大受众面,南社知识分子陈去病将《扬州十日记》绘制成图画本,林白水与刘师培等则在报纸上连载该书的白话版。了解了《扬州十日记》的这些流传经过,自然就可以知道,坊间传言称《扬州十日计》是晚清革命党人编出来的宣传资料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作为一段沉痛的历史记忆,《扬州十日记》一直顽强地在民间悄悄流转,只不过到了清末才因缘际会被革命党人重新发掘阐释,从少数人的历史记忆变成了全民族的历史记忆。从学术立场对《扬州十日记》进行质疑的经典文章,是张德芳的《<扬州十日记>辩误》。张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王秀楚在“五月初二日”的日记里写道:“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张德芳认为,八十余万人遇难的数据是不可信的。因为当时的扬州并不是一个拥有八十万人口的城市,周边地区百姓涌入城内的数量也有限;且《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兵屠城五天后放赈,拿出数千石大米,结果“转瞬一空”,也显示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百姓存活了下来。但张德芳并未否定《扬州十日记》是一份真实的史料。毕竟,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与史料中部分内容是否可信,乃是两码事。从前后文来看,王秀楚当时处在一种朝不保夕的逃命状态,自无可能亲自去“查焚尸簿”,所谓寺院的焚尸簿上记载焚烧了八十余万具尸体这个数据,只能是他道听途说所得。在天愁地惨的血腥杀戮中,陷入绝望的人们将某个数据越传越大是很常见的事情。就笔者的有限所见,明确全盘否定《扬州十日记》史料价值者,只有金宝森1989年发表在《满族研究》中的《<扬州十日记>证讹》一文。据《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介绍,该文作者乃“镶黄旗满洲人,兴祖直皇帝位下第三子索长阿之后裔。按清室划分属觉罗。”金宝森在文章中提出了如下几点主要质疑:(1)扬州并未形成南明和清两军的主战场。(2)对扬州府城人口密度的估算,可以证实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3)清军可能投入扬州战役的兵力只有“约二万余骑”。(4)清军在入关之初“执法较严”,多尔衮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是不会允许多铎采取屠城的野蛮行为的”。(5)“不足三万人的清军,要在五六天内,手刃八十万余人”是做不到的。(6)扬州所有的僧人“全部出动去运输集中如此多的尸体,也是不可能的。”金的这些质疑,仍主要围绕“八十万”这个数字而展开。很明显,这是抓错了重点。如前文所言,王秀楚作为一个满世界逃命之人,有怀孕的妻子和被清军砍伤的兄长要照顾,本就不可能掌握清军的具体屠杀数据,他载入日记的数据只能是听闻自其它难民——它不反应真实的蒙难者数量,反应的是民众在大屠杀中遭遇的空前恐慌。认识到这个数据的本质并不困难,有经验的治史者既不会轻信这类数据,也不会因这类数据不可信而否决整篇史料——相反,如果王秀楚提供了一份相当精确的大屠杀数据,那才是需要细究的问题,必须追问他为何能够得到此类数据。其实,《扬州十日记》的核心史料价值不在“八十万”这个数据,而在王秀楚记录的自己与家人在屠刀下宛转求生的详尽过程。比如,他见到清军“拥妇女杂行”后,转头便对自己的妻子说:“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妻子允诺。他担忧自己居住的房屋周边都是富人,会成为重点抢掠对象,于是与长兄一起带着家眷集体转移至二哥家中,只因二哥所居之地乃是城内的贫民区。在二哥家中避难时,众人白天皆“乘高升屋躲避”,也就是爬到屋顶的天沟里藏起来,以免被发现。后来天沟被人发现,王秀楚兄弟几人先是抛妻弃子惊惶下窜,后又觉得仅四人为伍若遇上悍兵必然被杀,“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又选择跑回了被清军控制的五六十人的大群体中。这类细节与心态,只有真实的大屠杀幸存者才能写得出来。此外,《扬州十日记》的文本也足证其写作并无反清复明之类的政治目的。近代史学者孔祥吉就此总结了三点,认定“此日记当系真作”。第一点,日记“对史可法所部入城后骚扰敲诈, 不胜其烦”,记录了扬州城内的明军大敌当前仍纵欢取乐、搜刮民众、要名妓作陪等劣迹。其次,日记并非只描述清军暴行,“对于明末扬州地方之不良习气, 以及民族败类之丑恶行为, 多有揭示”,这些都不是反清复明宣传品该有的内容。再次,日记作者也将自己人格里的丑陋暴露了出来。如记载清军大举进入扬州之前, 城内已有人组织欢迎,作者本人也主动“改易服色,引领而待”。孔祥吉认为,这种“只是为了苟活, 别无所求”的麻木不仁之人,“是不可能伪造日记的”。其实,从日记本身来看,王秀楚对自己的麻木不仁是没有感知的。比如他曾要求妻子一旦被抓就要自尽;从天沟跳下逃跑时也完全不顾妻儿;后来与妻子重逢一起逃亡,又把妻子留在一间有众多妇女避难的草房里听天由命;等到自己走投无路,又返回草房乞求众妇女让自己藏进草堆底部,靠着“众妇拥卧其上”避过了搜捕;再后来,妻子被一“狠卒”劫持以刀背乱打血溅衣裳,王秀楚也只是“远躲草中,若为不与者”,仿佛不认识险些被打死的是自己的妻子,并在日记里以妻子的告诫“倘遇不幸,吾必死,不可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子”做自我安慰。可是,另一方面,王秀楚又对那些挣扎求生的女性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比如他见到有女性为了活命逢迎占领者,便在日记里痛骂她们“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浑然忘了自己并不曾真正救助过自己的妻子,还曾在清军入城之前“改易服色”,欲加入到热烈欢迎的队伍当中。这种对麻木不仁的不自知,绝非政治宣传品所能轻易伪造。在日记的末尾,王秀楚写了一段话,解释自己为何要以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写下《扬州十日记》:“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惊惕焉耳!”
他希望后世之人读到这篇日记时,要多反省反省,不要暴殄了那得之不易的太平,不要暴殄了那极为珍贵的“无事之乐”。(来源:腾讯新闻)
[1]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2]《四库禁毁书丛刊 史部 72》,第189-199页。[3]吴清鹏:《吴氏一家稿 笏庵诗》,咸丰五年刻本。[5]朱新屋:《<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一个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分析》,《近代史学刊》第13辑。[6]金宝森:《<扬州十日记>证讹》,《满族研究》1989年第4期。[7]张德芳:《<扬州十日记>辩误》,《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8]孔祥吉:《我与清人日记研究》,《博览群书》2008年第5期[9]戴辉、杨绪敏:《明清鼎革之际杂史编纂探研》,《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