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改变北京大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会面之前,蔡元培与陈独秀已经是老相识了。
他们一起造过炸弹。
清末,为刺杀满清大员,蔡元培与朋友们组织了暗杀团。蔡元培后来谈起这段履历时说:“36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蔡元培在上海租了个房子,亲手制造炸弹,他找来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找来了陈独秀。
据陈独秀回忆,他由安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跟着试验炸药。
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救国图存的探索中,这些读孔孟之道长大的书生都甘于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献身,诠释爱国青年之血性。
十多年后,1917年,在一个黎明之前的觉醒年代,这两位大师再次相遇。
▲北京大学第二届文科哲学门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右4蔡元培,右3陈独秀
正如鲁迅先生在《小杂感》中所写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便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时局。
几经风雨,几经磨难,到了1915年,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革命党人,已经历清帝逊位、二次革命等走马灯似的政治大戏,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却依旧看不到国家的未来,心好累。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在华利益重新洗牌。日本以协约国之名参战,实则趁火打劫,派兵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抢占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野心勃勃地想要独占中国。
这一年,陈独秀正处于人生低谷。此前,他因参与二次革命失败,一度被袁世凯的亲信列为通缉犯,不得不告别妻儿,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与胡汉民、章士钊等办起了《甲寅》杂志,抨击时政。这本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还有时年26岁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等爱国青年。
陈独秀与李大钊最初相识,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国问题的争论,可谓“不打不相识”。
在该刊中,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的名字发表了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批评国人漠视国事,不理解国家为何物。
陈独秀不吐不快,如一个愤青,对现实社会发泄不满,说西方人所讲的爱国,与中国人的忠君爱国“名同而实不同”。欧美人视国家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当时的中国人,却仍将国家当做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优乐。”
辛亥革命革了个寂寞,执政者以旧的方式执政,民众也遵守旧的思想观念,仍然以草民自居。这才有了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复辟闹剧,以及一些人高喊奉孔教为“国教”的落后思想。
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流露出革命失败后的彷徨苦闷,也在苦苦追寻新道路。但是,文中痛陈国家极端黑暗,毫无可爱之处,甚至故作危言,说与其如此,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不少中国留日学生对这种言论感到不太舒服。
于是,李大钊作为代表,在1915年8月的《甲寅》第1卷第8号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对陈独秀的消极态度进行了温和的批判,说其“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
李大钊这篇文章的意思是,既然您觉得国家不可爱,那我们更要改变旧秩序,改造国民性,唤醒国人的自觉心呀。
兴许是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启发,陈独秀产生了新的觉悟。一个月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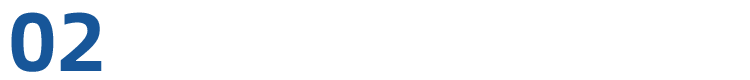
1915年6月,陈独秀妻子高君曼生病咳血,陈独秀接到好友汪孟邹的来信后迅速回国,与妻儿居住于上海法租界。
高君曼是陈独秀续弦之妻,也是他元配夫人高晓岚的妹妹。这段有违世俗的婚姻难免让人说闲话,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也因此跟他们爸爸闹别扭,多年来缺乏联系,常年在外漂泊。
这俩年轻人跟他们父亲陈独秀一样倔强,宁肯出去当打工人,睡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也不肯接受家里的经济援助。
作为继母兼姨母的高君曼于心不忍,托人说情,让陈独秀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当时,陈延年兄弟信仰的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攒够钱,到上海求学,考取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并在之后赴法勤工俭学。
据见过陈延年、陈乔年的人回忆说,这两兄弟的模样就像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多年后回国,他们改变了思想,终于成为父亲陈独秀的同志,却走向悲壮的结局。
1915年回国后,面对民族危亡的困局,陈独秀渐渐从意志消沉中走出。
陈独秀认为,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运动,仿造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全民带来新思想、新文化,让他办个八年十年杂志,一定能使全国思想改观。陈独秀没钱,只好将这一想法告诉私交甚密的安徽老乡汪孟邹。
汪孟邹当时是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欣然同意好友的创业想法,并由他出面介绍,拉来了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给陈独秀投资,议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
经过多方奔走筹备,1915年夏天,这本叫《青年杂志》的刊物横空出世,最初的发行量只有1000册。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
因为《青年杂志》跟当时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有些雷同,所以到了第二卷时,《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树立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热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责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陈独秀将希望寄托于那个年代的“后浪”身上,希望青年自觉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进而对青年提出了提出六个标准: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从此以后,陈独秀联合志同道合的战友,为了唤醒民众,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中最落后、保守、反动的愚昧迷信、旧道德与旧文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将改变一个时代。
李大钊经过与陈独秀的爱国辩论后,也成了陈的好友。听到陈独秀的呐喊声后,李大钊也在次年回国,成为其有力支持者,于《新青年》发表了《青年》一文,洋洋洒洒8000多字,用115个“青春”呼唤青年觉醒,读来令人激情澎湃。其中写道: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在新旧思想的对垒中,《新青年》面对着来自保守者的巨大压力。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宁可断头流血,也毫不退缩,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Democracy,民主)、塞(Science,科学)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塞两先生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
1917年,注定是《新青年》的里程碑之年。正是在这一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与《新青年》北上。
据当时北大部分教师的回忆录记载,1916 年,陈独秀为办《新青年》跑到北京募款,正好北大要引进人才,缺一名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
经过友人引荐,蔡元培翻阅了《新青年》后,决定聘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陈独秀起初不答应,他对其他朋友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说,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更何况,陈独秀还要主编《新青年》,事务繁忙。
蔡元培亲自登门拜访,告诉陈独秀,没有头衔不碍事,我们不搞论资排辈,还请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来办。陈独秀只好答应试干三个月,如果胜任就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回上海。
虽然一起做过炸弹,但蔡元培的办学能力更能让陈独秀放心。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期间,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他认为,在现代国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第一原则,在大学更是如此,若大学里没有思想自由,就算不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陈独秀答应了老战友的邀请,这也意味着,这场空前的思想运动从此将与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相连,蔡元培实际上成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保护者。
这一年,在张勋复辟时南避上海的李大钊,也应北京大学之聘请北上,担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同年8月,一位青年学者在日记本中写下《伊利亚特》第18章第125行的译文,“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之后从美国起程归国,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
他是胡适。
到了北大后,这名27岁的安徽人成为全校最年轻、薪水最高(月薪280元)的教授之一。他与51岁的蔡元培、39岁的陈独秀都是卯年生人,组成了“三只兔子闹北大”的文化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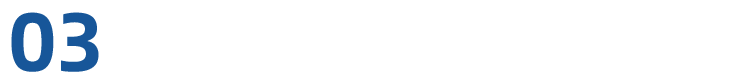
胡适认为,有三本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正如胡适所言,《时务报》代表戊戌变法时期,《新民丛报》代表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对政体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时代,而《新青年》,代表着新文化运动。
这只“兔子”,有一颗文学革命的心。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给朋友写信说:“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观!”
在胡适的回忆中,他发起文学革命的起因,出于留学期间的一段经历。
作为一名庚子赔款生,少年胡适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而当时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书记先生受了传教士的影响,经常利用机会印一些传单给老外做宣传,大致内容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等。
有一天,胡适又一次看到了这些宣传语,说什么“欲求教育普及,非用字母不可”。胡适一时动了气,写一封信去骂对方,说:“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
可见,胡适反对盲目的全盘西化。他认为,文言文是半死之文字,要让中国文字“活”过来,就要普及白话文。
1916年,经过安徽同乡汪孟邹牵线,胡适与陈独秀开始书信往来,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胡适说,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人,也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有他这样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推行者,不久就要形成一个“大力的运动”。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有趣的是,这篇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文章却是用文言文写的。
在收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作为主编的陈独秀也挥动如椽巨笔,立即写下了《文学革命论》,与《新青年》同人一同推动“白话文为文学正宗”。正是有了这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普罗大众都能运用自如的白话文。
这一时期,胡适与思想保守的卫道士之间发生了不少趣事。
即便在后来的特殊年代都坚持写文言文的章士钊,在担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期间,反对白话文,提倡旧道德。
有一次,胡适与章士钊一起照相。章士钊特意在照片上题了一段白话文送给胡适,说:
“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见状,也特意回了一首旧体诗,对章士钊表示尊重,以和为贵:“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当时,北大还有不少章太炎的门生,如黄侃,也反对白话文运动。
黄侃故意调侃胡适,说:“胡适之先生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我看您未必出于真心。”
胡适一听纳闷了,说,黄先生此话怎讲?
黄侃笑道:“如果胡先生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往哪里去’才对呀!”这些大师如果去吐槽大会,也没其他嘉宾什么事了。
胡适对这些刁难一一进行反击。有一个老北大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是有一次上课,一个同学激愤地反对白话文:“白话文不够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也多。”
胡适举了个例子,说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要复电拒绝,不妨请同学们用文言文来写一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数,还是文言文更简洁?
学生们都跃跃欲试,最后选出字数最短的一个答案,共12字:“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笑了,说我的白话电报,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并非孤军奋战。
当时,《新青年》的另外一名著名编辑刘半农在致同事钱玄同的信中说:“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与刘半农,是《新青年》的四大台柱。
1917年,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农也接到蔡元培的邀请,成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正是蔡元培不拘一格选人才,才有北大兼容并包的氛围。
刘半农在《新青年》出版第2卷时加入编辑部,与陈独秀相见恨晚,他翻译了大量世界名著,写了不少反映穷苦人民的新诗,批判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不公平现象,如他的第一首白话诗《相隔一层纸》,写一个屋子里点着炉火,屋内的老爷吩咐人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隔着一层薄纸,屋子外却躺着个叫花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刘半农还有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创造了用来称呼女性的“她”字。
汉语中原本没有与英语的“she”相对应的字,刘半农在他所写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率先使用了“她”字,影响至今。
在编辑《新青年》第4卷第3号时,刘半农与钱玄同唱了一次双簧戏,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保守派的身份写文章对刘半农进行种种责难。刘半农自导自演,对“王敬轩”的责难一一批驳,嬉笑怒骂,跃然纸上。
这场辩论,被称为“现代中国报刊史上精彩的一笔”。现在媒体人玩的这一套,都是老前辈们玩剩下的,依旧屡试不爽。
自称为《新青年》摇旗呐喊一小卒的钱玄同,是新学与旧学的“混血儿”,他与黄侃等人同为古文学家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又留学日本,接受过新式教育,坚决地反帝制、反复古。钱玄同还有个了不起的儿子,即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钱玄同比胡适激进得多。他有不少惊世之语,其中一句是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
因此,在1927年钱玄同40岁生日之前,他的几个朋友特地在报刊上发了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上面全是讣告、挽联之类的稿子,老搭档刘半农更是写了一篇《祭玄同文》。实际上,钱玄同当时身体还好着呢。
鲜为人知的是,钱玄同在当《新青年》编辑时,还催生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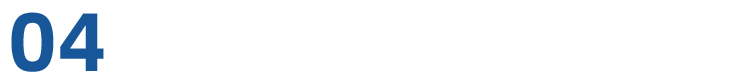
1912年,公务员周树人随教育部迁北京,居住于绍兴会馆,最初几年的生活苦闷而消沉,书倒是买了几百册。周树人无聊时就枯坐书房,只做两件事,一件事是誊抄古碑,另一件也是誊抄古碑。
周树人在北京的数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1917年,张勋复辟闹剧收场,各路军阀依然混战不休。
山河破碎之际,忧国忧民的周树人躲进自己的小屋,深埋故纸堆中。对于周树人消极遁世的生活态度,好友钱玄同很不赞成。
有一夜,钱玄同前去周树人家中,翻着那些古碑、古籍的抄本,说:“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周树人坦然回答:“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钱玄同突然认真地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懂钱玄同的意思,他们正在办《新青年》,也许是感到寂寞了,想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
可周树人还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而且从昏睡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次严肃的长谈,后来被周树人写入短篇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
周树人再次翻开书,悲凉地审视那个残破的时代,他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仰天长叹:“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振臂高呼:“救救孩子!”
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周树人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如同一声惊雷,响彻中国。
这也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陈独秀读完这篇小说,由衷地发出赞叹:“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自《狂人日记》起,鲁迅一共在《新青年》发表作品50余篇,他与同人们向青年传递了民主、科学、独立的思想与新文化观念,也将底层民众的心声告知世人。
鲁迅说,《新青年》的催稿就是他创作的动力,“《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但他说了,自己也是个拖延症患者。

▲鲁迅(1881-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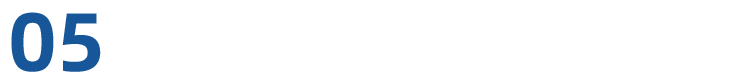
庶民的胜利
到北大任职后,李大钊结束颠沛流离的日子,生活总算得到改善。
当时,北大教职员的待遇十分优厚,李大钊月薪为140元(后来涨到200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供养三十口人。李大钊却将这笔钱用于学术研究与革命运动,以及资助北大的贫困学生,自己依旧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
那几年,每到开学季,北大很多贫困学生就会收到一个名曰“无名氏”寄来的汇款,直到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个“无名氏”是李大钊。
哲学系的学生刘仁静就得到过李大钊的资助。李大钊对北大的相关部门说:“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
现在,还有一张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留存:“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俄国革命起初并没有引起李大钊的注意。
在他眼中,俄国人直到二月革命时也不过是在走中国人的老路,而非后来说的,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
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送来了李大钊新的思想,并将彻底改变此后100年的历史。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觉醒年代,翻开了新的篇章。

▲李大钊(1889-1927)
《新青年》的“新青年”们,没有一个人空喊口号,他们都在为救亡图存而艰苦探索。
李大钊到农村去,到车间去,亲身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他告诉青年:“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为德先生、赛先生与新文学摇旗呐喊,之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胡适提倡白话文,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与语言的基础。
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笔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闰土等人物,就是现实世界的缩影。
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22年休刊,《新青年》走过了7个年头,之后在1926年7月终刊,共出版63册。
《新青年》吹响了青年为救亡图存而解放思想的号角,培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一位姓毛的学生,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发表了文章《体育之研究》,全文提倡“体育兴国”,充满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生观:“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后来说起陈独秀时,他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从1919年开始,蒋介石也对《新青年》情有独钟,从目前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直到1926年他率领北伐军北伐,都没有放下这本杂志。
无私无畏的李大钊,于1927年被张作霖送上绞刑台,临终前神色未变,从容赴死。牺牲后,他家没钱安葬,社会各界发起募捐,进行公葬。
据说,连政见相左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 块大洋。钱玄同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的困窘,至死都拖着病体为李大钊家人筹钱。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放下与父亲陈独秀的恩怨,回国参加革命。
1927年6月,陈延年秘密转移时,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父亲的友人汪孟邹营救。汪孟邹找到了胡适,胡适便请陈延年的老师吴稚晖帮忙。但因陈延年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来转变了思想,而且陈独秀还骂过吴稚晖为老狗,吴对此耿耿于怀,不愿出手相救,反而使陈延年的身份暴露。
7月4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刑场,因不愿下跪,站着被刽子手乱刀砍死。直到此时,汪孟邹和胡适才知道求错了人,为此抱憾终身。
次年,陈乔年也遇害,兄弟二人一年之内相继被捕,英勇就义。
那时候的青年,心怀理想,并为此宁死不屈。
作为“新青年”之一的鲁迅,曾在《热风·随感录》中如此寄语年轻人: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年代。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如果喜欢,顺手点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星出版社,2014耿云志:《<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回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06期桑兵:《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05期张家康:《<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传记文学2017年第02期郝思斯:《从<觉醒年代>看觉醒》,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