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现代汉语中还没有“体育”一词。而且,当这个词刚从日本引入时,当梁启超和其他人在1902年使用这个词时,它更多是指个人卫生和总体健康状况,而非身体运动。还要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体育”一词才成为今天的意思。1894年6月23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成立大会在巴黎举行。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1894—1895年)的惨败。这次惨败使中国的大部分精英相信,只有放弃传统的帝国身份,建立民族国家,才能生存。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适者生存”等理念,在思想上为中国人接受现代体育运动做好准备。正在寻找国家出路的中国精英分子,将现代体育运动与奥运会,同他们的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结合了起来。中国人不仅要参加体育竞技,也把参加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看作救国大计的一部分。不过,将中国人引向奥运赛场的,不是国际奥委会,而是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1895年,青年会干事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来到中国。当时,中国人刚刚败于日本人之手,正苦寻建设国家和适应国际新形势的出路。来会理是美国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的新毕业生。他到了天津后,开始孜孜不倦在中国推广现代体育运动。1899年,上海分会成立,到1922年,整个中国已经有22个分会。它主要通过资助比赛、报道和演讲会,来成功推广现代体育运动。正是在青年会的主导下,中国在1910年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10年运动会的官员和裁判主要是外国人,大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到1923年日本远东运动会举行时,中国代表团的领队还是格雷(J.H.Gray,青年会体育培训部的主任),他代表中国队在大会上发了言。♦ 《时报》1910年10月16日关于第一次“中国全国运动会”的报道在青年会的资助下,许多后来成为中国体育界领导的人,获得了到海外留学的机会,包括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还有张伯苓、董守义、郝更生和马约翰等。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努力恢复国家主权,青年会的影响才逐渐式微。
当然了,青年会只是众多对中国体育发展有影响的国际组织中的一个。日本也曾做过贡献。明治维新后,日本将西方流行的体育运动,例如体操、剑术、射击、骑马和滑雪等引入国内。1903年,清政府尝试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规定所有学校都要设体育课,采用了深受西方影响的日本课程。中国人采纳了现代体育运动后,便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对中国人来说,体育运动是一条通向民族复兴并实现与他国平起平坐的大道,是自己的国家成为受尊重的强国的方法。体育运动可以表述中国人的国家主义、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感,甚至作为中国人的意义。中国人认识和理解这一赛事,正是通过青年会。早在1907年,青年会的官员就有系统地向中国公众介绍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和即将举行的伦敦奥运会。据青年会的杂志《天津青年》所载,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在1907年10月24日的一次活动上,做过关于奥林匹克与中国的生动演讲。他介绍了奥运会在西方的历史,表达了希望中国有一天能派出奥运代表团的心愿。他建议中国从美国聘请奥运获奖选手当教练,为参加奥运做准备。张伯苓可能是第一个认真谈及奥运会并表达中国人参赛愿望的中国籍人士。《天津青年》在1908年5月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也透露了类似的情结。作者写到,尽管没有人知道中国要等多久才能参加奥运会,但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在将来不仅能参加而且还能举办奥运会,中国人有责任为此做好准备。青年会在1908年组织的一场演说,则提出了三个问题:
(1)中国什么时候能派出一个赢奖牌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3)中国什么时候才能邀请世界各国到北京参加奥运会?那时,亚洲的体育比赛总体水平较低。即使日本,也是直到1912年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成绩也不尽如人意。国际奥委会的第一个日本委员嘉纳治五郎,是在1909年国际奥委会柏林会议上当选的。♦ 天津青年会1905年举办“第三次运动大会”的章程为了缩小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体育上的距离,并为将来中国参加奥运会做准备,一些中国人积极张罗,推动了远东体育协会的建立。外交家伍廷芳在1915年担任该协会的主席。远东体育协会承办两年一届的远东运动会。美国人在远东体育协会的建立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远东运动会的基地菲律宾,在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第一届运动会于1913年在马尼拉举办,第二届运动会于1915年在上海举办。香港代表团曾多年代表中国参赛,其中以香港足球队地位最高,为中国赢得了好几次冠军。1934年,日本为了将中国境内的伪满洲国合法化,提出让伪满洲国作为成员参加远东运动会。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退出了大会。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地区性体育赛事,以中国的退出而告终。根据国际奥委会在1914年6月15—23日巴黎会议的记录,在萨拉热窝事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国家一起,是被获准参加当时定在1916年柏林举办的奥运会的33个国家之一。大战过后,国际奥委会在1919年决定,只有成员国才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比赛,只有国家奥委会才能派运动员参赛。也许是受到新规定的激发并得到青年会的资助,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1年成立,并在1922年获得国际奥委会认可为中国奥委会。同在1922年,王正廷成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中国委员,也是第二位来自亚洲的委员。这次参赛与其说是出于对这项赛事的热爱,不如说是决心进行国际化。原本,在1932年5月,中国的官方体育机构因为缺乏资金,已决定不参加第10届奥运会,计划只派沈嗣良作为观察员出席,就像1928年派出宋如海一样。根据沈嗣良的回忆,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拒绝为他的行程给予资助。但就在1932年6月12日,上海的知名报纸《申报》报道伪满洲国将派出运动员刘长春和于希渭参加奥运比赛,以达到日本人在国际上将其合法化的目的。刘长春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短跑名将,日本甚至声称洛杉矶组委会已经接受了这个计划。上述报道后来证明为误报。在史汀生主义的指导下,联合国不会承认伪满洲国。洛杉矶组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也拒绝让傀儡政府派代表团。但日本政府计划通过派出两名中国运动员,来实现伪满洲国参赛,这一目的却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舆论得知这一计划之后大为震怒。面对骚动,中国体育组织终于决定参加奥运会,以中国的名义派刘长春和于希渭出赛。刘长春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就移居到北平,他发表声明,宣称自己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绝不会代表傀儡政权参赛。最后也只有他能够成行,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因为于希渭很快就被日本人软禁在家,以防他代表中国出席比赛。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委员,一听到中国准备参加奥运会的消息,就立刻行动。因为向洛杉矶组委会报名的最后限期6月18日已经过了。6月26日,组委会接受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申请。中国社会精英在完成参赛的书面工作之后,开展了一场向大众募捐的活动。东北军事长官张学良捐出八千元,北平市长周达文给了刘长春一套新制服。在中国1932年参加奥运会的过程中,还有几位重要人物发挥了关键作用,较为显要的有天津市前市长张学铭、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和郝更生。张伯苓、王正廷等名流,也支持中国派运动员到洛杉矶代表国家参赛。7月8日,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一起离开上海奔赴美国。在启程前的送别仪式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主席王正廷把中国国旗和几面中华体协的旗帜交给刘长春,提醒他:因为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比赛,所有的目光都会投到他身上,期待他能为中国赢得荣誉。王正廷还告诉刘长春: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让中国的旗帜与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飘扬,这是本次参赛最具象征意味的地方。当刘长春登上去洛杉矶的船时,人们进行了一个特别的庆祝仪式,三呼国家万岁以送他们的英雄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刘长春在7月29日抵达洛杉矶,正好是开幕式的前一天。奥运会官方报道描绘刘长春是“代表四亿人民的孤单代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来自中国和哥伦比亚的一人代表团获得了众多掌声。中国运动员有四位官员随同,而哥伦比亚的乔治·佩里(Jorge Perry)则是孤身一人。”一位观察员评论道:“中国!有一位男孩得到我的欢呼,就只有他自己和几位教练。”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短跑比赛,但连前六名也没能进去。9月16日他回到中国时,表达了没有赢得奖牌、没能为国争光的失望心情。1932年奥运会常常会被世界史尤其是美国史所掩盖,因为当时世界正面临经济大危机。即便如此,刘长春的参赛,对奥运会和对中国人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正如郝更生在刘赴洛杉矶前的声明中所讲解的,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有四个宗旨:(1)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
(2)有一个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3)促进世界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4)让中国从世界运动大赛中得到观摩学习的机会。
再者,刘长春可以在大会上向人们讲述日本在他的家乡东北的侵略行为,为中国在世界赢得公众的支持。刘长春在洛杉矶期间,频频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他参赛的重要之处,也在于将奥运会的经验带回中国,他在奥运会期间坚持写下的日记,后来刊登在中国一份报纸上。刘长春也为自己在中国国际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自豪。他后来写道,虽然没有赢得任何奖牌,但他的“初衷是要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此行“达到了这个目的”。沈嗣良投入了很多精力到1932年奥运会中,他写道:“当第十届世界运动会在碌衫矶(洛杉矶)举行的时候,会场里破天荒第一遭的忽然发现了大中华民国的国旗和代表,这是何等足以使全世界注意而称道的一件事!这是何等足以使国人欣慰自豪而兴奋的一件事!……我国的参加,使中华民国的国旗,在会场中占着一个地位,确乎鼓起大会无限的精神,同时也使全世界注意到老大的中国,还保存着少年的精神,要在运动界里与列强角逐,绝没有自弃的观念和任人宰割的可能。”
中国参加1932年奥运会,是中国进入国际舞台的一个转折点,再也没人能将时间转回到早前与外界隔绝的日子。但还是有一些中国人为刘长春的表现感到失望,主张中国应该放弃参加西方的运动会。例如,天津报纸《大公报》的一篇社评提议中国人与其去参加奥运会,不如在“土体育”上多下功夫。作者还说,西方体育运动不适合中国这样的穷国,中国人无法在世界比赛中胜出。这种失败主义社评的写法,真实映照出了中国人取胜的热望,也表明了中国人总体上有多认真对待奥运赛事。通过1932年奥运会,大部分关心体育的中国人,对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水平有了现实的认识,不再期待他们在奖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取而代之,他们把眼光放在外交收获上——表达他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得到世界社会认可的机会。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期待与奥林匹克目标相吻合,顾拜旦说过:“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获胜,而是奋力拼搏。”中国人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更大的热潮。政府对柏林奥运会的强烈兴趣,源于其企图积极地通过体育来参与国际事务,这次派出了一个更大的代表团,共有69名中国运动员参赛,政府支付代表团的全部费用。有趣的是,许多代表团成员来自香港,例如足球队的22名球员中就有17个是香港人。除了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代表团,中国还派出42人的研学团体,到柏林和其他欧洲城市研究学习欧洲的体育。这个团体由郝更生带领,包括9位政府官员、23位高等学府的代表、9位来自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学员和1位军事代表。他们的行程共40余天,游历了德国、瑞典、意大利、丹麦、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尽管这次中国运动员团队要大很多,而且以精彩的武术表演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们还是没有在柏林奥运会上赢到奖牌。许多中国人为在篮球赛中败给日本队而沮丧,中国媒体声称中国可以败给其他任何队伍,但不能败给侵略中国的日本。中国篮球队的表现,在中国国内受到了强烈批评。“我国参加本届世运会失败,不能归咎少数选手技术不良,是与全国民体育有关,此不仅在运动队中是荣辱得失问题,而且是中国整个民族在体力上表现之强弱问题,亦即为与民族存亡有关的问题。我们要复兴民族,固必要增加人口,但根本上还要先求人民健康增进,欲人民健康增进,唯有促进国民体育之发展。”
也有部分中国人辩称,奖牌不是唯一的目标。比如沈嗣良在奥运会结束后评论说:大会“中国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在大街上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很明显地看到。我们代表团的英姿,迈着整齐的步伐,和其他人一样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参加比赛,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宣传。至少其他人现在知道了,我们是被看重的一个国家。”他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国家而赢得国际认同的成就,对于我们来说价值千金,远远超过我们在旅途中所花费[的金钱]……我相信[运动员们]所完成的,甚于数为大使在数年间所取得的成就。”
政府的官方报道也指出,中国参与奥运会的主要目标在于“鼓舞国民民族精神,增高国际地位”。通过参加1932年和1936年的奥运会,中国人希望向世界展示一张新的面孔,一个新的身份形象——还有对日本侵略的蔑视。1948年,国内战事激烈,中国参加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
在奖牌方面,中国代表团再次空手而回。当时的情况特别艰难:代表团资金短缺,无法像其他代表团一样住在奥运村,最后只得住到一所小学里,须自己烹煮食物。代表团的回程票也得靠团长王正廷个人张罗,好在最后幸运地借钱买到了。在这样的困境下,实现参赛已是最重要的成果。(来源:腾讯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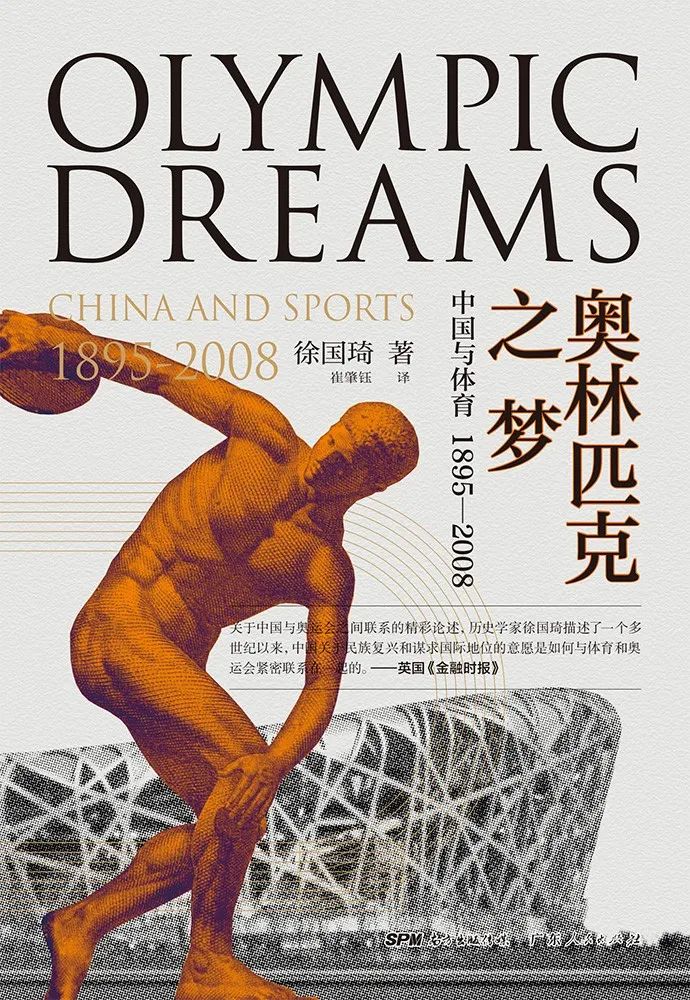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奥林匹克之梦》,徐国琦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已获出版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著有《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1895—2008》《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难问西东集》《美国外交政策史》《边缘人偶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