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 | 魏水华
头图 | 视觉中国
坊间流传着一个关于北京小吃的段子:一块北京烧饼掉路上。“啪”,一辆车碾过,没压碎,嵌进柏油马路里了。
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想把烧饼弄出来,但都失败了。最后,有位聪明人找来个工具,终于把北京烧饼撬了出来。
这个工具是北京油条。
客观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美食大国,作为首都的北京,确实没能担负起相应的地位。各种关于北京难吃的笑话,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No:1 壹
一个地区的饮食好不好吃,原因不外乎三点:食材物产、历史传承、烹饪技术。
国家首都是人才汇聚的地方,而人才的汇聚,必然会带来烹饪技术的进步。比如巴黎的法餐、东京的日料,即便不算是最顶尖,在本国也是上流水平。
但汇聚在伟大首都的人才和技术,似乎并没有拯救当地不堪的饮食。相比于中餐菜系川鲁粤淮扬的博大精深,食物到了北京,只能用“断崖式下跌”形容。
唯一的原因,是北京的食材物产和历史传承,实在朽木不可雕。

事实上,自建城起,北京本不是国家级文化和经济中心,作为汉地十八省的北部边疆,北京长期以来一直是区域核心而非国家标志。不管是战国的燕国、南北朝的前后燕、与宋并立的辽国和金国,本质上,这些建都于北京的国家,都是割据势力而非大一统王朝。五代时,北京为首的幽云十六州,甚至还被“儿皇帝”石敬瑭当作筹码割让,可见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眼里,北京连寸土必争的军事要冲都算不上,更谈不上经济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了。

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北京菜的底子就显得过分单薄。《史记》里的描写:“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当时北京市井里屠夫、刺客和音乐家们混杂,吃喝也没什么可说,当街酗酒而已。只拿两个字形容——“粗鄙”。
宋元以前,流传至今的一部分北京饮食,依然保存着这种粗鄙的习性。比如炸酱面,虽然增加了萝卜、黄瓜、豆芽等“菜码子”,但本质上,它就是黄豆酱拌面条。这种通过发酵豆类获取鲜味、节省盐的调料,虽然味道不错,但卖相确实不佳。北京人不是拿他做汤炒菜,化于无形,而是直接拌面条。优质中餐标准“色香味形”里的“形”这一项上可以直接打不及格。

比如炒肝儿,这种脱胎自中原地区胡辣汤的小吃,从外形和味道都颇有类似。但从前的北京人似乎不懂面筋面浆分离的工艺,也不懂以牛骨汤调味的诀窍,而是用不值钱的猪杂碎,加了酱油炒熟后勾芡复煮进行生硬地模仿。炒肝儿的味道见仁见智,但做法显然是简配版的胡辣汤。

再比如豆汁儿,这种制作粉皮粉条的下脚料发酵后,带着酸馊味道的浓稠汁水,在别处只能喂猪,但北京人却引以为本地美食之光。不管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大家齐刷刷捧着烫嘴的豆汁儿,配着咸菜大喝,如梁实秋所说,“不能喝豆汁儿的人算不得真正的北平人。”更重口味的,会直接拿发酵的豆渣炒来吃,北京人称为“炒麻豆腐”。炒的过程中还要加青韭、雪菜、羊尾巴油,又馊又咸又膻,但本地人乐此不疲,除了下饭,居然用来拌面吃。

相比于江浙地区精细的茶食、广粤地区洋派的酥点、川渝地区入味的红汤。北京饮食,在粗鄙的外观上,就能劝退一大群人。
No:2 贰
蒙元入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它改变了中国的走向,也改变了北京的命运。
因为四大汗国分裂、蒙哥汗在钓鱼城下暴毙、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等一系列偶然性因素,接受大规模汉化的忽必烈即位。他决定在自己蒙古大汗的头衔上,再增加一个称号:中国皇帝。并把国号改为汉字“元”。
同时,忽必烈放弃了成吉思汗的龙兴之地哈拉和林,转而寻找更汉族的城市定都。辽金的故地北京,成了忽必烈的首选。

对忽必烈来说,这是一块完美的地方:北京的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足以辐射中国内地;而北京的背后,穿过阴山山脉,又能及时回到蒙古人的草原故土,进可攻退可守:事实上,在被汉人推翻统治后,元朝皇帝的确安全地北归,还延续了三百多年北元国祚,只比后来的明朝少活十年。
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第一次被人为地分开。
自魏晋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就逐渐从开发过度的中原地区,向战乱较少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转移。这从汉族政权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的迁都路线就能看出端倪。衣食富足、社会发展程度高,让这些地区的人们在追求饮食细致和丰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京不在此列。


同样一条鱼,典型的江浙做法和北京做法
但神奇的是,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物产也不丰富的地方,却在元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一直作为中国的首都:燕王朱棣得国不正,放弃了朱元璋钦定的南京,以“天子守国门”的理由,选择自己的老巢北京;多尔衮入关,做出了和忽必烈一样进可攻退可守的决策,选择山海关内最近的大城市北京;北洋政府受禅自清帝,又为了远离国民政府的基本盘广东而选择北京;新中国选择北京,则更多地考虑了民族团结和历史沿革问题。
显然,北京的首都地位,来自于一连串的偶然性政治因素,饮食不好吃、物产不丰富这样的小问题,从不在开国领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No:3 叁
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但真正影响生活的时候,人总会想着改变。
深居北京的历代统治者们,从来没有放弃把这里变得更好吃的尝试:朱棣把在南京时最喜欢吃的挂炉烤鸭引进北京,成就了今天国菜的扛把子,更成就了南京烤鸭的江湖地位。

满清入关后,则为北京带来了满式风味的涮羊肉、萨其马。还引进了大量山东厨师充实御膳房,由此开启了鲁菜进京的历史,奠定了今天鲁菜作为北京菜的文化基础。

清中叶,爱下江南的乾隆帝又找来了大量江浙厨师,把淮扬菜带到了北京。仅苏州传奇厨师张东官一人,就为北京带来了苏造肉、苏造汤、苏造肘子、樱桃肉种种美味。

直到解放后,这种官方引进依然没有停止,一五计划期间,考虑到北京的服务业水平与首都地位不相称,周总理亲自安排上海的老正兴菜馆、美味斋饭庄、义利食品公司、浦五房南味肉食品店迁来北京。

但奇怪的是,所有饮食来到北京后,都会发生人设崩塌,比如精工细作的苏造肉,在北京流传百年后,居然走形成了一锅乱炖的卤煮。几乎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都认为,入味的烧腊要去广州吃、新鲜的涮羊肉和手把羊肉要去锡林郭勒草原上吃、正宗的葱烧海参九转大肠要去济南吃、浓油赤酱的红烧肉要去苏州上海吃……北京,更多时候只是没有选择的替代词。
难怪生活在北京的安徽人陈晓卿,会发出“食物有根”的感慨——其实即便有根,在这个物流发达、人才流转频繁的时代,移栽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事,只是北京的土壤种不活而已。

No:4 肆
近代的北京不是一座正常的城市。
清代,北京的满汉两族分南北城而居,八旗占领北城,按照1882年的估计,占到北京总人口的60%以上。满人不从事生产劳动,只是围绕着皇室担任仆役、官员和军队护卫。
这些满人,又向下养活了剩余的南城汉人,他们从事杂役、商贩工作。可以说,当时整个北京的GDP,都是为了政治中心而生,依靠全国的纳税供养。这种惯性之大,以至于今天的北京人,依然对“吃皇粮”“国家单位稳定”这样的思想有着异于别处的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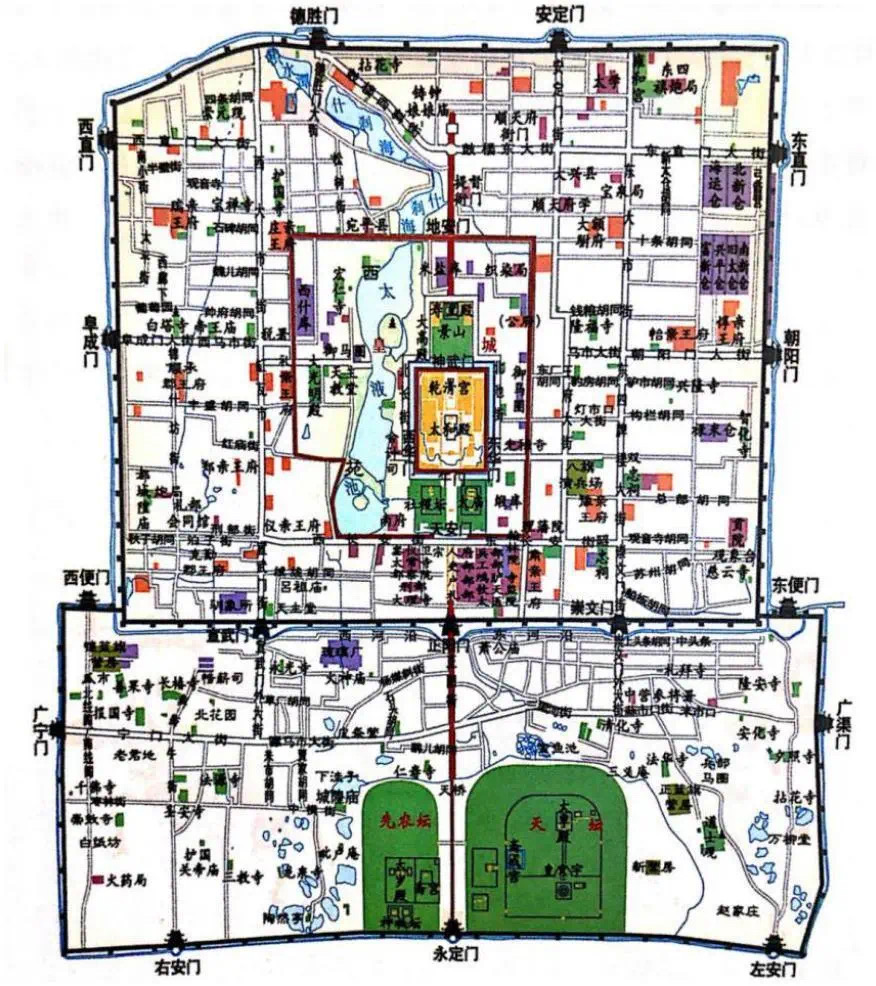
这也是北京土壤养不活外地饮食的根本原因之一: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愿意在首都工作,但没人愿意永远生活一个包容度低、自然环境贫瘠的城市。所以即便皇室引进各地技艺高超的厨师,也都如昙花一现,后继乏人。
而且,北京人曾经追求的“皇粮”,还带来了更为惨痛的后果:贫困。
1912年清帝逊位后,皇室宗亲纷纷逃亡,逃往天津之京官“日以千计”。与此同时,因为华北平原频繁的黄河泛滥、蝗灾,大量灾民涌入北京。这让这座本来就没有多少自我造血能力的城市雪上加霜,城市人口贫困化这个闻所未闻的新词得到了反映。大量欧洲列强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印象,多来自于北京。
1928 年,在一项国民政府针对北京贫困家庭的调查中,有 32.75%是曾享受过特权而又坠入底层的旗民。

不饱不暖,当然也就不思淫欲。民国期间客居北京的绍兴人周作人说:“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我们只看北京人家做饺子馄饨面总是十分茁实,馅决不考究,面用芝麻酱拌,最好也只是炸酱,馒头全是实心。本来是代饭用的,只要吃饱就好,所以并不求精。”
不巧的是,民国时期,也是今天中国饮食最后定型的关键期。流传于世,各地代表正宗口味的“百年老店”大多在当时出现。而当时的北京,还在失落的几十年里苦苦挣扎。再加上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后政治中心的南移,让北京错过了成为美食之城的最后机会。

-END-
威廉·戈尔丁说,“英国只有两种食物,一是伦敦扒房里牛扒,二是其他地方用于充饥的饲料”。
如果说精致的伦敦菜,是美食荒漠英国唯一的亮色;那么粗粝的北京菜,就是美食大国里最昏暗的小黑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