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场:是什么推动了战机涂装的百年变迁
新浪军事 2020年10月10日 0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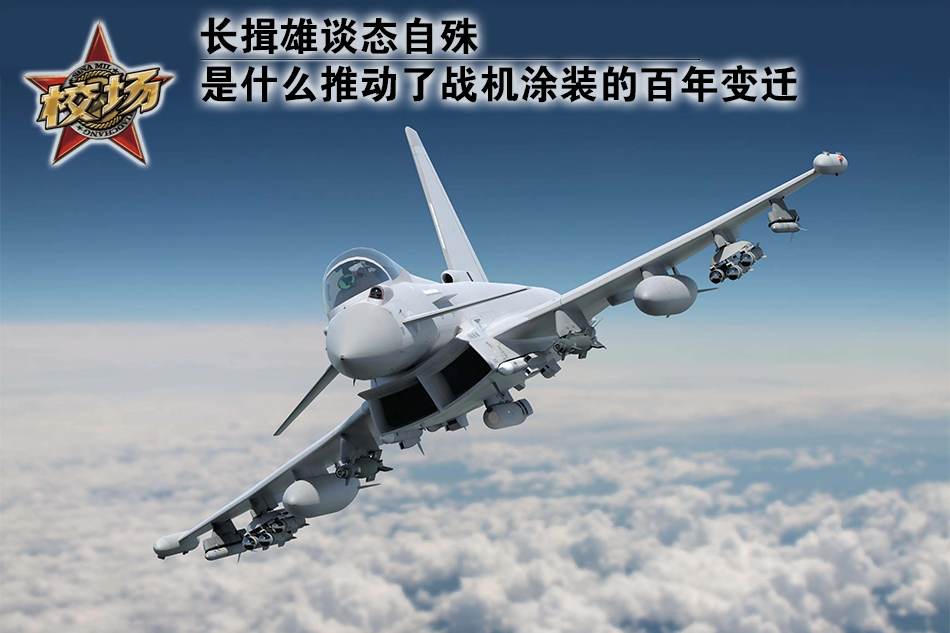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军兵种参加战争以来,飞机的涂装就是航空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百余年的发展,飞机涂装也从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专业科学。

涂装通常都有两个截然相反的作用:为飞机伪装和彰显飞行员或飞行队的个性。之所以说这两个作用截然相反,是因为伪装要求飞机在远距离上有较低的辨识度,难以被敌人发现;而个性化则要求飞机有较高的辨识度,通常要采用比较鲜明、艳丽的颜色,这就很容易破坏飞机的伪装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贵族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在成名后索性完全放弃了飞机的隐蔽性,干脆把自己的座驾完全涂成了鲜艳的红色。加上此人飞行技巧过于高超,砍下了整个一战最多的80个确认战果,获得了“红男爵”(Der Rote Baron)的诨号,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

不过,红男爵这样招摇的战斗机飞行员毕竟还是少数,因为优秀的伪装涂装可以显著降低飞机在远距离上被发现的概率,缩短敌人发现自己的距离。这在空战中能够让飞行员占得先机,在对地作战中也能降低敌军防空炮对自身的危害。因此,绝大部分正常人都会选择在不破坏飞机本身隐蔽性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涂装(一般也就是涂个鲨鱼嘴或者美女什么的)。这也形成了今天隐蔽色基底+小型机徽/个性图案的传统。

法国是最早在飞机涂装中引入隐蔽性概念的国家,1916年凡尔登战役时法国飞机公司纽波特就尝试了为自己生产的飞机喷涂与天空颜色近似的浅蓝色油漆来混淆低空飞机和地面防空火力的视线。不过使用这种天蓝色涂装的法国飞机在飞得更高的德国飞机眼里就成为了绿色田野中最靓的“蓝精灵”,使其并不适合应付空中作战。因此在1916年中期,法国人便又放弃了这种天蓝色涂装,转而发明了一种由褐色、翠绿色和深绿色组成的迷彩涂装,并在战斗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同为一战参战国的德国和英国在目睹了法国人的创新后也迅速推出了自己的战斗机隐蔽涂装方案。同时,两国都注意到了法国人迷彩涂装的问题所在:天蓝色涂装在面对低空和地面敌人时表现出色,但在面对高空敌人时却成了“蓝精灵”;三色迷彩在面对高空敌人时隐蔽性出色,但在面对地面防空火力时又成了最明显的靶子。为了兼顾对两类目标的隐蔽效果,德国人给出的方案是——透明飞机。

当时飞机除了发动机部分以外,均是由木质骨架和帆布蒙皮组成的。德国人的方法就是使用一种透明的树脂来代替帆布作为飞机的蒙皮。这样一来,不管敌人在飞机的上面、下面还是左边、右边看,都只能看见飞机的骨架、发动机和飞行员,隐蔽效果极其出色。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德国人发现,他们使用的醋酸纤维素树脂在天上会强烈的反射太阳光,让他们的透明飞机成了天上“最亮的那颗星”。因此,这种透明“隐身”飞机也随即被判了死刑。

另一方面,英国人则在仿生学的角度上设计出了一种可以兼顾上下方向隐蔽性的迷彩。我们都知道,虎鲸、大白鲨这类海洋生物的背部通常是深色的,能很好地与深邃的海水融为一体;腹部通常是浅色的,可以与透过上层海水的阳光融为一体。英国人的新型飞机迷彩采用了机背方向土地迷彩,机腹方向天空迷彩分别喷涂的方式,有效解决了此前单一迷彩的不足。这种混合迷彩在1938年首次问世,一经问世便风靡了全球。此后几乎所有的飞机迷彩均沿用了这种样式。

飞机迷彩的隐蔽性虽然很好,但作为一种不怎么高深的科学,各国飞机迷彩的演化基本殊途同归。都旨在让飞机在上面看起来和地面融为一体,在下面看起来和天空融为一体。这种趋同演化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了一架飞机,但只有近到能够看清机徽的距离上才能从涂装上分辨出来这是敌机还是友机。因此,在很多时候分辨飞机的外形成了唯一的敌我识别手段。而这种手段在敌军的飞机和我军的飞机长得很像的时候就不那么好用了,比如英国人就经常把自家装备的野马战斗机和德国人的Bf-109、Fw-190战斗机弄混。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盟军司令部在1944年试验了一种名为“入侵条纹”的增强飞机目视特征的涂装。这种涂装要求在飞机的机翼、机尾上图上醒目的黑白相间的条纹。可以帮助盟军的飞行员和地面防空火力快速辨明敌我。之所以要叫“入侵条纹”,是因为此时盟军正在准备入侵欧洲的霸王行动,而这种条纹正是为了这次入侵行动准备的。(注:英语语境中“入侵”,Invasion一词为中性,无贬义)

“入侵条纹”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盟军已经基本掌握了西线的制空权,“伪装”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那么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好像红男爵们又可以复兴了。但美国人思来想去,发现像红男爵一样把飞机弄得花里胡哨的好像没啥意义。不如直接省去涂装的步骤,裸机上场。这样一来可以省下油漆的重量(战斗机约几十斤,轰炸机约几百斤)并降低粗糙的油漆表面造成的额外空气阻力让飞机飞的更快,二来可以节省油漆钱和喷涂的工时增加飞机产量。因此,美国在1943年11月授权飞机制造厂商在生产战斗机和轰炸机时删除不必要的飞机涂装,裸机下线。而飞机制造厂商也在1944年初先后改进了自己的生产工艺,生产出了一大批只有铝合金本身的亮银色的飞机。当然,这种没有涂装的涂装仅适合陆军航空兵。至于每天要和高盐高湿环境打交道的海军航空兵,自然还是要涂上油漆防锈的。

二战结束后,追求速度的喷气机成为了战斗机的主流。此时不涂油漆的裸机在经过机体抛光后飞行阻力更小的优势就被放大了。因此,也有大量早期喷气式战斗机采用了这种涂装样式。比如苏联的米格-15、米格-17、米格-19;美国的P-80、F-84、F-86、F-100、F-104;我国的歼-5、歼-6等等。

另一种应用甚广的涂装方式是几乎纯黑的夜战涂装。二战时期,盟军经常在夜间对德国的战略目标进行轰炸,同时盟军和德军也都各自开发出了搭载雷达的夜战飞机。此时如果这些飞机使用通常的浅色迷彩,很容易成为夜空中最亮的仔。因此,美英开始尝试在夜战飞机上涂上黑色油漆来匹配黑夜的天空颜色。但事实证明这种涂装的效果并不完美,因为在晴朗的晚上,黢黑的飞机也很容易被发现。

1940年,加拿大人布尔(Burr)发现一架正在降落的轰炸机突然在跑道上空消失了。后来布尔通过研究发现,这是因为月光照在雪地上产生了漫反射,照亮了正在降落的飞机让飞机和夜空的光照度融为了一体。随后,加拿大海军通过这一发现设计出了给军舰进行夜间伪装的补光装置。这种技术随后也被美国海军航空兵拿来进行夜战伪装。在美国,这种飞机使用的补光灯被称为耶胡迪灯。但由于技术的限制以及雷达的普及,不管是军舰上的补光灯还是耶胡迪灯都没有最终投入实战。

在冷战时期,核大战成为了空军博弈的主旋律。因此肩负着核打击任务的轰炸机的涂装也开始从单纯的隐蔽性向功能性过渡。在冷战时期,防闪白开始成为了各国核轰炸机和核攻击机的涂装颜色首选。这种特殊的白色可以反射掉核爆炸产生的热辐射,保护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机组成员。这些轰炸机中最著名的当属苏联的图-160战略轰炸机。这是苏联第一种通身防闪白涂装的轰炸机,同时又有一个细长的“脖子”。因此也获得了“白天鹅”的绰号。

上世纪70年代,以F-14、F-15为代表的第三代战斗机开始服役。不同于追求高空高速的二代机,这些飞机更看重全空域,亚跨音速的近距离格斗能力。这也让飞机的迷彩有了一些其他的变化。众所周知,飞机向升力线(机背)方向进行机动的能力是最强的。所以一些国家为了迷惑敌军,让敌军对其飞机的机动能力产生误判,还开发出了在飞机的机腹涂上一个假座舱盖的迷彩样式。

同时,高中低空全空域作战的需求也让单纯追求高空隐蔽性的偏白的二代机空优涂装不再适合这些飞机。1976年,随着F-15的服役,美军公布了一种名为“罗盘幽灵”(compass ghost)的涂装方案。这种涂装主要由“幽灵浅灰”和“幽灵深灰”两种非常接近的灰色组成。其机腹部分为幽灵浅灰色,机背部分则为两色混涂形成的迷彩。相比于此前二代机偏白的整体涂装,这种涂装不仅有色彩伪装的效果,还能显著降低飞机的反光,广泛适用于高中低空域,堪称万金油。

鉴于“罗盘幽灵”涂装的优秀表现,美军又在这种涂装方案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希尔灰”、“鹰型”等涂装。这其中“鹰型”可能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美军飞机涂装方案,因为现役的F-15系列战斗机和F-22战斗机均采用了这种涂装方案。这与很多人“四代机的隐身涂料是灰色的,所以四代机都是灰色的,所以不是灰色的飞机就不是四代机(日常迫害苏-57)”的理解误区有很大出入。事实上,F-22的涂装方案与F-15完全相同(F-35的与这两者类似而不同),F-22隐身涂料改变的是F-22的颜色质感——由于隐身涂料中有大量细小的金属颗粒,所以F-22涂装的金属质感(色泽)要比F-15更强。

隐身空战的时代来临后,视觉隐蔽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传统涂装上与机身颜色迥异的标志、图案甚至雷达罩现在都显得格外刺眼。因此,从世界上第一种雷达隐身飞机F-117问世以来,低能见度徽标和图案就成了隐身飞机的标配。这种徽标往往会选择与飞机基底涂装相近的颜色来降低徽标的对比度,从而使其在视觉上不那么突兀。而一般军迷所说的“低可视化涂装”其实也就是使用了低可视化徽标的涂装。目前,美军的大部分现役战术飞机和我军的歼-10C、歼-16、歼-20都已经普及了这种徽标。

但雷达罩的问题却比徽标更加难以解决。因为徽标的问题无非就是换一个颜色的油漆。而雷达罩有独特的透波要求,不能随随便便用漆,只能用专门研发的雷达罩涂料(主要是最外层的抗静电涂层)。传统的雷达罩抗静电涂层通常以石墨作为添加剂,因此大多呈黑色。这非常不利于昼间战斗机的视觉隐身。因此以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为代表的“土豪”更偏向于使用金属氧化物作为添加剂。这种添加剂材料就允许把颜色做成类似于飞机基底涂装的灰色。目前,美国和欧洲的主力战机(如阵风、台风等)均已采用了类似的防静电涂层。但限于技术、成本等多方面原因,东方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目前仅有如歼-20、苏-57、苏-35等少量战机能够有此待遇。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战斗机设计制造中需要赶超的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