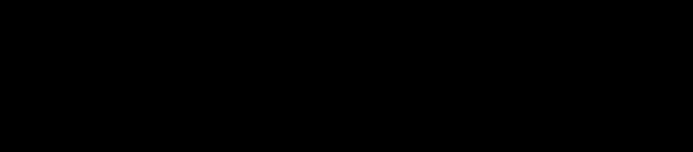

这是大家之选的第25篇文章
今日出品方:冰川思想库
本文作者:任大刚
点击了解《大家》编辑部开放计划
2004年前,当禾花雀还是一种“无危物种”时,每年都可以看到它们美丽的身影,成群结队,从中国东北及西伯利亚,迁徙到东南沿海或东南亚繁衍后代。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也不知哪个缺德鬼宣布它可以“壮阳”,这可怜的小家伙就噩运临头了。13年来,它从“近危”、“易危”、“濒危”,最近宣布到了“极危”,随时从地球上消失。
这是继穿山甲之后,又一个即将被吃绝种的野生动物。听起来让人伤心。

我不是动保主义者。我对动物并无特殊的爱惜之情,我坚决主张爱护动物,更多出于生物多样性更有利于人类长远利益的考虑。如果发生普遍的饥荒,我认为任何人在穷尽所有可能仍无食物的情况下,有权吃掉享受法律保护的动物,甚至那些保护等级最高的动物,也应成为人的盘中餐。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态度。
但现在是饥荒年景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生产出无限量的粮食和肉类,逐步解决温饱,越来越多的人吃出“三高”。对很多人来说,吃,已经成了负担。
但很奇怪,伴随解决温饱的过程,按理说,很多野生动物减轻了被中国人吃掉的生存压力。但实际上,扣除生态恶化因素,一些动物,从长江刀鱼到野生大黄鱼,从大鲵到白鲟……,包括上面提到的穿山甲,大众动物被吃成稀有动物,稀有动物被吃成珍稀动物,珍稀动物被吃绝种。
这个剧烈反差,隐藏着中国人内心深处变态的形上体认和历史遭遇。如果这些深入骨髓的饮食认知不改变,还会有一些不幸的动物排队进入中国人的口腔之墓。

悠悠万事,惟吃为大
在中国,吃,从来就是个等级森严的政治问题。
饮食的品种上,《国语·楚语》中有明确记载:“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庶人是没有资格吃荤菜的;士,也只能吃到烤鱼为止。
餐具的使用也是如此。剥掉“鼎”的文化与权力内涵,说白了它就是炖肉的锅子,《公羊传·桓公二年》提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位置越高,炖肉的锅越多,鼎,顺理成章引申为政治权力。

既然吃饭与政治关系如此紧密,利用吃饭解决政治纷争,也就成了常用手法。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场饭局,一个是鸿门宴,一个是杯酒释兵权。参加过这两场饭局的,都青史留名了。
最高权力的行为有最强大的示范作用,连土匪窝子也不例外。梁山上号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在吃饭问题上,彻底暴露出森严等级——“交椅”的整齐摆放,一方面是为了坐下喝酒吃肉不至于挤成一团,便于服务员上菜,但同时,交椅的摆放秩序,也是地位、权力大小的象征,坐在聚义厅门口的,肯定是地位最低的,与宋大哥对视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上述这些吃饭的规矩变了吗?根据2014年《济南时报》一篇介绍山东饭局文章,没有变!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按山东规矩,请客的主陪右手是最主要和尊贵的客人,左手次之。主陪对面的副陪右手是第三,左手第四。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山东饭局上的座次图
这是政治饭局与江湖饭局的有机统一。
中国饭局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甚至可以包括男女勾搭是否成奸。像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场饭局恰到好处;贾珍贾琏叔侄二人勾搭尤氏姐妹,饭局没组好,酿成悲剧。
既然中国饭局功能如此强大,连人这种高级动物都身不由己被席卷进去,区区野生动物,智商为零却满体含香,犹如三岁小儿捧金过市,有何能力幸免于掠夺?

非山珍海味不足以显特权

在中国,饮食的目的不仅是延续生命,享受愉悦,由于它长期以来被赋予权力意味,因此通过饮食获取更大利益,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日常情况下,我们在家吃饭,总要讲究填饱肚子,营养均衡,味道可口,但一到饭局,情况大变,尤其是宴请尊贵客人,则非山珍海味不足以显示尊敬与礼貌。
以今天的标准看,山珍海味大多属于法律保护的珍稀动植物,技术进步后,有一小部分可以人工饲养。但总的来说,在饭局当中,只有吃到珍稀动植物,宾主双方才有体面可言。
请客的一方为何必须如此?
其一,显得对客人费尽了心思,表达用尽心力的照顾、诚意或忠诚;其二,山珍海味的高昂价格,用以匹配客人的身份和等级,与前述天子吃牛羊猪三样,诸侯吃牛,卿吃羊,大夫吃猪,只能吃一种,是一个道理。通过山珍海味,让客人体会到等级和特权所在。
但这样一来,势必使野生动植物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贵,这更加促使不法者偷猎偷采;越是偷猎偷采,它们更少,减少得更快,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禾花雀的遭遇,就是如此。
这种变态的饮食文化不改变,法律睁眼闭眼,则人民富裕之日,就是野生动植物遭殃之时。


禾花雀


成为盘中餐的禾花雀

大家都是饿死鬼投胎
《舌尖上的中国》热映时,我便想,要是有人能够拍一部《舌尖上的饥荒》就更好了。
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文化多样性强,决定其饮食品种和方式繁复。但是,决定这一特点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饥荒。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在世界上的文明级国家中,自然灾害最多。上古传说,基本都是以讲水灾开端,“禹之时,天下大水”“燧人氏时,天下多水”“浩浩洪水方割”“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
有了文字记载后,灾害的记载准确多了。《中国食文化批判》一书称,据历史考证,西周至清末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发生1.7次。
另一组统计数据称,秦汉两代自然灾害375次,三国两晋南北朝304次,隋唐515次,宋朝874次,元朝513次,明朝1011次,清朝1121次。
伴随自然灾害的,往往是饥荒,尤以明清两代居多。明末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陕西大旱,人相食,直接导致李自成起义,明朝灭亡。清末“丁戊奇荒”,北方五省赤地千里,共饿死1000余万人,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随着旱情发展,灾民根本找不到食物,“人相食”再次上演,1877年冬,在重灾区山西,人吃人现象随处可见,吃人肉、卖人肉,比比皆是。
“人相食”的记载,随便翻开那本厚厚的《中国灾荒史记》看看,从秦汉到民国,那真是太多太多了。哪怕在今天,对大规模的饥荒留下深刻印象的在世中国人,最小的不过60来岁而已。
一旦发生饥荒,粮食和肉类短缺,人搜寻饮食的范围便会迅速扩大。
首先是植物界,据植物学家调查统计,中国人吃的蔬菜有600多种,比西方多6倍,除了纬度跨度大,植物品种多的原因,不少难以下咽的野菜是在反复发生的饥荒中,被培育成蔬菜了。
其次是动物,一旦饥荒形成,家养的马牛羊鸡鸭鹅先被杀,平时不吃的猫狗随其后,地洞里的老鼠,土里的蚯蚓,肮脏的蟑螂,都是盘中餐,遑论更为可口的飞禽走兽。
动物的内脏,先民们一开始只会烧烤时,我猜是不吃的;学会蒸煮后,也不一定喜欢吃;只有等到调料丰富烹饪手法更多并且食不果腹时,才开始大量食用动物内脏。这种饮食习惯延续至今,全球独步。
天灾带来饥荒,如果与人祸比如战争或救灾不力等等同时发生,必定造成耸人听闻的人道灾难,《中国食文化批判》提供了史书上所记载的人肉别称:“想肉”(女性乳房做的菜肴)、“双脚羊”(婴幼儿肉加入补药)、“地鸡”(少女肉腌制的人肉干)、“地鸭”(少男肉腌制的人肉干)、“福禄酒”(人血和鹿血一同煮熟)、“饶把火”(老而瘦的男人肉,意思是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不羡羊”(年轻的妇女肉,意思是这种人肉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还有什么“和骨烂”,实在不忍再写下去了……
长时间的、频繁的饥荒,连普通动物都能做到的“不食同类”一再被反复突破,饥饿最终成为一种文化乃至生理基因,埋设在中国人的肌体和脑筋深处,举凡是能跑动的动物,不管大小,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能吃吗?老一辈尤其如此。很多小型动物,提供不了多少肉类,但哪怕身上只有一根小指头粗细的净肉,也在劫难逃。
饿死鬼投胎的太多了,或者说,我们都是饥荒幸存者的后代。手无寸铁的野生动物,和一群有饥饿基因的人同在一片蓝天下,瑟瑟发抖。


作为补品,再补一刀
逃过了权力意志,又逃过饥民幸存者,是不是可以安稳生存了呢?不,还有被当作补药补品一关。
路过中国的禾花雀,在山林里苟且偷生的穿山甲,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栽在一个“补”字上。
我没有能力对传统中医的“补”做出一番专业的批评,只是想说,很多野生动植物,都被视为有“补”的功效。
很有可能,某种介于中药材和食品之间的动植物,可以有改善健康状况的能力,但有些传说中的“补”,不外是一种“以形补形”的巫魅,禾花雀之所以可以“壮阳”,大概也是这个思路——以形补形,以鸟补鸟。
禾花雀能不能壮阳,吃过的人才知道,但吃补药的人,多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再说,请客者也是一片好意不是?尤其近年来,在一些不好明说的原因之下,一旦某样东西被成功宣称能够“壮阳”,人们一定趋之若鹜。
可怕之处还在于,吃名贵补药补品的,多是中年油腻男女,这个群体消费力最旺盛,消费力有时候是一种破坏力,它完全可以使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灭绝提前到来。
穿山甲,禾花雀,以及无数的后续动物,要想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法律的保护力度是一个方面,但变态的饮食文化,离奇的进补方式如果不做改变,种群减少还将继续。毕竟,我们不可能派出无数执法人员去守住每家每户的锅边,揭开他的锅盖,看看他炖的是什么。

今天指责中国人把动物吃绝种,并不是要掩盖另一段历史:有些动物,同样被以文明著称的欧洲人吃绝种了。典型如美洲大陆美味的北美旅鸽,欧洲人来到美洲之前,据信有多达50亿只,但19世纪被美国人吃绝种。毛里求斯的渡渡鸟,也是被18世纪的欧洲人吃绝种。
任何一个文明体,无论它如何标榜自己的历史如何悠久,文化如何繁盛,但如果它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不能建立一种理性化的关系,那么它在其发展进程中,往往出错。欧洲人把北美旅鸽和嘟嘟鸟吃绝种,就是不知道如何与自然建立理性化的关系;而中国人饮食文化上充满权力意志,蒙昧的中医理论大力支持各种滋补,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前现代。
欧洲人走出去了,甚至过头到“绿色恐怖主义”,而中国人还在瞻前顾后,半信半疑中,干掉一种又一种动物。
本篇头条文章由冰川思想库出品 汇聚思想 分享锐见。
团队成员:连清川、陈季冰、魏英杰、任大刚、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