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我,你有多久没有看电视了?或者,你有多久没有打开过家里的电视机了?再或者,你是否正犹豫着要把电视从新装修的客厅里,彻底给赶出去?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白人左派教授们的矫揉造作。
当下,如果要寻找一处最为萧条的家庭空间,寻找一种最为落魄的家用电器或者传统媒介,那么中国人的客厅和客厅里曾经的绝对核心——电视,将毫无疑问地胜出。
1926年,英国人约翰·洛吉·贝尔德发明了一只黑色匣子,人们把这个能发出声音和显现图像的盒子称为“电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就这样诞生了。

贝尔德在一次实验中“扫描”出木偶图像,被视为电视发明的标志。
在1939年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人们兴奋地将电视机和尼龙、录音机、塑料、磁带以“建设明日世界”的主题一齐展出。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人能够否认,不论是作为媒介的电视节目还是作为载体的电视机,开始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现代人的生活。
但最近,一切开始改变。
你自己知道你有多久没看电视了。当然,数据也知道——仅北京地区的电视开机率已经从3年前的70%下降至30%,且收看电视的主流人群为40岁以上。
电视被年轻用户所抛弃,几已成为现实。其背后是iPad,智能手机,电脑的普及以及网络视频节目的爆发。
久已不打开的电视机开始蒙尘。代替曾经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同一个节目的,是虽然都还坐在客厅沙发里,但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电脑或者平板在刷刷刷。

同时,一场关于电视机到底是否还应该存在于客厅的争吵,已不再是暗流涌动,而成为一种大众呼声。
“为何你家的客厅与99%的中国家庭撞脸?”
“是时候把你的电视机赶出客厅了!”
“电视墙+电视+茶几+沙发,天啊你还没厌倦!?”
在各种非装修论坛上,这样的帖子也不再是少数。现代人的视频娱乐需求在电脑和手机上,已经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这让电视在客厅逐渐沦为摆设。
因此,每个中国家庭都曾有过或者正在拥有的“电视墙+电视+茶几+沙发”的“经典”客厅格局,正在连同这个空间的始作俑者——电视一样,正在遭受现代人的嫌弃和驱逐。

在信息接收渠道和娱乐方式相对单一的年代,电视机屏幕就是家庭中唯一的屏幕终端。因此,作为家庭几何空间的焦点,电视机在哪儿,家庭空间的重心就在哪儿。其他的家具和摆设都要以电视机为中心而展开。于是,电视机像佛像一样,被用一整面墙供起来,成为现代家庭的“神龛”。


俯拾皆是的“中国式客厅”。
威廉·曼彻斯特曾在《光荣与梦想》里,描述当时一个拥有电视的典型美国家庭: “他们并排地、而且常常并肩地坐在一起,看上几个小时电视,连目光都很少交换。如果他们交谈,也是气鼓鼓的,为这个或那个节目的好坏而争吵。”
在中国普及电视后的二三十年间,每个中国人的客厅也曾经是类似的场景。电视也确如“神龛”一般,长久地在家庭空间之中传播信息和“布道”。不同代际的年轻人们都曾和家人或者同学围坐电视机前,追看《西游记》《渴望》《上海滩》《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超级女声》……
更不用说,那些曾经和电视黄金年代一同高光过的“仪式”和“狂欢”一般的全民节目,比如中国人的“春晚”,美国人的“超级碗”。

那些年,在客厅硝烟四起的遥控器大战中,谁败下了阵来?
那是电视帝国一统天下的年代。其勃发始于1962年,美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这使得世界上任何地区发生的新闻都能通过卫星进行电视直播。于是,电视开始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姿态关注着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从遥远非洲的饥饿,到人类第一次登月,都可以被这个黑匣子传播到人的眼前。
可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现代人是通过电视来认识世界和记录当下的。从当下热映的李安电影里,我们回忆起那些年,在电视机里中看到的海湾战争和911事件。从最新一季的美国总统大选里,我们想起了被称为“电视总统”的肯尼迪和与美国总统选举相伴而生的电视辩论。

尼克松(左)与肯尼迪(右)的电视辩论
正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所开创的广播“炉边谈话”一样,肯尼迪对电视的热衷,也使其成为政客运用媒介塑造自我形象的典范。充分认识到电视传播潜力并加以利用的他,被称为史上第一个“电视总统”。
加之此后发生的肯尼迪遇刺事件,通过电视传播到每个美国人的客厅,“在那四个不可思议的、令人震惊的日夜里,电视成为全美国人生活的中心,如同吃饭、睡觉一样重要……过去曾经是最不被看好的、最不受重视的媒介,此刻变得让人们无法回避。”
“肯尼迪无疑是第一位电视总统,在我们的记忆中,他永远只有46岁,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假如他活到今天,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历史学家、传记作者罗伯特·德勒克认定他是首位真正懂得利用电视的总统。
眼下,不仅是中国人的客厅不再欢迎电视,作为曾经与美国总统选举关系最为密切媒介的电视,也不再是政客唯一和主要的公关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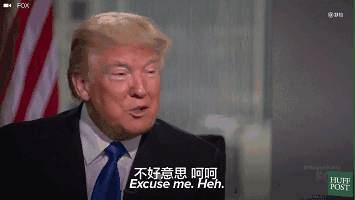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西方哲学家任性地宣布了太多的“终结”和“死亡”。从尼采的“上帝之死”,米勒“文学的终结”,到丹托的“艺术的终结”,人们发现没有什么范式和概念能够适用和通行无阻于任何一个时代。
过去,我们通过电视,窥视和目击世界。不论种族,阶层,地域,每一个电视机前的人,都能通过它看到远方的风景和故事,以及新近发生的新闻和潮流。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从电视里去认识世界。“事件如果没有在电视中呈现,就如同没有在世上发生一样(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其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视觉和观看的民主化”。但它也带来一个巨大的困境和矛盾:电视展示的是真实吗?还是仅仅展现了一个被选择、剪辑、编辑后的世界?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媒介所蕴藏的巨大张力,20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今天,即11月21日为“世界电视日”。
他们是基于以下的判断:“世界电视日不仅只是一个庆祝电视这种工具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认可电视所代表的哲学——它是现代世界的传播和全球化的象征。”
在第20个“世界电视日”,我们不无失落但也无比坦然地发现曾经的媒介之王正在经历式微的生命历程。此刻,就像它曾经战胜过的对手们——印刷媒介、电影、广播一样,它正告别黄金年代,和当下以及未来可以想见的各种新媒体共存,但不再是霸主。
而“终结”也不是死亡。准确来说,是成为无中心、碎片化年代的诸多碎片之一。告别也不意味着失败,而且它已经在进行。
比如最近,我刚刚就目睹了其中一场。主角是被称为“电视直播教父”的美国人大卫·希尔。
如果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个在电视直播中度过最多人生时间的人,那么作为今年“双十一狂欢夜”总导演的美国人大卫·希尔毫无疑问会当选。

从1988年开始制作后来家喻户晓的英超联赛,到20多年间负责每一年的美国“春晚”——超级碗的直播,大卫·希尔制造了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在今年双十一晚会开始前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68岁的老爷爷依旧敏感和好奇,整个过程里,他对前排一位来自某国内知名直播网站的主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发布会结束后,按捺不住的他马上跑过来反客为主,举起自己的手机绕着那位身形瘦削的中国男主播拍了一圈。
“你知道,我们那种电视节目直播已经很过时了”,“电视直播教父”兴奋地对着那个主播和他手里的手机吼道: “而你,太棒了,太神奇了,你代表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