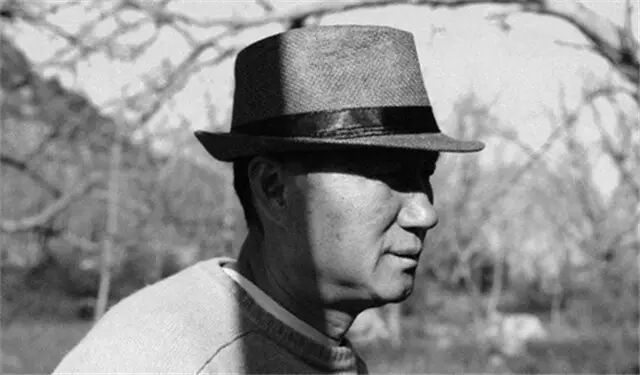
文 | 鞠白玉
每年春秋两季,仍在云艺美术系任教的毛旭辉会带着学生进入圭山写生,每次两到三周,和他学生时代的写生惯例一样,他们吃住在老乡家里,按照农村生活的时间表作息,直到他们的写生簿上满是圭山的秀色、农庄的细节与角落,又启程回到昆明城市里。
即使不带着学生,以毛旭辉的职业艺术家习惯,每年他也会孤身将自己放回圭山,这个乡村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提供至关重要的供给与慰藉。
而圭山有什么呢,它只是西南部典型的落后农耕生态的一隅,它既不富庶也毫无奇观,猪牛羊鸡遍地走,有明晰的四季,秋风一起自会萧瑟,冬雪降临一片白皑,无论春耕或秋收,都只是默默。
其实它也不存在乡村的凋敝,因为它从来没有怎样兴盛过。圭山和它的村落像是瞬息万变世界里被遗忘的故城,但它自己独有的瞬息却都被艺术家常年地描绘着,记录着。

作为美术界八五新潮的重要人物,毛旭辉是少有的牢牢固守在故乡的艺术家,在1994年初冬他也曾试着和北上的艺术大军一同迈入政治波普的洪流,但不到四个月,北京街头飘着柳絮时他便离开了,同时还带着已经在央视任职的妻子,无论人们当时如何劝说和假设前景,他一定要回到昆明他自己的工作室,回到他熟悉的生活里去,只有回去,才能在地理和心理上都靠近圭山。在北京,他内心的感觉是“脆弱”。
艺术家为何如此依恋村庄?经历了二十年在村庄的徘徊与观察,他意识到当时的回归是对内心世界的一种保护,因为只有这里的变化是缓慢的,在这里没有和旧日的剧烈的撕裂感,人和旧日的距离并不遥远。对于这样总可随时触摸到的旧时光,艺术家认为是充满诗意的。而诗意似乎从来不在新事物中。诗意在他的创作意识里尤为重要,他既在保全,也在寻找。
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北京发生的艺术潮流中,作为新人所创造的新事物,那不被他所眷恋,他也不认同艺术的中心或是世界的中心说,在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里,人便是中心。
所以人为何要为所谓的事业在世界上东奔西走呢,只有移居,只有背井离乡才能在精神世界里索求吗?不和父母兄弟分离,不去陌生的土地去和陌生人做邻居,不付出任何割裂的代价,不去获取日新月异的信息,甚至不跟从世界的变化,只有一种缓慢中去思考,去创作,又很努力地保持着一种稳定不变,会影响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吗?
令人羡慕的是艺术家可以仅依靠艺术语言与世界对话,而且这份语言愈是独特愈是个人化,声音才更持久有力,艺术家下意识保全的是个人的纯粹自然的状态,他们不愿意加入到任何一种迫不得已的系统里去,“一个艺术家应该悄悄地创作”,这句话也是刚获诺奖的鲍勃·迪伦在1967年之后的座右铭。
艺术家逃避的不是辛苦,不是孤独,而是逃避可能的名声和其他世俗的不必要的负累,因为他们只想“自私”地去独处去创作。所以毛旭辉既是回归,又是流放,因为没有创作的生活,活着就仅是虚度,他们的存在感甚至不在他人的认同感里。而回归将生活变得简单——更好地画画,更好地活着。
人际关系变得纯粹,在他的工作室里总是他的学生们,他的交际名单上总是那几位老友,从学生时代至今的挚友,逢年过节他们相聚,或结伴去圭山。
同样放逐自己的艺术家还有曾久居昆明的吕楠,除了他的策展人,甚少有人了解他的行踪。
在引起巨大轰动的《四季》之后,他仍然没有借着名气将日常浮出水面,每一个新展览他都会为自己取一个新的名字,他总是“新人”,他也从不出现在自己个展的开幕式上,甚少接受采访并且从不允许摄影记者拍他的肖像。
他要求那些钟爱他作品的藏家只能按照系列购买作品,因为任何一张单拆开来售出都会破坏作品信息的完整性,那是他用岁月与之交会的大地,大地上的作物和大地上的人。
即便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他的作品,他也还是在昆明一个老旧的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砖楼里生活,这所房子也并不属于他,是一对热心的夫妇借出的。
他成心以一种清贫的方式生存,一个房间放置所有的工作用具,另一个房间则是三面书架,唱片书籍直堆到天花板,一张八十年代样式的沙发和同样年代的台灯,沙发磨旧的角落表明他的主人曾长久地坐在那儿阅读。走廊沿墙边放着一排西红柿,冰箱里只有农户送的土蜂王浆和鸡蛋。他按书上的营养学安排饮食,不在烹饪上浪费时间,而且根据他常年的体验,一天两餐饭才是最科学的。
除了这些基本用物,可谓家徒四壁。一个在艺术界享有声望的人,他选择了一种看起来异常孤独的生活,每次他从村庄,山区,或其他少有人涉足的地方回来,放下拍摄的行囊,在这间屋子里整理作品,编纂校对,从凌晨到深夜,在这间屋子里他阅读,听音乐,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独享这些。

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广袤大地上穿行,在旷野上,在鲜有人涉足的私密之地去拍摄,除了沉重的拍摄器材,他的行囊里是书和唱片,在星空下跋涉时听着他喜欢的古典乐,孤独不是令人生惧的,孤独成为一种享受。
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将所有作品的收益继续投入在昂贵的创作成本上,他不被财产所累,甚至爱情和家庭仿佛也不需要,他脸上的神色是一个世间最自在快乐的人。他虽然在孤独中行走和创作,呈现的既不是乏味的苦难,也不是挣扎,而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对自然的顺从。
吕楠和毛旭辉这样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人生课题里是没有房产、税金、汇率、资源争夺的字眼,艺术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自然和创作的关系,他们视野里的这个世界远比世俗社会界定的世界更深远,他们在此获取的能量足够创作也足够快乐地度过此生。
莫奈在画了半个世纪后曾写道:“我唯一的愿望是与自然亲密地融合,我不向往其他的人生,我只想要与她的规律和谐地工作与生活。站在她的伟大,她的能量,她的无情旁边,人类不过是颗卑微的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