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用当下的话来说,那就是:
活人也要破地狱。

他叫阮籍,魏晋风度代言人,竹林七贤之一。
他在世的时候,人们就说他狷狂旷达,好像名士都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其实,没有几个人懂他。
他只是故作狷狂,故作旷达。他的内心十分苦闷,十分悲痛。
他时常驾着车子,狂奔在遍布荆棘的岔道上,直到巍峨的高山挡住了去路。
马儿失蹄,车轮打滑,他再也冲不过去。
无路可走,他颓然痛哭而返。
一个没有出路的中年人,在乱世的落寞形象,莫过于此。
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看魏晋,我们总以为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但阮籍用他的颓废,用他的焦虑,否定了这种错觉。
魏晋易代之际,从名士开始站队,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他是曹魏政权的拥趸,面对司马氏的咄咄逼人,若不想死,该如何自处?
于是,他的一生似乎都在醉着。
醉酒,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对抗。
他有一次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三百斛好酒,便主动向司马昭要官。
上任之后,真的就是喝酒,没日没夜地喝。
司马昭想和他结为亲家,他不愿意,又不敢直说,就喝得酩酊大醉,一连醉了六十天。
故意搞得司马昭连提亲的机会都没有,只好作罢。
司马昭晋封晋王,想借用他的名气,要他写劝进文。
他不想写,又不敢推掉,于是又喝得大醉。
这次没能躲过,人家把他弄醒了。
他没办法了,提笔一挥而就,写了一篇富丽堂皇的劝进文。
但他不忘在文章里挖坑埋雷,搞弦外之音。
诗,和酒一样,也是他表达苦闷的方式。他写了好多五言诗:
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人生写得如此孤独,如此悲凉。他的内心跟嵇康一致,但没嵇康那样刚烈,缺乏正面斗争的勇气。所以,他在沉重的现实里追求思想的自由,灵魂显得更加的痛苦。他看不惯小人,尤其看不惯伪君子,就写文章讽刺,以隐喻的形式:群虱之处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他不敢直接骂儒家的伪君子,故而用虱子比喻这帮人,说虱子在裤裆,躲在深缝里,藏在坏絮中,自以为住的是豪宅;走路不敢离开线缝,行动不敢跑出裤裆,自认为很守规矩。他是个大孝子,很爱他的母亲。但在母亲的丧礼上,他偏偏不哭,甚至喝酒吃肉。等到吊唁的宾客都走了,他想起来很悲痛,大声嚎啕,连连吐血。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所谓的狷狂,成了他的外壳,用以保护他内心的真。起因是他在云南姚安的知府任期将满,上级官员要向朝廷举荐他升官。没想到,他一听到升官的消息,拔腿就跑。他是一个真实而坦荡的人,直言做官只是谋生的手段,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从不去夸夸其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嘴上不说,他却比空喊口号的官员清廉得多,口碑和实绩也都好得多。不愿同流合污,坚守内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场生涯痛苦的根源。这种抵触未必是行动上的抵牾,但其内心有棱有角,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承担家庭与家族责任,20多年里,他不得不收起触角,摸黑前行,孤独痛苦,难以言表。一个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担,内心有巨大的压力,他只有默默忍着,不敢出声,尤其不敢顺从自己的个性,好好任性一把。再苦再累,再泯灭个性的光辉,也只有咬牙坚持。哪怕牙断了,只能和血吞。他始终清楚,一个中年人活着的意义——为妻子而活,为子女而活,为父母而活,为家族而活,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这期间,中年李贽经历的苦难一点点磨砺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释放他的枷锁。他的至亲,包括他的父亲、祖父、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几年内陆续去世。那段时间,他说与妻子黄宜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生命中有太多无法承受之重。连李贽都只能把这一连串的重击当作梦一般,以此麻痹自己的内心。54岁,在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纪,他却辞官重新出发了。从选择落脚的地方,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般官员都是告老还乡,发达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成功了也没意思。而李贽,没有选择回老家泉州,却去了湖北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他的理由貌似很纯粹,因为这里有朋友,生活不用发愁。“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他说。事实上,他不愿回老家泉州,与他的个性有关,他平生不爱被人管: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 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这个理由,与他辞官时所说“怕居官束缚”是同样的道理,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渴望。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按照当时的习惯,李贽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绝不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然而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他标榜个人价值,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宗族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维系所谓伦理关系,目的则是为了争夺财产继承权。62岁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却留下胡须,成了个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样。不过,他剃发的真实想法,在另外一些场合,坦率地表达了出来。他在一封信里说,之所以落发,是为了对抗家族俗事,让家族中人彻底死心,不要指望他还能回去。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反正世人都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怎样?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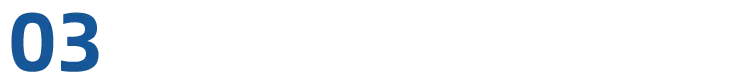

朱字去掉“牛”为八,耷字去掉“耳”为大,故而此次易名是去掉“牛耳”之意。牛耳,指的是在某方面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物。失去“牛耳”,沦为牛马。除此之外,他还用过一堆外号,每一个都很不把自己当回事。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丧气逼人的人物,才能如此怡然自得地自嘲?其实,他出身显赫,是朱元璋的十世孙,典型的皇室血统。然后就是父丧妻亡,一个人能经历的家国沉沦,他都经历过了。崇祯帝上吊后,所有人都以为明朝的历史已经写完。只有活着的子民,才知道这不过是翻页而已。无论是一条鱼,一只雁,一只凫鸟,眼神总是似睡非睡,死气沉沉。我既然无力反抗你的统治,我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不行吗?清代鸡汤文大师、《幽梦影》作者张潮,写过八大山人的逸事:予闻山人在江右,往往为武人招入室中作画,或二三日不放归。山人辄遗矢(屎)堂中,武人不能耐,纵之归。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人强行把他请到家中作画,一画就要好几天,山人不爽想怠工,就在人家客厅里拉翔。这画风,跟唐伯虎有得一拼。当年,唐伯虎得知宁王朱宸濠蓄意谋反,遂装疯卖傻,公然裸露下体,宁王受不了,放他回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