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最笨最笨的人,有很多事我想去做,但实现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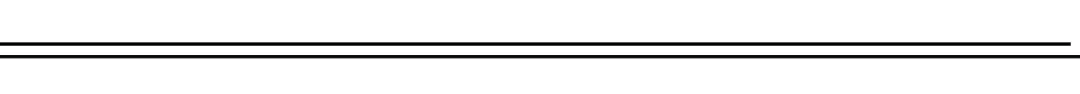
配图|《白日梦想家》剧照
1983年,我的堂舅马海阿甲出生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一个乡村里,从懂事起就在家里帮着放牧。
1990年,凉山州出台了关于义务教育的实施办法,马海阿甲周围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开始陆续上学,他也在11岁这年上了一年级,学费是10元钱。第二年因为家里没钱,没能读二年级,13岁直接跳级继续读三年级。到了四年级,学费变成了60元,老师说他成绩好,可以免掉30元的学杂费。如果把家里唯一的老公鸡卖了,正好可以补齐30元学费,于是,马海阿甲和姐姐打算一起将这只鸡卖了。出门时,马海阿甲的母亲一边责备一边朝着他掷了石子想要阻止他,她认为如果他继续上学,家里的牲畜就没人管了。马海阿甲和姐姐走出门一段时间后,他后悔了,他让姐姐将鸡抱回了家。
马海阿甲放弃了上学,但他并不甘心一辈子留在村里放牧,他决定离家出走去投靠隔壁盐边县的叔叔。家乡没有汽车,马海阿甲就只身一人走着去,走之前,他带了一把打火机,在路途中饿了,他就可以生火烤路边的土豆和玉米充饥。走到快天黑时,马海阿甲遇到了一辆北京吉普212,他搭上了这辆车。没想车是往回走的,于是他在半途的姨妈家里住了一晚,这次离家出走的计划也就作罢了。
此后的两年里,马海阿甲如母亲期望的那样,管理着家里的牲畜,直到1998年的到来。
1998年,马海阿甲16岁那年,他们家从盐源县搬到了盐边县,住得离县城近了些,家里买了一台小录音机,还买了几张山鹰组合的磁带。山鹰组合是1993年时成立的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原创音乐组合,三个成员都是来自凉山州的彝族青年,他们的歌曲也因此在凉山地区家喻户晓。听完这些磁带,马海阿甲觉得自己喜欢上了唱歌。

在盐边县,马海阿甲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姐夫因为97年国有企业改革,获得了一个矿产的经营权,家庭条件很好,家里有五辆用来运输的东风车,还有两辆小车,一辆摩托车和一辆挖掘机。
马海阿甲想继续上学,去找了这个姐姐求助,被拒绝了。但她承诺,只要帮她家放几年羊,就可以让他学车,以后可以当司机赚钱。马海阿甲觉得能开一辆大车,也很了不起,便同意了。
17岁,在生活中惯常使用彝语交流的马海阿甲,尝试着用汉语写了他人生的第一首歌。因为没上过几年学,写出的歌词并不能表达他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他还记得歌词里有这么几句:“我是一个最笨最笨的人,有很多事我想去做,但实现不了。”这时的马海阿甲觉得,等到自己赚到钱,读了书,也许真的有机会成为一个歌手。
给姐姐家放了几年羊后,马海阿甲得到了跟车的机会。但带他的司机并不给他真正驾驶的机会,他觉得没意思,再一次选择了放弃。他心想反正他这辈子也不可能买得起一辆自己的车。生活依旧窘迫,唱歌对他来说,成为只敢想一想的事。
21岁,马海阿甲结婚了。这一年,他和一个从外地人一起做松脂生意,靠着驮马与对高山地理环境的熟悉,他赚到了1000元,准备带着老婆回娘家(原本六个月前他们就该回娘家,但因为没路费而耽搁)。
在去程的班车上,马海阿甲看到一名乘客在喝一瓶易拉罐包装的汽水,易开罐的拉环被拉开的瞬间,汽水溅到了后排乘客的脸上,两个人起了争执。他上去劝架,被汽水溅到的乘客突然拿着拉环说道:“这个拉环好奇怪,上面写着奖金38000”,说完这句话,车上的其他乘客开始争相买这个拉环。
坐在马海阿甲身后的乘客说,可以和马海阿甲一起买,兑奖之后,马海阿甲分30000,那个乘客分8000。马海阿甲心动了,最终,他在这场竞价里,用700元买下了这个拉环。买完之后,之前哄抢的人都陆续下了车,马海阿甲开始觉得不对劲,他想要上前拉住那个卖他拉环的人,但被另外两个人压在了座位上。就这样,马海阿甲又没钱了。
24岁,马海阿甲第一次拥有了10000元钱。那时,马海阿甲家住的是木头搭出来的木楞房,房顶用牛毛毡盖着的,从外面能看到里面,从里面能看到外面。因为房顶只是一张牛毛毡,有时候,喜欢往高处爬的山羊的尿,会从牛毛毡渗下来,滴落到家里的地上,下雨天就更不用说了。
选择生存,还是选择梦想?马海阿甲选择了后者,他不准备用这10000元钱修缮房屋,而是要给自己做一首歌。
马海阿甲想唱歌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了,也持续了太多年,他觉得:“只要我能出歌,我就很了不起了。”

当时,有一个从马海阿甲家乡走出去的阿夏组合,正当红,马海阿甲在盐边县城里看到了阿夏组合的专辑,并关注到专辑封面背后印着的“成都摩尔音像制作公司”及其联系方式,他立马给这个公司打了电话,询问能不能帮他制作专辑,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可以。
就这样,什么都没多问的马海阿甲,孤身一人,带着10000元去成都找这家公司。他走的时候,除了老婆,没再告诉任何人,他从小做决定都不爱问人,因为他觉得问了也没人懂,他想:“有钱有权的人可以怕,但是穷就不能怕了,死也不怕。”
到了成都,马海阿甲见到那家公司的老板。
老板开口就问马海阿甲带了多少钱来?马海阿甲说带了8000。老板让他把钱都给他,随后给他开了一张简单的收据。他后来才知道,这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制作公司,这个所谓的老板最主要就是做磁带的盗版生意。没有网络的时代,只要换个地方卖盗版,根本没人知道。
成都待了两三天后,那个老板给他推荐了制作阿夏组合这张专辑的编曲师,陈泽坤。这是个真实的音乐编曲人。但陈泽坤不在成都,在北京,住在北京的一个叫东坝乡的地方。马海阿甲再次出发,坐着火车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马海阿甲坐着公交车到了陈泽坤的住所。在那里,他意外地见到了尼玛泽仁·亚东,一个在西南地区很有名的藏族歌手,也是陈泽坤的合作对象。
见到亚东,马海阿甲觉得很亲切,因为两人都是来自四川的少数民族。在与亚东交流中,他了解到亚东正在计划拍一部藏族电影,预计要花1000多万,这个数字让他很震惊:“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么多钱!”。
亚东和他说,少数民族一般都能歌善舞,所以有这个梦想是对的,但还是需要学习一些乐理知识。马海阿甲一点乐理知识都不懂,他说那时的自己“什么是节拍,什么是谱,我都不懂,都是乱来的”。
到了陈泽坤这里,马海阿甲通过哼唱的方式将前几年积攒下来的歌曲都展示给了陈,陈泽坤录下来之后帮他做谱,但其中很多歌曲因为不标准而没法做。
即便如此,马海阿甲还是为自己能“独立”作词作曲而自信:“我可以这么说,我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谈不上歌手,在我们彝族音乐爱好者这个圈子里,是唯一一个自己作词作曲的人。其他人多多少少都是向山鹰组合里的吉克老鹰拜过师或者接触过的人,受过他的影响,但我没有,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我怕他看不起我。”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马海阿甲住在陈泽坤住所附近的一个宾馆里,一天十块钱。和大多数第一次到北京的外乡人一样,马海阿甲去了天安门,他去的那天,正好赶上了汶川地震的默哀活动。
马海阿甲不懂什么叫做默哀,他只是听到有声音响起来,身边很多人站定,有的人脱下了帽子,大家都低着头,于是他也跟着大家做起同样的动作。
一天傍晚,马海阿甲走在路上,抬头看到了飞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飞机,他感觉飞机离他很近,所以他就一直跑,保证飞机一直不出视野:“我觉得我能追上它,近距离看它一眼,我一直跑,一直跑,我看不到飞机了,也很累,我就往回走了”。
马海阿甲在北京待了十多天,曲没有编好。陈泽坤告诉马海阿甲编曲需要时间,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让他回去等。
回到家后,马海阿甲就一直等一直等,偶尔会给陈泽坤打一打电话,只是,过了一段时间,马海阿甲联系不上了陈泽坤。他后来听说,那段时间陈泽坤的母亲去世了,而且他给成都老板的8000元,陈泽坤一分也没有收到。
那个成都的老板,马海阿甲自然也没能再联系上,他说:“在那个年代,报警也没用,因为找不到那个人。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没有再想过专辑的事。”
28岁时,马海阿甲的生活条件好了一些,出专辑也变成了一件比较容易的事:“似乎只要有点钱,大家就都能出专辑。”凉山地区出了很多他觉得不够好的专辑,他听着很烦,“我自己放弃了音乐,对唱歌的人也很反感。”
当时,有两个家乡的朋友想要成立一个组合,邀请马海阿甲一起。马海阿甲请他们吃了饭,但拒绝了加入组合的邀请,然后用2000元支持这两位朋友去做音乐:“其实彝族这个群体里,很多人,特别是25岁到40岁左右的人都喜欢音乐,也都想要做音乐”。
31岁,马海阿甲再次去到成都,在路边偶然看到一家叫做“爱琴海”的音乐制作公司,便进去问了问。他想继续把那张没有完成的专辑完成。
巧合的是,他在成都又遇到了陈泽坤。
陈泽坤没有食言,他早就把当时答应马海阿甲的四首歌写好了,但一直找不到他。
这一年,马海阿甲顺利地做出了《等你回来》这张专辑。
专辑做好后,马海阿甲就拿去卖。
那时的音像店都会做盗版,售卖的也大多是利润更高的盗版。马海阿甲知道,通过音像店销售,他几乎是赚不到钱的。于是,他就自己拿着专辑去各个地方叫卖。摆着地摊,拖着音响,在街边唱歌吸引大家去买他的专辑。他去了凉山的很多个地方,总共卖了三万多元。
马海阿甲对自己这张专辑的具体传播效果并不清楚,只记得:“当时有人在QQ空间里赞扬我,也有人用QQ和我联系,说听了我的歌之后,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如果能见到我一面,死也行。”
马海阿甲后来才知道,他的歌曲被爱琴海公司上传到了酷狗和一些其他网站上。
卖第一张专辑赚来的这笔钱,马海阿甲用来办了一个养猪场,只是时运不济,遇上猪价下跌,亏了不少,他没有钱再去做新专辑。
因为一直没有出第二张专辑,当地有人传言说马海阿甲已经死了,他一度非常生气。
2015年,又有了一些积蓄的马海阿甲,决定拍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色盖玛》(彝语音译,意思是:怪人,离经叛道的人)时,他找到了《惹格进城》中演“色变阿普”(彝语音译)的演员出演,这位演员很早就接触了影视行业,不仅会演,还会拍、会剪辑。
《惹格进城》是几年前的电影,它是第一部民间自制的彝语喜剧片,以刻录光盘形式进行售卖,销量很可观。其中,“色变阿普”这个角色因为身体缺陷显得滑稽,也被许多凉山地区观众熟知。
《色盖玛》拍出后,反响不错,这部成本只有4000元的电影,光盘卖了40000多元。电影里的很多台词,至今仍常常出现在凉山地区部分彝族群体的交流中。
马海阿甲说:“我本来自己就很喜欢喜剧,我很喜欢赵本山,所以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那个角色的形象设计就是模仿的赵本山在小品里的经典形象。”
马海阿甲(左)在《色盖玛》中的形象,模仿了赵本山在小品《不差钱》中的形象
2016年,马海阿甲又拍了《色盖玛2》,但拍完这部电影时,VCD、DVD在凉山地区近乎被完全淘汰,快手开始流行,没什么人买光碟了,《色盖玛2》没有赚到很多的钱。
2019年8月,马海阿甲又拍了电影《嘿觉》(彝语音译,意为感动),并将电影上传到一个叫做“票圈”的小程序上售卖,每个人每观看一次是6元钱,平台抽4毛,作者能拿到5.6元。电影《嘿觉》总共卖了11万多元钱,刨除成本,马海阿甲赚了7万多。
2020年3月份,马海阿甲拍了他的第四部电影《喜剧之王》,这部电影被放在了他的快手账号的小黄车里,赚了3万多元。
马海阿甲的四部电影都是名副其实的小制作,演员大概十来个,只有一台摄像机,没有专门的摄像和剪辑,都是演员同时兼任,全程拍摄大概三四天,成片45分钟左右。
马海阿甲既是导演,也是编剧,但他从来没有写过剧本,这些电影的情节都在他的脑海里,在拍摄时,他直接口述给演员们。
演员出演基本都是免费的,甚至在刚开始的第一、第二部电影中,有些演员觉得出现在视频里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愿意自费来出演。
2017年,马海阿甲注册了快手,但到18年11月,他才开始正式运营自己的账号:“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直播,是在跑车(在西南部分地区,因为山路崎岖,大巴车运行时间较长,且有时间与班次的限定。于是部分司机便用私家车当作客运车跑一些长途线路,这些车因为没有客运许可,因此也被当地人们称为“黑车”)休息的时候,我随便播了一下,就收到了180多元的礼物,我把这个事告诉我的哥哥,我哥哥不相信。”
因为之前出过个人专辑,马海阿甲的直播一开始就有人看,也有人打赏送礼物:“以前盗版磁带的传播,倒是让我有了一些知名度。因此,我一开始玩快手,就有了一些粉丝。在直播中,亲朋好友支持给了我很多钱,可以说,这三四年来,生活上确实不缺钱了。虽然并没有大富大贵,但生活上的开支确实都能满足了。”
马海阿甲之所以知道玩快手能挣钱,是因为当时在大凉山地区已经有很多网红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过一个叫做“阿比起”的网红,他自称凉山徒步第一人,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作假的,他经常坐车。不过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别人在直播间给他刷1000元,他就承诺给别人涨1000个粉丝,他确实能做到,不过听我一个朋友说这些粉丝,当晚涨完之后,过一两天天就又掉了,我那个朋友刷了38000,当晚确实涨了38000 的粉丝,不过了两天之后,就只剩两三千了。”马海阿甲怀疑阿比起背后有一个团队。
刚开始运营快手账号的第一年,马海阿甲直播的频率大概是一周一次,一次播一到两个小时,主要就是聊天,对着屏幕一直说话:“没什么技巧,别人说什么,我就回应什么。我确实也很能说,当时所有的彝族主播里我觉得最能说的两个人就是我和查尔木嘎,别人可能说一个多小时,就没话可说了,但我们俩能一直说。他比我还厉害。我一个弟弟对我能一直这么说的情况,也感到很惊奇,他问我这么一直说话不累吗,我确实没觉得累过。”
刚开始直播时,马海阿甲的粉丝只有1000多,直播间有100多人看,现在他有六位数的粉丝了,还是只有100多人在看他,马海阿甲搞不懂这是为什么。当然,马海阿甲直播间最多的时候,观看人数也达到过1万多。
更让马海阿甲觉得奇怪的是,他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给他刷礼物的人反而是最多的:“我一直讲,就有人一直刷,我让他们别刷,他们还一直刷。那个时候,我觉得别人给我刷礼物,我很害羞,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让我别直播了,他们觉得我像是一个网络乞丐,一直在和别人要钱。其实现在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不能接受。他们觉得我们是网络乞丐,但我觉得这个时代,越有能力的人越累。只有那些什么都不想不做的人,才会过得轻松”。
玩快手确实会上瘾,刷礼物也会上瘾。马海阿甲看到过有的人连包好烟都不敢抽,却能一百一百地给别人刷礼物,包括他自己:“这几天我就给别人刷了1000多元。我看着那些主播在直播时,给他刷一个棒棒糖他也很高兴,给他刷一个啤酒他也很高兴的样子,而且还不断地夸我,我也被弄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又给他刷了其他礼物”。
第一年开始玩的时候,马海阿甲在快手上的收入大概总共有五六万。
玩了一年后,马海阿甲发现了一些快手的规律,如果停播一段时间,人气就会减少:“比如说,我今天播了,停上三四天后再播,就会明显感觉到直播间里的人变少了,刷礼物的也少了。但如果我每天都播的话,总是会有一些人来看。”
所以马海阿甲就开始每天都播,一般直播的时间是晚间8:30,有的时候也会不准时。马海阿甲身边的人说他自从玩了快手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变少了,马海阿甲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一到晚上,我心里就会想,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我就没有心情去和他们交流。”
“我的任务其实是我给自己规定的一个硬性标准,就是每晚直播收入都必须到500元,不到500元我绝不休息,就算播到第二天早上,我也要播。”
每一天直播的收入和直播的时长和内容都有关,有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就有人刷几百元,有的时候,播三四个小时,一块钱都没有。有时候实在没人刷礼物,马海阿甲就会不断地对着粉丝们说“给一点嘛,给一点嘛”,这样依旧没人刷礼物的话,他会下播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播。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去倒一杯‘支诵’( 一种彝族传统的祖灵信仰仪式,在一般彝族人的家中都会有一个位置放置着酒与吃食,以敬祖先,祈祷祖先庇佑),祈祷一下,再去播。
总之,马海阿甲的日收入目标一般都能实现,最晚的一次,他播到了第二天早晨六点。
不过,真正会给马海阿甲刷高额礼物的都是与他不相识的陌生人,熟人其实反而不太会刷礼物。
曾经有一个很厉害的大哥,网名叫潇洒哥,每次到马海阿甲,都会刷两三千的礼物。有一次,马海阿甲直播到夜间12点过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刷了8000元的礼物,“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人是一个米易县的彝族女性,在外做生意,做得挺大的。这几年,厉害的彝族同胞很多了,很多彝族女性也组团外出务工,比如说做足疗,月收入也能在三万左右,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花钱也没有以前那么谨慎了。”
“我加了一些给我刷礼物的人的微信,但一般情况下,他不联系我,我就不联系他。因为害怕打扰到他。在这一点上,其实男女不一样。女主播之间可能会出现通过微信私信来进行“你偷我大哥,我偷你大哥”的情况。比如说,今晚我在你直播间看到一个大哥(在直播间,经常给主播刷礼物的观看者,与主播互动的频率较高,也会在直播间外互动,比如微信私信),那我就会加那个大哥的微信,联系他,让他变成我的大哥。但我们男性就没有这种情况。也因为这样,我们和女主播pk,一般都赢不了,因为她们大哥比较多。”
由于马海阿甲通常都在晚上直播,第二天上午睡觉。长时间的熬夜,他感觉自己的记忆力减退了。但偶尔几天不播,他就会觉得自己亏了。这种每天都播的频率大概持续到了2023年8月。那时,马海阿甲的月收入大概在两万左右。一个月除去开销,他能存下一万左右。
尽管已经运营了快手账号五六年时间,但马海阿甲从没有专门去学习过如何运营自己的快手账号,他的经验都来自于自己的琢磨。
“直播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很古怪,它不是说你有才艺就一定有人看。有的主播就是有人看。有的主播坐半天才说一句话,也有很多人看。有的主播一直不停在说话,却没人看。但有一点我很确定,能砸钱就一定能成名,因为钱能买粉丝,比如说花两三百万买五十万粉丝,在这五十万粉丝的基础上直播或者带货,就能把成本收回来了。但我们大部分彝族同胞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除非背后有能够实力比较强的公司去运营。”
“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次我跑车到昆明,另一个同行的司机和我一起,他看见我直播,他也跟着直播。和我一样把手机放在面前,我在这头对着直播间里的老铁说话的同时,他也一直对着他的手机屏幕在说话,还不断地说着‘给我榜一榜二关注一下’,我好奇看了一眼他的手机,发现他的直播间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问他,‘你在和谁说话?’他说,‘你不也这么说吗?’他只是在模仿我的行为和言语,但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懂得怎么直播。他只是觉得我以这样的言行可以赚钱,他就重复这个行为。”
马海阿甲总结自己的经验发现,只要多跟那些粉丝多的人互动,多和他们pk,就能涨粉丝。
*直播间pk是指一个直播间的主播对另一个直播间的主播发起挑战。直播PK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主播在PK阶段获取的用户打赏价值作为积分。PK时间结束后,获取PK积分较高的主播赢得本场PK的胜利,胜利方主播可以按照PK的规则惩罚失败方主播。“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打pk是提前商量好的,其实除了那种非常大型的pk之外,一般的都是随机的。提前约好的pk也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有矛盾,至少90%都不是,只是一种攒人气的方法。不过也有一些真的生气的时候,比如我和某个凉山网红有一次大型的pk,就是因为他说他家族的人有多厉害,如果我和他pk,我肯定会输,所以我就很生气(凉山地区的彝族家支观念是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就和他说,如果你真那么看不起我的家族,那我们就约一场试试。第二天我就联系了很多马海家族的人,我还专门拉了一个500人的微信群,让他们晚上来帮我打pk。那晚我就赢了。他输了的惩罚是喝了六瓶矿泉水。”
“其实很多网红都是玩套路的,我前几天看一个凉山做衣服的主播,刚开始看的时候,只有110多个人在看,我就在她的直播间里一直吵吵吵,后来就吵到了300多人,可是她不懂,把我拉黑了,其实我是在帮她凑人气。我后来去跟她说明原因,她还是不领情。所以其实说不准,谁有什么能力就会有粉丝”。
直播多年,当然也遇到过黑粉,马海阿甲会把他们说的话当耳旁风,他说聪明的人都是这样。实在看不下去,就直接拉黑,踢出直播间。对他而言,最让他生气的是,他在直播间唱歌的时候,有的人在下面评论说“现在是个人都能唱歌”。
“玩快手,大部分时候我都挺高兴的,只要能得到钱,我都高兴。而且我觉得人千万不要活在别人嘴里,有的主播虽然一直被骂,但相对应的,收入也不菲,如果不被骂反而赚不到钱。对不对?反正管他怎么说,只要有我的好处就行了。”
“其实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你变好了他们要嫉妒你,你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会骂你,事实上能帮你的人没有几个。我收藏了一个视频,主要内容就是只有你认识的人才会害你,不认识你的人不会。‘狗咬人咬生人,人咬人咬熟人。狗咬生人为主人,人咬熟人为自己。’所以不能活在别人嘴里,反正我们玩快手,就是很低级的网络乞丐,每个人都会来说几句,来阻拦。但你不要管这些,只要有自己的目标,你自己觉得对,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成功。”
尽管马海阿甲很看不上用人为制造矛盾的方式去获取流量的方式,但他在直播中,如果发现一直没人刷礼物,他通常还是会使用这种方式:“这个时候如果和别人连麦pk的话,两家的粉丝都会使劲刷礼物。”
只是在pk之后,他往往心里并不舒服,“我都会觉得良心不安,谁赚钱都不容易,感觉是我骗了别人的钱,但确实没办法。特别是一想到给刷礼物的大部分是在外打工的彝族青年,是我的亲朋好友,他们一个月也就赚几千块钱,他们家里的经济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很过意不去,也想过很多次停止玩快手,但一停下来,到晚上没事干的时候,刷一刷快手,看着别人玩,特别是看到我觉得比我差的人在玩,或者说就是在平时交流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都在玩,并且也有人支持,这就刺激到我在想,那我为什么不能玩呢?所以我就又开始玩。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家庭条件困难,没有别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我的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合适,之前在跑车,但除掉油费,过路费以及车辆的维修保险,也不剩什么了,没办法满足平时的人情往来所需要的费用。”
马海阿甲也带动了一些身边的朋友来运营快手账号:“比如现在快手上的‘阿喾阿佳’、‘阿喾阿呷’、‘沙玛歌金’、‘马海剑锋’等好几个彝族网红都是我带出来的。其中一个网红本身是一个农村姑娘,曾经在我的直播间里,给我刷过很多的礼物,所以我也带动着她,让她有了一些粉丝。她刚开始玩的时候,家庭也很困难,无法负担基本人情往来的费用,因此她还外出在足疗店打工过,她的丈夫也总是酗酒,赚不到什么钱,日子过得很难。自从她玩快手之后,我们经常互动来帮助她涨粉,她现在也没有在外打工了,而是在家全职地直播,家庭情况改善了不少。她在快手上的收入,基本可以满足她孩子的上学供养,人情往来等。”
“对我们来说,快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对于整体的快手平台而言,平台的好处比我们多几千万倍。特别是从去年开始,从快手提取现金,实际到手的比原来更少了,我个人能理解收取20-30%的手续费,但现在确实太多了。”
马海阿甲的收入全部来自于快手,手续费的变高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水平,他直播的时间越来越少,频率也变得越来越低。
马海阿甲认为:“按照现在这种玩法,最多再玩三年。因为如果一直就这样低级的pk,p来p去的话,人们就会慢慢觉得没有兴趣。现在已经有人去玩抖音了,因为对快手有一种疲乏感,已经没有好奇心了。”
“如果几年后,又出现新的东西,那快手就会被淘汰。”
刚开始接触快手时,马海阿甲觉得自己最多能干五年,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未来,马海阿甲还会直播多久,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