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印度各地数百万的女性来说,家政工作不是向上流动的道路,而是终身监禁。社会认为她们比性工作者更值得尊重,但也仅仅是高出那么一点而已。

我同意举家迁往印度,但有一个明确的条件:我要毫不愧疚、大手大脚地聘用家政人员。我要把购物、准备食材、烹饪、清洁和洗衣的活儿统统外包出去。汤姆的事业把我们推向印度,但我决心让我的工作也从中受益。我开始安排一个新的家庭模式,除了陪孩子和写作,我什么都不做。
全球经济再一次站在了我这边。印度的劳动力甚至比中国还要便宜。一个全职工人的工资,哪怕按照当地标准慷慨地支付,对我们的家庭预算也几乎不构成任何影响。所以,到德里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物色保姆。
我们是在夜深人静时着陆的。我第一眼瞥见印度,是透过出租车车窗望见的昏暗灯光下的片段:夜里罩上油布的市场摊位,在水沟里梭巡的野狗,在人行道上沉睡的人。在街边摇曳的昏黄灯光下和雨点的浸泡中,所有事物都模糊不清,一切都在雨季的侵蚀下慢慢地分崩离析。
最后,出租车停在一座服务式公寓大厦前,这栋楼极为干净,非常现代化,附在一座闪闪发光的巨型购物中心后面。我们用瓶装水刷牙,陷入无梦的昏睡,三个半人躺在大床上:汤姆、马克斯,还有肚子已经很大的我。汤姆的手机闹铃在早上响起。他冲了个澡就不见了。
我看着儿子马克斯,马克斯看着我。他如何理解这次行动——跨国搬家,转运行李,在我肚子里还有一个宝宝?
在自助餐厅,我在他盘子里放了一堆火候过头的煎饼、油腻腻的鸡肉香肠、木瓜片和菠萝。咖啡发酸,但我还是喝了一壶,牛奶在杯子里慢慢凝结。回到套间,我拉开窗帘,观察这个城市白天的样子。疑虑潜入内心。眼前的景观与我的想象不符。
汤姆几年前去过德里。他描述了成群的绿色鹦鹉在棕榈树上筑巢,摇摇欲坠的莫卧儿古墓,奔放的热带花朵。他曾邀我飞到印度参观泰姬陵,但我当时忙着在贝鲁特报道突发消息,没能去成。从那时起,印度就作为浪漫和错失良机的象征萦绕在我们心头。
现在,迎接我的是毫无特点的高楼和空地。德里的这片区域满是平淡无奇的建筑、无精打采的人和成堆的垃圾,就像其他一百个我从未想过要称之为家的城市一样,这里也隐约带有后末日的气息。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汤姆马上又投入到全面的报道工作中,安顿家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们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保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一切都似乎要把时间耗尽。这一切,包括乘坐出租车穿过拥挤得让人窒息的街道,到达拥挤的市场,通过危险的楼梯进入商店。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汽车擦肩而过,马克斯连站都站不稳当,于是我把他架在腰间,挺着一个大肚子,拽着一个德国牧羊犬那么大、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摇摇晃晃地爬上楼。
我需要一部手机和一张SIM卡。我需要一个医生帮我接生。我需要弄清楚去哪里买菜,这样我就可以在我们的小厨房里糊弄一顿午饭。我需要一个插线板。我需要拿着这个插线板去换一个能用的。我需要洗涤剂来浸泡水果和蔬菜。我需要水果和蔬菜。我需要回去看看为什么他们没有激活SIM卡。我需要护照照片。我得回去取护照照片。我需要再去一趟,带着孕妇的愤怒大吵一架,这样他们才会激活SIM卡。我需要驱蚊剂。
闲下来时,我和马克斯跟着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穿梭在德里各地。她穿着长裤套装,拿着写字板,对一切都很乐观。我们参观了鹿苑附近崭新闪亮的公寓,乔巴格地铁站房子典雅的大理石纹路,以及高尔夫球场公寓生硬的殖民地风格客厅。
租金太高了,通勤时间太长了,对着的街面太吵了。汤姆早就发过话,他不会住在建筑工地旁边,现在我意识到新德里几乎每个街区都在施工。我们继续看房,看更多的房子。
然后玛丽来到我们身边。
我开始写的是“我们找到了玛丽”——但感觉不对。不被找到,玛丽就不会罢休,在寻找着的一定是她。她是选择者——一个充满行动力和决断力的女人,永远如此,阿门。
通过邮件列表中一句无关紧要的评价,玛丽来到我们身边:“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把大孩子和婴儿都照看得非常好。”
我知道这则广告的简短可能是个不好的信号。大多数即将结束雇佣关系的雇主会用推荐信来弥补自己的负罪感,这些推荐信里充满了溢美之词,像小说一样不真实。这些女性是“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的”“不可或缺的”;她们是玛丽·波平斯和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混合体,所以聘请她们的机会不容错过!
当然,这些神圣的人物在午餐时给孩子们吃软糖和微波炉爆米花,或者在橱柜里塞满没洗过的盘子,或者害得一家老小食物中毒时,虚假的广告只会加剧幻灭感。但我是一个乞丐,没法挑剔——怀着身孕,筋疲力尽,迫切需要有人帮忙照看孩子。我打电话给她,她来了。
其他候选人会闻一闻,转动身子,焦急地环顾酒店套房,好像我们的临时住所预示着家庭不稳定。玛丽没有这样。她安静地坐着,双脚稳稳平放,双手放在结实的大腿上,脸宽大而镇定,注视着我的眼神带着聪慧。她的家族定居在不丹和印度之间的边境地带。她在大吉岭跟随修女学习过。她是寡妇,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由她在阿萨姆邦的婆婆抚养。
我等着发现她简历中的瑕疵,但没有找到。玛丽常年帮人照顾双胞胎。她在美国总领事家里工作多年,上过急救和儿童发展方面的课程,可以流利地说多种语言。警方已经核实过她的经历,而且为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她也接受过背景调查。
我告诉她,我不确定我们会住在哪里,但我列出了一些正在考虑的社区。
“没问题,夫人。”
我解释说,开始时她只能在酒店套房为我们工作,我知道这既不正规又很尴尬。
“没问题,夫人。”
“你不用叫我夫人。”
“好的,夫人。”
“不,我是说真的——”
“好吧,夫人。”
“哦……”我尴尬得说不下去了。
每周工作五天半,她的起薪是每月一万五千卢比,约合二百三十五美元。每月除工资外,我们还多付给她五百卢比的电话费,加上两千卢比的公交车费和午餐费——总共约四十美元。我们承担她的医疗费,每年给她两次五十美元的置装费。加班还是休息,选择权在她这里,如果加班每小时工资是一点五美元。六个月后她就可以加一次薪,此后每年都会加薪。
玛丽没有吹毛求疵,我并不惊讶。我做了调查,没有人比我们付得更多。我听说德里全职家政工人的最低月薪只有一百美元。玛丽接着解释了她唯一的条件:她不想住在用人宿舍里,德里的用人宿舍与许多中产阶级公寓是连在一起的。她的丈夫是尼日利亚人,两人在教堂相识,对他来说,和印度的用人们住在一起很不舒服——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人们有一点种族歧视。”她温和地解释道。
我向她保证,无论她住在哪里我们都不介意。
她就这样来了。她飞奔而来,大喊大叫着,微笑着。她原谅了我们的无知。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暴雨袭击了这座城市。马克斯站在窗边,对着那模糊、一望无际的银光惊叹道:“下雨了!”
玛丽打电话:“雨太大了。我来不了。”
“下雨了,所以玛丽不能来。”我告诉汤姆。
“给她回电话。”他说,“让我跟她谈谈。”
我把电话递给他。“玛丽!”他说,“听着,你今天得来上班。我不管你怎么到这儿来,但你一定得来。”
“她说什么?”他把电话还给我时,我没好气地问。
“没说什么。她说好的。”
“你确定——”我搜寻着合适的表达。
“她不能每次一下雨就不来上班。”汤姆打断我的话,感到难以置信,“我们不能开这样的先例。”
突发新闻闪过。玛丽住的社区被洪水淹没了。地铁关闭。公共汽车无法通行。进入紧急状态。
“哦,上帝,”汤姆说,“她为什么不跟我说情况有多糟?”
“你当时说得好像她不来就要炒了她似的。”我生气地说。
我们打电话想让她回去,但打不通。汤姆焦躁不安,皱着眉头,内疚地在窗前踱来踱去,一遍又一遍地拨着玛丽的电话。我和马克斯静静地玩。终于,有人敲门。玛丽浑身湿透了,裤子卷到膝盖。我准备好接受严厉的谴责和辞呈。
“实在是对不起。”汤姆赶忙说,“我不知道这场雨造成的后果这么严重。如果知道,我决不会叫你来的——”
“好的,先生,没事。”她说。
然后她开怀大笑起来。
马克斯午睡时,大家都要强制性地跟着休息。这种强制休息是我以前保持室内沉默的狂热残余:我要将我的反噪音巡查改头换面,作为慷慨的“停工时间”分配给所有人。我回到卧室写书,至于玛丽,在确信我是真的不想让她在马克斯睡觉时做任何事情后,她开始蜷缩在沙发上打呼噜。
一天下午,她跳起来朝门口走去:“我去上厕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侧身探头,朝着客厅问,“你要去哪里上厕所?”
“我去楼下,那里有个卫生间。”
“但是我们这里就有卫生间啊,而且有两个。”
她看起来有点困惑:“我不舒服。”
“噢!”我不知所措。要么她是在警告我,我们的感官即将受到一场特别奇异的攻击(如果是这种情况,那还是去楼下大厅吧!),要么一直以来她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她那卑微的帮佣的屁股不应该玷污我们神圣的厕所。
我陷入对玛丽私人需求不必要的沉思之中,对自己说的话感到后悔。“我是说——”我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不舒服,当然——”
“你不介意吗?”她打断我的话。
“介意你用我们的卫生间?当然不会!”
“好吧。”她害羞地说。
看着她走进卫生间,一阵悲伤将我裹挟。玛丽一直被视为贱民——禁止进入家庭厕所。习惯了更为自信、大胆的北京阿姨,我对此情此景感到震惊不已。我刚到印度,还不知道家政人员通常被禁止坐在雇主的家具上,用他们的杯子喝水或者用他们的盘子吃饭。
我还不明白,对于印度各地数百万的女性来说,家政工作不是向上流动的道路,而是终身监禁。社会认为她们比性工作者更值得尊重,但也仅仅是高出那么一点而已。她们愿意在别人家里工作,这表明她们很脏,不受欢迎。
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会懂的。
我过去做记者时的一个场景在街上真实出现了:成群的记者和卫星网络直播车挤满了整条路。我很想知道购物中心旁边的法院里正在上演什么国际新闻,于是给正在工作的汤姆发了条短信。
“是个强奸案。”他回答。
他只能说这些。乔蒂·辛格(Jyoti Singh)遭遇的强奸暴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我甚至知道这起案子涉及一个购物中心,但我没有意识到——现在我宁愿自己根本不知道——那个购物中心正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家的地方。乔蒂·辛格年仅二十三岁。她被诱骗到一辆公交车上,然后被人用金属棍强奸,直到器官撕裂,最后被丢到路边等死。现在强奸犯就在大楼下面受审。这是我们进入印度的首个窗口之一。
我感觉到我们住的酒店里也在酝酿着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但一开始我说不出是哪里特别。早餐时,我注意到婴儿和同性恋伴侣的数量异乎寻常地多。大多数伴侣都是白人,来自国外,他们彼此似乎并不认识,但仍然被一种情谊联系在一起,而我的家庭却被默认排除在外。他们意味深长地交换眼神,驻足欣赏着小婴儿,在彼此的耳边嘀咕着。慢慢地,我从无意中听到的对话片段中了解到真相:附近有一家著名的代孕诊所,在前往印度认领新生儿的伴侣中,我们住的酒店又刚好很受欢迎。
这些家庭疲惫不堪,倒着时差,还陷入了把孩子带回家之前要经历的跨国官僚机构的困境中。其中一些人已经困在这里好几个月了。然后我出现在那里,在一个明显有人居住的子宫的重负下蹒跚而行。
当我重重地沉进椅子里吃早餐,试图转移马克斯每天要吃甜甜圈的请求时,我并没有忘记人们会惊讶地回头多看我两眼:你在开玩笑吗?我本人既是其他客人无法拥有的一种身体状态的化身,同时也是对他们为人父母的未来的惹人厌弃、不甚美好的一瞥。一个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和一个可怕的两岁大的孩子,身处无法怀孕的人群中——我这是走的什么运啊。
但是,在被孤立许多天后,一个陌生人终于打破了我们周围的沉默。
“早上好。”他用欢快的美国口音说。
我抬起头。一个中年男子站在我们的桌子旁,一只手拿着热气腾腾的杯子,脑袋像鸟一样好奇地歪着。
“早上好。”我说。
“还有你,早上好。”他转向马克斯。
“你好。”马克斯轻声说。
我的新朋友是一位和蔼的美国教授,他的丈夫是一位好脾气的欧洲医生,正在帮我跟马克斯讲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好处。他们正试图把他们的新生儿带出印度。事实证明,美国的情况很复杂,所以现在他们把目标瞄准欧洲,在那里,他们会暂住在一位祖母家,同时解决美国的问题。
我不知道是什么激发他们接近我们,但我太想跟人说话了,根本顾不上别的。我描述了找房子的艰辛,而他们也抱怨着这几个月在酒店过的日子。我们吃完早餐还舍不得走,一杯接一杯地续着咖啡。
几周后,他们走了。走前给我留了张手写的便条,上面写着:“赶着出发。设法订到了机票。很高兴见到你和马克斯。请保持联系。”
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他们真的很有同理心,主动向我伸出援手,因为他们看出我当时过得很难,即使他们自己也身处挫败中。他们对马克斯一直很和气友好。他们考虑得很周到,原本可以直接去机场,消失不见,却特意给我们留下一张纸条。我想,这样的人一定会成为非常出色的父母。我很高兴他们找到了让自己的家更加完整的方法。
但在花了那么多时间思考母亲的身份和女性的消失之后,我也发现这种弥漫着的代孕氛围令人不安。怀孕的女性在酒店里无处可觅。她们的身体被世界各地的富裕家庭作为孵化器租用。有钱人家的胎儿从她们的循环系统中获取氧气,从她们的血液中汲取营养。胚胎汲取钙质形成骨骼,却让代孕母亲的牙齿松软、骨骼脆弱。但这些女人并不是母亲,婴儿并不是她们的——孩子生下来就要出口到国外。
我用手捂着怀孕的肚子,试着想象自己没有权利去爱那个在肚子里扑腾的小家伙。我试着想象,但什么都想不出来。我不是在谴责或宽恕,只是现实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些女性——甚至大多数女性——必须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度过孕期。我们都会出卖东西,为什么子宫不能卖呢?酬劳很不错,又急需这笔钱。
“我不喜欢那个。”玛丽断然说道。
我在马克斯午睡的时候问她:“你知道这些家庭在做什么吗?”哦,是的,她当然知道。玛丽从供应方那头了解到代孕。她认识一些为了钱生孩子的女人。
“酬劳很好。但是一旦孩子出生,就没有人照顾这些女孩了。”玛丽说,“她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她们会得病,年纪轻轻就死了。他们把钱给了这些女孩,然后把她们赶走。这种情况我见过太多次了。”
话很快说了出来,倾泻在空中。接着她回过神来。我问她的意见,但没有透露自己的态度。她看到过我在楼下和那对伴侣聊天。
“不过我也不懂。”她很快补充道。
“我想你是懂的,”我说,“你懂的比我多。但是,这些人、这家诊所声誉很好。可能没有你看到的那么糟糕。”
你是对的,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干干净净。当然,总的来说,你是对的,但这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女人们被扣在宿舍里做人质,以免伤害肚子里的挣钱工具,她们被迫通过Skype向远方的认领者展示隆起的肚子。但是有些女性不能怀孕,有些伴侣没有子宫,收养又很棘手。世界上到处都是被遗弃的婴儿,要获得一个孩子的监护权却非常困难、缓慢和昂贵。一些印度家庭让女婴挨饿,免得在她们身上浪费食物,然而,领养一个婴儿既昂贵又繁复。一切都安排得很糟糕,给每个人的选择太少了。我自己过去也急切地想要一个孩子。
可我仍然在想:为什么不管想要什么,你都能找到一个售卖它的可怜的女人呢?你可以买屁股、阴道、嘴巴或舌头。你可以买一个子宫,一个人类的温室,用来盛放人类的种子。你可以买双手来换尿布,可以买声音来唱童谣,可以买背和手臂来带孩子,可以买乳房来哺乳。你可以买到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个女人遭到残忍的侮辱,然后被人用阴茎塞住嘴,直到她吐到狗食盆里。这样的视频很受欢迎,男人喜欢看。但是,当然,男人从来不承认看过这种视频。说到罪责,总是别人的错。
流行文化要求我们把这些片段分成单独的现象:性工作、色情作品、家务劳动和代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交易都存在于同一个连续过程中——你可以从一个女人那里买到任何东西,然后把剩下的扔掉。
我是同谋。我直接而有意地做这件事。甚至就在我打字这会儿,我租来的女人正在书房外扫地,我能听到扫帚划过木地板的声音。读者们,你们也是。你可能认为你不是,但你可能是。你买的那些便宜的衣服和食物,你知道它们的供应链吗,你能溯及其原材料吗?你不能,也不想。我向你保证:任何便宜的东西都不是出自偶然。你们吃着奴隶制,把它穿在皮肤上,睡在它的怀抱里。我不是指隐喻意义上的奴隶制,我指的就是纯粹的奴隶制,那种很久以前就应该被废除的奴隶制。
另一种观点是,如果女性得到报酬,那就是赋权,其余免谈。我凭什么说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妇不应该把她的子宫租给富有的美国人,好为她的儿子挣学费?我凭什么说一个年轻女人不能在镜头前做享受被噎住的表演?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作为一个付钱租赁别人、害得母亲与孩子骨肉分离的人,我还有什么资格感到内疚?我有什么资格呢?我是谁?
我不确定了,因为那些女人都不愿说出我的名字。她们称呼我:对不起。夫人。
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所以你最好冒险一试。我应该以后再想这些,等我的孩子长大了,等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等我不会试图强迫丈夫待在家里,自己从事一份甚至都不想做的工作,到头来让我的家庭崩溃。等我终于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再来诚实思考就安全无虞了。
最近,我和刚来新德里时结识的那两位父亲中的一位互通电子邮件。他善良大方,提出要从美国给我们寄一个爱心包裹。他刚刚拒绝了回印度工作的机会,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在印度时的记忆。
“我拒绝了。”他写道,“那里离代孕母亲被强制拘留的地方太近了。也许等回忆褪色一点再来吧。也许。”
也许他也不想面对供应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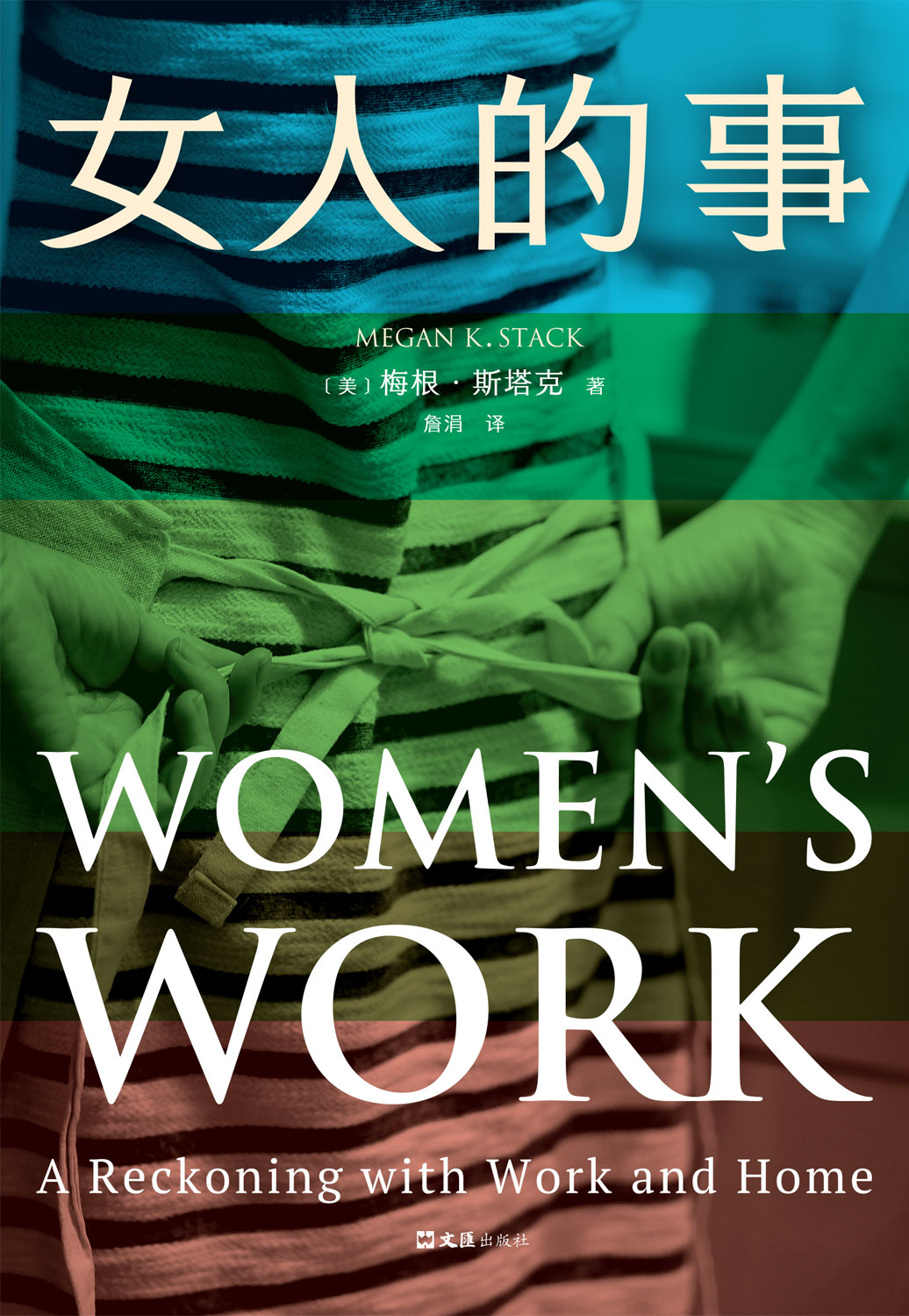 | [美] 梅根·斯塔克 著、詹涓 译 / 文汇出版社 / 2023年8月
| [美] 梅根·斯塔克 著、詹涓 译 / 文汇出版社 / 2023年8月
美国作家、记者。
曾任职于《洛杉矶时报》,
现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