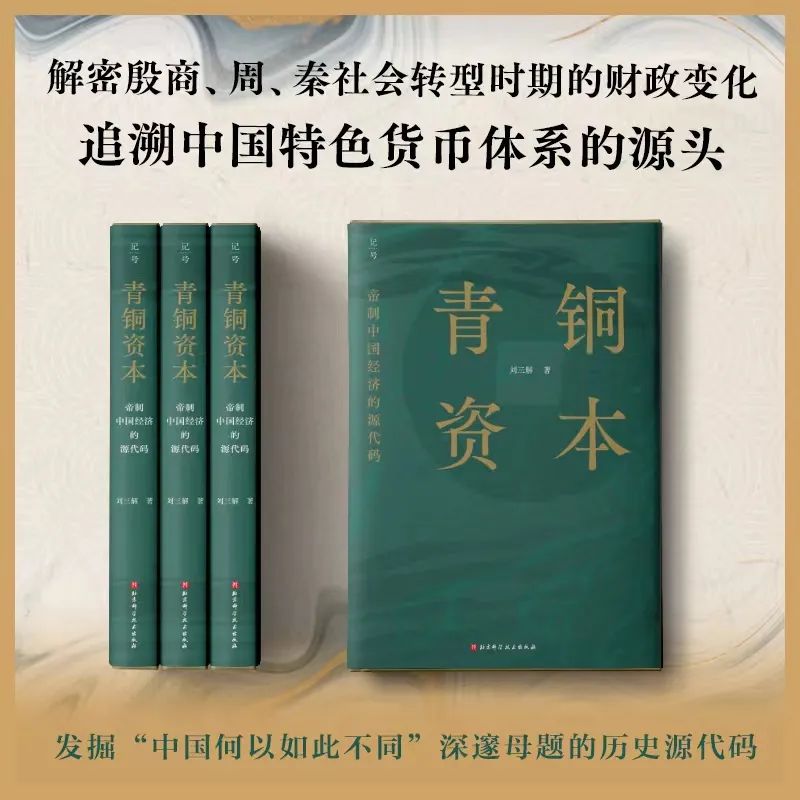
本文系刘三解著《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书摘
秦国,一个僻处西陲的小国,曾经被中原各国视同戎狄。可在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100多年后,秦王政一举扫灭六国,可谓弱者逆袭、弯道超车的奇迹样板。
在过去的2000年间,无论在价值判断层面,如何指斥暴秦,儒家知识分子对于“耕战政策”的效果都相当认可。陈陈相因之下,甚至大多数现代人也普遍认可“关起门来种地、尚武”,就是秦国并吞天下的关窍所在。
其实,这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灭六国的真正倚仗,是一项鲜为人知的“黑科技”。
一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这段话,是商鞅变法十年后,对赵良自夸自己治秦的成果,意思是:
秦国原本弥漫着戎狄的落后文化,父子的小家庭都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我商鞅教化秦民,为他们确立了男女之别,又大修咸阳宫室、都城,让秦国的教化可以像鲁卫这样著名的文明国家看齐,你看我治理秦国,和秦穆公时代的贤臣百里奚比较,谁更贤能?
显而易见的是,自秦汉之后备受推崇的“耕战之术”,并没有成为商鞅本人自夸的理由,他更关心的是自己将秦国落后的文化提升到关东各国“基本文明”的水平线上,说得直白点,商鞅本人都没觉得自己的“耕战之术”值得自夸,为什么呢?
因为种地求富,尚武图强,这是当时知识界的常识,无论是儒家的荀子,法家的申不害,或是被称为齐法家的《管子》,兵家的《吴子》、《司马法》,都是这个调子,这是当时的生产水平所决定的,往远了说,西周时代的邦国国人,照样是闲时务农,战时为兵,根本是一脉相承的产物。
可见,商鞅变法的功绩,不过是将一个落后的、与戎翟为伍的落后邦国拉进了当时的强国基准线上,所谓“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公允地说,商鞅从三晋之一的魏国带到秦国的“成文法”制度成果,只是让秦国得到了战国列强的承认,而不是什么“弯道超车”的灵丹妙药。
真正让秦国超越群伦的,另有其人。
《战国策·秦策一》中说:
蜀地就是今天的四川盆地。过往对秦惠文王夺取四川盆地的意义,往往从天府之国的农业生产入手,这是基于李冰修筑都江堰,大大提升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能力,进而引申出来的想象。
其实,蜀地四塞,东有三峡之险,北有大巴山、秦岭阻隔,对外运输粮食和用兵都是高成本、高风险的难题,除了司马错乘舟载粮,顺长江出三峡伐楚之外,再无大规模用兵、运粮的记录。至于北上支援关中,就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究其原因,成都平原至汉中有大巴山拦阻,数百里崎岖山路靠人力背负,运粮民夫还得吃饭,怕是到地方只剩下空麻袋了。到了汉中之后,交通条件虽略有改善,西汉水可通陇西,褒水、汉水可通南阳,可终究没有直达秦国关中腹地的水路捷径,只能翻越大山栈道,故此,无论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如何发达,对于秦统一战争都是远水难解近渴。
那么,蜀地凭什么能让秦国“轻诸侯”呢?

二
答案很简单,矿。
目前考古所见的商、周时期铜、锡矿主产区有八处:
(1)以赤峰—林西为中心的辽西铜矿及锡矿开发区;
(2)燕山南麓以承德和唐山为中心的铜矿开发区;
(3)中原中条山铜矿开发区;
(4)赣北铜矿开发区、赣北锡矿开发区;
(5)皖南铜矿开发区;
(6)常宁—衡阳一带的锡矿开发区和长沙一带的锡矿开发区;
(7)以大冶为中心的鄂东南铜矿开发区;
(8)成都平原西南邛崃一带的铜矿开发区。
从地理上看,地处中原地区的古矿区,只有今山西省中条山一处,战国中前期,都在当时的霸主魏国的控制之下,而诸夏文化区之外的几处矿区,秦国能够染指的,就只有成都平原这一处了。
要知道,蜀国一度相当强盛,《华阳国志》记载,“卢帝攻秦,至雍”,雍为秦国都城,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可见蜀国当时已全取褒、汉之地。到了战国时代,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秦国伐蜀汉中夺取南郑,同年即被夺回,10年后,蜀国又出兵攻楚兹方,能与两大强国在汉中往来拉锯,蜀国的国力不容小觑,这与蜀地丰富的资源禀赋密不可分,铜矿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流域、青衣江流域和成都平原边缘地带,如邛都 (今西昌)、灵关(今芦山)、徙(今天全)、严道(今荥经)、青衣(今雅安)以及朱提 (其北达今宜宾)等地,其产量之大,可以从广汉三星堆和古蜀国发达的青铜文明上窥见一斑。在今天被秦粉们津津乐道的秦国“流水线”兵器,主要材质就是青铜,来源,自然也就是这些蜀地的矿石。
巴蜀还有一项特产是黄金。据《华阳国志》记载,涪县(今四川绵阳市)、晋寿县(今四川广元市)均产金,其民“岁岁洗取之”,刚氐县作为涪水源头,也有金银矿。岷江、沱江、涪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也盛产砂金,或为山石中所出金,或为水沙中所出金,这些自然金的颗粒绝大多数极小。这些黄金矿源,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蜀地灿烂的黄金文明的物质基础,铸成了大量器物,而另一部分则通过与楚人的贸易,辗转流入了中原,成为了楚地富庶的见证。
夺取汉中、巴蜀之后,真正让秦“强、富”的,实则是充裕的铜料和黄金资源,前者可以铸造青铜兵器,后者则为秦王室提供了充裕的阶层内共识货币。尤其是为战国中期之后,列国之间动辄万金的礼赠、贿赂创造了条件。
据学者统计,《战国策》涉及“用金”的记载,共计53次,其中“千金”出现18次,“三千金”2次,“万金”3次,合计59010斤/镒,放在战国时代250多年的时间尺度上,实在不算多。可待到秦始皇统一前,《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到,“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始皇已经可以拿出战国七雄250多年黄金礼品总数的5倍来贿赂六国豪臣,秦国之豪富,可见一斑。
要知道,耕地里可是长不出黄金和青铜的。秦国是在占据青铜、黄金主产区之后,王室施行“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的政策,垄断金、铜资源产出,从而傲视群雄。
不过,你以为这就是秦灭六国的“黑科技”?当然不是,黄金和青铜顶多只是资源条件,既然是科技,就必然有创新之处。
三
提到黄金,大家当然会想到货币。感谢中学课本,告诉我们战国时代有齐刀币、晋布币、楚蚁鼻钱、秦半两钱等等货币的种类,那么,在这些货币出现之前,我们的老祖先们,在使用什么货币呢?
考古发现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货贝”,也就是原产于大海中的一种特殊形状的贝壳。货贝作为实物货币,几乎遍布东周全境,完全不受政权国境的限制,这意味着,货贝只能是基于价值共识的、区域经济自发组织的交易媒介,核心功能是提供“地域通货”,由于天然货贝的缺乏,骨、蚌、石质的货贝也被广泛使用,印证了区域经济存在根据自身自然条件“自发”制造通货的行为,可以归类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自由的货币”、“流通的货币”。
据张天恩1991年在《东周列国贝化的考察》一文中对出土春秋战国货贝的统计:“贝化在东周列国的大多数国家中均有出土,共计出有各类贝化约5万多枚。其中有些发掘报告没有介绍具体数字,以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准确数目者计有47950余枚。这些贝化从质地上大体可以分作十类,有海贝、蚌贝、骨贝、角贝、金贝、包金贝、银贝、铜贝、石玉贝和陶贝。另外还发现陶贝范45件,铜贝范5件。”这之中,铜贝有27341枚,占总数的57.01%,包金贝则只有72枚,金贝69枚、银贝4枚。
值得注意的是,秦国出土货贝的地点,均在陕西境内秦的本土,且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之初的秦国墓葬中出土的货贝只有两种,数量较多的是石贝,另有少量天然海贝,且前者出土的地点和数量都超过后者。
与之相对,春秋晚期的晋国都城新绛,已经发掘出土了铸造铜贝的币范,也就是浇铸模具,且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发现形制相同的铜贝,可见秦国相对于晋国的落后程度,乃至于资源的匮乏程度,在晋人铸造铜贝100多年后,秦人仍在用石头磨制石贝,当做货币。
恰恰是因为落后,秦国开启了一项管理技术上的“弯道超车”。
在秦惠文君二年(前336年)“初行钱”,形制就是我们熟悉的圆形青铜硬币,不过,不止有方孔,还有圆孔,故此,应该称之为“圜钱”。秦国自献公、孝公时代即开始与魏国在泾水流域展开拉锯战,魏国又是学界公认铸造圜钱最早的国家,存世魏圜钱中即有“漆垣一釿”,漆垣地处上郡,秦惠文君八年(前330年)并入秦国,故此,秦圜钱应为仿魏钱之制铸造,而且,战国时魏国铜器、钱币多标“釿”之重量,约15克,与秦制1两相近,且存世魏钱有“半釿”,半圆形制却没有铸造地字样,秦之“一珠重一两”圆孔圜钱应即仿魏之“漆垣(垣、共)一釿”之制,而“半两”钱则仿“半釿”之文。
也就是说,秦国“初行钱”,直接跨越了铸造民间流通的铜贝阶段,开始即仿造了三晋霸主魏国以重量标识钱文的“圜钱”。
这一步追上了200年的差距,铸造“圜钱”是不是秦国的“黑科技”呢?
抱歉,还不是,因为它只是拉齐到同一个起跑线上,远远算不上超车。

四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十月一日,一位名叫“尊”的秦人女子因“择不取行钱”被捕,经问审、复审,拒收行钱的犯罪事实无误,当月,由名叫“起”的益阳县令和县丞“章”、令史“完”判处“弃市”之刑,就是将人杀死后,在市场上暴尸十天,再由徒隶将尸体扔到乱葬岗抛弃。
秦始皇对拒绝使用法定货币者的惩罚竟是死刑。这个案例,恰恰补全了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中“毋敢择行钱、布”规定的后果,展示了秦朝对“行钱”的态度:“不用就去死!”
这个思路在经济学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名目主义”(chartalism),其创始人英尼斯在1913年就提出了,货币是政府债务的“代理人”,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政府要求人民用货币纳税,只要货币能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公平流动,哪怕它只是一个贝壳,一样拥有购买力。
这就意味着,秦国、秦朝的货币体系,直接忽略了价值、价格衡量这一步,人为指定衡量其他商品的货币尺度,用严刑峻法来维护“钱”的“无限法偿”,“钱文”标识的重量是虚假的,“含铜量”自然也就是虚假的,无论是在钱文上标识“半两”、“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四”,还是“两甾”等重量单位,其实都无所谓。
打个比方,假设1斤铜能够铸造50个铜钱,而官府定价,一斤铜在市场上卖100个铜钱,任何人为了脑袋,也必须无条件执行,当然,官府收税时,也必须按照这个定价来执行,这样,秦钱就如“名目主义”所说的,可以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公平流动,哪怕所有人都知道,秦钱就是一种纯粹的“不足值”货币。
问题是,秦的县级地方财政中货币收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计簿”的科目中,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钱的科目只有5种,占总数的17.86%。按照“名目主义”的理论,秦国有限的货币税收根本不足以赋予秦钱足够的信用。那么,秦朝货币在政府和民间的流动,一定是“出超”的状态。
按理说,市场上的货币供应过多,应该会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局面,可秦朝的特殊的财政体系,却恰恰借此开发出了货币的一项新的功能——借债。
正是这项新功能,促成了秦国最终扫灭六国的壮举。
在没有银行机构的情况下,秦国少府、各郡工室铸造出的新钱,竟然也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各县,县廷再用功赏赐钱或政府采购的方式,释放给秦民,这无疑是在没有金融行业的大背景下,创新出了金融业务。
五
事实上,秦民无论是受赏还是卖货所得的秦钱,本质上都是若干枚“一般债务凭证”,秦民将对应数量的“财富”(实物)出借给了“县廷”,“县廷”又将此“财富”出借给“皇帝(秦王)”,就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债务关系。
秦民在市场交易中支付“一般债务凭证”,获取的对应数量的财富(实物),就是一次债务转移。在稳定状态下,钱的持有者购买商品的过程,就是要求兑现“一般债务凭证”,完成一次“偿债”。
按照秦律,这一债务转移过程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市)、规定的方式(标价)、规定的流程(持券)进行,且必须持券留底,交易双方各拿“出”、“入”券,并将交易记录副藏于官。那么,在秦民主要从事耕种,手工业产品多出自官府“工室”,私营工匠也被聚集在“市”中售卖产品的背景下,秦钱所承载的债务转移,就完全处在政权的监控之下,无所遁形。
秦国的政治权力更将市场分割为两个大场景:
其一为王畿拥有大型市场和商贾聚集的都邑,如咸阳、栎阳、雍等中心市场;
其二为各县境内的小型区域市场。
相应的,货币流通环境也出现了分层,在都邑中心市场中,黄金的阶层内循环与行布的交易集散并存,又大量存在以行钱为单位的民间交易;在县域小型市场中,则是以行钱为单位的民间交易为主,行布参与的零星交易为辅。
当然,在这些交易之外,还有零星的社区内交易发生在“里”中,诸多核心家庭的互通有无,借用的地域通货就是货贝,低面额、可储存,只是不能纳税。
这些交易场景的区分,根源就是秦法对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所有居民被户籍严格控制在著籍地,使秦国境内形成一个又一个以县为单位的网格,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市场化的物资、货币跨区自发流动也遭到了禁止,各县到都邑的物流网络只能通过行政力量铺设,人为地恢复到了西周时代,距离遥远的诸侯国齐聚王都入贡的状态。
这就使得都邑的本地化商业相当繁荣,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到,秦文公、秦穆公都雍,举陇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多贾”,秦献公迁都栎阳,北临戎狄,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秦昭襄王治咸阳,后来成为汉朝帝都,长安与各陵邑,都是交通枢纽,人口众多,所以,百姓都乐于经营末业。
外来商路集中到都城,提供了商品的多样性,正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概括的,“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翠凤之旗、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作为“太仓”和“大内”的所在地,四方诸县、封君的剩余物资和采购需求在此聚集,都城中为皇室服务的“官营刑徒经济”可以提供远比县级市场更多、更好的商品,外国商人“邦客”也向此处汇集。
不同于畸形繁荣的都邑,各县封闭的货币区保证了货币不会自发地向区域外流动,物资却可以在行政命令下运输,同时,秦律将交易行为严格约束到市内,“择行钱弃市”的律令结合“告奸连坐”的管理手段才可以最大效率地执行。
换句话说,哪怕“行钱”、“行布”被换成纸片,通过对交易双方的人身控制,乃至于对生命安全的威胁,秦人也能赋予秦钱价值,并逼迫商品的提供者自发地为“一般债务凭证”来偿债,并接受政府债务的“债务转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当政府大规模超发货币时,就已经开始向百姓预借了相当于他家庭产出若干倍的财富,比如10年、20年,30年的未来。
六
那么,秦国货币制度相对六国的压倒性优势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性质完全不同。
因为东周、三晋“布币”的诞生与西周的“点对点”统治模式休戚相关,更与黄河流域的交通、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经过春秋时代的灭国征伐,今陕西省东部、陕西省中南部、河北省西部、河南省中北部的广大地域中,数目众多的“邑”被纳入了晋国的版图,固然有晋国诸卿的分治,地理上的阻隔,犬牙交错的归属,都让统治成为新的难题。
统治又分虚、实两道,虚者如同周人重视“仇匹”关系,晋人通过侯马盟书中常见的盟誓方式,在“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自然结构家庭”日渐兴盛的背景下,重新建立君臣效忠关系;实者则无过于军、财二事,即本地的军事权力归属和财政收入归属,后者更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可晋国诸卿乃至于后来的三晋领地不只是山川险阻,甚至还有隔绝的飞地,让这些领地仅承担军役和象征性的贡赋,不但无法供养没有连片王畿围护的王都,还容易积蓄力量形成新的、独立的政治中心,最终分裂国家。
在此条件下,由中央朝廷铸造可以在王都纳税的青铜铸币,以目标地的应纳贡赋为价值保障,由户籍编列于都城邑中的商人远途贩运物资,商人通过“操奇赢”获得“什二之利”,王都则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商人的租税和远方的物资,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官商利益共同体”。
此时,标识地名的青铜铸币就是一种仅限于王都和目标地兑现的“支付凭证”,这种货币的首要目的不是自由地流通,为民间交易提供便利的通货,而是为了更顺畅、更经济地获取财政收入,当然应归于马克思·韦伯口中的“行政货币”之列。
直白地说,六国的货币,是为了“点对点”的运输财富,当然也可以超发来预借财富,但其范围,却小得多,偿付能力也小得多。而秦国则无限发挥了半两钱的举债功能,甚至将其上升为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总结的,“‘债’是法律用以把人或集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束缚’或‘锁链’,作为某种自愿行为的后果。”在秦国,债务也是吏治国家与平民建立联系的一种重要模式。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两周遗留下来的制度传统中,“仇匹”关系和“策命”制度只能在精英阶层内适用,它与精英阶层“族”的代表身份息息相关,当自然结构家庭代替“族”之后,周制统治也就失去了对社会的全覆盖。
在此背景下,承认自然结构家庭对“族”的替代是一种模式,也就是关东六国,尤其是楚国的发展方向;直接由吏治国家替代“族”的角色则是另一种模式,也就是秦汉国家延续至今的发展方向。
秦汉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将人变成官吏账本上的“数目字”,成为国家随时可以调用的资源,对人的物化成为制度。这种物化不存在例外,君王之下的精英阶层也被置于这个逻辑之下,只能通过分润权力拥有相对权利,又因权力的不稳定,随时会丧失权利。
恰恰由于“物化”进行得彻底,国家对个体的核心家庭的剥夺也就越疯狂,逼迫核心家庭的生活质量,长期处于一个吃不饱、饿不着的水平线,而国家则可以通过货币,将其生命历程未来可生产的资源大量预借,反而让被剥夺者产生一种自身进行财富积累的“幻觉”。
结语
现实是,西周制度中的“族内公有制”传统在秦制下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尤其是“所有权”的全面虚化,让秦王、秦皇帝和贵族、百姓的“私家”实则置于同一个残缺的所有权主体地位之上,故此,王室逐利、贵族逐利、百姓逐利,无论如何口头上“崇本抑末”,都无法遏止秦民走向全面的利己主义。
在此条件下,要利用利己主义就要控制“利”的承载和表征,将“利”控制在政权手中,简言之,将财富置换为国家债务,秦民积累的所有财富都是国家债务的累加,物质表征就是作为“一般债务凭证”的货币,无论是官铸的青铜半两钱还是官营手工业出产的麻布,价值基础都是国家的债务,让秦民在“拜金主义”的驱使之下,与秦政权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自觉自愿地把统治的“锁链”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创造性地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