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生了孩子并不是罪恶……真正的罪恶是不对自己坦承,也不对孩子们坦承;真正的罪恶是留下一个不能说出、不能写下也不能透漏的黑暗秘密死去。”
“你绝对会后悔没有生孩子!”2008年,当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开始进行一项名为“后悔当妈妈”的社会调查时,这句警告始终回荡在她的脑海里。
母性是天生的吗?成为母亲是女性的天职吗?奥娜历时五年,与三代母亲对话,听她们说出这份被视为禁忌的“后悔”,从而写就《成为母亲的选择》一书,奥娜在“结语”中希冀:
“我们女性需要把世界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女性需要主宰自己的身体和人生;也需要主宰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想象力。”
本文选自第五章,在奥娜抵达之前,一个女性后悔成为母亲了,她能说出来吗?能向谁说?能获得理解吗?最关键的对象——她的孩子,要告诉TA吗?
最近几十年,情势已经变化到我们可以谈论母亲身份,以及母亲身份所引发的情绪。尽管“好妈妈”的形象形成一道屏障,使女性难以坦承她们在处理养育小孩而衍生的困难时多么受限,并导致她们隐藏自己的感受。
近几十年来,这道神话的围墙正在慢慢坍塌,虽然社会仍然期待女性要表现得和睦稳重,但已经有更多的母亲坚持她们有权利表现出她们的失望、敌意、沮丧、苦闷和矛盾。
特别是,这样的改变肇因于现今时代更广泛的变迁:今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要求拥有发言权,他们要求获得地位和权利,让他们能够积极地表达自我并最终让情势产生变化。然而,尽管世界已经这样变迁,关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限制正在被打破,但母性的感受远比单纯的喜乐和满足更为复杂。人们认为这些母性感受正日益与固有的“天生的”母性经验互相冲突——那些不满的、困惑的和大失所望的母亲的发声,仍容易受到限制与谴责。
举例来说,2013年4月,伊莎贝拉·达顿撰写了一篇文章。达顿是英国人,是个妈妈,也已经当了祖母,但她后悔自己有孩子。达顿所写的文章在发表后得到数千个评论,如以下这些:
“多么卑劣、冷酷又自私的女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替她肯定已经读过这篇文章的孩子感到难过,想想她的孩子会因此而多么伤心,尤其这居然还是印出来让公众阅读的文章。真的太可怕、太让人伤心了!我也不知道她的丈夫要怎么看待她,谢天谢地!孩子们至少还有个慈爱的爸爸可以照顾他们!”
“为什么你要说出这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保守秘密?你的孩子真是太可怜了。”
有人可能会说达顿活该承受这些打击,因为她在没有隐瞒姓名和长相的情况下袒露了她的后悔。但是用化名和匿名,在避免孩子得知真相的情况下来讨论一位母亲的后悔,是否就能避免这样的打击呢?我们可以在德国关于后悔的母亲的讨论下看到类似这样的意见:
“下一个我们要在网络上加上热门标签,一边顾影自怜一边公开讨论的人生后悔事物是什么啊?……好好改变你的生活吧,我想向那些母亲和父亲喊话:把你生活中的灾难归咎到孩子身上实在是不厚道。因为你的哭哭啼啼而把责任推到一台婴儿车上,实在是太容易了。”
“但你公开这么说……,说如果你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你绝对不会生孩子,你对自己成为母亲这件事感到深深的后悔,我觉得这太让人震惊了。先不说你周围的其他母亲、伴侣、朋友、邻居,就说你自己的孩子吧,因为他们有一天会读到这些文字并了解其中的含意,他们的母亲想要把他们‘退货’,那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你读了文章,然后发现你是你母亲一生当中最大的灾祸?”
事实上,不管母亲的叙述会不会暴露孩子的身份(不论是因为主动曝光或是因为暗示而曝光),结果没什么差别,这显示在这些谴责之下还隐藏着其他东西。他们重申那些关于母性的陈旧“真理”,那些痛苦忧伤的母亲经验没什么好谈的,谈论这个是十分粗鄙的事情,而且这样的女人会被视为是病态的。他们就分类等级和传统观点来评判这样“任性”的母亲,认为这样的女性经历是没有价值、文化低级的,所以她们都应该依照社会期望让她们的主观感受——作为女人或作为母亲都是——继续维持缄默或是重新整理一番。
女人和母亲会因为广泛的社会认知而受到谴责,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为了一点小事就抱怨的“嗷嗷叫时代”,所谓的自我放纵流行病横行的年代。我们可以说:正因为有越来越多不同的社会族群已经“获得允许”现身为自己发声,以破坏这个压迫性的社会秩序,因此这个社会更会迫不及待地为这些母亲贴上标签——“另一群被宠坏的、夸大的、言过其实的懦弱家伙”。(当然,不会有人去听这些母亲诉说的,因为没有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集体的如意算盘是,让“后悔”继续成为母亲简历上的一个内疚的秘密,是个人的失败,一切都是因为她们自己的问题。无怪乎这些后悔为人母的女性,谈到这些时都面临极大的恐惧,不管是在家里、家人间、朋友当中及工作场所都一样恐惧。
我在2011年3月与提尔纱碰面。她先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仍在为了研究而继续寻找访谈对象。她在一份以色列的报纸上看到这件事,有兴趣参与。
几天后我去她家拜访。提尔纱时年57岁,独自住在以色列中心的一个小镇中,两个孩子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他们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自立门户——而且也已经为人父母。
我们在她的厨房里进行访谈,而事实上,我们从那之后就一直在讨论这件事。她一开始告诉我的其中一件事情是她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她试着和同事谈到她后悔成为母亲,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
她对我说:“我的生活一直围绕着婴儿、父母和生育治疗,所以我知道很多女性的想法跟我一样,但她们自己都不敢承认,遑论告诉那些和她们最亲近的人。我理解那有多难,我深深明白,那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艰难,当社会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如影随形时,要从既定的秩序中剥离出来实在是太困难了。
“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有许多人是医生,他们不懂我想从他们那边得到什么。对他们来说,我像是只奇怪的鸟,他们不认为我是变态或其他什么,而是一只怪鸟,是的,他们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当我开始试着简短地跟他们谈起这个话题时,他们都努力地避开话题并逃跑,他们改变话题并驳回我的想法以试图压制我。在我们单位,我的想法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我工作的部门负责生产并鼓励孩子出生,而我的想法受到谴责。我觉得很遗憾,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也不想去了解,像只鸵鸟一样把自己的脸和耳朵埋入沙里,只随着惯性的力量移动。”
直到今天,提尔纱还持续在她的工作环境谈论她对母亲的观点,但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想去理解。
参与本研究的其他女性也提到类似的感受,她们试图和配偶、朋友及其他家庭成员(如母亲和姐妹)谈这个话题,或是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谈到这个。
布伦达有3个20岁出头的孩子。她说:“当我试图要跟朋友谈起我的感受时,他们马上不让我继续谈下去。‘你想跟我谈这个?试着感激你所拥有的一切吧!’我想,这真是当头一棒啊!所以我喃喃地对自己说,就安静吧,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送去医院治疗,接受吧,继续活在这虚伪的幸福中吧,戴上面具表现得跟其他人一样,继续这场游戏。也许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或许不是全部,但也有些人跟我有着相同的处境却不敢说出来。”
关于这一点,索菲亚则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她有两个不到5岁的孩子。这样的压力甚至是来自她的家庭,她的另一半。
“我的心理医生知道我有这样的幻想(想抹去母亲身份),但我不认为她非常认真地看待我的幻想。……我的丈夫逃避现实,他不许我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他要我装作没事,装作和其他人一样。……当我在网络论坛如‘我的人生已经了结’上写到这件事时,我立刻成为毁谤的中心。某些人很难接受这件事,他们的反应很大。许多在论坛上的孕妇都很害怕将来也会跟我有类似的感受,所以在我发言后她们马上又发了其他主题来试着让自己振奋起来。”
害怕被压制或害怕被指为异常,使得某些女性在接受访谈之前从来没实际触碰过这个话题。而另一个导致她们自我强制消音的原因,是害怕破坏她们亲人的人生,她们希望保护她们的挚爱,希望他们永不知情。
马娅有2个孩子,一个不到5岁,一个不到10岁,受访时还怀着身孕,她说:“我的丈夫不知道,我所有的朋友也都不知道,因为我不希望这个负担落在他们的肩膀上。他知道了以后又怎样?他会说他有个惨兮兮的老婆吗?我不需要这个,他脑海中的事情已经够他操劳了,他的生活很不容易,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把这个强加在他身上。所以这是我的坚持,我不和其他人谈论这个。”
在我询问她们是否公开谈论过后悔为人母,以及她们是跟谁谈论时,这些女性非常健谈,许多参与者表示她们会跟周遭的人谈论起这件事。
欧德雅有1个不到5岁的孩子,她说:“我的姐妹知道,她们非常清楚我很后悔,我曾经很明白地告诉其中一位姐妹说:‘你知道我的想法和感受,如果你可以帮帮我——就帮帮我吧!’而她对我施以援手。……我的姐妹理解我。”
巴莉也有差不多大的孩子,她说:“我的母亲知道,我的伴侣也知道,他们知道那件事(同时和婴儿玩耍及说话)对我来说有多艰难,那对我有多可怕。”
“还有其他亲友圈的人知道吗?”
“没有了。”
“为什么?”
“我难以坦承这件事,这就像是……耻辱。我觉得很羞愧。”
几位母亲提到,在谈论“我后悔当妈妈了”时,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幽默感拐着弯说。能避免招致羞辱的方式是嬉笑着谈论自己的苦痛,然后其他母亲能够加入一起吐吐苦水(而非直接说出后悔),或是跟那些还没成为母亲的女性谈这个。
夏洛特有2个孩子,一个十来岁,一个十七八岁,她说:“当我在职场谈这件事时,我的同事一开始被我吓了一跳,这话题让他们发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在夸大,这就是我应付这个的方式。而且我注意到,当我在跟人对谈时,如果我把所有的底牌亮在桌上,她们就会比较愿意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件事情,突然间这件大家一直不敢言说的事情也变得没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的策略是公开说明,这样的策略能保护我和我的孩子。”
在我采访提尔纱的几个星期后,她给我写了一封详细的长信,在长达8页的手稿中,提尔纱试着厘清更多她想在访谈时分享却没能说出口的其他想法:
“在我努力写这封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正在试着努力组织起我脑中的想法),并解释我个人为什么后悔生了两个孩子时,我发现这些文字正在减轻、削弱并推开那些令我痛苦的事实所带来的负担,而除了文字以外,我没有其他用以沟通的方式。(当然没有。还是说其实有呢?也许可以用跳舞的方式表达?)这些话使得那些难以承受的代价变得……让我比较能够忍受吧。”
这些试着找出对策来应付后悔这个情感态度的发言,本身就可能是折磨人的,而当人们和孩子讨论到这个问题时,社会将变本加厉地认为这样的讨论应该被视为危险的行为。
在过去的八年中,我针对后悔的母亲进行研究,一次又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些母亲们会跟自己的孩子提到这些事吗?”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答案远比“是”或“否”要复杂得多。而对我来说,更耐人寻味的是:我察觉到,问我问题的人几乎都期待听到否定的答案——也就是听到这些母亲不会在家里谈论这件事,因为他们觉得母亲跟孩子说自己后悔为人母是邪恶中的邪恶,这是一个邪恶母亲确凿的罪证。有时候让孩子知道母亲后悔了,比母亲后悔为人母本身更可恶。
提问者在问这个问题时,浮上脑中的脚本是:一个母亲因为她自私的需求而投注仇恨的目光在孩子身上,因为他们毁了她的生活,所以这个母亲后悔生下他们,她毫不考虑这将如何影响他们及整个家庭关系。
我们可以在下面这段话中看出这样的单一脚本:“没有孩子应该从他们的妈妈那边听到她不想要他们,这很残酷,很不公平,很不人道。”
这样的内容在现实中也可能上演,一个女儿对一个后悔为人母的妈妈颇有感触地写道:
“在孩子出生后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存在对母亲来说是个耻辱……这完全不是件好事,你不仅需要很多勇气,还要像病态人格那样冷漠。我向上帝祈祷,这些孩子永远不会听到妈妈怎么看待他们的出生,但我敢肯定他们都能感觉到母亲不想要他们、他们不该在这里、不该存在,这样他们的妈妈会比较好过些。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她因为我的出生而指责我,即使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对我大吼:‘要不是因为你,我的生活会截然不同,我会比现在快乐。’那时候这件事让我几乎昏厥,我的肩膀被压上一个重担,直到今天。我花了很长时间来了解我的母亲曾经受到怎样的伤害,她是多么无奈而有那样的感受,我明白了她有多么不成熟,直到她……”
我不能也不愿忽视这个痛苦的女儿的陈述,她需要承担来自母亲的责难,而且这不是她的错,她的声音必须被世人清楚地听见。然而母亲和孩子间不同世代的关系也存在其他可能性,例如,我们可以在另一位有着后悔母亲的女儿的叙述中看到:
“在我12岁时,我的妈妈告诉我,她后悔生了我。‘我希望你在成为母亲之前能够用够长的时间好好思考一番,’她在一个温暖的夏日早晨这么告诉我,‘如果可以让我再选择一次,我不敢肯定我是不是会生小孩。’
“天哪!在我12岁时,她的话刺痛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或者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真的希望我没有出生吗?而到了现在,20年后,我自己有了3个孩子,我才懂她的意思。那并不表示她不爱我,并不是说她希望没有生下我,而是因为她明白为人母意味着:她的人生不再完全属于她自己了。”
在说与不说的两难间进退维谷。母亲们除了在不考虑孩子幸福的情况下责怪孩子以外,还可能因为多种原因而情感紊乱,继而迷失方向。
英国裔澳洲学者萨拉·艾哈迈德将在社会及情感上迷失的经验,比拟为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或是在房间里面蒙上眼睛:如果我们身处一个熟悉的房间(因为我们先前曾经去过那儿),可以伸手去摸索并判断触碰到的是什么,先前的经验使我们得以确认自己身处的空间;但如果我们身处一个不熟悉的房间,伸手摸索无法协助我们导航。我们不清楚即将面对的是什么,这使我们不确定和无法决定什么时候要转弯,在这种情况下迷失方向是必然的。而在这之后,我们会怀疑人生是否真是一条直线。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处的境地并不稳定,而且这种时候我们会开始想象其他的可能性。
当成为母亲的体验里包含后悔,想做出正确的选择,却无法获得外部指引时,许多母亲会感到孤独。她们觉得自己被留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中,迷失了方向,必须重新展开探索,以找到原本的人生脚本中不存在的可能路径。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参与本研究的每一位母亲都在两难困境中(说或不说自己后悔、明确地表达或间接地提到为人母的困境、讨论为人母的不值得及不为人父母的可能性)试着找到自己的方法。
有些参与研究的女性基于三个理由而决定不跟孩子提到她们的母亲经验及后悔:为了保护孩子、为了维持和孩子的关系、为了保护自己。
索菲娅说:“为什么我不参与论坛(以色列的网络论坛‘不想生孩子的女人’)上的讨论?我差一点就那么做了,但……我怕有一天他们长大时会读到论坛上的文章,这让我十分害怕。当然我可以使用假名,但我还是害怕他们会发现我不想要他们。当然他们都知道,孩子们其实都知道。他们可以读懂我的心,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些时间,他们对这些事情很敏锐,但我不希望他们真的读到那些文章。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孩子的话),我想写的东西都可以成一本书了,我会公开做这件事并说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我真的很害怕孩子们会受伤。”
布伦达说:“(对于我要引述她的回答)我没问题,你可以以你需要的方式引用,但请依据我们签署的保密协定,不要泄漏我的真实信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到‘如果妈妈可以选择的话,她不会生下任何孩子,她事后回想起来,觉得后悔生了孩子’。但这主要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根本没有父亲,在孩子们的父亲已经抛下他们以后,如果他们知道妈妈也不想要他们的话,孩子们会怎么想?你能想象这样的情况吗?”
卡梅尔有1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我问她:“你身边是否有人知道你后悔了?你的家人知道吗?”
“嗯……他们可能知道,因为我曾经几次脱口而出,但我不跟他们谈这件事情。其他很多人也知道,老实说我没有隐瞒,我会小心选择坦白的对象,可是我不曾真正去隐瞒。这很有趣,当我听到有人说她后悔,我会上前鼓励她,告诉她:‘好。很好。继续坚持你的真实想法。’这真的很有趣,我跳出来鼓励她。”
“你是指其他不想要孩子的人吗?”
“是的。”
“你怎么说?”
“这样很好,我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你跟伊多(卡梅尔的儿子)谈过这回事吗?”
“不,不,那毫无意义,我只告诉他我很高兴只生了他一个,但没有告诉他,嗯……也许我会告诉他,因为以色列的情况,所以我现在不会生孩子了,或者其他类似的话。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将来也不会告诉他,那有什么用?那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
我问她们是为了保护谁而保密及保持沉默,以及要保护他们免除怎样的危险?有些母亲,像索菲娅、布伦达和卡梅尔,已经决定不会跟孩子们谈论她们为人母的经验和后悔,无论是暂时性的保密还是彻底保密,这都是为了让孩子不会受伤,她们认为“告诉孩子”是多余的。
她们希望保密的原因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在面对孩子时,人们很难清楚区分“后悔当妈妈”和“后悔生孩子”、“后悔当妈妈”和“爱孩子”、“当妈妈可能不像社会所告诉我的那样,值得我付出一切”和“我后悔生了你”。在跟孩子谈到这个议题时,如果没有办法妥善区别这些差异,那么告诉孩子母亲后悔了,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母亲的后悔会被解读为后悔生了孩子,孩子们可能会无可避免地认为他们的妈妈不想他们出生在这世界上。
此外,这样的认知可能会导致孩子们落入内疚和害怕的处境——以为是他们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引发了母亲的后悔情感,而没想到母亲们后悔的是“成为母亲”这件事,而不是孩子本身。
但就算不谈到害怕孩子们会内疚而影响他们的人格和行为,她们也会考虑到孩子们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的出生是种罪恶,自己让母亲受到折磨痛苦,让母亲的人生变调。这种复杂的忧虑可能导致母亲害怕她们跟孩子的联结会崩解,也许母亲并不认为母亲身份本身有多大价值,但她们还是可能非常珍惜和孩子之间的联结。
孩子和母亲之间的纽带通过对彼此不对等的认知而构成:社会期待母亲对孩子的一切知之甚详,但依据“不适当法则”,社会往往认为了解母亲作为人类的感情世界和见解是一种负担,是必须避免的负荷。正如卡梅尔所说,“没有必要。”
在现今的社会文化期待中,人们很难把母亲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并独立于孩子之外,母亲们被视为次要的,社会期待她们保持沉默。这个文化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是孩童导向的,社会并不将母亲视为有着需要和愿望的人类。
例如说,对卡梅尔而言,后悔是可以公开谈论的事情,但她不能在家里谈,为了保护儿子,她划出一个需要保密的“私人领域”,以及另一个可以自由公开讨论的“公共领域”。她们在家里保守秘密,将自己调整到完全符合孩子需求的状态——即使孩子们可能已经进入青春期或成年了。
除了希望保护孩子并保护母子关系以外,对自己的后悔保持沉默还能保护另一个对象:母亲自己。
提尔纱说:“要我跟儿子这样说:‘抱歉,我觉得我犯了个错,我不应该生孩子,我是个坏妈妈,我不想当个妈妈,我对此毫无兴趣,为人母使我感到厌倦,母亲身份毁坏我的人生并持续困扰着我。’这真是太难了——但那些话是事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
“我从没跟孩子们谈过这件事,但我肯定他们能感觉出来。很多时候我这样想:在死去之前我得写封长信好好说明这件事。但这是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什么而写这封信?我要在信里写我很抱歉自己不是个好母亲,(我没有)给予他们,(我有所)保留,我缺乏耐心,我对他们跟我说的事情、对我们之间的游戏和哼唱的歌曲毫无兴趣?”
她进退两难,她认为和孩子谈后悔是没有必要的,又觉得跟他们谈这个有其价值,能让孩子了解她。现在她仍然徘徊在隐瞒和坦承之间,为了逃避孩子们的视线,因为孩子们可能会凝望着她,批判她和其他“标准妈妈”比起来是个坏妈妈。在摇摆之间,她让自己保守秘密,她使用“保持缄默的权利”,希望能够借此保护自己。
提尔纱认为自己夹在谈论后悔及坦承自己是“坏妈妈”的两难处境中,然而卡梅尔不像她,卡梅尔划分得很清楚,她知道自己后悔为人母,但她也深深了解自己眼中及孩子眼中的母子情谊。
“就个人来说,现在的我知道自己根本不该成为母亲,这并不是因为我欠缺为人母所应有的能力,相反,我是个好母亲,伊多在任何时刻都会认同这一点。”
因此,对那些在研究中认为自己符合“好妈妈”标准的女性来说,她们之所以在孩子面前保持沉默,是因为要保护自己不被强制标记为“坏妈妈”,被贴上“不适任”的标签,而这样的标签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上——后悔是糟糕的情感态度,而且这样的态度必然反映出母亲的行为不当。
不同于这些决定不谈论后悔的母亲,其他母亲也可能为了同样的理由——保护——而做出不同的决定。换句话说,母亲可能为了保护孩子而对自己的后悔保持缄默,但同样地,母亲也可能为了保护孩子而选择跟孩子们谈论自己的后悔。
苏茜有2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她对我说:“你认为他们能自在地接受我的观点吗?因为我跟他们谈论了我的后悔。”
“你是怎么告诉他们的?”
“我说如果……嗯我记不清楚了,这星期我女儿问我,嗯……‘如果你可以让时间倒流,你会不会生孩子呢?’我回答她我不会。……我说了‘不会’,现在我夜夜难眠,担心得要命。”
“如果你的女儿未来告诉你,她不想要孩子呢?”
“我会告诉她生孩子确实没必要。”
德布拉有2个十来岁的孩子,我提问:“你觉得有一天你会和你的孩子谈论这个吗?”
“某种程度上我会和他们谈论。我无法直接走过去和他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因为没有孩子应该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会说的,尤其是和我的大女儿,告诉她我从来都不想当妈妈。她知道这个。她之前听我说过。有时候她会用这个来回击我:‘噢,你根本不爱我。你甚至都不想要小孩。’我告诉她:‘是的,我从不想要小孩,但是我有了你,我非常非常爱你。有孩子和没孩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你长大之后会做出自己的选择的。’”
罗丝有2个孩子,一个不到10岁,一个再大点,“在时机恰当时,我很确定我要跟孩子来一场‘母子对谈’——至少我得告诉他们我有的信息和认知,让他们知道为人父母是怎么回事、不当父母的合理性等。”
不管怎样,有些母亲决定和她们的孩子谈论为人母及后悔的经验,或是考虑在将来和孩子讨论,因为就她们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对孩子的保护。在她们的观点中,对为人母的主观感受保持缄默,可能会危及孩子和自己,因此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她们必须跟孩子分享为人母的苦难及这样的苦难可能不值得的想法。
贾丝明有1个很小的孩子,我问:“你觉得自己有一天会跟孩子谈你的后悔吗?”
“跟谢伊(贾丝明的孩子)谈吗?我很确定我会跟他谈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我读了很多关于为人父母的书及学习谈话的方法,而且这些书里也谈到我们必须跟孩子谈,即使他才两岁大。所以,每天睡前和起床时,我们都有几分钟的交流时间。
我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我告诉他我的感受。……从怀孕时我就拍了许多照片,它们非常令人惊奇,其中一张照片上我有着大肚子。我们坐在我的房间里面,我告诉他:‘知道吗?谢伊,就在两年前我有了宫缩。’我开始跟他分享,我说话,而他坐着静静听我说。我给他看了一张他还在我肚子里面时的照片,告诉他我的感受,生下他时多辛苦,我一开始对他的感受如何,而他的魅力又是如何让我渐渐地爱上他。
我真的跟他谈论这些,而且我相信我该这么做,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养育我们长大的,她告诉我那些我可能不喜欢听的话,这使我成长为现在的模样,而且这是好方法。停止讨好孩子吧。我不讨好谢伊,他是我的儿子,我不是他的朋友,我不相信明确的分界,而是相信完全的开诚布公。我真的如此相信。虽然在现实中要这么做并不容易。”
马娅说:“看吧,我一直这样想,并告诉我自己,等我女儿长大了——我会跟她谈这个。……但同样地,我们无法预料未来会怎样,她可能会想要孩子,而她也可能真的生了孩子并且一切都好,但我知道如果她生了孩子并有了跟我一样的感受——那将全部都是我的错。如果她在往后的人生里有跟我一样的后悔,我会知道我在最重要的时刻犯了错。
在这些忧心忡忡的话语中,马娅指出了一种对女儿的特别责任,一个许多人没想到的观点:“为孩子的人生做准备。”这是父母的重要功能之一,社会期待家长们能教育他们的子女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让他们能够融入这个世界并受到社会大众的接纳,找到自己的归属。
一般来说,这样的引导多半是通过教导孩子重复其他人曾走过的路,包括那些父母曾经做过而且有效果的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孩子的人生做准备也包括引导孩子不要重复父母曾有的错误和不当行为。
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当父母要孩子们谨慎小心,希望拯救自己的子女免于伤害时,这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小心!换个方式吧!”但婚姻和生儿育女例外,不管父母感受到的挫折有多深,或是在离婚或疏离后感到多失望。但看起来大多数人还是引导孩子寻找伴侣及生儿育女,不仅是以爱为名,也因为社会的共同假设:这是必须遵循的“自然人生轨迹”。
因此生育的传统被一代一代传承,社会鼓励我们一起前行,从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走到下一个里程碑,这个假设使得所有的男孩和女孩朝同一个方向“长大”,并自然地导致他们走入婚姻、为人父母,即使他们其实并不想要。
酷儿理论反对这样的假设,酷儿理论认为童年是一个更多元化的历程,孩子并不是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前进”,在他们眼前其实有许多“岔路”。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幼儿在玩乐及自我探索时是毫无顾忌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变成喜欢的任何模样。他们可以在想象世界中成为消防员、航天员或是环游世界的旅人。对他们来说,一切皆有可能。青少年(虽然他们大多数会因为同侪压力而羞于与众不同)则常常反抗成人的禁令,并以“事情如何运作”为起始点问出一大堆问题。
正因为孩子不会自然地趋向同一方向发展,所以社会认为孩子们需要被好好引导“调整”一番,以便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的欲望、取向及存在模式一开始就已经是规范化及异性恋的,那么父母不需要严格指导我们便能将我们全体推向共同命运——结婚、抚养孩子、异性恋生殖。”
也就是说,“男孩和女孩们需要引导和大力的推动,去走那条笔直的路线”这个假设本身,恰恰证明了这些孩子是没有秩序及不受时间左右的紊乱者,所以“推动”他们走向摆在面前的道路(而非其他岔路)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男孩和女孩们只能从周围环境放在他们眼前的有限选项中选取。他们会偏向于我们所提供的任何东西,任何“靠得够近”的东西,任何摆在他们面前的各个领域的东西:阴柔气质、阳刚气质、性别认同、性倾向、婚姻、怀孕和养儿育女。
与这样的引导相反,有些母亲可能会拒绝(或考虑拒绝)继续让下一代复制这条“笔直的路线”,她们的方法是利用一种不同的亲子对话——就如同马娅所陈述的,希望保护孩子们,不要重复父母犯过的错误。因此,通过谈论父母身份的含义,特别是探讨后悔,这些父母向孩子展示其他可能的路径,一条和异性恋规范及推崇为人母的文化截然不同的道路。
德布拉说:“她(德布拉的女儿)的确谈到有一天会找个男人交往。至于孩子,她说:‘如果我有孩子或孙子,那么……’我很喜欢她用‘如果’。我说自己是个好家长,好吧,这件事更证明了我是个好家长。我让孩子有权利或能力去考虑她的选择,处理这些事物,并为自己做决定。而我认为这是我们身边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特别是孩子们。
“如果这件事是最重要的,那我要说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了。在我的世界观中最好的。我很喜欢我女儿——在正视我这些事的时候——还愿意给那些被认为是十分明确和十分必要的事物打个问号,我真的很喜欢她这点。你知道吗?如果我想的没错,我甚至不期望有外孙。”
提尔纱:“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在我的儿媳妇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我买了一本《女人所生》给她,让她读一下。我不知道她是否读了那本书,送她那本书的时候,我脑中所想的是想让她知道为人母是怎样一回事,孩子是怎样一回事,为人父母的政治学及母亲身份代表的意义,她需要为她的后半生付出怎样的代价。”
除了试着通过送书传达信息以外,提尔纱还没下定决心——从受访那时,直到今日——是否该跟孩子们直截了当地谈论她身为母亲的经验以及她的后悔。她在受访后寄给我一封信。信中,提尔纱还在继续思考着不去遵循社会所给出的唯一路径: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孩子(特别是对女性来说),我们应该教育他们,消灭那些我们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及自我辨明,这是很重要的。这一切是为了不要落入刻板印象和因循守旧的网中,是为了不继续对自己说谎,并对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辈坦承。我们要以外科医生的精确程度,去检视那些已经变得如此“正常”和“自然”的委婉话语,例如“孩子是一种喜悦”“孩子是一种祝福”“血浓于水”,或者“家庭第一”。如果我们不去小心看待这些委婉用语的破坏力,它们就会构成社会和文化DNA的一部分,我们就会相信事情应该就是这样的,并且永恒流传。
“后悔生了孩子并不是罪恶。……真正的罪恶是不对自己坦承,也不对孩子们坦承;真正的罪恶是留下一个不能说出、不能写下也不能透漏的黑暗秘密死去。”
然后,提尔纱描绘出另一种世代传承:父母有义务向孩子说明其他路线的存在,而不是直接引导孩子沿着“那条直线”走。然而,如果她透露了自己的另一面,可能会影响孩子、影响她自己、影响亲子关系,所以她仍然不确定要采取怎样的方式:
“我找不出什么理由去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写下来,但我应该这么做的。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这么做。我还在思考着这是否重要,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的想法和我对为人父母的态度,这所有的一切。”
在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之间的仔细斟酌,源自于反复考量说出或者不说出后悔可能会导致的后果。虽然母亲可能会为了多层面的保护而选择沉默,但选择不将自己的后悔说出口,可能会使她们付出昂贵的代价:为了继续留在那条“好妈妈”的狭窄道路上,社会希望这些母亲能够绕开她们的真实经历并自我筛选,以创造出一套符合社会期待的说法。
那套说法会是偏颇的,只包括社会期待她们说的那一部分,好让她们能被视为有道德的女性和母亲。她们被要求只表达那些得到同情和赞赏的部分,只留下社会“允许”她们说的部分。而那些不符合霸权体系的部分必须被摒弃、过滤、抛在脑后。
这种希望母亲能对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保持沉默以保护儿童的社会期待并不罕见。我们可以在各种文献(无论是大众文学或学术资料)中看到不同的案例,它们都希望母亲不要从她们的观点来叙事。
这既是因为缺乏语言,也是因为难以想象她们的故事如何不破坏她们所珍视的东西:保护孩子,让他们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而这会压缩母亲的空间),与孩子保持一定的联结。在我所找到的最好的散文集之一《为何是孩子们?》里,编辑说他们找过那些对成为母亲这件事感到不满的女性。他们确实找到了,但这些母亲却不愿意撰写文章。因为这些女性担心如果承认自己有多么不喜欢当妈妈的话,将会伤害到自己的孩子。至于那些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当妈妈的女性呢?一样的,还是“孩子在知道妈妈不想要他们时是会受到伤害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很难找到母亲来谈论那些违反(各种角度)她和所属社群定义的“好妈妈应有的想法、感受和举止”的事。而当有人愿意谈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有许多人陷入了困境,在符合她们经验的自述和符合社会可接受范围的表述之间徘徊。
夹在自己与孩子之间,她们继续付出代价。当妈妈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被社会接受而无法跟孩子分享自己的经历时,孩子就无法从母亲的重要经历中得到借鉴。他们无法得知“成为母亲”可能只是文化和社会期待的副产品,“成为母亲”并非是或不完全是遵循自然;而那些分享真实经验的母亲,则被从家庭人际关系中切离。
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而将她们的陈述包装成符合社会期望的样子,但这可能会阻碍孩子了解母亲作为一个人是怎样考虑、思索、评估、渴求、希望、梦想、记忆、哀叹、想象、欣赏及决定的。
在这些方面,公众眼中、家人眼中及母亲自己眼中,母亲形象是没有脸孔的,或是往往隐藏着自己的脸孔,就如同露西·伊利格瑞精妙的描述:“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快有了女儿,成为母亲。在这两个形象之中,哪个才是真正的你?你自己的空间在哪里?哪一个形象是你纯粹的自我?你该如何越过所有的面具,让自己真正的脸孔显露出来?”
(本文选自明室Lucida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为母亲的选择》,略有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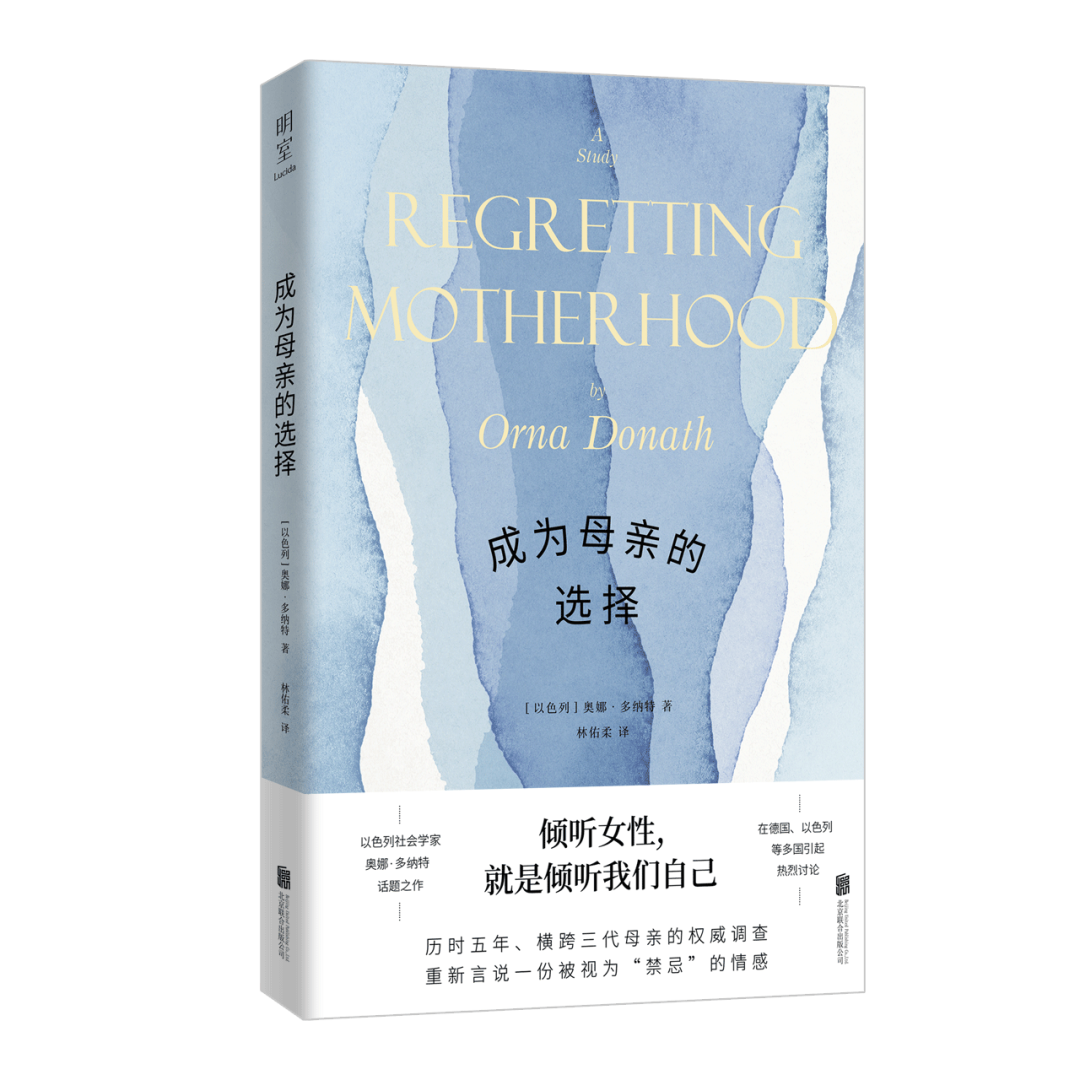
| [以色列] 奥娜 · 多纳特著/ 林佑柔译/ 明室 Lucida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02月
1976年出生,
目前于以色列高校任教,
研究领域为
女性所面对的社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