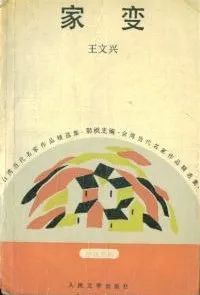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
作者:黄子平
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向度的和有意义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过程只有在社会的注视下才能完成。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巴金的《家》是一本幸运的书,它的续篇《春》和《秋》也跟着交了好运。正如一切关于幸运的故事的开头,最初,《家》以《激流》的题目在上海《时报》连载的时候,颇为命乖运蹇。若不是巴金跟新换任的编辑说最后几章的稿酬不要了,《时报》上的这部长篇小说便会成了“断尾巴蜻蜓”。随后,开明书店的单行本却大受欢迎,仅在1949 年以前便出了三十多版,销行数十万册。此后,到 1978 年,仅北京一地就印行十五次。它还先后三次被改编拍摄成电影,亦曾被改编成话剧、粤剧、越剧等等。
谈论一本书的命运,尤其是谈论像《家》(包括《春》《秋》)这样的书的命运,在这里颇有点意味深长。依照巴金的说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写命运(旧家族的命运以及旧家族中的年轻的生命的命运)的大书: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不能忘记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无数年轻的有为的生命成为垂死制度的牺牲品,这是不公平的命运,“是的,我要反抗这个命运。我的思想,我的工作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我写《家》的动机也就在这里。” 命运被一分为二了:一是“必然趋势”,无可挽回的灭亡的命运,属于那个旧家族旧制度,以及作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个人;一是“不公平的”,作为旧制度的牺牲品的命运,应该反抗,因而也就可能改变的命运,属于旧家族中那些可爱的、有为的、年轻的生命。
巴金在解释《秋》的书名时曾对此作过象喻式的说明:《秋》里面写的就是高家飘落的路,高家的飘落的时候。高家好比一棵落叶树,一到秋天叶子开始变黄变枯,一片一片地从枝上落下,最后只剩下光秃的树枝和树身。这种落叶树,有些根扎得不深,有些根扎得深,却被虫吃空了树干,也有些树会被台风连根拔起,那么树叶落尽以后,树也就渐渐地死亡。……高家这棵树在落光叶子以后就会逐渐枯死。琴说过“秋天过了,春天会来……到了明年,树上不是一样地盖满绿叶”的话。这是像她那样的年轻人的看法。琴永远乐观,而且有理由乐观。她绝不会像一片枯叶随风飘落,她也不会枯死。觉民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必须脱离枯树,而且他们也一定会脱离枯树。(高倘若对这种象喻作学究式的推敲,就会觉得”脱离枯树的绿叶”这样的意象颇有几分古怪。问题不在于学究式的推敲是否过于迂执,而在于为何这一象喻对作者和读者都显得如此自然贴切毫无疑义。)
“秋天”被必然地派给了枯树枯叶,“春天”却理所当然地“属于我们”。我想指出,将命运作这种一分为二,对《激流》三部曲,对作家巴金,乃至扩大而言之,对近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生存策略。不妨略略比较一下法国作家左拉。巴金二十四岁时在巴黎和马赛,用三四个月的工夫一口气读完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的二十部小说。三十年后巴金回忆道:
我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我尊敬他的光辉的人格,……但是我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尽管像《酒馆》、《大地》等等都成了世人推崇的‘古典名著’。我只有在《萌芽》里面看到一点点希望。坏人得志,好人受苦,这且不说;那些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
青年巴金的这种“读者反应”颇能说明问题的症结,巴金确实深受左拉的影响(亦以《萌芽》作书名,反覆征引”我控诉”的名言以自况等等),可是左拉那个身穿社会生物学的绝望外衣的命运女神,却断难被巴金和像他那样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爱弥尔·左拉,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似乎有必要参照一下从严复起数代人对达尔文、斯宾塞的“创造性误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存”二字的光辉照耀百年来中国人摆脱生存困境的道路。“变异”压倒“遗传”。“五四”以来写大家族衰亡的长篇作品多矣,“遗传”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却显然未被重视。(曹禺的《雷雨》似乎是个例外,易卜生《群鬼》的影响是重要因素,更有戏剧写作与小说写作不同“惯例”的制约等等。)“肖子” 不再是文学兴趣集中的形象,人们乐于看到或者写出两类“变异”了的“不肖之子”: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蛀空树干的虫子”(克安、克定之流),和大胆反抗命运的叛徒——“脱离枯树的绿叶子”(觉慧、觉民、琴等等)。他们分别代表着一分为二之后的两种不同命运。微妙之处在于,谴责前者的“不肖”与赞扬后者的“不肖”意味着对先辈采取了某种不易为人察觉的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这一点我们放到后边讨论。
令人感兴趣的是叙事观点(角度)历史性地完全转移到年轻的叛逆者时,“遗传”的重负似乎已被胜利地卸去。我们记得鲁迅的“狂人”的绝望,背负几千年“吃人历史”的被吃者也难逃吃过人的干系,希望仅仅在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那么谁来救他们?吃过人的父亲们是否能够、是否有资格来救未吃过人的纯洁的孩子?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便是由《说唐》的一个情节转化过来的那个著名意象:“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里去”。这篇文章的题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点明所取的叙述角度正体现着先觉者的全部承载、负担、反省和救赎。当叙述角度完全转到纯洁的孩子们这边时,他们已然立足光明决绝地向黑暗宣战,命运的截然二分至此才告彻底完成,“脱离枯树的绿叶”这类颇有几分蹊跷的喻象才从不引人怀疑地流通于世。
孩子们认同后——命运的唯一中心依据便是他们是孩子,同义反覆的叙述圆圈构成一整套空洞的能指符号(青春、生命、幸福、爱情、美丽、新、时代、未来等等),因其空洞而激动人心,因其空洞而获得强大的解释力量,并终于在一九三年代成就一个完满的现代意识形态神话(而鲁迅却在此前后宣布自己的“进化论思路”完全“轰毁”)。《激流》三部曲的成功和幸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种神话性写作的完满体现。
鸣凤投湖自杀的第二天,觉慧在湖边,愤恨、内疚、绝望:“我是杀她的凶手!”觉民劝解半天无效,最后念出一段觉慧平日常念的、屠格涅夫的《前夜》中的话:“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紧接的一段描写充分说明了上述“中心依据”的神话治疗功能: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
另一个“同义词”——“爱情”——亦具有同样的咒语般的治疗或反治疗作用。爱情既是后一命运的解药又是前一命运的毒药。对奔向新前程的孩子们来说,它是信念,旗帜,屏障,是射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是社会乌托邦的情感对应物,唯独不是爱情本身(《激流》三部曲中的“爱情”甚至有意无意地涤除了其中的性爱成分)。每当琴这个人物出现在高家花园里总是带来色彩和亮光(尤其在《春》与《秋》中),她就是爱情的光明的象征。在高家花园里,只有爱情无法实现的痛苦,爱情被“父之法”摧残阻挠的痛苦,至于爱情本身的痛苦(嫉妒、猜疑、失常、兴奋、争吵),爱情实现之后的痛苦(”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则被一概掩入叙述的盲区。显然,非如此不足以保证爱情的纯洁性和战斗性。这种纯洁性和战斗性必然要求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殉道式的献祭。鸣凤、梅、瑞珏、蕙,湿淋淋的尸首,停放在破庙里的棺柩,死者的形象既是控诉又是升华。爱情作为神话咒语的两重功能:诅咒与超度,完满地实现在这些死者美丽凄婉的形象上。
巴金对自己的小说常作意犹未尽的解说,那些序、跋、后记、创作谈往往自行解构了小说本身。实际上,巴金的大嫂虽亦曾被迫到城外生产,却并未因此去世;“梅”的原型在有情人未成眷属之后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十几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儿女,……成了一个爱钱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鸣凤”的原型翠凤亦未投湖,她拒绝做巴金远房亲戚的姨太太,宁愿后来嫁给一个贫家丈夫。加工证明了意识形态完满性对作家的控制,意识形态的交战杀死了小说的人物。死者封闭了探索爱情作为意识形态神话的途径,或者说,正好标出了“五四” 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的位置。女性被历史性地凝结在两个互补的瞬间姿态上:逃向死亡的美丽而凄婉的姿态(鸣凤),逃向生路的美丽而决绝的姿态(淑英)。“家”之门被抛在她们身后,沉重的关门声回响至今。这一画面定格的解疑,在巴金的创作中,要到《寒夜》才见端倪:“新女性”曾树生进进出出的“家门”多元化也复杂化了。后话不提。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价值的递升是价值虚无主义的逻辑思路,总是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来否定我当下的执着。治愈觉慧的内疚的良药不正是“事业”、“社会”、“广大的世界”么?北京来的新书报、《利群周报》社的活动、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和文章,这些在《激流》三部曲中占了相当篇幅的叙事,尽管对后来的读者的阅读耐力可能是个考验,却是小说必不可缺的部分。一切在”家”里失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友情、爱、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倘若巴金拟想中的第四部小说的书名是《群》,则这些活动正是从“家”走向“群”的预演或排练。“青春/衰老”的二项分立具有时间向度和生理学的意味,“年轻女性/糟老头子”则叠加上了性别和美学的色彩,“家/群”、“狭的笼/广大的世界”更展开为空间性的二项分立。然而“群”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家” 呢?至少,巴金本人在1950 年的上海首届“文代会”上曾真诚地说:“会,是我的,我们的家,一个甜蜜的家。”
六十年前的巴金当然无法料及类似从“家”到“群”再到“牛棚”这样的历史性演变,然而到了一九四零年代,路翎的蒋纯祖(《财主的儿女们》)已然置身“群”中而茫然失措。因此,《激流》三部曲中“群” 的意识形态完满性依然是“五四”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的又一表征与遮掩,非如此不足以反抗命运、救己救人救世。
至此,我们已然对建基于近百年来的“启蒙神话”而作的命运二分法,引发其内含的重重矛盾和抗辩对诘的嘈杂声音。
二分法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其实就聚焦于贯串《家》《春》《秋》全书的人物,大哥觉新身上。他是青年(只有二十六岁),却已历尽沧桑(丧父母丧妻儿);他是“子”辈,却支撑家业的相当部分(长房长孙);他是痴情的恋人,却又是遏阻这些爱情的“同谋”;他是新思想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觉慧最早读到的《新青年》即由他那里得来),却又兢兢业业维系一切旧的礼数规矩。他是夹在书中两类“不肖子”中的唯一“肖子”,承受了最大的心理压力(高老太爷们只承受来自“新时代”一面的压力,觉新则还要承受来自高老太爷们的压力),承受了最多的苦难灾难和责难(巴金似乎执意要把全世界可能有的不幸都堆到他头上)。他仿佛是两种命运的中介,他既不属于黑暗也不属于光明,亦无肩着黑暗的闸门的英雄姿态,毋宁说,他以其昏黄暧昧的形象,颠覆了正反价值二元互斥的现代神话。
反讽的是,当觉慧放心大胆地一走了之逃出生天时,是这位大哥以子辈的身分履行父辈的功能,支撑着“狭的笼” 中那部分家业,养老扶小,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使“家”的叛徒们得以在“广大的世界”里驰骋。在那个“弑父”的时代,“大哥”的身分是最为暧昧不明的,他既是“父”的代替物,又是“子”们的同辈,使得“子”们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排解必得采取更为复杂曲折的形式。许多时候,觉慧觉民对觉新的愤怒比对高老太爷克安克定们更甚,倘若觉新身心交瘁而死,早已派定的凶嫌是不会疑心到他们身上的。或许这也顺便解释了觉新最后并未如同其生活原型般自杀身亡,而是有了个差强人意的结局:他在书快结尾时终于挺直腰杆站到作为叛徒的“子”的一边。然而,正是在这里,父子冲突、黑暗光明的二项分立、两种不同命运的搏斗等等显得最为晦暗不明。
《家(2007)》中的二哥觉民、大哥觉新、三弟觉慧
在《秋》的(也就是《激流》三部曲的)临近结尾处,两类“不肖之子”之间终于爆发郁积已久的一场正面冲突。叛徒觉民长篇大论痛斥他的叔叔败家子克安克定,历数他们勾引老妈子、调戏丫头、包妓女、闹小旦、吃鸦片烟诸般丑事,真个是义正而辞严:你们口口声声讲礼教,骂别人目无尊长。你们自己就是礼教的罪人。你们气死爷爷,逼死三爸。……你们只晓得卖爷爷留下的公馆,但是你们记得爷爷遗嘱上是怎么说的?你们讲礼教,可是爷爷的三年孝一年都没戴满,就勾引老妈子公然收房生起儿子来!你们说,你们在哪一点可以给我们后辈做个榜样?
准则是礼教的准则,权威是爷爷的权威,产业是先辈的产业,支撑““严辞”的”正义”并非来自叛徒们信奉的“新思想”,而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传统礼教。恐怕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仅仅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策略运用,“不肖孙”与爷爷之间的某种同质性正从话语的缝隙中向我们昭显——他们都是某种新家(事)业的开创者。何况,谴责“蛀虫”不免就认同树干,认同使树木生长繁盛的那些“基本原则”。然而,更根本的认同当是情感方面的认同。“家”作为空间形象,相对于陌生、危险、动荡、广漠、孤立无助的世界,它狭小却亲切,昏暗却温暖,平庸却安全。它荫庇童年的生长,维系血缘的亲情,繁衍延续的生命,传递历史的记忆与讲述。高家花园(后来还有《憩园》)的充满深情的反覆描写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因此,甚至于像《激流》三部曲这样立意于“控诉”的家族史长篇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写成一曲挽歌(高老太爷临终时与觉慧的对话是最动人的一幕)。而这正是这部小说在历史和美学两方面的魅力之所在。
“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在工业文明的世界性进程的威迫之下,支撑中国社会两千年的旧家族制度确乎走向了灭亡的命运。倘若把“家”定义为维系安顿生存意义的基本空间单位,那么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已然将它摧毁了。说来蹊跷,不是我们从“家”中逃亡,而是我们将“家”从“家”中驱逐了,居住在空出来的位置上的,是现代的“更高的价值”。重读《家》中高觉慧的那句最重要的话(巴金自己亦反覆征引):“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我总会想起王文兴写于一九七年代的《家变》。王文兴用繁冗累赘语无伦次的文字,戏谑地颠倒了“五四”新文化神话凝定的叙事规范,老父离家出走,留在家中的“不肖子”却比他父亲还像他父亲,小说显示了“父子冲突”模式中“家”本身的存在或消失的荒诞性。如果说《家变》中的人物是《家》的人物的历史的倒影,《家变》这本书就是《激流》三部曲的历史的倒影——我们从中读出了“社会注视”的转移衍变,读出了书和书所谈论的人、事、物的身世沧桑、命运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