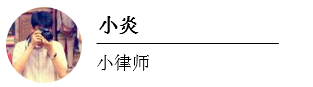《有的人》剧照
点击联系人间编辑
在我对母亲漫长而痛苦的思念里,曾无数次地设想,母亲当初若是果断地离婚该多好,至少肯定不会有后来的悲剧,至少,她不会永远地离我而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二十三年前的那个夏日。
蝉在枣树上躁鸣,声音尖锐刺耳,无休无止,钻进人的头脑中萦绕膨胀,就要炸裂。
沉在西边的落日,殷红,冰凉,凝固,似乎被什么东西定格,永远不会落下。
家门口的小河,经受烈日的炙烤后,露出大片河床,淤泥里,有跳跃的青蛙和滚爬的蝌蚪。
风从很远的地方吹来,扫过河畔淤泥中林立的荷叶,将一股淡薄的清香灌入家中堂屋,冲淡了防腐剂福尔马林的气味。
随着时间流逝,关于母亲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有时,我甚至对她的模样、高矮、胖瘦,都说不太出来了。
或许对于一般人来说,儿时与母亲相处的时光不过是一些属于私人的记忆,没有太多的乐趣与奇妙,但对于我,却如吉光片羽,是灵魂中最珍贵的东西。
那些农闲的午后,面对波光粼粼的小河,母亲陪我坐在家门口,我们捡起落满院子的杨树叶,各挑一片树叶,将叶柄绞在一起,然后各自拿住树叶的另一头,用力往自己这边拽,看谁手里的叶柄更结实。如此简单的游戏,母亲陪着我,可以玩过整个下午,直到傍晚时分她起身进屋做饭,我仍然意犹未尽。门前,大堆断了叶柄的树叶,躺在温暖的霞光中。
我会看许多小人书,然后跟母亲讲述书中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天马行空,离奇荒诞,不知所云,但母亲总是听得很认真。在少有的记忆里,我至今还能想起,母亲很爱干净,即便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她每月要换两次床单,夏天的夜晚,没有方便的淋浴,她每天都会用铁盆打水洗澡。
像所有吃苦耐劳的农村女人一样,母亲做得一手好饭。那时已经包产到户,饥饿已基本不存在,母亲做的玉米煎饼、糊糊,总是让我味蕾全开。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亲友,还能吃到白面,母亲蒸出的馒头,泡酥香甜,回味无穷,望而生津。
每年春节,母亲又会买回鲜活肥美的鲫鱼,巴掌大的鱼身,破了肚皮,放盐腌渍,丢进滚烫的油锅,炸得脆酥喷香。鱼不能马上全都吃完,大多数要捞出来将油沥干,串起,挂上房梁,等拜年的亲友到来时,母亲再将脆鱼取下招待客人,数着人头,每人一条。
很多年以后,每当我再想起母亲在幽暗厨房中的忙碌身影,依然可以感到那种笼罩全身的温暖。
然而,每当父亲出现时,这种温暖的光晕,就无可挽回地消散了。
在我人生最初的记忆中,充斥着父母之间的无尽争吵,家庭的不幸,让年幼的我变得孤僻,敏感,自卑。要到很多年以后,我才能尝试去理解那些令人心碎的争吵和更大的悲剧。
山东煤城兖州,于我熟悉而又陌生,我的祖父与父亲都曾在那里工作。兖州距离家乡所在的小村庄只有五十余公里,但是现在这里的人与那座城市已经没有什么联系,很少有人再去那里上班。
祖父谈起自己的往事时总是两眼放光,他出生在农村,虽然年轻的时候都说“当农民、工人或者干部差别不大”,然而,他还是毅然选择离开农村,成为一名“吃国库粮”的工人——“差别不大”实在很难自圆其说,从“农民”变成“工人”的祖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挣着比乡亲们高的工资,还有白面馒头可以吃。他每月都将白面馒头省下来,带回家孝敬家里长辈。
在我对父亲不多的了解中,只知道他大致的经历:赶上高考制度取消,父亲读完高中,直接回了家继续当农民,后面几年里,推荐工农大学生的资格一直没有落到他头上。1980年,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他也去了兖州,接班祖父的职位,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在这个距离孔孟之乡不远的村子,传统的习俗还以相当稳固的形态存在着,母亲与父亲的婚事,由爷爷做主定下,而父亲本来是不同意的。
父亲平时住煤矿宿舍,每月回农村老家,待上几天,就又匆匆离开。在他变成那个暴躁易怒的男人之前,在长辈们的交口称赞里,这位高中文凭的煤矿工人,工作上进,富有同情心,会帮助讨饭的乞丐。
父亲有许多“不务正业”的爱好:吹笛子,种花,听录音机里的惆怅情歌。那时的农村电力供应不足,时常停电。父亲会奢侈地在收录机里装入四节1号电池,只要他在家,各种流行音乐的抒情旋律,就会在这个农家小屋内萦绕不绝。父亲喜欢迟志强,总是跟着哼唱,“愁啊愁,愁就白了头……”、“是谁,制造的钞票……”
母亲来自邻村,家里姊妹四个,她排行老二,没上过一天学,打小就开始做农活,照顾弟妹,吃苦耐劳,宽厚隐忍,将精力全部贯注到日复一日的生计劳作中。那些忧愁的情歌、悠扬笛声、侍花弄草的雅趣、收音机里牵动人心的家国大事,母亲都无法与父亲产生足够的默契,她只知道自己的丈夫,在那个尚未完全开放的年代里,是国营企业里有文化的工人、共和国的骄子。
父亲工作的国营煤矿在经历数十年的僵化运转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企业改制大潮中,父亲被调整回到采工区,要深入井下800米,在不到一人高的巷道里采煤,工作面作业时间8小时,加上漫长的下井、升井,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
工人们失去了光环、收入和社会优越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转岗之后一年,父亲再也没有耐心待在深井下以中年人的身体和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出卖体力。体检时,父亲做了手脚:将葡萄糖滴入尿样。于是,他被确诊为糖尿病,开始享受“病保”待遇,每月领些病假工资,回家“养病”。
父亲与母亲在家时,不是冷战,便是争吵,这成了笼罩我少年时代的阴影,我的心几乎每天都悬着,对父亲说话,总要小心翼翼。父亲在家时,总是闷闷不乐,一脸忧愁,我现在大约才可以体会,他身上那种危机感:曾经的返乡知青、顶替父亲职位的中年煤矿工人,就要被时代抛弃了。
总在家闲着不是办法,“病保”工资太少,除了地里的产出,母亲没有更多收入。父亲开始自谋生路,跟同村的二庆叔一起去城里批发衣服、鞋子回来,等村上赶集时,摆个摊就在街上卖。
二庆叔家中兄弟三人,他在最小,前面两个哥哥结完婚,到他这儿,家里已没钱再盖房子。加上二庆叔小眼睛、塌鼻子,面相不好,找媳妇就更困难。但他最终娶到一个漂亮的媳妇——二庆婶不仅人漂亮、会打扮,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在村人眼里是一个“显眼”的女人。
这种反常结合的背后,是二庆婶身上的问题。曾经,她与高中的男友相约一起考大学,对方考上了,她却落榜了。在当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优越的社会地位,毕业包分配,吃不完的国家粮,考上与考不上大学,意味着巨大的阶层鸿沟,所以二庆婶就被男友抛弃了。更致命的是,她为男友流过产,在观念未开化的农村人眼里,没人愿意娶她。于是,她只能嫁给娶不上媳妇的二庆叔。
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贩卖服装,并不是一个有前景的营生。不久,二庆叔去了外地,在建筑工地干活,留下妻子二庆婶一个人在家抚养两岁的儿子小鑫。
因为一起做生意的关系,家在外地的二庆婶跟我家走得很近,时常抱着小鑫来我家串门,找母亲聊天说话。有时赶上母亲下地干活,二庆婶带着小鑫来时,家里就只有我和父亲两人。我很喜欢二庆婶来我家,因为她的到来会让父亲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二庆婶的存在似乎总能让父亲安稳下来,情绪平和,不再无常地愠怒。这样家里的氛围轻松许多,我也不用总是战战兢兢,承受这个失意中年男人的无名之火。
我初谙世事后才明白,其实二庆叔的婚姻也是一场有着重重矛盾和危机的婚姻:漂亮又有文化的二庆婶,嫁给丑陋而贫穷的二庆叔,难免觉得委屈。二庆叔一家只是迫于经条现状,勉意找了一个生孩子的女人。婚后,这个家庭充满争吵:二庆婶未婚流产的污点,让她在村里再也活不成一个正常的人,每天被旁人异样眼光指指点点,活成一个卑微、扭曲、变形的人,并最终殃及到我的家庭。
没人真正知道二庆婶在什么时候开始放纵自己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不干净”、“被人甩了的”、“没人要的”,一直是这个女人身上的标签。那些混乱的男女关系曝光后,道德谴责的滚烫口水,再次将这个扭曲变形的女人诛灭。
只是后来等我意识到自己天真的动机会怎样为惨痛的悲剧添油加火时,真是追悔莫及。
记得那是一个上午,母亲出门赶集,只有我们父子在家。父亲忽然笑眯眯地对正看书的我说:“你看家里太冷清了,你去找个小孩儿来家里玩玩吧,好热闹点,看看小鑫在家吗?”
大概是有些心虚,他说完上一句,停了一下,又刻意的掩饰补充道:“别的小孩儿也行。”
难得看到父亲对我笑着说话,我有些受宠若惊,连说声“好”,然后走出家门。我先抱回了李叔家的小齐,父亲却满脸不高兴,我向他邀功,却只得到一声冷淡的“嗯”。我在心里推想着:父亲看到小鑫时会满脸堆笑,看到小齐却满脸不高兴——其实他只是想让小鑫来家玩吧?于是就直接去了二庆叔家,二庆婶推辞不来,我未得她允许抱起小鑫就走——我太想讨好父亲了。
父亲一见到小鑫,就赶忙一边问小鑫“你妈呢?”一边让我拿苹果给小鑫吃。不一会儿,见二庆婶赶过来找儿子,父亲脸上堆满了笑容:“小鑫妈,你来了!”二庆婶嗔怪我不该抱走小鑫,父亲赶忙替我解围:“没事,在这待会儿,去屋里喝茶……”
看到父亲脸上的笑一直没有散去,我心里一阵高兴。
没想到,当天晚上,母亲就忽然问我,白天二庆婶是不是来家里玩过?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母亲说了一遍,抬头看她时,她眉宇间凝聚出的不满,让我一下子感到事情似乎哪里出了问题。
● ● ●
父亲依然坐在家里,长吁短叹,抽许多的烟。十余年的矿工生涯,除了获得当时还算丰厚的收入,病退以后,他并没有习得什么谋生的一技之长。他的苦闷和忧郁,家里总是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母亲则依然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劳作,在手上磨出厚厚的肉茧,为这个飘摇欲坠的家庭,消耗着体力与青春。
我上初一时,二庆婶时常来家里给我辅导英语,她依然穿着新潮,说话缓慢柔和、轻声细语,她与父亲之间的聊天,也显得比较得体,他们会聊一些我根本没有听说过的书名。
一天夜里,我忽然被一阵吵闹声惊醒,我爬起来,顺着门缝看过去,母亲哭着进了里屋,父亲紧随其后,“咣”一声将门关上。父亲高亢的质问声传过来:“你大晚上的去找我干嘛?”
母亲哭着解释说,她不是故意去找父亲,只是白天时,小鑫在我们家玩,鞋落这里了,她是去二庆婶家送鞋,没想到竟撞见父亲也在。
“我去行,你去就不行!” 父亲恼羞成怒。
“你说你们什么都没干,开门的时候你躲在门后面干什么,这不就是你心虚吗?这大半夜的……”
我已经听明白一些东西。父亲粗急的喘气声传来,我意识到,他又要动手打母亲了,我立即冲了过去,猛地推开门,指着父亲骂道:“你真不要脸!”
父亲完全没有料到我会忽然冲出来,愣了一下,就对我大喝:“你说谁?!”
一瞬间,我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全在往上涌,头脑剧烈地一懵,随即感到异常清醒,我提着父亲的名字,一字一句地说:“说的就是你!你不要脸!”在这之前,我从未敢如此顶撞他,但这次,我要保护母亲。
父亲似乎被我忽然升腾起来的气势镇住了,自知理亏,不再说话,只是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还在气呼呼地喘粗气。
母亲哭得很厉害,嗫嚅含混地规劝父亲,说小鑫的爷爷就住在隔壁,要是被人发现,该要打断他的腿了。说完,母亲一下子坐在床上,抱着我哭,泪水顺着我的脸颊、脖子往下流。那湿湿粘粘的感觉,多年以后想起,仍然让我感到攥心般的难过:父亲将母亲伤成这样,她竟然还在为他的安危着想。
我替母亲难受,却不想哭出来,我扶起她的肩,以我难以想象的坚定劝慰她:“真不能过,干脆就离婚算了,不要受这种气。”
可母亲只是哭。
母亲也考虑过离婚,当她把想法告诉姥姥和姨妈,她们都不同意,即便有好几次,她被父亲打了跑回娘家。姥姥和姨妈们说,女人,尤其是中年的女人,不该轻易放弃家庭,应该隐忍。我恨透了这些散发着裹脚布的陈腐气息的观念,在我对母亲漫长而痛苦的思念里,曾无数次地设想,母亲当初若是果断地离婚该多好,至少肯定不会有后来的悲剧,至少,她不会永远地离我而去。
我大胆指责父亲的那个夜晚,在母亲伤心的哭声中结束,第二天一早,父母像往常一样喊我起床、吃饭、上学,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在狭小的乡土世界,不存在什么秘密,二庆叔很快知道父亲晚上去找二庆婶的事情。
一天中午,二庆叔气冲冲地来到我家,要找父亲算账。他阴沉着脸,头发又长又厚,凌乱不堪,还粘着工地上带回的泥土。
“你说吧,这件事怎么办?”二庆叔念在旧情分上,没有马上动手。父亲只是低头坐着,不吭声。母亲却把话接过来:“这事怎么能全怪别人?你自己媳妇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她又不是只跟俺家男人好,村旁开小卖铺的二军、打石头的二狗子,不都跟你媳妇有一腿?你也不好好管管自己家媳妇!”
“别人我都找了,把他们揍了——你家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二庆叔气急败坏地说,理气已被压下去一成。
“我家男人好不好我来管着,你还是回家管管你媳妇!”母亲凛然地说出这些话,竟让二庆叔一时无法反驳,只是涨红了脸,转身气呼呼地回家了。
事情平息后,父亲对着母亲笑,表情里掺杂着愧疚,感激,谄媚:“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以后我会好好过日子的。”
母亲的脸仍然很平静,一句话也没说。
我以为家里冰霜开始融化,没想到,更大的暴风雨很快就来了。
● ● ●
刚上初二不久,一天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班主任忽然把我叫了出去,说有人找。我出去一看,在教室外等我的人是大爷,他低声告诉我,母亲病了,让我回去看看。我只是“哦”了一声,就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
在路上,我就有不祥的预感:一般的病,怎么会立即把我叫回家?一路上,大爷反复跟我说“回家一家要听大人的话。”我意识到,母亲可能出事了。
十分钟的路程忽然变得好漫长。
大爷直接把我带到他家,一进屋,我差点被吓倒:屋里坐满了人,全都表情肃穆,几个住在城里、只在逢年过节回家的叔叔大爷也到了,好像都在等我。爷爷在靠门内侧的角落里,坐在小马扎上,眼睛通红,我靠着他坐了过去,还没坐稳,爷爷竟突然趴在我的腿上哭起来:“我没管好你爸,爷爷对不起你啊……”
爷爷的话说得含混,我听得懵懂,一时不知所措,那种恐怖的预感越来越逼近了。这时,大爷也哭出声,走到我跟前告诉我:“小炎,你妈没了!”
我听完,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上,大声地哭起来。我想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已说不出话。大爷抱起我,走到我家已经设好的灵堂,泪眼朦胧中,我看到很多街坊邻居们站在两侧,充满同情地看着我。
灵堂里,母亲全身盖着一张白纸,躺在一张由高粱秆子编成的席子上。我一下猛扑上去,想看母亲最后一眼,但身后众人都拉住我,无论我怎么努力,母亲的最后一眼,我最终也没看上——事后我想,也许不看是对的,喝农药的人,面相不会好,我宁愿让母亲那张模糊却温暖的脸庞永远印在心里。
接下来的很长时间,我都在痛哭中度过,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到了什么时间。大爷把我背到他家的里屋躺着,我哭得力竭,睡着后梦到了母亲,她正低头纳鞋垫,不时拿起针在头发上蹭几下,齐耳的短发,让她看上去非常可亲。我正看得入迷,她忽然抬起头,定定地望着我问我:小炎,你还记得我吗?
我一下子惊醒坐起来,伸手去抱她,却只碰到墙壁。我想起了悲剧发生前的夜晚,母亲就是坐在油灯下纳鞋垫,我一边吃饭,一边抱着《天龙八部》看得入迷,母亲担忧我,便温和地劝说:“小炎,你得好好吃饭,现在正是你长身体的时候,多吃饭,你将来才能长个大个子!”
这是我记忆中,母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关于母亲的死因,家里人一开始想瞒我,但经不住我追问,终于说出母亲是喝了农药。听了,我脑子一嗡,什么都明白了。
出事那天,我早上去学校后,父亲母亲又大吵了一架。本来,母亲想给我买个随身听学习英语,以此弥补之前二庆婶对我的辅导,但她去柜里拿钱时,却发现钱没了,她向父亲质问,父亲才承认,那些钱给了二庆婶。争吵中,父亲不停地说二庆婶是个苦命的人,而且还承认与她依然还有瓜葛。
这些,终于让母亲崩溃。
办丧事那天,两个本家哥哥架着我的胳膊,抬着我完成丧礼的仪式。我哭得天昏地暗,悲痛,怨恨,委屈,全都宣泄出来,似乎把我一生的眼泪,都提前流完了。
● ● ●
母亲过世后,父亲停止了病假,又回到煤矿上班,在井下当了一名维修工。他开始学着生炉子,打理一切从前不会关心的家务。我不知道,他心里如何想,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未聊过这个话题。父亲自婚姻开始就对母亲不满意,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共同话题,更没有共同爱好,十几年的婚姻,父亲也没有真正尊重过母亲。父亲心里,可能一直也很憋屈,要顶替父亲的工作,就要接受家长的安排。母亲过世后,面对双方长辈、亲戚的责备,还有我的冷漠,甚至敌视,父亲倍感煎熬,我能感到,他的心里对母亲也有愧疚。后来,他也再婚了。
我将母亲唯一一张照片放在钱包里,随时带在身上,萦绕于心的愧疚、遗憾和时时发作的隐微痛感,终究无法消散。
二庆婶后来也安分了,依然和二庆叔生活在一起,前几年我回老家,见她在地里摘棉花。她老得很快,满脸憔悴,青春的绰约风姿早已褪去,而那些酝酿悲剧的习俗与观念,那些“杀人”的礼教,却从未消隐,甚至还在复活。
编辑:朱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