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易人间特约插画师/关斌斌
点击联系人间编辑
前言
2009年,我在丹麦博物馆里屏住呼吸,透过玻璃凝神静望——玻璃后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正式的、法律承认的“同性结婚证书”——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整个心魂都被震慑了。
如今很多大都市里,当人们看见一对表现亲呢的同性,可能会反感或侧目,但不至于再大惊小怪、大呼小叫。更有无数同志,不惧歧视,勇敢出柜,真诚表达自己。
这是文明的进步,只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多少前辈不懈抗争、奋力争取权利的结果。
怀着对这个群体前辈的敬意,笔者历时一年多,数经波折,采访了数位圈中长者,记录下他们当年的过往经历、心路旅程。
彩虹往事 | 连载01
口述人:老巴黎,71岁,教师
很早以前,我就在东单公园听说过“巴黎女孩”这个名字,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个妙龄女子,后来才知道是“巴黎老人”的误传。
对于“巴黎老人”的故事,常去东单公园的同志们都有所耳闻,他俨然已成为东单公园的一个历史人物、一段永远流传的传说。
巴黎老人今年已经71岁了,他的年纪比始建于1955年东单公园的历史还要长,他见证着这个公园如何修建,如何慢慢变成一个同志的聚点,如何发展成为今天的模样。现在,他也和这座公园一样,渐渐老去。
从这位老人那里,我听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如果把他所经历的人生大事和波折,用时间和地点标明出来,几乎就描绘出了北京同志聚点的历史地图全貌。
从小我就知道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个女孩子
时间:1962年 地点:西单公园
老巴黎原姓肖。1962年,23岁的他在西单体育场文化广场遇见了一位法国人。
那天已经接近黄昏,广场上的人并不多。他穿着一身白色:白汗衫、白褂子、白裤子,还系着一条白围脖,法国人就坐在他的对面,40岁左右,高大魁梧。他心里很是喜欢这个外国人,法国人冲他笑笑,他也笑笑。
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法国人突然用汉语对肖说了一句:“我爱你!”他倒也不矜持,用外国人的方式回了一声:“谢谢!”法国人说:“我们出去谈谈好吗?”他说:“好。”
肖和这个法国人还见过几次面,后来才知道他是法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厨师。
法国人有一个习惯,每次和肖温存之后,都喜欢给他点零花钱。肖生气地说:“我不是卖的,我不要。”法国人就把钱扔给他,说:“你去买点化妆品吧。”说完丢下钱就跑。肖没有办法,只好把钱留了下来,那时候都算是外汇。
西单体育场的朋友都问他,那个外国人是谁。肖说:“他是法国巴黎的。”
于是,大伙就开玩笑叫他“巴黎夫人”,肖笑着说:“我们还没有结婚呢。”于是大家就改叫他“巴黎先生”。

△巴黎先生年轻时的照片 作者供图
有一次约会,法国人没到。肖也就没再打听。再后来,肖就看到他跟了别人。
“他们好像把这个也不当回事,但我这个人是比较重感情的,有过那种关系之后就久久不忘。”他没有想到这个法国人这么风流,心里有些生气,也有些嫉妒,就没有再跟法国人打招呼。等法国人回头找他,肖也没有再理他。
再后来,法国人就没有再出现。两人就此断了联系,但是“巴黎”这个名字却伴随了肖的一生,成了别人对他的称谓。
● ● ●
从小,巴黎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喜欢上了同班的班长小春。因为两家住得很近,经常一块上学,慢慢就产生了些微妙的感情。有时一块儿做作业,巴黎经常忍不住对班长做些小动作,小春倒也配合。
“当时也就是朦朦胧胧的,我喜欢他,也喜欢亲他。结果有一次就让我妈给逮住了。哎哟,我妈把我给打得半死,屁股疼得几天都坐不了。我妈是街道治安主任,要面子,她就说,‘我挣多大脸,你给我现多大眼。’我妈也跟小春的小妈说了,他妈妈回去就打了他。”
这样的经历倒没有让巴黎感到可耻,只是因为害怕再被母亲毒打,他们再没敢呆在一块。小学毕业后,巴黎上了别的学校,两人就这样分开了。
真正懂得同性恋这回事,是在巴黎1953年上了初中之后,那时他在学校跟几个男同学非常要好,他们一群人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都像女孩子似的。他们一起喜欢班上的体育老师,一见到他就给他做个万福,说:“老师好!”体育老师便慎道:“这帮臭丫头!”他们再一哄而散。
学校里有个高年级的同学,姓赵(此人后来调到外地的京剧团,自己还编导了一出戏),在剧团里演丑角,经常会给巴黎他们一些戏票,然后要他们到卫生间去。“他就摸摸我们的屁股,也让我们摸摸他……当时心里就觉得挺害怕的。”
虽然这种抚摸令巴黎感到害怕,但是他却是喜欢的。
初恋,一生最不可磨灭的记忆
时间:1956年 地点:空白
1956年,巴黎从北京八中毕业,考上了北京第一师范学校。一到学校,巴黎就看上了班上的一个同学——他是巴黎的初恋,名字叫亮。
亮比巴黎大三四岁,20岁左右,来自山东农村,哥哥在崇文门花市的崇光电影院当经理。巴黎和亮住同一个宿舍,睡上下铺。宿舍十来个人,数他俩最要好。
有的时候,巴黎在夜里醒了,就故意晃悠床,把亮也一起摇醒。亮醒来后,巴黎就爬上亮的床,在他身边躺下。“当然,主要是我主动,他则是积极配合”。碍于宿舍里有其他同学,他们不敢每天都睡在一起,只是在夜里醒来之后就躺在一起。
跟亮在一起的日子,是巴黎一生最不可磨灭的记忆:亮完不成的作业,巴黎就帮他完成;每个礼拜六晚上亮都回一趟哥哥家,亮总要巴黎等到礼拜天,带着很多好吃的回到学校,两人再一起回巴黎家。
巴黎跟家人介绍亮是他的同学,但他母亲多少也能看得出他们俩的关系,也只好在心里默认了把亮当成了自己的姑爷。即便母亲后来完全知道了真相,也只能无奈地叹口气:“唉,我哪辈子缺德,生了这么一个儿子!”
亮虽然来自农村,但因为哥哥的社会地位,多少有点少爷脾气。亮重感情,对巴黎很专一,很在乎他。只要巴黎跟别的男生说话,亮就吃醋不高兴。他们班上有个叫英军的同学,有一次和巴黎闹着玩,抱着巴黎亲了一口就跑开了,亮看到后,伸手就打了巴黎一个嘴巴。巴黎也生气了,觉得亮太自私,决定要跟他从此了断。
可到了晚上,亮又向巴黎道歉:“我错了,我不应该那样,求你原谅我。”两人又和好如初。
就这样,中专两年、大专两年,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四年多的时光。
等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巴黎突然无意中看到亮的一封家书。信上说:“孩子很想你,你还是回来吧,不要因为我们夫妻关系不好,就连孩子都不认……”
巴黎这才知道,亮已经在老家跟女人结过婚还有孩子了,一直瞒着自己。他感到既震惊又愤怒,质问亮:“你结婚了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亮回答他:“这是家里包办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上大学的学费也是她天天纺线卖钱来供我,我也不能狠心把她给抛弃了。我和她之间没有感情,可是有孩子。我并没有骗你,我也没法跟你说,说了你肯定不高兴。”
巴黎觉得这是自己受到的最大的欺骗——自己“竟然‘嫁’了个有妇之夫”。
巴黎结束了自己的初恋,只留下一张亮的照片,一直保留到现在,即使后来的生活发生了无数动荡,他也没有让这张照片丢失。
临近毕业,巴黎为了争取成为三好学生,学习很用功,也没有再交男朋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男四中。
直到最后,他也没能给他说一句再见
时间:1960年 地点:东四人民市场
毕业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巴黎和同学一起去逛东四人民市场,意外发现那里竟然是一个同志聚点。当时北京有几个聚点,一个在东四人民市场,一个在台基场二条,还有一个在前门河堰。东四人民市场是巴黎知道最早的一个聚点。
那天,巴黎刚好内急,去了一个公共厕所,厕所里有两排 12个蹲位,站着很多的男人。巴黎进去后,发现有很多人都在看他,眼神多少有些暧昧。
巴黎立即意识到了什么——“没想到社会上还有这么多(同性恋),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这样,以为同学也是受我影响才这样。”
从厕所出来之后,就有好几个人跟着他,有的还挺好看。巴黎选择了其中一个搭话,旁边那几个人就打了起来,巴黎一看,马上就吓跑了。一边跑,一边还觉得挺逗的——他好像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
很自然的,巴黎开始频繁地到东四人民市场去。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些年龄相仿的同志,跟着他们四处转,一转,巴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的同志这么多,“台基场最热闹,还有的人是开着少见的小汽车去的”。
从那以后,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巴黎的心也开始“花”了,碰见哪个好看,就跟哪个玩。尽管心里依旧渴望一份长久、稳定、纯真的感情,但现实让他觉得,在这个圈子里不容易找到专一的人。
● ● ●
1964年,粮食困难刚刚过去,巴黎被分配到另一所学校。这一次,他遭遇了一场轰轰烈烈、荡气回肠的恋情。
一个周末,他从东四人民市场出来,乘公交车回西单的家。上了公交车,巴黎看到了他——那真是个少有的美男子,十八九岁的年纪,站在青春的小尾巴上,没有成熟男子的油滑,也没有少年的稚嫩,像是刚刚长成的一株玉树。刹那间,巴黎心里只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人。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巴黎主动上去和那个男孩攀谈:“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你。”
男孩说:“不会吧?”
巴黎说:“真的,你是哪儿的呢?”
男孩很实诚地说:“我是北京工业学校的学生,马上快毕业了,家住卢沟桥。”
巴黎说:“我家住在西单,是XX学校的老师,正准备下车,见到你真好。”
这个叫阔海的男孩当时19岁,当天正从学校坐车回家。
巴黎问:“咱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一面聊聊吗?”
阔海说:“可以呀。”
“下礼拜周末行吗?”
“下礼拜不行,我得俩礼拜回一趟家,才有机会见你。”
“那就下下礼拜。”
“行,就这么定吧。”
这个时候,公交车正好开到北海,巴黎食指一指,说:“咱们就在这儿见吧,北海公园门口。”
到了西单,巴黎下车,目送着公交车载着阔海渐渐远去,最后消失。仅仅是一个口头的约定。他此时并不确定此生还能否见到这个男孩。
● ● ●
两个礼拜以后,巴黎踌躇去还是不去赴约,他甚至连男孩长什么样都记不清楚了,脑子里只剩下“喜欢”两个字。可是,这又能怎样呢?他会喜欢他吗?他和他会是一样的人吗?
等巴黎到了北海公园门口,阔海已早早在等着了,阔海对巴黎说:“我等了你半个小时,以为你不来了。”巴黎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约会的晚上正赶上灯会,公园里的人很多,他们躲开了喧闹的人群,来到景山上,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聊天。一看四下没人,巴黎便表白说:“我喜欢你。”阔海脸红了,一边用手遮住脸,一边说:“肖老师,您真逗,我这么丑,您喜欢我干吗?”
巴黎说:“你别叫我老师,那多官腔啊!”
“那我叫您什么呢?”
巴黎说:“你叫我大姐得了。”
阔海笑了起来,脸唰地又红了。巴黎越看越喜欢,忍不住牵住了他的手,看到他没有拒绝,巴黎终于鼓起勇气亲了他。
分别的时候,巴黎问:“下次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呢?”
阔海说:“下礼拜吧,这次不用等俩礼拜了。”
巴黎说:“那就下礼拜天,在天坛门口见。”
可故事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第二次约会的那天,正赶上天坛门口举行支援亚非拉游行。巴黎就在天坛对面的路边,却怎么也没有办法穿过马路。他知道阔海一定就在马路那头等着他,可是游行的队伍像一道人为的屏障,将他俩生生隔开了。
两个钟头后,游行的队伍渐渐散去,巴黎这才急急过了马路。可是,天坛门口早已经没有了阔海。巴黎就这么呆呆地站在原地,心里千头万绪,像有无数的蚂蚁在爬:他一定是等不及他,他一定是以为他不来了,于是绝望地离开了。
他们就这样断了联系。
● ● ●
半年后的一天,巴黎和家人到前门买东西。在茫茫人海中,他又突然瞥见了阔海的身影,他开始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或者是在做梦。但那的确是真的,就在巴黎恍惚的刹那,阔海也看到了他,他们呼唤着对方的名字,如此亲切和热烈。
阔海问:“那天我去了,你怎么没去?”巴黎说:“这不是赶上游行吗,我半天都过不去,过去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意外的重逢让两人又惊又喜。巴黎哪里还顾得上买东西,他跟家人找借口说遇上了老同学就和阔海一起走了。巴黎带着阔海去了前门河堰一个同志聚点,但又不希望阔海知道那里是个“点”,于是带着阔海在河堰的南面走。
这次恋情刚开始的时候,两人是每个礼拜见一次面,渐渐地,阔海越来越离不开巴黎,他要求一礼拜见两次,再后来又要求见三次。“那时候我学校在动物园,来一趟忒远啊。”直至今天,这段回忆依旧是幸福甜蜜的。
很快,阔海告诉巴黎,他入团了,还被评上了先进工作者。在那个年代,这些荣誉对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是那么的重要。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1966年4月开始,巴黎每周末要带着学生在光华路的冰箱厂“学工学农”,每次活动结束都是晚上八九点了,所以跟阔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法见面。
等巴黎给阔海家里打电话约他见面时,阔海的家人接到电话显得很是意外,问:
“你不是来闹事的吧?”
“闹什么事啊?我是他同学。”
“阔海人已经死了。”
巴黎一惊,连忙问怎么回事。
“你是他同学你怎么不知道?他投井自杀了!”
巴黎惊呆了,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赶忙去了阔海单位。
● ● ●
阔海之前住在单位的宿舍,舍友是一个比他大十来岁的男同事,已经结婚了。五一的时候,男同事的老婆来探亲,本来按照惯例,单位应该给夫妻俩另外安排团圆房,但由于领导工作忙忘了这事,结果他们仨在只能在同一个屋子里睡。
半夜,那对夫妻温存后,男的起身去上厕所。一旁的阔海本就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不自禁一下就站了起来,这个举动让同事老婆受到了惊吓,她随即大叫:“干嘛你?臭流氓!”同事听到叫声立刻跑回来,揪住阔海就把他扭送到人事保卫科。阔海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单位便把他关在单位二楼,不许他五一回家。
结果5月2日,趁没人注意的时候,阔海从二楼的窗户跳下去了,在院子里摔了个跟头,爬起来偷偷跑了。他一路奔跑着回家,在家里转了一圈,将年纪还很小的弟弟叫到自己身边,说:“你要好好孝顺爸妈,哥走了。”冲出家后,阔海便在村头投井死了。
一直到死,阔海也没有向巴黎说声“再见”。
巴黎一个人打听了很久,才在阔海家的村头找到了他的坟墓。站在那个埋葬着他爱人的土堆跟前,他想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又不能,只能压抑着自己的悲伤。
阔海离开时刚好23岁。从那以后,每年的5月,巴黎都要到他的坟前去看他。
我觉得自己喜欢同性并没有错,可是那个年代,这就是最大的错
时间:1970年 地点:西单文化广场
阔海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黎都忘不了他。很多年过去,巴黎都没有再交朋友,他的心里只有阔海,觉得别的人都不如他。那张脸,巴黎铭记了一生,永远那么年轻、那么俊朗。
26岁的巴黎,心里特别苦恼,就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他在学校里成了个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不仅是班主任,还是年级组组长。他积极向上,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然而,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黑党支部里的“红人”。
“我的头发有些自然卷儿,他们非说我是烫的,说我卷花头,于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之类的帽子就扣给我了。一下子给我推了个阴阳头。不管是斗也好、批也好。我一心只想着他(阔海),只在心里骂:混蛋、王八蛋,净是给你们逼死的!”
当时西单文化广场也是一个同志的聚点。那里有一个外号叫“小英杰”的人,是海淀评剧团管灯光布景的。此人个子很高,由于在剧团里和一些男演员有过关系,所以文革一开始,人就被揪出来,遣送还乡了。
几年后,小英杰要求在北京的父亲替他平反,恢复工作。巴黎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小英杰,但并不知道他的历史。
巴黎常跟自己的伙伴“小兰英”在一起,后来又认识了“白大姐”和“卫生局”,他们“四姐妹”非常要好,经常一块聊天、吃饭。小英杰就在旁边看他们,有时上来跟他们搭几句话,他们看他长得又不好看,脏里吧唧的,也就没怎么搭理他。
有一天,小英杰尾随着巴黎回到了家里,巴黎一见他,吃惊地问:“你怎么上我这来了?”小英杰说:“你别紧张,我从这路过,我知道你在这住,原来就知道。我求你点事儿,我想买捧金沙织毛衣,跟你借点钱。”
巴黎想,他既然知道自己家了,得罪他也不好。当时巴黎一个月的工资是47块5毛,便借给了他40块,还说:“你可别不还我。”
小英杰说:“我们经常见面。我怎么能不还呢!三天以后还你。三天后我们在西单门口见。”
可后来,小英杰一见巴黎就跑,巴黎觉得奇怪,小兰英就说:“你不知道他是骗子啊,到处骗人!”
巴黎觉得特别生气,再见到小英杰就骂他:“骗子!还我钱!”
“我要是早知道他的为人那么差,那些钱我就不要了。”后来巴黎后悔地说,“有一天,小英杰在珠市口浴池出事了。他在那里‘摸’了不是同志的人,就给弄进去了。派出所一看他这段历史,就又要关他。当时不是时兴揭发检举吗?他就说,他认识一个老师,也是这种人,经常在天安门西宫、台基场二条、东单公园进行这种流氓活动。”
巴黎的单位接到派出所的检举信,特别重视,赶紧把他的课停了,还给他办了“学习班”,让他交待自己的“罪行”。巴黎坚持不承认,学校领导又问:“你不是认识小兰英、白大姐吗?”巴黎说:“我没接触过这些女人。”
虽然抵死否认,但在1977年,快40岁的巴黎还是以“鸡奸嫌疑”被判强制劳动三年,被送到了天堂河农场,他的母亲也在这期间过世了。
“进去以后,就让你跪在搓衣板上,搓衣板上本来就沟沟坎坎硌得慌,他们在上面钉钉子,倒着钉。一跪,血全出来了……四个警察,拿着电棍吼,‘你是不是流氓?’”
巴黎最怕听到“流氓”这个词,他觉得自己喜欢同性并没有错,可是那个年代,这就是最大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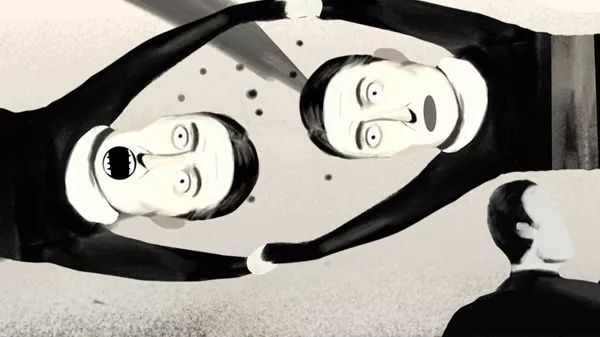
△网易人间特约插画师/关斌斌
在劳改农场,有一个男孩长得非常漂亮,巴黎心里很喜欢他的,见到他的时候就点点头,也不敢跟他说话,没有什么非分之想。那时犯人们每餐就是“白菜游泳”的伙食:两个窝窝头、一碗汤,光看到汤看不到白菜,每天下地干活根本吃不饱。巴黎每天偷着给那个男孩一个窝窝头,但被发现了。
“他们认为我肯定跟他有关系,要斗他,说我们有鸡奸行为。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无中生有。他们拿我当狗似的打,这三年害我一辈子……”
三进宫,只有活下去才是唯一的希望
时间:1980年 地点:惠泉浴池
等巴黎从农场出来,单位不再让他教书,派他去搞后勤。曾经的知识分子,只得每天跟着学校的临时工人一起干活。那几年,巴黎过得很不遂心,家也回不了,生活好像没什么指望了。“他们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叛思想,冤得慌。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方式又改不了,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改不改的问题。我要追求我自己的自由!”
抱着这样的想法,巴黎又开始了同志生活。
有一天,巴黎到惠泉浴池洗澡,躺在浴池里唱着哼着,发现旁边一个人在斜眼看他,于是就拿脚去勾搭他。那人也跟他配合,巴黎这一蹭,他那也一蹭。巴黎心里说:“咦,这个可能是哦!”于是把身体移过去,那人也跟着配合……
就在巴黎放松警惕的时候,那人蹭一下站起来了,拽住巴黎的头发说:“你丫表演得够充分的。”巴黎一愣,心想:“谁让你跟我配合的。”但他没说出来。那人道:“走,上派出所!”巴黎说:“去你妈,上派出所干嘛?”那人说:“你耍流氓。”巴黎说:“谁耍流氓了?你不是也硬了吗?”说完,他挣脱那人,马上走出去穿上衣服,想避开事端。
没想到,那人光着屁股就追出来了,把巴黎摁在地上就打,打完了以后,把他带去了派出所,交给了别的警察,说:“我逮着了一个兔子。”
巴黎说:“我承认我是同性恋,但是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还积极配合。”
派出所里的人说:“他是我们这里的警察。”
巴黎道:“警察就可以诱发犯罪啊?是他引诱我的,我一进浴池,他就用眼睛勾搭我。”
巴黎终究还是没有能够逃得过这次牢狱之灾,他先是被送到宣武分局,接着又被送到了大兴的团河农场,罪名是“思想意识差、流氓、恶习不改”。
万幸的是,农场的指导员特别同情巴黎的遭遇,对他说:“我知道这种毛病是改不了的,其实这不是一种病,但是你得克制自己,不要自由放纵。”
在团河的两年,巴黎并没有像天堂河时那样要扛一百多斤的东西劳动,因为里面的人文化程度普遍都不高,指导员安排巴黎给他们进行文化补习。巴黎白天上上课,晚上再值一下夜班,老老实实接受着“改造”,两年里走路、说话从不敢抬头。
巴黎觉得,指导员可能跟他是一样的人。
● ● ●
等巴黎刑期结束出来,单位不肯再接收他。他去找单位的领导时,领导对他说:“你能不能自己去找工作啊?你自己去联系一下看看,不管什么单位,我们都放你。”
巴黎说:“我自己去哪找啊?”
领导想了想,对他说:“要不这么着,你上学校的联防吧。”
巴黎心里说:“上什么联防啊,我现在最恨的就是联防。”
可总要有个地方找碗饭吃,他最后还是去了。学校就在东单公园附近,联防队尽在那里逮人,因为不服学校的安排,每天进行治安巡逻时,巴黎总是暗中作对,“救”了不少同志。
到联防才一个月,巴黎就出事了。一天,巴黎一个人上东单公园,遇见了一个从外地来北京的小伙子,二十出头的样子。小伙子脸上长了很多青春痘,自己觉得不好看,就来北京看医生。巴黎跟小伙子一聊,这个小伙子也挺爽快,就跟着巴黎走。
“我就又爱上人家了,就等着发展——就是通过咱的细致工作,慢慢地让他懂了、接受了。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不爱找圈子里的,圈子里的都是油子,我想找新鲜的,于是就勾搭他。”
两人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巴黎想:可别让人瞧见了。可是,联防的人还是瞧见了他们,在马路的那头一直跟着,巴黎却一点也不知道。
最后,联防的人把他们堵在厕所里,因为巴黎是北京人,年纪稍长些,又在联防工作,所以审讯的时候联防队员只拿小伙子开刀,骂道:“你是人?你是狗!你猪狗不如!”
不管他们怎么骂,巴黎就是不理睬,可是当他们开始打那个小伙子的时候,巴黎看不下去了。于是他只好说:“是我勾搭他,他什么都不懂,你把他放了,弄我得了。”
“嘿,你老家伙还挺仗义的。”
说完,他们又把那个小伙子往死里打,小伙子就眼巴巴地看着巴黎,仿佛说,咱们承认得了。
为了救那个小伙子,巴黎主动把所有的罪名的承担下来了,联防也就把小伙子放了。巴黎又被拘了起来,一拘就是3个月。
拘留结束之后,从1984年到1986年,他又被判了两年教养,送进了东北的农场——因为北京的改造农场已经满了。
三次磨难,让他的生命变得黯淡无光。巴黎的言语当中充满了无奈:“可能是压制力越大,反抗力越强。我说我没罪,我根本没罪,我从开始就没错……”
● ● ●
等巴黎从东北回到北京后,单位已经把他开除了,他只好做点小买卖。
他看到别人卖故宫的明信片卖得挺快的,就跟老太太们一起卖明信片和北京地图。他把身上仅剩下的5块钱全用来买了地图。1毛2进货,2毛卖出,因为得给别人公交车票可以回去报销,他等于卖1毛8,一张地图只能赚6分钱。
卖地图有时候站上半天,都赚不到1毛钱。地图才卖了3张,就被城管抄了。巴黎给城管跪了下来,说:“我就这5块钱,就这点收入了……”
讲述到这里的时候,巴黎哭了出来。
整整一个月,他一天就只吃一顿饭,甚至比在农场吃得还少。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块别人吃剩的面包,他捡起来吹掉灰尘,就把它吃了。
他每天早上6点起来就去景山中街开始卖地图,一天最多能赚10块钱。景山中街的厕所就是个同志的据点,好多以前认识的朋友拉他去,但他一次都没有去。一直到1989年,巴黎都没有再出现在同志圈里。他咬紧了牙,一心一意做买卖,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和命运。
他怕自己如果再出事,剩下的这半生也完了。他曾经爬到5楼楼顶,想跳楼自杀。他在楼顶上想了很久,他在北京连家和亲人都没有了,如果他就这么交代了,那多冤啊。
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昔日无法重来
时间:今天 地点:南礼士路公园
1991年,万延海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同性恋在北京》,文中提到了包括东单公园在内的北京多个同志据点。从此,东单公园“名声大振”。90年代中期,中国同志的生存环境开始有所好转,当巴黎重新出现在同志据点时,他发现世界已经变了。
对于同志来说,老无所依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巴黎在36岁那年曾经在家人的逼迫下结过一次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和妻子分了居,分居半年后,他们终于离了婚。他们有一个女儿,离婚后,女儿被判给了妻子,妻子又带着女儿改嫁了。
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巴黎见过她一次,后来再也没有见过。
如今,巴黎认了一个异性恋的小伙子做干儿子,是13年前在南礼士路公园附近的工地上认识的,小伙子在那儿打工。
巴黎跟他一聊:他8岁就没了妈妈,爸爸被判了8年,回来后脚也残疾了,他才18 就从河北出来打工……巴黎觉得这个孩子命真苦,而他一个人也挺孤独的,就说:“你给我当干儿子住我那吧,我给你另找工作,不过你得孝顺我、给我养老送终。”小伙子答应了。

△巴黎先生现在的照片 作者供图
为了认这个干儿子,巴黎专程去了一趟河北,见了小伙子的亲生父亲,又见了他们村的村长。河北的手续办妥之后,巴黎又通过北京这边的派出所和居委会把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合法化了。
巴黎的干儿子也已经30岁了,他不是同性恋,还是基督徒。他知道自己的干爸爸是同性恋,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在他看来同性恋是一种罪,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试图去改变谁。干儿子觉得干爸爸虽然有这种爱好,但并不是坏人,而且这也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巴黎现在年事已高,不能工作,只能靠吃低保过日子。
● ● ●
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巴黎和他的初恋情人突然又一次相遇了。
那天,巴黎到牛街去买药,在药店的门口遇上了亮。他们彼此认出对方,可是,即使曾经的爱恋再浓再烈,如今见了面,也只是淡淡的,只是那份亲切感还在。
他们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看着彼此,交谈着分别之后所历经的种种。巴黎这才知道,亮后来离婚了,又再婚了,现在也马上要退休了。
昔日无法重来,偶然的重逢之后,又是长久的分别。
编辑:沈燕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