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梓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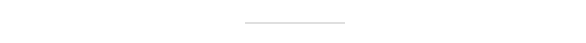
2017年,“中年”刷屏,与“丧”一起争夺年度热词称号。继刺杀金正男的“1988年的中年妇女”之后,许知远和马东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年大叔一对照,又给“中年”添了一把火。
满口新词语,发着表情包的年轻人,口口声声说自己中年了。这件事让一批按说已经中年了,内心却没有多少中年感的人感到困惑,比如我。
究竟这个世界,中年是否提早到来?抑或是,“中年”只是被年轻人流行话语文化消费的一个热词,像“丧”一样,代表一种消极的抵抗?
毕竟,说着自己很丧的人,还在不断健身、加班、到各种小店和音乐节打卡,在朋友圈秀旅行。
那么,说着自己已经“中年”的年轻人,是不是已经让真正的中年人在当下的传播语境失语了呢?
许知远的拷问,在我看来,是一种中年人试图以意义、价值、传承等指标来表达自己在话语权上仍然占据主导者和思考者的地位。但是,年轻人不关心意义,先关心这件事有没有趣。
在过去数年之间,传统的文字大厦随着传统媒体一起崩塌,每天都有新的表达形式出炉。我还在听着哈狗帮,但我的孩子的新偶像是欧阳靖(HiphopMan),原因是他会比较多的语言,能够杂糅在一起rap。
在这个年龄感混乱,文字感也混乱的年代,我采访了五位写作者和文化研究者,他们年龄都在30-40岁左右,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一定的成功,在过去几年也有不少生活轨迹变动,由他们来谈谈,他们身上的中年感,以及他们怎么看待年轻人文化,特别是新时代的话语文化。
36氪媒体助理总裁张卓,是在前几天36氪主办的“没想到游乐园”互联网粉丝节上意识到自己和年轻人不一样的:“那么热的天,她们排着长队,买五块钱的小仙女发卡,就为了戴上发自拍。这件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张卓觉得自己的中年感很强,不仅外貌在发生变化,法令纹加深,皮肤下垂,精力也没有以前充沛了,同事加班后还会去熬夜K歌,她再也不会参加了。还有一点她觉得特别明显的是,她变得不会生气了,即使生气也能控制在10秒钟内,心里就开始算性价比,我这么生气有用吗?
“当然,大多数生气是没有用的。”她笑着说,“愤怒是年轻的状态。”
而身居厦门的作家张春,在家里一堆堆书墙之中深居简出。她所供职的“犀牛故事”办公室搬到厦门岛外之后,她便大多数时间在家上班。说起今天的年轻人和自己以前最大的不一样,她的感受是现在的年轻人“有钱。有的毕业没几年就能有一两万月薪。早早就能开车上班。” 而且他们原生家庭经济状况也不错,所以他们不担心太多物质上的事情,她身边几个年轻同事不害怕结婚这件事,而且欣喜迎接孩子的到来,这让她觉得和自己当年有很大不同。
著名战地记者周轶君,最近常到大陆工作并宣传她的新书。她常常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偷听年轻人聊天。她的印象是,年轻人现在的话题太窄,太雷同。一般都是在谈办公室政治、房子等等。他们对跟自己日常关联度不高的东西兴趣不大,比如国际时事。现在公众话题缺失,通常就是娱乐八卦。“我最近听了很多薛之谦。”她说。
以我自己的经验,我是在接连听到两个女孩非常坦然地说自己拍过艺术裸照,其中一位还说允许摄影师将自己的照片放到网站上的时候,觉得自己和年轻人“有点不同”。当然,我还对三明治年轻同事对咖啡的高度依赖,对猫的极端迷恋也略为不解,虽然这些事可能和年龄无关。
新一代90后中国人和70后、80后的不一样几乎不言而喻。他们的独立意识,自我表现意识,杂糅在他们那些社会中坚的父辈阴影下,有的脱颖而出,有的也对父母言听计从。那些从40、50后普通家庭中走到大城市顶端的70后,当年更多凭的是先斩后奏的勇气,他们对生存的渴望和用力,是80、90后不可比拟的。而80后作为第一批独善其身的代表,在一个并不充分宽裕,但足以保证自己小资的氛围里,并无过多改写世界规则的雄心,直到90后的出现。
《智族GQ》杂志总主笔何瑫是85后,他也感觉到自己的同龄人,在刚毕业之后,就进入了焦灼的实用主义。他认为这和90后大为不同。这种实用主义决定了他们无法去过度游荡,狭窄的选择空间使中年感提前降临。
这种对今天年轻人的艳羡,以及认为他们包袱更小,更易成功的评价,似乎和今年90后对自己的认知不完全一致。90后可能会看到他们的前面已经有太多利用资源红利时代先出名或者先富起来的群体,反而陷入一种困难感。
今天的年轻人心目中,对自己和已经成名的先行者的距离判断,究竟是不屑一顾,另辟蹊径,还是觉得鞭长莫及,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谜。
他们的进取心,比起受物质困扰更多的70、80后,究竟是更强了,还是更低了?
2001年,我开始混迹“西祠胡同”,当时最大的中文互联网社区之一。我给自己起的ID叫做“新语言”。
起这个ID的时候,我正在广州大道289号12楼的《南方周末》办公室蹭着电脑,脑子里想的是,互联网时代来了,BBS上的语言都是新的语言。而中文的写作语境,也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了。
后来,我用这个笔名给《新周刊》写稿。某一天,令狐磊在Msn和我说,主编不喜欢这个笔名,你得改一个。
看来,“老革命”们不喜欢“新语言”。
今天,我们好像也成了不喜欢“新语言”的“老革命”。
平心而论,我觉得像“不明觉厉”这样的词还是很传神的,足以入选新时代《成语词典》,可惜像这样的词语不够多。
周轶君加上了一个她喜欢的新词:“喜大普奔”。她说自己偶尔也会用,但她会抵抗用这种词的频率,因为思维会被动漫化控制。因为这些词本身就像是表情包。
她对新的词汇持包容态度:“语言是活的。我虽然对书写文字还有洁癖,心里也有矛盾,不会迎合用这些词汇,但它们有自己的逻辑可以生存。国外青少年发短信,那些缩写你也看不懂的。但这些潮语的生存寿命有多长,得打个问号。”
她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传播的载体变了,“都说古人简练,那是因为以前刻字费劲。同样,手机阅读滑屏,最适合的是找金句,看图片。再往后,可能文字都不存在。但文字的有效性,现在还没有别的载体超过。比如要从视频里搜索关键信息就很难。”
看起来,“中年人”们有太多理由为今天的文字担忧了:微信上流行的是一句一行(还要居中),然后配动图的鸡汤文。一批批的流行新词,使年轻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用上这些万众雷同的表述方式。他们自己的话语不见了。小孩子变得不爱写中文,甚至连字都写不好。他们的英文可能比中文还好。
但是在何瑫看来,很多人感到悲观,可能是有认知的偏差。因为社会的圈层从来都是类似的。他赞同马东5%和95%的论断,认为当年喜欢《读者》、《知音》这类的受众,在现在总体的比例没有变化。
“人性变化的层面其实非常慢。以前的网络不发达,传播上不直观可见。一个人自己在读《南方周末》,可能就觉得身边的朋友都是在读《南方周末》了。现在的朋友圈,所有人混杂在一起。他们所阅读的东西,千差万别,观感就会和以前大为不同。”何瑫说。
以我以前混过的西祠胡同BBS为例,在当年,那些帖子的标题,甚至昵称的名字,已经属于背离传统,吸引眼球的了。那是王朔的“痞子文化”流行的时代,我记得班里的一个同学起了一个昵称,叫做“我那么帅容易吗?”,就令我印象深刻。
而在今天,不仅人的名字被解构了。一切看似一本正经的权威也自动放下身段来亲近受众。其转变之快,令人刮目相看。比如各地政务发布的官方微信公号,用网络词语之高频,不比其他网红少。而像之前刷屏过的新华社“卖萌体”,更令人产生错乱感。
在纸媒彻底衰落,所有人的主流阅读都是网络化的情况下,网络化的内容就几乎占据了我们可见的视野。
话语权看似被年轻人占据了,因为他们永远在发明新词,永远在更新表达方式。但与此同时,罗振宇、马东等中年人却在背后策动着引擎。
周轶君认为,今天很多大V,都是从上一代互联网,甚至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来的。
何瑫则认为,今天每个人各占山头,无论中年人、年轻人都可以有话语权。以前的时代有大众偶像,但现在没有。不要看吴亦凡、鹿晗很火,但他们比不上邓丽君、周杰伦的影响力。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对他们出过什么专辑没有印象。80后这一代,所有人都知道韩寒、郭敬明,但可能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到现在,我们连90后共同知道的新作家都没有了。
话语权不在谁的手里,每一个人都是话语平原上的游勇散兵。
扎着辫子,浑身上下打扮非常亲近青年文化的张安定,是青年市场研究机构“青年志”的联合创始人。他还未到40岁,却说自己的中年感在30岁时便已来袭。
“那段时间就是觉得一切都没劲了。创业也好,音乐也好,做到一定程度就觉得事情都差不多了。其实中年危机烦的不是年龄,而是感觉人的创造力和价值感急剧降低。”
近几年,他在管理青年志的同时,重新投入到声音艺术的创作。每天晚上9点开始,孩子睡觉之后,会给自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在他位于顺义的别墅里,写写音乐,写写字,或者呆着什么都不干。
国内的一些声音艺术节也开始邀请他演出或者做展览,“感觉恢复了自己一些文化脉络。这些社会上的文化网络是以前你遗失了,或者放弃了的。” 和同好喝着酒,讨论着声音艺术,他仿佛回到20岁出头在复旦大学读书的状态。
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不服“老”,尤其在30-40岁之间这个“前中年”时期,他们虽然感到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不如前,但是内心的创造力并未损分毫。他们也不愿意被社会简单冠以“中年”的标签,这个标签会带来太多的误读。
像张卓,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叮嘱我,不要把她当做中年的代表。对于有创造力的人,年龄并不是问题,“无龄感”对他们更加适用。
但是,有更多的人,在还没有机会舒展出自己的创造力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原因束缚住了,畏缩了。所以他们早早体会到一种所谓的中年感,这种中年感的来源,部分来自他们惯常看到的父辈生活方式,惯常看到的狗血电视剧。他们对中年的定义也是刻板的,那就是:犹豫不决、无力改变、压力重重。
对这种传统中年感的厌恶,也使很多“中年人”更愿意和年轻人站在一起。张春最近发觉自己在一个瑜伽群里快呆不下去,因为所有人都在说着“感恩”、“成功”,她认为那是一种非常落后的表达方式,相比之下,她更爱和年轻人呆在一起。虽然,他们有时在办公室突然开始唱流行歌接龙会使她有所错愕。
张安定认为,中年感和实际年龄无关。今天的年轻人说的“初老症”,本质上和中年危机是一样的。他们在生存上的本能欲望很低,但其实对个人的价值感有深深的焦虑。在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法的状态下,他们普遍是在游荡。他认为,最反映这种状态的,是最近火起来的《明日之子》冠军毛不易,他生于1994。

《像我这样的人》
词曲/毛不易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还在人海里浮沉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早就告别了单纯
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去换一身伤痕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
https://res.wx.qq.com/mmbizwap/z ... sprite.2x26f1f1.png);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webkit-background-size: 37px; background-size: 37px;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background-position: 0px 0px; 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no-repeat;"> 像我这样的人毛不易 - 明日之子 第8期
像我这样的人毛不易 - 明日之子 第8期
张安定说到最近他们的青年文化社群接了一个有趣的小业务:腾讯的一些高层让他们寻找一些职业和生活状态各异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一些小KOL,互加微信好友,互相观摩朋友圈。
他认为对于年轻人新的东西,看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可以去看一看,这样才能有开放的大脑。今天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平原,今天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年人和年轻人的问题,是信息蜂巢的问题,信息太多元了,但多看一看终归没有坏处。
而对于许知远提出的,后一代人会不会觉得这一代留不下一些什么文化遗产,张安定认为,历史的,宏大的和当下的、碎片的、流动的表达方式,是现今互相结合的两种表达方式,为什么就认为年轻人对历史不感兴趣,没有讨论过宏大命题呢?在豆瓣、知乎里面,很多重要的议题都被讨论过多次。
何瑫也认为,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是经过精选的,直接拿它们来和当下的东西比较,是不公平的。每一代都会有很多留不下的东西,也总会有东西留下来。
他在所供职的智族GQ杂志,用特稿语言写着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比如鹿晗粉丝,比如MC天佑。但他也非常深刻地感受到,特稿这个圈子越来越小,让人孤独。
而曾经操刀过《人物》杂志多期封面报道的张卓,现在已经不写特稿了。但她也有点遗憾地看到,很多年轻人现在不知道精致的文字什么样,读书习惯很快没了,中文功底比较差。
周轶君有点怀念之前的博客时代,“那时博客的文章还是挺规矩的,有很多文笔很好让人惊艳的作者。在当时,文笔好还是很重要的,大家推崇文采。今天文采不那么被关注。今天的表达也不那么节制了。”
我和张卓也有同感。我和同时代人的阅读习惯,天然倾向于更有内涵的文字。在某些时刻,我会为生产这些美好文字的人越来越少而担忧,害怕他们因为生存,因为功利的吸引而去生产迎合年轻人的文字。这种忧心忡忡的状态,本身就像那时看到流行歌词就慨叹世风日下的老年人。现如今,李宗盛的流行歌词已经被当成华语典范。
或许,文字这样的载体本身会变得面目全非,但文化总在各种缝隙里流动。它们会寻找自己的出路。
用张安定的话说:“文化变成了颗粒,但不代表它没有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