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凌岚
现在学校课堂配备多是塑胶白板加彩色马克笔,高级的课堂用电脑投影、smart board。我上大学时的课堂配备基本是清一色黑板粉笔,那时北大中文系有许多奇人,其中一个以板书出名,不是说他粉笔字有多工整漂亮,这位教授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右手执粉笔写字,左手执黑板擦擦字,一边写一边擦掉,几乎同时进行。座下的学生根本看不清他写了什么,再写再擦,如此循环往复,90分钟课他留下的永远是一张空白的黑板。他的那些妙论,只存在于须臾之间,你只有全神贯注,不眨眼地盯着看,只字片语在他左手黑板擦到达前才可能被你看到,否则就消失了,比雪泥鸿爪还快。
这个奇特的习惯据说是文革后遗症,不愿意留下白纸黑字。90年代初的大学生已经有不少配备了小录音机,当堂录音的同学并不少,板书没有了,但声音还在,好像碳排量,不留痕迹是困难的。

晓征用文言文写的中篇小说《换头》,收于作者新近出版的小说集《美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读《换头》不时想起这位先师奇特的书写习惯,晓征没有一边写一边擦,但她选择用一种冷僻的语言,在中国社会普遍引进白话文,白话文完全代替文言文的一百多年后,她宁可退回到文言文来写作,她需要一套相对陌生的语言的保护和遮蔽,才能铺陈她的故事,这种姿态在当代中国的文学风景中也是一个奇观。
像我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基本没有碰过文言文,如今忽然读《换头》,等于在迷宫寻宝,很花了一番功夫才能习惯。好在《换头》是用浅显的文言写的,中文读者需要一些耐心,训练眼睛习惯文言的节奏和用词,就能跟上故事的发展。有朋友提醒我《换头》行文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它更类似于《红楼梦》这种早期章回小说的语言,用的是文白结合的一种混合语言,但恰恰是这种典雅的文白混合体是我的阅读障碍,我读不懂“云卷云舒”、“亦悲亦喜”这种套语,这些词汇貌似典雅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是一种烟幕,我的理解,这种利用章回小说的套语,达到文意的含混,是作者有意为之,跟此前文学史上女性作者的秘密写作是一个意思。
女性的秘密写作,最著名的例子是简·奥斯丁和她家吱吱作响的门,女作家不肯把门修好,那扇门的响动等于是来人的报警器,让她可以迅速把正在写作的草稿藏起来。奥斯丁写作的纸张大小是19厘米×12厘米,用大幅的书信纸裁出来的,从现存的1000多页奥斯丁手稿可以看到这种小小的纸片,它能很容易就能被夹在书页之中。但奥斯丁写作并不躲着家人,奥斯丁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她的第一读者,终身的粉丝团,她给家人朗诵自己的小说是家族中长期保留的晚间节目,奥斯丁在吱吱作响的门后要躲避的是来客和家佣,她不是秘密写作的极端例子。
著名的勃朗特姐妹,安·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在以合集形式发表小说的时候,用的是男性笔名,以致《呼啸山庄》很长时间里被认为出自男性作者之手,《呼啸山庄》的阳刚的文笔,对肉体之爱狂热赤裸的直写,使英国读者深信不疑它是男作者写的。在笔名上乔装改扮,让艾米莉·勃朗特可以突破读者预期,获得言语表达的自由,可以自由书写,不再受到女性写作传统的禁锢。
秘密书写的极端就是“女书”,这种湖南江永地区流传了千百年的密码一样的文字,像秘密结社一样神秘,它只在底层女性中传播,只有女人才能读写。据说“女书”起源于当地女人不能进学堂读书识字的习俗,“女书”貌似汉语,但跟汉语完全没有关系,这种对汉语和汉语代表的价值世界完全拒绝是秘密书写的极致。
退回到文言或者早期白话小说的传统,这种倒退的目的主要是躲避周围熟悉的人,《换头》并不像“女书”那样完全在地下流传,它公开出版,作者对《换头》流传于陌生的读者反而感觉安全,所谓小隐隐于市,《换头》是隐于陌生读者,隐于半文言这种语言的迷宫。
《换头》开始是伤感故事,“七年之痒”遇上蒲松龄的经典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的《换头》原故事,写一个下了阴曹地府的书生在言谈之中跟阎王爷结为知己,惺惺相惜,阎王爷决定插手帮仕途坎坷的书生一把,不仅帮书生的老婆换了一个姿色妍丽、青春焕发的头颅,而且还在书生还阳前帮他把肠子(腹中诗书)理顺,这样书生可以在科举考试中一展才华,赢得功名,从洞房到仕途,书生获得第二次人生,最重要的这第二次人生必须是成功的人生,这样才不枉“换头”的代价。
唯一的,伟大的蒲松龄没有顾及的问题,就是那个被换头的主人,书生的发妻,那个女人可否愿意“第二次人生”,她是无辜的,她在没有任何选择,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情况下,忽然身首异处,掉进一个“无我”的陷阱,在被谋杀之后她必须开始第二次人生。可怜的葆贞虽然没有花费一分钱去韩国整容就获得一次免费的容貌升级,但是她失去了原来的旧我。
这跟原来男性视点的设计完全不同,“原来的设计”,用换头“主刀手”虬髯客的话,并不会有故事,换句话,被替换下的“旧头”不会有新人生,它就像换下的破轮胎、用秃的毛笔、摔裂的砚台那样被丢弃, 蒲松龄原故事中的被换头者,就跟猫或者狗被换了头似的,并无任何异议,虽是人身但没有人格和个人意志,是一个可以任意取代的符号或者物件。
晓征的改写,就是从这里开始,被换头的她,有名有姓有个体意识,有心中的不愿意,她被咔嚓后掉进无我的陷阱后还存在知觉和意识,而且还活着,好像爱丽丝跟在疯疯癫癫的兔子后面掉进洞里,进入二次元,晓征版换头故事就开始了。蒲大师的经典被引入女性视角,好像在经典叙述的厚壁上开了一个窗户,让光线照进来,这样一来原来按部就班的一切立刻乱了,价值观被颠覆,世界变得魔幻,你不知道故事后半部分的那些奇丽的探险历程是来自主人公的内心风景还是主人公的“真实”历程,你不知道那分道扬镳,花开两枝的人生,是故事中人物的结局,还是象征性寓言,内心的伤口开始说话,甚至还开花结果,这是《聊斋》没有的,这是晓征的创作。
《换头》不是探讨男女之爱的,是讨论一夫一妻这种婚姻家庭制度的。小说男女主人公常生与葆贞,自青梅竹马的真爱开始,他们表面琴瑟和鸣的婚姻关系,其实并不能抵挡虬髯客一个小小的建议。常生居然相信给妻子“换头”这种奇葩的办法能改进婚姻生活,可见他的厌倦之心,厌倦后又想蒙混逃避,走捷径,以小改变达到大改观,好像东北话里说的“一番翻洗一番新”;而葆贞虽然贤淑,却对自己心爱之人内心的郁闷孤独一无所知,这种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混沌,是装不知道呢,是女性维持婚姻以及自我保护的大智慧呢,还是对夫妻恩情的执着呢?葆贞是圣人的话,常生日子更不好过,跟圣人过日子不容易。
一夫一妻制婚姻结构下的责任和压抑,常生有次借梨花感叹:
“常生折梨花一枝,于手中把玩。殊不料满树花光秀色,一旦拘执于掌中,倒令人颇感讶异:其色也薄,其香也淡,始知古人云——聊赠一枝春,实乃诳语:春色惟在梢头树巅,陌上山间,可远观不可亵玩,岂容折之于掌,怀之于袖邪?”
译作白话:到手就不稀奇了,奇花丽人都是如此。
在《换头》中跟一夫一妻制度对照的,是少数民族莫歇人的走婚制度,近似于现在说的开放婚姻,夫妻双方都可以各寻所爱,没有道义上的责任,没有婚姻牢狱所累。常生对异族婚姻的羡慕,隐含了自己的无选择自由,常生唯一的解脱办法是把老婆杀了,这真是黑色幽默,过去我一个希腊裔女友说的“寡妇好过离婚单亲”跟常生的换头法有一拼,想想英美社会高离婚率,有说离婚率超过社会成婚人口的50%,这是社会进步与开明的表现,可以离婚,而不需要动刀子换头。
更黑色幽默的是,常生最后收到那具表明真爱的头颅,他的反应不是电影恐怖片里那样吓得尖叫,而是特别文明的“亦悲亦喜”,悲可以理解,发妻头颅在木头盒子里啦;“亦喜”就非常怪异,他是真把收获头颅作为发妻对自己的爱情宣言,常生变成猎头一族,写到这里,晓征的创造力,对荒诞的把握,已经远超过蒲大师。蒲松龄的故事是起点,晓征站在大师肩膀上,触摸到家庭生活,两性关系中的基本困境。
颠覆中国传统小说的套路,戏写经典,在当代文学中最著名的作者是余华。他的1988年发表的作品《古典爱情》把赶考书生私会小姐、私订终身的章回小说套路,改成大饥荒年代人相食的惨景,书生最后抱起已经被卸下一条腿的小姐狂奔,小姐这时有一个食品类的别名,“菜人”。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写“两千年历史”,“密密麻麻写满‘吃人’二字”,被余华坐实。当代中国文学对中国传统经典的回顾和戏弄,似乎止于余华的《古典爱情》。直到这种写法被《换头》继续。《换头》没有余华的暴力血腥,它是幽默地戏写,无奈,调侃,但总的来说温情脉脉,这从结尾对头颅的佛学处理就看得出来,常生对旧头之留恋不能自拔。
幽默和念旧,都难掩常生在两次婚姻中的孤独,围城内孤独,出走后长河落日,高山秀川中也孤独,右手永远在写,左手须臾擦掉,人就是这样自我矛盾,不止不休,这是《换头》最打动我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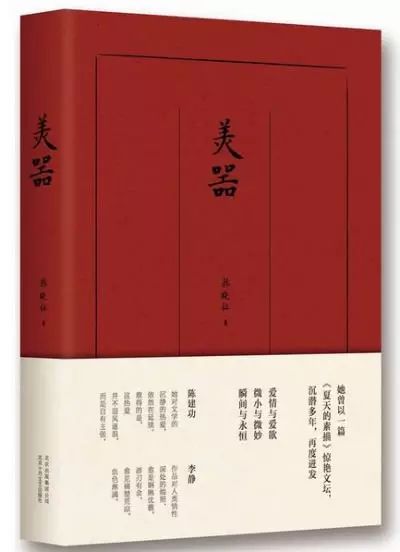
图书信息:
《美器》
作者: 韩晓征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页数: 372
定价: 35.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30215319
(本文原标题:《女性的秘密书写和反抗》)
【作者简介】
凌岚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写字是一生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