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潘向黎
有一位朋友,读过我所有的散文,问我:“你怎么不写写你的童年呢?”
我的童年?是呀,人对自己的童年总是有许多记忆,何况我是一个能用笔将记忆再现的人,为什么在我的再现里偏偏没有我的童年呢?朋友的问里含着轻微的责怪,一时间,我说不出话,心里竟有了几分伤感,好像一个自尊而卑微的人,对所有的恩情一直等待着能够涌泉相报的一天,不料老大蹉跎,竟被人当成了不知好歹。
但是怎么说我的童年呢?我至今不知道它真实的面目究竟是怎么样的。倒是一些小事,它带给幼小的我的滋味,到现在还没有淡漠。就像我九岁那年出车祸小腿骨折,接骨后为了恢复连续几个月吃一种叫“健步虎潜丸”的药丸,黑乎乎的,非常苦,而且有一种刺鼻的难闻气味,那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的观念,据说那药是用虎骨煅成灰做的,每天要吃一大把。为了早日能走路,也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每天总是很痛快地几乎带表演性地把它吃下去。
妈妈总是说:“这孩子从小很会吃药,再苦也不怕。”爸爸假期回福建,被这药的气味熏着了,为了了解它难吃的程度,居然自己吃了几颗,他脸上的表情尚属平静,但吃完马上对我的“吃药勇敢”表示了赞赏,颇有点“孺子可教”的意思。其实过了很久,只要说“健步虎潜丸”这几个字,我的嘴里立即会泛起一种怪味,如果不转移注意力,胃也会抽痛翻腾起来。爸爸在多年之后表示:那药的味道是他吃过的所有药里最难以忍受的。而我也明白了爸爸当年尝药背后对女儿的怜惜之情。

不回忆童年,难道是因为那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被忍耐、被掩饰过去了的苦涩,让我不愿或者不敢去重温吗?
有一次,在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的操场上,在围墙上掏洞,把土块拿开,有一棵鲜绿的羊齿植物猛地弹出来,吓了我一跳。原来它一直在土里面活着,我搬开重压,它就直起腰来了。从梦里醒来,我想,许多往昔,就像那棵羊齿植物,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活着,尽管我的意识忽略它,但它依旧生气勃勃。
现在是一个初夏的周末。我的窗外有树,树间有孩子在捉迷藏,找了一会找不到,一个就急了,开始喊:“你在哪儿?”另一个迟疑了片刻,似乎听出这不是游戏中的诡计,而是真的在寻找,就答道:“我在这儿!”那一个欣喜地:“你在哪儿呀?”“我在这儿呀!”同样兴奋的。稚气、清脆、饱含汁液的声音在树间弹溅,在阳光炽烈的正午,使人觉得十分凉爽。
我相信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过去、现在、将来是在不同层面上同时存在的,时间并不真的流逝,人的成长过程,不过是同一个“我”(灵魂)穿越昨日的我、今日的我、明日的我这样一个个躯壳而已。那些躯壳在不同的“层”上存在,只是我们处在一个层的时候看不见其他的层而已。就是说那些过去、未来的故事现在就在不同的地方上演着,但是我们不能触摸,无法改变那一切。
如果我对另一个我——“童年的我”呼喊:“你在哪儿?”我能不能听见她的回答呢?我是多么希望和她见面,问她究竟遇上了什么,使我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她是否受过什么伤害,使我有那些心理上的禁忌?使我总有一种到哪里都是异乡,找不到同类的压抑悲哀,经常一意孤行仿佛胸有成竹其实十分缺乏自信,凡事担忧悲观,总是预想不好的、不利的可能,甚至因为长久的忧虑以致坏的结果到来时反而觉得踏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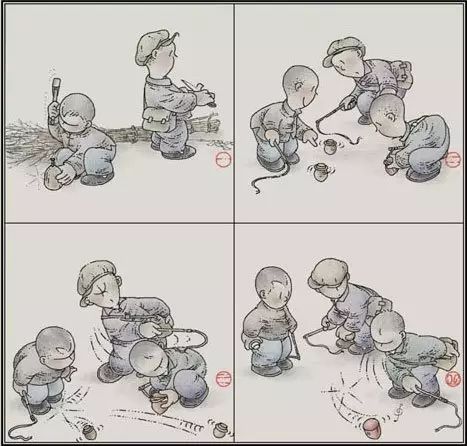
真的,“你”在哪儿呀?“你”能不能告诉我,帮我解开这些结?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是“你”做了什么,应该受到惩罚,那也不该株连到今天的我呀。可是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有什么应该惩罚的呢?那么,是不是缺少了什么留下的后遗症?缺少关心?缺少赞美?还是缺少同伴?缺少自由?缺少安全感?我不知道!
我多么希望当时的一切能够重来一遍,让今天的我能以旁观者的立场了解真相。我不会像电影《时光隧道》里的人那样企图改变历史,但是我也许会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安慰一下幼小的自己,我会说:“没有什么的,小姑娘,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等你长大,你都会想不起来的。”可是她站在漆黑的走廊上哽咽着,非常伤心,没有听见我的话。在梦里那些事仍在上演,仍有泪水打湿今天的眼睛,但是当我醒来,我就又忘了是什么让我悲伤。曾经在一个网上的聊天室里,我在个人资料的“梦中情人”一栏填的是——“醒来就忘了”,有些悲伤虽然也忘了,但是它们的余波依然使白天变得沉重。
每个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无忧无虑的。那种认为只要是孩子就无忧无虑的看法,不但错误,而且因为带着成年人特有的偏见固执而显得不公平。
我不记得那是几岁的时候了,总是在学龄前。我和母亲住在乡村中学的宿舍里,深夜,她在改作业或者备课,我没事可做,又没有人理我,就坐在一边发呆。所有能看的小人书早就翻烂了,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不是在做功课就是被督促上床了,我真是无聊。于是,我开始胡思乱想。想些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想着想着,就自己溜出去,也不敢走远了,就到隔壁一幢教学楼去。楼里没人,灯也都灭了,走廊上黑漆漆的。我记得我走到中间一根柱子旁边,是用红砖砌的四四方方的大柱子,就对着它说话,最后我说:“我怎么办呢?”它默默地守着我,似乎也很无奈。在那样的黑暗里,我感到了人生最初的莫名的孤独和安慰。此后我经常到那儿去,总是到第二根柱子面前,对它说话,和它讲故事,对着它叹气,有时把脸贴着它哭。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家,柱子和我共有了许多秘密,它变得像我的亲人一样。我的母亲不知道这些,幸亏她不知道,否则她一定会担忧的。
我的童年最重要的几个因素是:父母被迫分居,我在12岁之前是由妈妈带着的;生活环境即使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相对清苦贫乏的,不仅因为在乡下,而且因为妈妈一直盼望着早日调到上海和爸爸团聚,这个盼望如此急切以至于成了日常生活的障碍,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带了临时凑合的色彩——这一凑合,就凑合了十几年。妈妈后来许多次无限后悔地说:“早知道会在那个地方那么久,至少放在泉州你外婆家的那架缝纫机要搬过去!省得一针一线的缝。”这种临时凑合心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什么样的影响,说不清楚了,但是影响是肯定有的,也许我无论到了哪里,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是处在漂荡之中,源头就是要从那时说起。但是我不能肯定,我的思想如果是灯,灯柱之下,内心仍有一块昏暗不清的地带。
那时和成年人在一起,他们的话我似乎都听得懂,而且时常插上一句不像孩子说的话,他们就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有些异常似的,后来我就只听不说,那样他们就不注意我了。妈妈的同事经常说我“早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听多了就有点反感。后来爸爸说:他们用词不当。可是当时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是老老实实的孩子,所以功课和表现都一直好,年年三好,奖状贴了家里一墙,还当了中队长、大队长,因为父母都是教师,所以我的老师们经常说“龙生龙凤生凤”(当然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老师就让他和我坐,希望使他近朱者赤,这证明在老师心目中我是好学生。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作为孩子是有些乏味的,正统得呆头呆脑。
幸亏我喜欢看书。我不太喜欢和小朋友出去玩,一做完作业就只喜欢看书。有时上课老师讲的内容我懂了,也在下面偷看小说。我的阅读速度快,大学里曾一个中午就看完了《百年孤独》(从上午的课结束到下午的课开始,因为急着要还,没吃午饭),现在还能一个通宵看完四五十万字的小说,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训练出来的。
在同龄的孩子中间,我算是有条理的。书包里总是很整齐,一发新书就用包书皮包得漂漂亮亮,闲下来喜欢整理文具盒。
自幼父亲不在身边,又没有哥哥,自己又没有什么本事,所以特别胆小,容易紧张,但出于自尊心表面上却总是很镇定,那么小的年纪便学会了“故作镇静”。“无忧无虑”这个词对我的童年是不适用的,我经常为了一件小事而难过、沮丧,为第二天一件要面对的事而提前闷闷不乐。甚至会为与我无关的事而心虚恐惧。
记得有一次班上有一个同学的钢笔丢了,老师决定查所有人的包,我一下子手脚冰凉,心狂跳起来,咚咚咚的越来越响,好像全教室都充满了我的心跳声,我觉得老师和同学都听见了,并且开始怀疑到我,于是更加紧张,只能拼命地低下头去。当老师走到我面前打开书包时,一种可怕的预感几乎让我晕倒——我觉得那支钢笔一定在里面!而我的人生就因此而毁掉。但是没有,当然没有。最后钢笔找到了,不记得是在谁的书包里,还是在地上了。因为过度的紧张已经使我昏沉虚弱。不知道能不能用原罪意识解释这一切,如果不能,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爱干净,很知道爱惜衣服,一般不会弄脏,脏了就很难受,一回家就马上换下来洗。我的衣服保持得都很完好,后来留给妹妹穿时大多数都还七八成新。只有一个例外。有一次妈妈给我新做了一条蓝色的裤子,是用海外亲戚送的衣服改的,料子厚厚软软的很舒服,第一天穿了去上学,回家时不小心在坡道上摔了一跤,把膝盖处磨破了。我难过极了,回家时都不知道怎么对妈妈说。但是妈妈却问我膝盖破了没有,我说没有。妈妈看了看,说:“咱们老家有句话,叫‘皮破裤不破,裤破皮不破’,你看是真的。”她这样说时笑微微的,因为我没有受伤而很欣慰的样子。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条早已不知去向的蓝色裤子,记得穿上它时感觉到的快乐和温暖,还有它破了的时候感到的深深的母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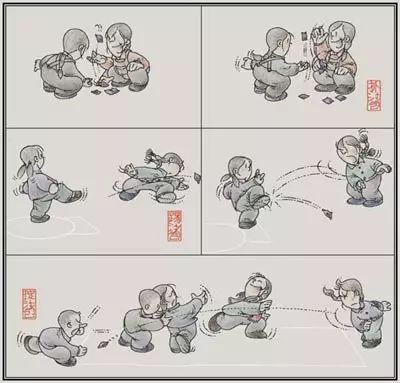
那时爸爸每年回家一次,带来一些肥皂、白糖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凭票供应的,还有给我的椰子糖和万年青饼干、杏元饼干。椰子糖和杏元饼干浓郁的香甜和万年青带葱油的香脆,是我童年记忆中无上的美味。每次爸爸走后,我都要把这些好东西分成几份,放在不同的铁罐子里,好有计划地慢慢享受它们。后来爸爸还给我买过一双红色的小皮鞋,上海产的皮鞋样子好,而且颜色如此鲜艳,是所有小朋友都不曾拥有的奢侈品,一下子成了所有人赞美和羡慕的焦点。我不但穿它上学,而且穿着它踮起脚尖跳芭蕾,吴清华倒踢紫金冠没有学成,倒把鞋尖给磨毛磨白了。
爸爸对我文学上的启蒙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他自己深知“文章满纸书生累”,当时的氛围下绝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再沾这些惹祸的东西。但是我想看书却没有书看,我已经看完了所有我能买到借到的书。在我反复的要求下,他给我抄录一些古诗词,其实不是抄,就是凭他自己的记忆写下来。后来当我为此感激他时,他才说:“我是实在不忍心看着你读那么多有毒的垃圾。”每次他回家就给我抄上几首,写在文稿纸的反面,非常工整,都是繁体字,有李白、孟浩然、王唯的诗,后来有苏东坡和岳飞。第一首词就是“怒发冲冠”。因为太小,爸爸又不在,许多意思根本不懂,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们很有意思,很美,而且爸爸说趁记性好先背下来,以后长大就懂了,所以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很努力地对待这门学校之外的功课。小朋友们在玩在闹,他们觉得我看书不可理解,我觉得他们都在浪费时间,其实是无是无非,各得其所而已。记得背岳飞的《满江红》时,我在“凭栏”的“凭”字边上写上发音“平”,就这样爸爸的蓝色钢笔字旁站着我的铅笔小字,这样的课余读物伴随我渡过了童年许多时光。等到下一次见面,我总是主动要求爸爸检查,我站在他面前朗朗背出烂熟而不知其意的文字,爸爸专心地听着,然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有时还会和妈妈交换一下微笑的眼神。虽然他们并没有夸我——他们坚信爱孩子就不要随便夸奖她,但我已经非常高兴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自信满满,那样的亲情交流,那样的甜蜜完满,真是我童年的好时光,也是一生中难得再现的好时光。
此后我再没有勇气说,都好了,你检查吧。因为我一直没有准备好。作为一个成年人,要让父母满意,让他们为我骄傲,需要做的事太多太难了,而我再不能像童年那样专心致志了,有太多的牵绊和矛盾耗费着我,而他们也渐渐地老了,我只能用掩饰痛苦、报喜不报忧来表达我的爱了。这大概也是人生最无奈的几件事之一。然后,十年前,父亲竟然离去了。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陷于劳作之中,心情也常像钟摆一样,在厌倦看破和焦虑愤懑之间来回摆动。不止一次,我问家里人:你说,如果爸爸还在,他会对我现在这个样子满意吗?虽然家人都说会,但是我只是叹息着,不想讨论,因为曾经没有把握,现在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然而,我的童年毕竟拥有过爱,就像一棵得到及时灌溉的植物长得生机盎然那样,我从小就懂得感情,和由此而来的悲哀。
有一天晚上,我们家隔壁的雪蕉阿姨(她是位数学教师)在我们家闲坐——她是我们家的常客,也是母亲当时最重要的女伴。妈妈拿出她自己抄的歌本,唱起了其中的苏联歌曲。都是我听过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
妈妈是俄语专业出身,她可以用中文唱也可以用俄文唱,舌头一卷一弹的,很好听。妈妈一唱俄文,我就有些担心,总觉得她变成外国女人不再是我妈妈了,等到她唱回中文,我就会很高兴,好像妈妈从远方回来了一样。我最喜欢用中文唱外国歌的妈妈,就像看见她穿上了一件外国衣服,显得很漂亮,但眉眼还是我的妈妈。
那天晚上除了雪蕉阿姨,后来又来了几个妈妈的同事,不知怎么妈妈唱了一支我没有听过的歌。我当时在一边看书,那歌声吸引了我,我停止了读书,静静地听她唱。
那首歌是多么奇怪啊。“当年我的母亲,整夜没合上眼睛,她坐在灯下,为我缝一条手巾……”,我还那么小,小得不知道忧伤的旋律和歌词里的离愁的厉害,只知道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起来,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要离开家离开妈妈的人,觉得妈妈正在灯下为我缝手帕,然后我们伤心地分别,我回头向她挥手,然后分别,走得很远很远,但是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她啊……突然,一声惊叫惊醒了我,“看,小丫头流眼泪了!”是雪蕉阿姨的声音,我回过神来,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我脸上,我才知道她们在说我,然后才发现自己早已满脸是泪。那一刻我非常窘,同时有点怨恨,似乎她们破坏了一件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心爱之物。
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妈妈问我为什么哭,我觉得她很奇怪,自己唱了那样的歌,怎么还问别人。我说听到有人离开妈妈,心里很难过,好像是我自己。妈妈说傻孩子,以后不要这样了,那是假的。妈妈说时似乎有点心事重重。

现在想起来,那是我对艺术或者说非现实的东西最初的领悟和感动。但是妈妈有点像个解构的高手,她明明那样感动了人,自己却又否定消解了它,好像我的这种流露是一种不应该。是不是因为在当时,这也属于资产阶级情调,会遭到批判、带来麻烦?但也许是我误会了,妈妈只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此善感又不会掩饰,为我的明天、我的一生有些担忧罢了。
如今的我,依旧是容易被感动的。并且我还写作,想通过写作来感动别人。但是常常达不到。也许因为别人没有我当年那样柔细纯稚的心等待感动,也许是我没有妈妈唱歌那样的感染力。也许所有的艺术家都会羡慕我妈妈,因为她唱歌毫无目的,纯凭一时的兴致,却赢得了一个孩子最清澈的眼泪。
关于童年,好像我还是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多余的探寻,因为童年并没有离去,我们的成年只是现实的白天,而童年是梦,会在夜里来访;喧闹时它远遁无影,沉静时它又会出现在我们左右,轻盈地玩着捉迷藏。
我们确实走得很远了,回头张望,来时的路上已云雾横遮,但就在那苍茫之中,有暗夜露珠般隐隐约约的啜泣,和细细柔柔清清幽幽的歌声,那就是童年。
(本文原标题:《我的童年》)
【作者简介】
潘向黎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文汇报特聘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