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巫蛊,正在形成一个隐性的市场。巫师算命、职场巫术、给他人下电子“诅咒”等花样层出不穷,一些和巫蛊相关的内容流量达到几千万次,还有著名的集团公司公开招聘玄学博主。
题图 | 《甄嬛传》中,安陵容对华妃行巫蛊之术,被皇后发现。(图/《甄嬛传》)
在原始社会,巫术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叫魂、拆姻、炼蛊、扎小人、斗风水,因其暗黑而被称为“黑巫术”的巫蛊衍化出多种形式,以供人类处理与自然、社会以及他人的矛盾,一直是神秘而让人战栗的存在。
巫术也是最古老的一种玄学消费,不少古人愿意为各种虚无缥缈的仪式散尽千金。请巫师作法,祈求消灾免难、多财多福,属于巫术中的“白巫术”(或称“吉巫术”),类似于求神拜佛。
今天,巫蛊现象仍不鲜见。2024年,贵州省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网红“苗圣”案,男子杨某某打着治病消灾、驱瘟解蛊等旗号,自称掌握“能量玄学密码”,对粉丝实施诈骗。同年,湖南省凤凰县一男子自称“下蛊大师”,声称可以通过“下情蛊”挽回爱情,兜售三种级别的“下蛊套餐”,有17名受害者受骗。此人同样被公安机关抓获。
如果说巫蛊是无稽之谈,那它为何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仍广泛存在?
邓启耀是一名人类学家,三十余年来致力于中国巫蛊现象与文化的研究。他以科学实证的精神深入多民族的边远乡村,遍访巫蛊实例,甚至亲身“试蛊”,破除种种巫术之说。他的研究,最后汇成《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一书。他发现,巫蛊术并不纯然是一种心理行为,即使是原始时代的巫师,在药物等方面的知识也相当惊人,如对毒蘑菇、仙人掌碱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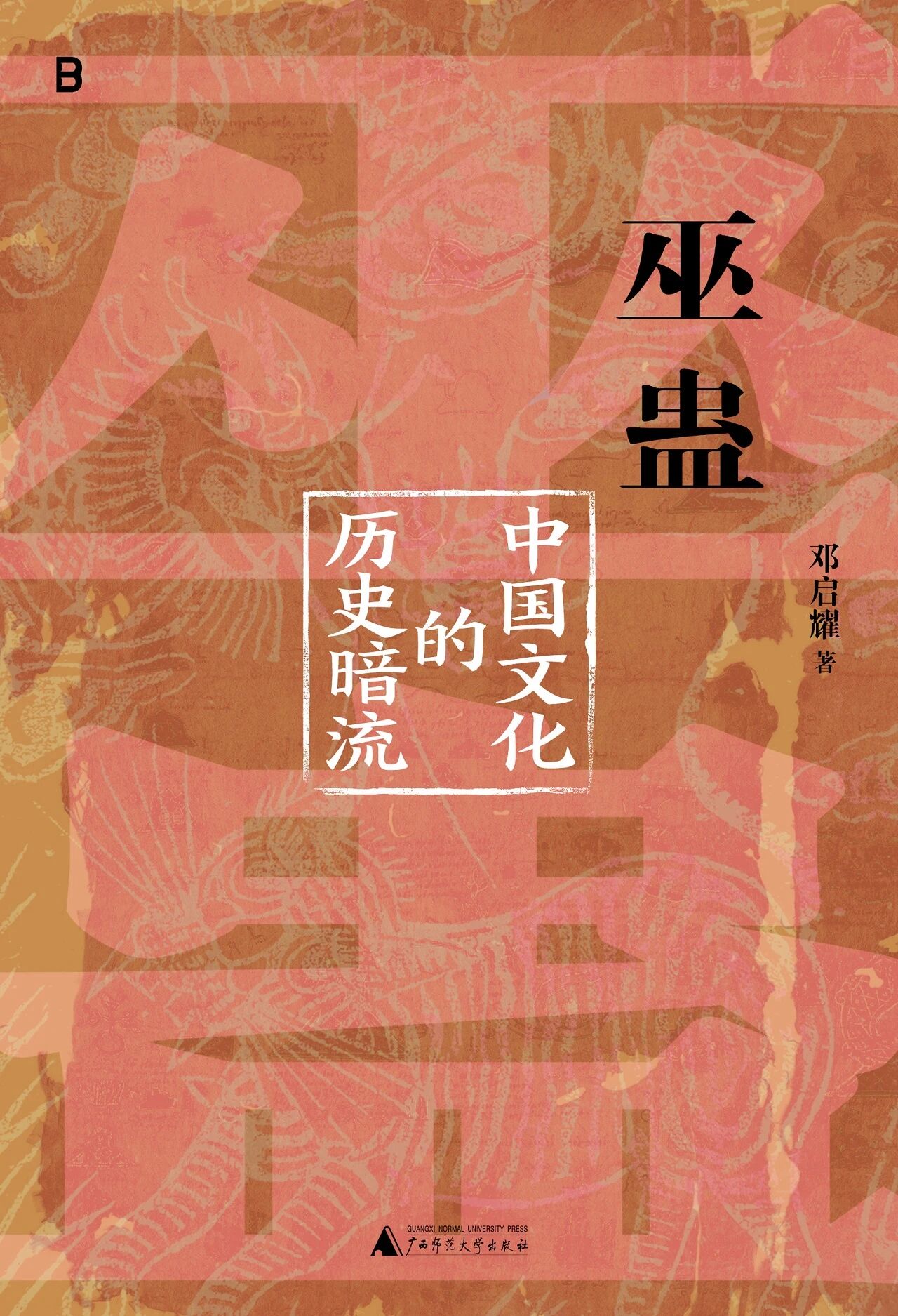
《巫蛊:中国文化的历史暗流》
邓启耀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2025-4
近年来,邓启耀开始追踪各种社交媒体上的巫蛊话题和生意。在他看来,网络上存在很多赛博巫蛊现象,如巫师算命、职场巫术、给他人下电子“诅咒”等。巫蛊成了一种在当下延续的玄学消费,各种打着“巫术”旗号的博主扎堆挤上流量赛道,还有大公司公然招聘玄学博主,这反映了当下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泛巫术”心态。
由此可见,巫蛊远非一块“文化化石”,而是一股持续至今的历史暗流。以下是《新周刊》和邓启耀的对话。
人类学家邓启耀。(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聊聊在巫蛊的田野调查中你觉得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
邓启耀:我不希望人们以猎奇的心态去读这本书。我是很严肃地研究一种貌似荒诞的文化现象。我不信邪,好处在于不会受任何东西暗示或蛊惑,没有什么会吓到我;坏处是“隔”了一层,因为我不在那种语境里。
在怒江大峡谷,当地人说有一条箐沟,如果人在阳光照进去之前进去,会撞上邪灵,导致精神失常;翻在这里的车也不计其数。有一天晚上,我陪做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夫人去录音,中途返回拿电池,独自路过了这个所谓阴森、恐怖的峡谷——虽然脊背一阵发凉,但我还是把手电筒关了,拿出照相机,准备在碰到鬼怪时抢个镜头。当然,最后什么都没见到。
真正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事情,是我发现巫蛊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影响竟然能达到那个程度。
2001年,云南盈江蛮胆老寨。寨子外面,总有一些隐秘之地,承载着民间的信仰。(图/邓启耀 摄)
《新周刊》:是,我看你书里的一些案例时,惊讶于巫蛊对于女性的迫害。
邓启耀:对,绝大多数被指控制蛊、蓄蛊、放蛊的人都是女性。我当知青的时候,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突然被说成是放蛊的。被当地傣族称为“琵琶鬼”(指放蛊婆或蛊女)的人,过去会被赶出寨子,甚至捆了跟房子一起烧掉。现在不能这样做了,大家就孤立她。
当时,知青们不信这个邪,想为她找回清白。据民间传说,真“琵琶鬼”不敢从晾晒女性衣物的绳子底下走过,因为会现出原形。知青们觉得这太简单了,只要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走过那条绳子,谣言就不攻自破。可悲的是,当大家去动员这位姑娘时,她竟然不敢这么做——她自己也相信了这个谣言。后来,她过得很惨,直到年纪大了才嫁给一名吸毒者,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在历史上,这样的事不是孤例。包括国外的猎巫,杀害的基本都是女性。它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病症,对社会的影响很大,确实让人惊心动魄。学者项飙评论我这本书时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说得很到位:要警惕这种群体性暴力及其对他者的异化,它甚至会变成一种合法行为。
2018年,云南盈江蛮胆老寨。江边的简易祭坛,流水将带走一切邪秽。(图/邓启耀 摄)
《新周刊》:写怒江大峡谷的经历时,你提到“神话和巫术是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精神需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需要?它为何会存在?
邓启耀:神话和巫术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神话是远古人类最初解释世界的语言遗产,巫术是他们试图控制事件的行为方式。它们存在了几千年,有的分化为文学、宗教、哲学,有的成为法术和伤人暗器,因为有现实性需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是互相敌视的,把他者妖魔化,就是为了利益,甚至有人只是因为嫉妒而去污蔑他人。
比如前面说的漂亮女孩,她只能选择一个人,其他得不到她的人就会给她泼脏水,目的是满足自己那种病态的心理——见不得别人好。这种事情从古至今都大量存在,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需要,是病态的。
“蛊界”,云南德宏纸马。(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也追踪了社交媒体上的巫蛊话题。在你看来,当下形成了哪些新巫蛊叙事?
邓启耀:我觉得赛博巫蛊的所谓“新”,只在于使用了新媒介。其实它的内核是很旧的,还在用传统巫蛊那一套,只是表述方式有所变化而已,用一些时尚的词和当代人关注的话题进行包装。这也说明,虽然国人几乎连走路都在埋头看手机,但是他们看到的信息不完全是现代信息。
过去,巫蛊用一种比较原始的办法来实施。比如《红楼梦》里马道婆“魇魅”贾宝玉和王熙凤,剪两个纸人,写上二人的年庚,再剪十个青面白发鬼,各自掖在两人床上。这种事情如今仍然存在。比如很多地方就有“打小人”习俗,这就是一种公开的巫术行为:我恨谁,或者我认为谁是小人,就在纸上写对方的名字,然后用鞋底击打。
现在的“网暴”虽然不一定可以和巫蛊相提并论,但肆意伤害他人的心态是相似的;因其匿名,有人以为自己隐身了,所以恶的本性更发泄得肆无忌惮。而这种藏在暗处伤人的方式,与巫蛊心态处于共同的段位。
《新周刊》:打小人在现代都市得以传承,你觉得原因何在?
邓启耀:这是一种变成民俗的巫蛊行为。虽然打小人被伪装成一种民俗活动,但实际上它的基石还是巫术。这种东西在社会中都见怪不怪了,比如银行门口常常放置着一对大石狮子,它们跟银行的业务有关系吗?放置的人心里很明白,一个原因是风水,另一个原因是它有吞削他人财气而蓄财于己的“意头”,这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巫蛊行为。但谁都不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有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源自非常糟糕的心态。这些东西,有些成为民俗,有些则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谁也不会去质疑,好像存在即合理。
《新周刊》:巫毒娃娃在2006 年前后一度畅销,后被禁售。你觉得其畅销的原因是什么?
邓启耀:巫毒娃娃也是典型的黑巫术——做一个线扎的小人,在上面扎满钉子,恨谁就写谁的名字。这竟然成为一个市场,据说还卖得很好。有些客户甚至是小学生,他们觉得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就想报复一下老师。这是一种糟糕的心态,出了问题不是反思自己或者探寻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而是陷入一种情绪的发泄,从而做出这种病态的事。它一度流行,说明是有潜在市场的,隐藏在人心中的恶魔,才是最可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