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本院校铆足了劲凑横向,为的是保本申硕,而一本院校凑钱的目标则是:向“双一流”看齐。
吴建军在北方一所理工类院校任讲师,他说:“从学校各类文件通知来看,我感觉在冲‘双一流’,从上到下卷得很。”
2021年8月,吴建军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靠投简历,入职了这所一本高校。学校实行预聘制,首聘期4年,通过聘期考核后,才能转为长聘。他和学院签订了任务书,首聘期内,他需要完成累计100万元的科研到账经费。他努力完成了指标。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处的老师告诉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来,得累计150万。
“我今年咬着牙,还得再弄50万。”吴建军说,文件解释权在学校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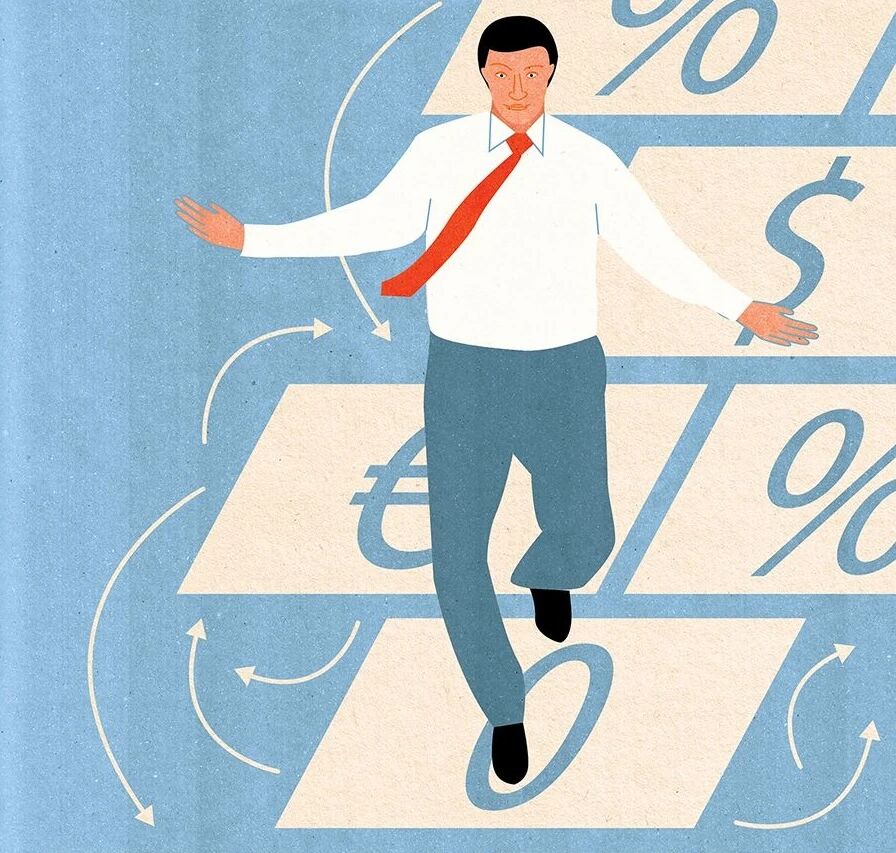
无论是因为领导要政绩,还是学校要名气,这两年,吴建军面临的业绩考核一直在加码。他举了个例子:假设学校有100个任务,10个二级学院,一个学院肯定不能只分10个,至少得分12个;学院分给老师,又会再加系数。
这突然增加的50万,吴建军虽然无奈但也有信心,这是因为,他也早早给自己加了系数,“为了完成100万的任务,我给自己定了300万的任务,这样我才有把握完成100的任务量”。
交流起来,吴建军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工作前三年,他特别恐慌,整日里状态都很紧绷。虽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业合作上有优势,但即便项目谈成,经费到账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干完了,手续还没走完,焦虑的时候,吴建军也曾去银行研究过能否贷款,“但没有走到那一步,我的业绩从去年开始慢慢上来了”。
为了拉横向,吴建军还去北京读了个博士后,“去想办法,拓展合作”。如果能拿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那就是“碾压式地”“毋庸置疑地”能通过考核,但数据显示,2024年度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为15.54%,对师门不够强大、人脉资源匮乏的普通教师来说,难度太大。学院内部也有派系,吴建军说,以市科技局的纵向项目为例,对院长派系的教师们来说,申报容易,他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他所上交的150万,都是实打实向企业争取来的横向经费,纵向他“根本拿不下来”。
在吴建军看来,阶级固化在高校也很明显。如果他是富二代,家里不缺钱,200万大笔一挥,他就能过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长江学者的门生,发论文、出成果,也会方便。
如果能顺利通过首聘期,接下来,吴建军下一步的规划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觉得,“所谓的学历脑力劳动在权力和资源面前是很微弱的”。努力搞“横向”的这两年,他对科研的认可度逐渐降低,“其实人生要有机会当领导干部,何必要搞技术”。
和吴建军一样,王森也对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岁,博士毕业后,在山东一所公办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她是文科讲师。今年年初,学院向她摊派了70万的横向到账经费任务——她的年收入不过10万元。
她拿不出这个钱来。学院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她把房子抵了,再自己注册个公司。“有些老师的确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间有什么闪失,房子没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养老钱去做这种有风险的事。”王森说。
现在来看,王森觉得,领导就是在PUA她。他对王森说,别看你是博士,现在博士也很卷的,30岁的博士,我们都嫌年龄大。
王森在2017年开始找教职,那是博士进高校最好的时候。那两年,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合并“三本”院校,许多地方学院升级成为大学。但短短几年后,高校教师就快速“超编”了,博士进高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王森觉得,现在的高校教师和公司里的员工是一样的,拉横向课题,就像在拉赞助、卖保险。
过完年,王森选择了辞职。除了无法完成的横向任务,王森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放弃做科研了。本该专心做科研的时候,她总是患得患失,陷入灾难化想象:这个立项书要是投不中怎么办?情绪和状态都非常差。
读博的时候,她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读完博士,她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适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她不擅长。但是,付出了那么多,她又没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欢的教学部分,也几乎成了高校里最不重要的事。在王森的感受里,疫情之后,教学就变味了,出现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
首先是写材料。入职七年,王森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修改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但实际上,日常教学很难按这个大纲去安排。去年,为了应对为期半个月的学科评估,王森来来回回地写材料,忙活了一年的时间。吴建军也有同感,“各种材料,无数次不定期地随时抽查,随时推倒重来。”这些材料包括基础的学生作业、期末表现,还包括教学分析报告。
然后是全流程监管。吴建军感到,所谓的信息化办公系统,就是用来不间断地对老师和学生进行监控。一个新概念是“无感听课”。教室里装上几个摄像头,360度全天候监控,领导不定期查看监控画面,教师必须时刻站在能拍到的范围里,前三排学生得坐满。另一个概念是“抬头率”,学生抬头听课的比率,只有保持抬头状态的学生,才算是在认真听课。
这些监管让吴建军身心疲惫,他的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它(学校)一检查,我就生病。”吴建军说,“马上感冒,嗓子不舒服,浑身不舒服。”
江苏的石云觉得,教学已经变成表演,“最重要的是拿数据,让各个环节都看起来很努力,有事情在做”。她所在的学院从不给教师批假或调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是去开学术会议,还是病得严重,只要人还活着,就得去上课。因为病假调休关乎到另一项数据,影响学院之间年底的排名。
传统印象里的高校教师,工作稳定,自由,有寒暑假。但这两年,“青椒叙事”早已不是这样了。石云说,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加班。她如今身兼数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早上睁开眼就要工作,晚上12点还在给同事发消息。对有科研志向的青年教师来说,寒假更是不可能休息。每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接受送审,从12月开始,教师就得为自己30页的立项书精雕细琢。
高校教师的性价比逐年降低。石云说,如果让她给博士毕业生建议,她会讲清楚所有弊端,但如果对方对科研有热情、有理想,她还是会鼓励他们进高校。
她自己就是这样。虽然不能成为所谓的学术大佬,但石云说,她对学术仍然有理想,如果离开高校去做公务员,或者去教培机构,谋生当然可以,但精神层面的滋养,就会弱很多。
再三思虑后,王森决定告别科研。她感觉自己从读博到工作,一直走在世俗层面“正确”的道路上,但她越来越感到,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她想要的,她没有找到科研的真正的意义。辞职前不久,她在三个星期里感染了两次甲流,也是因为生病,她突然意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手的。在辞职报告上盖完公章,她感到释怀,“它(辞职)就在我的计划里头的,博士毕业时我就想休息一年,无奈父母像催婚一样催我尽快工作,这一等就晚了七年”。
之后,王森打算去做独立老师,给学生提供学业规划咨询。教书育人仍是她的热情所在,她希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帮助他们找到擅长之处。这是在如今的大学里,她难以实现的。
应对方要求,文中唐文生 石云、刘一均、吴建军、王森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