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一条报道了建筑师赵扬
在大理建成的第一个作品——
有9个院子的“竹庵”。
2025年,他的新工作室和新家落成,
隐匿在洱海边一个寻常的白族村落里。
大理湾桥,赵扬的家
赵扬是80后,重庆人,
清华建筑系本硕毕业7年,
又在30岁的年纪前往哈佛攻读建筑学硕士。
2012年,他一回国,
直接跑到了大理,
当时中国还没有乡建的概念,
赵扬一头扎进乡村,一待13年。
从大理古城既下山酒店,
到香格里拉先锋书店,
“在地”,是他最不可磨灭的标签。
13年里,赵扬也曾经历信念的动摇,
“这是作为建筑师最困难的困难”,
当他真的长到了本土的社会里边去,
他发现,中国乡建浪潮下,
大多数的对于乡村的认知
还是过于肤浅,过于着急,
乡村成了一个背景,
来烘托所谓的“作品”。
徐沪生与赵扬 两人在院中对谈
6月,一条创始人徐沪生前往大理探访赵扬,
两人进行了一次深谈。
编辑:夏 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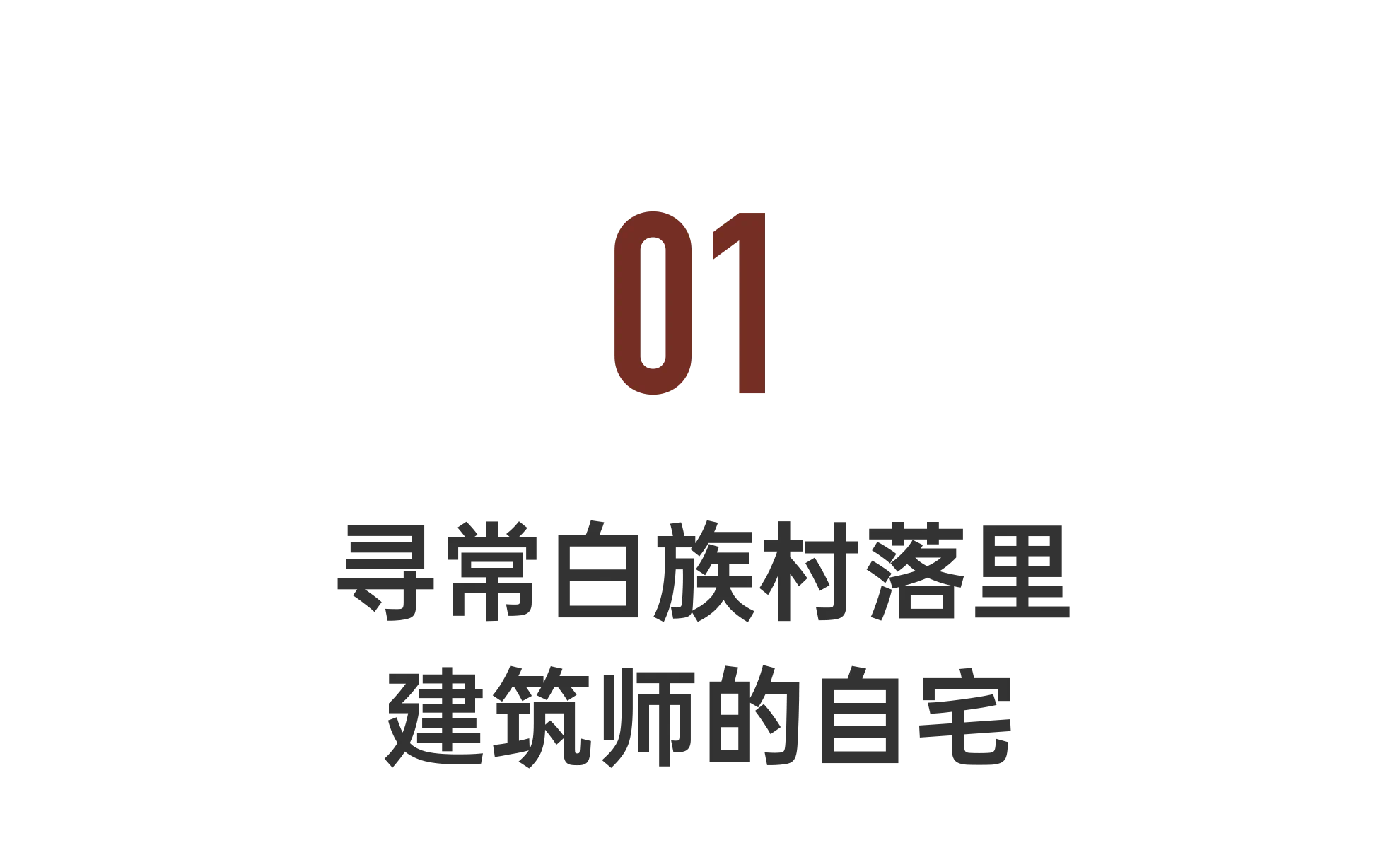
以下为赵扬的自述:
苍山脚下的村子,民居都是坐西朝东的,因为它要背靠苍山、面朝洱海。我这个院子在村子里,旁边邻居房子离得太近,正好南面比较疏朗,所以就转了一下,变成坐北朝南。这里原本是我给本地人小黑一家设计的宅子,因为各种原因,现在是我的工作室和居所。从2020年开始设计,到今年我们搬进来,5年过去了。
它是现代的,但是放在这么一座白族的村子里,一点也不突兀。
我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就围绕着院子发生。两进院子,从前院到后院。前院呢有点像一个过渡,转过来就到一个廊下,算是登堂入室了。
回廊,是这座宅子设计的核心思路之一
从中间的廊道开始往两边分流:西侧是工作区,东侧是生活区,核心还是院子。
院落这个事情,在传统的白族村子,包括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宅基地之间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只能内向。我们一旦外向,就要对外大量开窗,好像你在窥探人家的生活一样。
两只猫南迦与巴瓦,好几次在边上“临渊羡鱼”,好在从未得逞
工作区是安排在一个统一的木结构屋顶下面,有5个高差,它有一种画廊的感觉,大概七八个同事每天过来上班的。
正好白族的传统木结构,屋顶上有一条条的椽子,就在构造上做了一点研究,把它变成了带状的窗,拉通整个空间的天光。
竖窗、田野与苍山
最上面那层西北角榻榻米的位置,我开了一个高一点的窗户,正好可以透过邻居家的屋顶,看到北侧的田野,看到背后苍山的莲花峰。
其实村子本来很普通,一个竖向的窄窗,就能把一些很有趣的景色抓进来。
在自己的小工作室中画图
西边这个位置,在以前就是白族的正房,坐西朝东面对院子的,现在是我自己画图的地方。
再转过来坐北朝南的空间就是起居室。窗户朝南,但因为太阳高度角的原因,夏天其实南边的光线进入的很少,特别阴凉。冬天,起居室朝南的窗户阳光特别好,又有一个壁炉在,特别暖。
赵扬在起居室
徐沪生在餐厅,餐厅与起居室隔庭院相望
起居室隔着庭院和水池,对面就是餐厅,它们在东边由厨房串接起来。
这样,在大理的雨季,我们是可以不被淋雨,就能够走到这个房子任何一个地方。
我平时差不多9:30吃完早饭,看见同事们陆续就过来了——他们住在古城,或者湾桥旁边的村子。然后就开始处理一点工作,大家开个会,有时候做点设计。
在这,就算你待在工作室,也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因为我是对着院子,我发呆也好,甚至对着院子打个电话,它就是一种生活。
餐厅与家具
屋子里基本所有的家具,都是我从以前的老房子搬来的。我之前在古城旁边的一个小区里,我住西侧的一套公寓,工作室在东侧。在工作室的氛围就太“工作室”了,好像我不工作的话,在那就是不对的。
但是在这儿,我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也就像在家里一样。这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一个状态。
房子之外,便是白族村落的点滴
我很仔细地去处理这里每一个角落的空间关系,其实是希望这个空间,本身有点像一个建筑的教材一样。希望年轻的同事们在这里边耳濡目染,慢慢就能够理解。
走上三楼,在房子的制高点,看到整个苍山脚下就是白族的村子,你能感觉到这个房子跟村落融合在一起。
我们即使是用传统的方式,仍然可以做当代的空间。
以下为徐沪生与赵扬的对谈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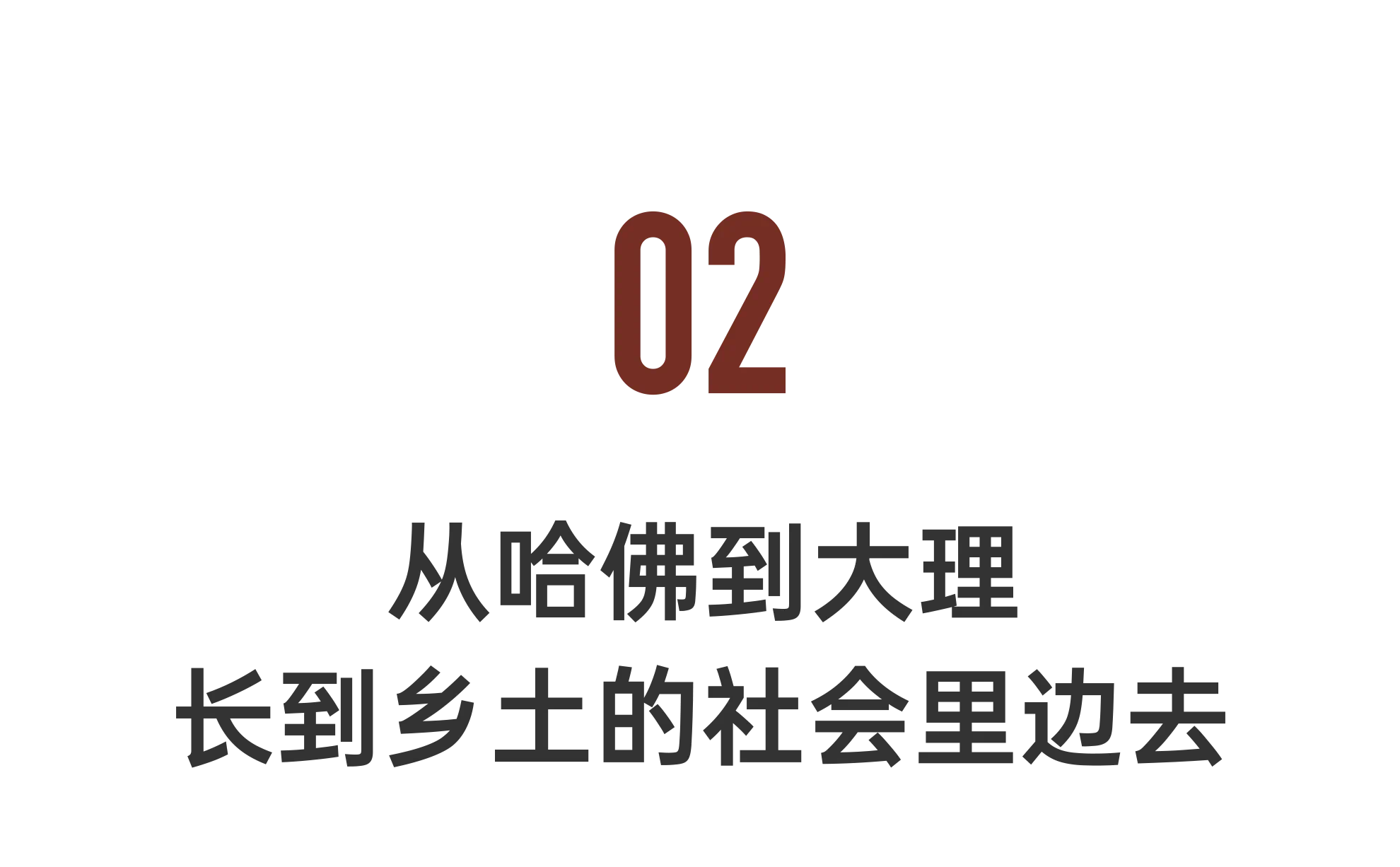
徐:其实大家还是蛮好奇的,当时你从哈佛直接到这里是什么契机?
赵:当时有个朋友,和我说要去大理盖个房子,我说,我跟你去看看。2011年的大理,气象还是挺向上的,来大理的这些新移民,他要创造生活,他不是说我就来躺平。
徐:都是有点像梁漱溟当年的那种心态的。
赵:不是说我过来我盖一个房子漂漂亮亮,我自己躲在里边。大家是觉得我要融入整个地方,这个场域里面有很大的营养,而我也感受到这种营养。
我从小号称是在古镇长大,重庆的一个叫磁器口的地方。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王路他是研究乡村,带着我全国乡村尤其是浙江到处跑,其实培养了这种感情。
徐:读哈佛跟这个有关系吗?
赵:我是在哈佛获得一种视野,你会看见什么东西,真的有长远价值。对于整个文明来讲,我觉得乡村是有意义的。中国的城市问题有点过于复杂,可能不是我作为一个个体能够一下子去解决。乡村那个时候还是没太多人去探索。
赵扬与导师妹岛和世
徐:初到大理,如何融入?
赵:我12年夏天来大理,我刚到大理其实很不顺的,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并不真的了解中国乡土。
转变发生在2012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劳力士的一个艺术导师计划,马上就被妹岛和世认可了。我记得13年我接受的采访,那叫一个密集,中文的英文的,其实是帮到了我在大理的起步。
14年的时候,既下山的创始人来找我做第一个古城既下山,我获得了第一阶段的几个能够落地的项目,慢慢就走上了正轨。
大理古城,既下山
梅里,既下山
徐:因为我是农村的,好不容易考了大学。所以人就很奇怪,我们从小在乡村的,对乡村反而没有太多的迷恋。
赵:其实我来大理,我不知道我在做乡建,后来过了几年才有乡建这个词。乡建其实是城里人关注更多,真正的乡村的人,他们一直在这样过日子。突然“我们”感兴趣了——对他们来说是这种感觉。
大多数的对于乡村的认知还是过于肤浅,过于着急,乡村成了一个他做的事情的一个背景,来烘托他的所谓作品。
香格里拉,先锋书店 摄影:王策
徐:城里的知识分子,他对异质文化,他既缺乏了解,又缺乏尊重,又缺乏耐心。他以为乡下是一个乌托邦,其实乡下盘根错节比城里还要厉害。
赵:城里人观念里面的乡建,你要说什么叫成功,我开民宿赚到钱了,我成功,但实际上这个事情跟本地的“乡”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我看到喜洲那么好的一个地方,现在像城北村,喜洲边上面对田野那一片,盖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网红建筑,很突兀,但它太赚钱了,这种成功带来的就是对于本地的一种破坏。
我觉得建筑跟人一样,你得有教养,你到一个地方,你如何Behave(表现得体),如果显得自己特别自以为是,不知道旁边在发生什么,那就太没文化了。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要和而不同,你首先要和,我觉得东西方皆为此理。
我待了这么多年,我就站在苍山脚下,一眼望去,还是灰瓦屋顶跟苍山匹配。你想让整个地区几十万白族村落的人,都跟你玩现代主义?这不可能,大家没有这种亲切感。
赵扬的家,隐藏在村落之中
徐:回过头来聊聊这座房子,你说这里其实并不是你给自己设计的。
赵:2019年以前,没有过大理本地人作为我们的甲方,没错,之前其实都是新大理人。
这个宅子的甲方是本地人,姓黑,这是下湾桥村这座村子的大姓,我们都叫他小黑,他爹就住在旁边,我们叫老黑,他有个哥哥叫大黑。
徐:我特别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审美背景、知识背景?
赵:小黑在这长大,大学考到了内蒙古,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云南。这块地就是他的父亲分给他的。小黑找我盖房子时,他已经研究了我的网站,他对我每个作品都如数家珍。
苍山与洱海之间,遍布着白族村落
当他想要回到这块地盖房子,他的想法就已经和老一辈不一样了——大理这些白族村子,远看是漂亮的,很统一,但你真正走进去,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可能房间做得很大,流线不合理,设计的比例也不协调。
因为从真正传统的乡土民居,到现在村子的宅基地新房,这个发展进程没有任何过渡,就像是在断裂之后,哗地一下突然出现。没有思考,没有文化的准备,当然也没有设计师的准备。
小黑委托我做了这个设计,我才真正开始触摸大理。所以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现在还能在大理?可能就是从那个点开始,我真正跟这个社区、跟大理发生了关系。
如果我们稍微乐观一点,往后其实就是乡村本地人、大理人要发力了。
博物馆,就坐落在古城中心的五华楼之侧
徐:所以你是很享受这种在地性?
赵:我蛮享受的,有一种你可以跟它贴身肉搏的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在大理古城做一个博物馆,有了这个房子的经验,我知道如何把一个当代的空间,和一个传统的结合起来。我们去汇报,白族建筑专家完了就会握着我的手说:“你其实为古城的建设找到了一条很好的道路。”
我觉得这就够了,没有人比他给的这个认可更重要。


赵扬在云南
徐:2012年到现在13年,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赵:之前那个时代,我们建筑师群体,还是有很多人是对建筑有宗教情结。这个过程本身就要吃很多苦头,其实也有心理准备。具体的困难就太多了,项目都要黄了,看不见一个比较稳定的商业途径,但是这些东西就一点点摸出来的。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反倒是出现在疫情前后,我发现好像时代的方向和我的预期不太一样。最困难的困难,我觉得对建筑师来说,你的信念动摇了。
在赵扬看来,做建筑是一个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
徐:蛮群体性的。
赵:对,信念动摇挺特别艰难,对我来说具体的困难都不难。
徐:你觉得这个信念现在是修复了,还是说?
赵: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它一直是一个向上的曲线,你不觉得社会它可能有时候会以退为进,走两步退一步。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稍微有一点历史的视野来看整个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面对的这种处境非常正常。
我倒挺感激这段彷徨的时间,这个过程也把自己身上的一些思想上的泡沫给滤掉。
我经常跟别人说,我在大理待这些年,读了一个“学位”,这个学位绝对不是之前清华也好、哈佛也好,可以教给我的。

喜洲古镇,竹庵
大理,葭蓬村驿站
徐:最核心的收获是什么?
赵:是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就能清醒地看一个一个的情境,这些情境背后它的各种因果关系。
你得真的有耐心,慢慢你会去体谅当地人,甚至体谅当地的政府。你能理解背后的原因,你就会有同情,有了这份同情,你才有可能在现实基础上稍微做一点事情。
有几年好像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些更大的房子,更大的事情,外面有一些机会,你觉得你作为建筑师好像得当仁不让地去干这些事情。
但是后来疫情来了,好像世界变了,反倒是在这,我可以有进退,我在云南我永远有事情做。
徐:因为我是哲学系的,包括你像中文系、历史系,你中文系火的时候,你招了大批的人,其实有些是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中文系就业不好了,他就不来报了。像建筑系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差一点。很多人没有认真地沉浸在建筑的艺术里面。
赵:那天碰见(刘)家琨老师,他是说“你不能说因为现在生意稍微不好做一点,你就否定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的变化,在未来,技术性的层面越来越会被取代。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存在,还有哪一部分是有价值的?我们传统的教育已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传统的建筑的教育,它都是在应对上个时代的市场,就是巨大的建设量来准备的,它的价值一下子就崩塌掉了。
建筑学的“痛苦期”,却也是重建的开始
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要重建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痛苦期。还是会有些人要学建筑,慢慢地也会有一些更靠谱的学校找到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教育的方法。
好像我们这一代建筑师,都是对人文比较感兴趣,我实在是觉得如果你不坚守这个阵地的话,建筑学也没有什么阵地了。
其实现代主义所有的技术、设计手段,这些都已经研究到位了,这个时候反过来其实应该把这个事情松下来,去关照真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尺度、什么样的村子、什么样的城市,现在反过来应该是解构建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