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婆就像这焦黑的锅灰猪肝,外表淳厚朴实,内里却柔软细腻,在我缺爱的幼年,她用一颗细腻的心温暖着我,在炭火与猪肝的碰撞中,我们将爱传递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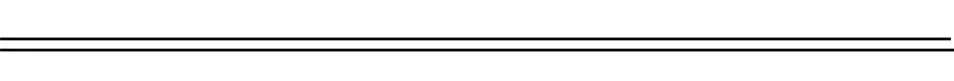
我的老家在眉山市的一个偏僻小乡村里,2021年国庆节,我带着家人美好的祝福和祝愿,幸福地嫁到了200公里外的遂宁市船山区。
我出嫁的那一天,站在人群中的家婆哭得最厉害。我踩上被子,即将离家时,她伸出两只满是老人斑的手,深陷眼窝的双眼微红,紧紧抓着我不肯松开。旁边的母亲一边抚摸家婆的背脊,一边安慰道:“现在交通发达得很,你外孙女又是个有孝心的,肯定会常常回来看你的!你放心!”
我也反手握住家婆冰冷的双手,劝慰她:“我会幸福的,家婆您放心!有空我就会常回来看您的!”
可现实却与誓言截然相反。婚后,工作的忙碌加上与婆家相处有些摩擦,生活处处不得意,每天都忙着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身体也出了些问题,让我的“常回家看看”就搁置在角落。
那段日子,我无心吃饭,却时不时想起家婆做的“锅灰猪肝”。婆婆虽然有时挑刺我的性格,但是也看不得我日渐消瘦。她在网上搜找到“锅灰猪肝”的制作方法,一步一步地制作,甚至还烧了辣椒,加入眉山的泡椒,弄了点烧辣椒蘸水——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因为常年生活在潮湿地方,所以格外喜好重麻重辣,祛湿暖身。
可吃着婆婆做的这道菜,我却适应不了,总觉得少了一些味道。
跟在家婆身边时,锅灰猪肝我吃的不少,但是从来没有亲手做过。当时,我总觉得“烤肝”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就是把抹好百草霜的猪肝,放在炭火里埋着,炭烤一小时就行了吗?”因而我压根儿就没考虑过学习这道菜。没想到,不学会这道菜,长大了嫁人离家,就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上“家的味道”。
过了2年,等我和老公的工作基本稳定下来,与公婆也能融洽相处了,我才终于得空回娘家。提前一晚,我就把给家里人准备的东西收拾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催促着老公急忙开车上路。乘坐了近3个小时的汽车,终于赶在中午前到达。即使身体很疲惫,但闻着不远处空气中飘来家里饭菜的阵阵香味,我内心格外兴奋,久久不能平静。
我大包小包从车上下来时,家婆早已佝偻着背,在门口张望着。她两鬓都斑白了,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古铜色的脸上已刻下岁月留下的皱纹,望见我们的车近了,她两步并做一步,佝偻着身子,颤颤巍巍地朝我们走来。
虽然已经身形佝偻,可是一看到我们回来,菊瓣似的笑容从家婆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离我出嫁才过2年,我悲凉地发现她变得更老了,不由得眼眶湿润,上前一步抱住家婆瘦小的身躯,哽咽地说:“家婆,让您等久了,我回来啦!”
我出生在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年,在我上小学之前,一直是由家婆带着的。那时候,在我的心里,家婆是比妈妈还要重要的存在。
当年妈妈刚生产完,重男轻女的奶奶嫌弃我是个女孩,在月子里对妈妈诸多为难,导致妈妈月子没坐好,身体落下了病根,连带着我也长了鱼口和湿疹。眼瞅着我因为生病渐渐消瘦,妈妈央求奶奶从中公里拿出一些钱给我治病,奶奶以买了粮种和肥料没钱而拒绝。无奈,妈妈只得厚着脸皮回娘家借钱,家婆二话没说拿着钱,抱着我去治病,最终我的小命才被保下来了。
恰逢这时,奶奶大儿子因得病刚去世不久,或许是害怕自己年老得不到供养,遂在爸爸耳边吹风,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强烈要求爸爸跟妈妈再要一个男孩子,愚孝的爸爸耐不住奶奶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就同意了。妈妈虽然气愤爸爸的懦弱不作为,但是在“丈夫就是一层天”的传统思想浸淫下,她还是妥协了。
当时正值计划生育时期,抓超生特别严格,为了躲避搜查,爸爸向家婆提出将年仅8个月的我交给她照顾,他们就去工地躲起来,直到生产完再回来。因为心疼女儿,家婆没与家公商量,单方面同意了,把我抱回了家。可刚踏进家门,家婆就遭到了家公一家的反对——舅舅(注:家婆的亲儿子,妈妈的亲弟弟)当时还没结婚,正在跟舅妈耍朋友;我才8个月,嗷嗷待哺,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闲钱买奶粉喂。家公很生气,怒斥家婆不考虑家里的实际经济情况,只顾自己当老好人。
面对众多的非议,家婆以强硬的态度,坚决要照顾年幼的我。她说:“不管其他的,燕燕是我女儿生的,是我的亲外孙,我要养!”就这样,我在懵懵懂懂中,来到了家婆家。
长大后,舅舅一家对我小时候的事如数家珍。我刚来家婆家才8个月,面临没有母乳喂养,喝牛奶拉肚子的窘境,家婆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去给我买维维豆奶粉,加上一些熬得软烂的米粥兑着喝。每当我饿的时候,我总会趴在家婆耳边,说道:“家家,xu~家家,xu~”家婆就会知道我饿了,起床给我兑奶粉。吃饱后,我就会摸摸自己圆圆的小肚子,打个奶嗝,再趴在盖满毛衣的枕头上,沉沉地睡去。
农忙时节,家婆还会用布条背带把小小的我带去山坡上,把我放进箢篼里,给我盖好小被子,就下地干活了。家婆总念叨那时候的我很乖,很听话,说了不乱动乱爬,我就会乖乖在箢篼里睡上一个下午,让忙碌的她很省心。
从我记事起,家婆就炒得一手好菜,其中最令大家赞不绝口的就是她做的“锅灰猪肝”。
每逢农历单数的日子,镇上会赶大集,小小的我总爱赖在家婆身上,和她一起早早在门口等三轮车,和村里的表叔表婶们赶大集买猪肝。猪肝价格低廉,也容易烹饪,小小一块猪肝在贫苦人家的家里,是解馋的好东西。
可要想猪肝吃着不腥,选猪肝也是有秘籍的。
家婆常念叨“眼见不一定为实。人一样,食物也是如此。”最好的猪肝是粉肝和面肝,这种猪肝质均软且嫩,手指稍用力,可插入切开处,熟后味鲜、柔嫩。不同的地方是前者色如鸡肝,后者色赭红。最不好的猪肝是病死猪肝,这种猪肝色紫红,切开后有余血外溢,少数生有水泡,即使挖除无痕迹,但熟后无鲜味。
买回猪肝,家婆会先打一桶井水,倒入盐和面粉,仔细地将其里里外外进行清洗,把血水洗净,接着会把洗干净的猪肝放在大铁锅锅底,均匀地抹上一层百草霜(锅灰)。在抹灰这里,家婆的烹饪步骤也比其他人家多了一些细节。在抹百草霜的时候,她会把柠檬树的叶子紧贴猪肝,慢慢地给猪肝上色,“囡囡,你要记到,这样啊,猪肝吃起来有种柠檬叶的香气。”到了炭烤环节,家婆会烧一些炭火,把抹好百草霜的猪肝埋进老灶里面,盖一层薄薄的草木灰,再用果树的碳在老灶里面煨上一个小时左右,慢慢煨熟。
家婆家的老灶起的时间久远,土泥巴已经在慢慢开裂了,露出了里面的一些稻草,台面上一些黑乎乎的印记彰显它曾经的辉煌,可即使是这样,我依旧觉得只有它烤出来的猪肝和红薯最好吃,最香甜。
直到鼻子边传来一阵阵带着焦香的肉味,我就知道“熟了”!家婆从容地从老灶里把它拿出来,拿着菜刀一点点刮去猪肝身上的焦灰,紧接着切成一片片的薄片,放入盘中,再烧一些二荆条,佐以眉山泡椒,弄一碗烧辣椒蘸水,搭配猪肝,那味道,不摆了!
每到这时,家公总会拿着他的酒来到桌前,一边嘬一口酒,一边夹一片猪肝进入嘴里,边嚼边享受地说:“哎哟哟,这东西一顿不吃就想得慌!心慌慌!”说完还会朝家婆不停地眨眼睛,眉飞色舞,“老婆子你辛苦啦!”足可见其美味程度。我也笑眯眯夹起一块儿,放进嘴里慢慢感受这一刻的美味。跟着家婆生活的日子里,我渐渐爱上了这种焦香中带着些许苦味的猪肝。
在我们村儿,跟家婆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表婶们都会做锅灰猪肝,但是大家相互品尝,都一致认为家婆做得猪肝更香些,味道更浓厚。
每每有人上门询问做菜秘诀,家婆总是笑呵呵地倾囊相授,从不遮遮掩掩,她常说:“人与人都是相互的,有香东西大家一起吃嘛!再说也不是啥好贵重的东西!”家婆总是这么乐观,做菜如做人,家婆做菜的味道好,“秘方”或许就是她乐观的心态吧!

家婆的锅灰猪肝,是从她母亲那里学的。
家婆嫁到家公家时,才十六岁。那时候,她的父亲因为疾病撒手人寰,连带着也欠下许多外债,眼瞅着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需要吃饭,家婆本打算出去打工还债。恰好,家公家托媒人上门提亲,彩礼也给得足足的,家婆的母亲觉得条件好,家婆本人也没意见,就按照习俗合了双方的生辰八字,再起香倒一盆水,放入两粒黄豆,供在堂屋里,一夜过后,象征家婆和家公的两粒黄豆对上了,自此,他们就成为了一家人。
在出嫁前,家婆母亲担心女儿嫁人想家,就教了她这道“锅灰猪肝”,说想娘的时候就可以煮这道菜来吃,那时嫁人嫁得远,交通又不方便,成为别人家的媳妇儿后,一辈子都可能和娘家人再见不了几面,家婆自然是学得认真,想把娘家的味道印刻在舌尖上。
对于家婆来说,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菜,更多的是母亲对自己的爱。
只是,我上幼儿园那年开始,家婆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几次锅灰猪肝了。
因为家里位置不够,家婆家的老灶起在院子里。也许是老灶活得太久了,土泥巴砌成的砖块早已疲惫不堪,露出了稻草般脆弱柔软的心,如果被雨长时间淋,就容易垮塌。我懂事之后,接过了保护老灶的重任。转眼间到了夏天的尾巴,按照惯例,家婆家公要去山坡上扯花生,收拾干净的花生将会被菜贩收购,换得一笔不错的钱财,而这也是家婆家一年中重要的收入来源。我贪玩,看电视入了迷,忘记了窗外正在淋雨的老灶,等我反应过来,家婆家公已经回家,老灶的灶梁连带着灶门也已经被下了一天的雨淋出了一个大洞。
“诶,这样正好不用补了,直接就垒个水泥新灶吧!禁用些!”家公放下篮子里的花生,用帕子掸去身上的雨水,不在意地说道,“正愁它占位置,晒谷子找不到地方晒嘞!燕燕啊,你做得好!”家婆没有搭话,只是沉默地拉出雨布盖住破碎的老灶。从此以后,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婆才会掀开老灶的保护,再做一次锅灰猪肝。
家婆对老灶的感情,比我想得还要深。家公家慢慢富裕起来后,家公一度嫌弃老灶占位置,不方便在院子里晾晒谷子,说把老灶拆了,重新起个灶。可家婆却拒绝了,她说:“这灶啊,跟人一样,活久了,相处久了,就有感情了,我舍不得这位老伙计啊!”
据家婆说,这老灶养活了一家三代。“在闹饥荒的年代,你太祖祖(注:四川方言里“祖祖”不分男女,外祖母、外祖父统一称呼为“祖祖”,高一辈就加个“太”,有些地区是“高”)靠这个老灶烧炭,养活了一家人。后来熬过了那个时间,你祖祖又靠这口老灶整豆花豆腐,又养活了一家人。现在,我接过这根接力棒,继续用这口老灶,生火做饭,养活你们。”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每到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时候,家婆早早地起床,将灶台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然后在老灶门口点上香烛,摆上水果和酒等祭品,还不忘在锅中放上一盏清油灯,我问家婆为啥要点灯,家婆说这是为灶王爷上天照路,请他保佑我们来年能吃饱饭,一家平安。
家婆家住在一个斜坡下面,旁边就是一条大马路。我还跟着家婆住的时候,家婆最喜欢每天端着垒得满满的饭碗,悠闲地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吃饭。每当村里的人下工回家,经过大门口时,家婆总是会摇着筷子,热情地招呼那些舅舅表婶们来家里吃饭。虽然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可能吃的是过油泡菜和稀饭,家婆却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依旧很热情。
当时,村里家家户户经济情况都差不多,吃不到多好,也吃不到多差,即使面对家婆热情的邀请,也很少有人会真的进门吃饭,大多数都是客套地应和,然后再摆摆手回自己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丧父丧母的大舅舅(注:家公的堂哥的儿子)一家。
大舅舅一家三口人,有项神奇的技能,总能精准踩到家婆家的饭点,准时出现在家门口。每次家婆看到他们,总是会拉着他们一家人的手,让他们到屋里吃饭。刚开始他们会直接进来,可后面就在门口徘徊。
一个晚上,家婆像往常一样,准备好晚饭,等待干活的家公下工。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发现躲在门口枇杷树叶子后面的大舅舅一家,热情的家婆小碎步上前,一把拉住大舅妈的手,直往家里带。
可大舅妈的身体却往后面拱,脚也往后面用力退,连带着枇杷树的叶子也被她拉扯下数片。这样子一看,大舅妈肯定是被大舅舅骂了一顿,让她少往家婆家蹭饭,毕竟家婆家也不富裕,吃饭的嘴也多。
丝毫不会掩饰坏情绪的我,没好气地朝他们做鬼脸,气呼呼地说:“又来了,我的口粮又不够了!烦死了!”随即往堂屋跑去,准备护住自己的猪肝蒸蛋。
大舅妈的儿子不知道是不是智商有问题,每次看到我,总是会立即追过来,张着一嘴漏风的门牙,冲着我乐呵呵地傻笑,不停喊着“妹妹,妹妹......”这样一来,大舅妈也被迫进了家婆屋。
家婆常说:“进了屋的都是客人。”来都来了,自然是要吃口饭再走。家婆端来一大盘猪肝和一碗烧椒蘸水,还把我的猪肝蒸蛋也舀了2勺给大舅妈的儿子,还嘱咐他们:“多吃点,多吃点,吃饱点。”
当时,我在一旁气得直跳脚,吊着嘴巴埋怨家婆偏心,“好的东西不留给舅舅家公,只晓得送给外人吃!”家婆不恼,反而笑眯眯地给我解释:“一个人吃也是吃,几个人吃也是吃,人啊,没有必要那么斤斤计较,想开些!”
我还差一年上小学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就喜欢跟着村里表婶家的哥哥们去探秘。
家婆的村子上,住着一个“怪人”。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她从哪里去,只知道她住在村子入口的一个废弃破旧的变电房里,昏暗潮湿的屋子里,蛇皮口袋零散地落在地上,塑料瓶堆满了一个角落,几块砖头架起一口黑乎乎的小锅,这里就是她的“家”。
我们最爱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跑到“怪人”的屋子里,把她的塑料瓶拿出来,藏在村里的各个角落,美其名曰“藏宝游戏”。而“怪人”总会拿着杆子,在杂草里一通乱找,找自己的塑料瓶子,看她着急的样子,我们觉得好玩,总是会笑得前仰后翻。
一次放学,我又跟着哥哥们去探秘了,却不想被刚干完农活的家婆发现了。她怒气冲冲向我走来,有力地拉着我的胳膊,径直往家的方向走。路上,她面带怒色,一言不发,我心里怕得直打鼓。
好不容易到家了,她一把将我甩在地上,拿起旁边的笤帚,往我身上打,我一边哭喊着“我再也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一边抱着头躲笤帚。家婆打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把拉过板凳,喝了几口茶水,训斥我说:“你个兔崽子!你在干啥子事!你这是造孽啊!欺负别个苦命的老婆婆干啥!你脑袋有包吗?分不清好坏吗?哎哟,我愧对你妈,我没有把你教好......”
说着说着,家婆掩面哭了起来,我见不得家婆哭,急忙冲上前抱住家婆,“家家,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我会做个乖娃娃!你别哭了嘛!我真的错了......”
也许是家婆的眼泪觉醒了我内心的良知,年幼的我第一次没有当嗷卵犟(四川方言:固执倔强的人),直面了自己的错误,以至于在此后的岁月里,凡是我看到路边乞讨的老人,我总是会买一份饭,再给一些钱帮助他们。
后来,我发现家婆总是时不时地给这位老婆婆送煮好的米饭以及榨好的菜籽油,有时家里开荤,她还会特意舀一碗冒尖的肉给她送去。
我不理解,一个陌生的“怪人”有必要对她这么好吗?家婆却说:“人生来就是赤条条来,死了也是赤条条走,哪里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存一份善心,做一份善事,算是积德了。”
据村里的人说,老婆婆是被婆家赶出来的,她男人常年家暴,再加上她没生出娃,家里的人也不愿意再养一个废物费口粮,就把她赶了出来。至于为什么没有回娘家,村里的一个表婶说:“娘家嫌丢人呗!再说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没法给家里带来好处,为什么要免费养着你呢?”也许是无奈吧,老婆婆无处安家,四处游走,靠捡破烂谋生。这几年才流落到我们村子里,在村口的废弃破旧变压房安了家。
一次,我跟着家婆去镇上赶集,在村口偶遇了那位苦命的老婆婆,她看到家婆,非常开心,急忙招手让她过去摆会儿龙门阵(四川方言:聊天的意思),“这就是你的外孙女吧!这模样真俊呐!”她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准备摸我的头。
我不想被她摸,头一歪,错过了她的手,“你的手脏兮兮的,别摸我!”家婆愣了一下,随即笑嘻嘻地打趣:“小娃娃嘛,臭规矩多!别在意!”说着她就伸出手,紧紧地握住老婆婆还没有收回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回到家,家婆很认真地跟我说,“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不然要伤到别人的。”紧接着,她对我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有刚才的动作,还说老婆婆是个苦命人,我不能因为她的外貌和脏兮兮的穿着就觉得她是个坏人,也不要嫌弃每一个拼命活着的人。
可惜,家婆和老婆婆的这段姐妹情谊没有维持多久,就散了。
没过多久,有村民反应,破旧的变压房存在安全隐患,废弃的电力设备有极大的漏电危险,而且年久失修的变压房也属于危房,小孩子进去玩,容易垮塌,不安全。多番考量下,村支书便带领一群村民,找到专业的电工,拆除了变压房的一些老旧设施,连带着变压房这个危房也拆除了,老婆婆又被再一次驱赶了。
临走前,老婆婆提着一口袋红苕来找家婆告别,“老姐姐,变压房拆了,我也没有家了,我要走了。这一次我跟你见面之后,不晓得下一次见面是好久了。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妹妹我没得啥子东西可以给你,这是我卖塑料瓶买的种子种的红苕,没有好多,送给你,就当答谢你的照顾了。”
家婆紧紧握住老婆婆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老妹妹,别说这些!我们都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这把身子骨能撑多久嘞,也不知道你这次走了,我们姐妹俩下一次见面是好久了,人生苦短,你一定,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涕泗的泪水糊了一脸。
现在我都已经结婚了,家婆还常常提起她,她总念叨“如果变压房不拆除,我那个妹子应该会继续留在这里,说不定她也会在这里找到一个好归宿,而不是.....”
说着,家婆望向远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我回到了爸爸家。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家婆分开了。
随着家婆上了年纪,患有高血压和心衰的她身体远不如年轻时孔武有力,虽然还是能做些撒玉米粒,栽种小葱这些简单的活,但是长时间做饭拎勺就变得有些有心无力了。渐渐地,掌勺连同掌家的权力就落到了舅妈(注:家婆亲儿子的媳妇)的身上。
但每次周末我去家婆家玩耍,她总是能够亲自下厨,给我端来一盘香喷喷的猪肝,我告诉她身体都不舒服,这种费力大喘气的事情就别做了。可家婆却一脸认真地说:“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机会做了。”
我一时语塞,张大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家婆心疼我,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她亲手带大的,更是因为我是她最爱的女儿生的,她爱屋及乌罢了。妈妈并不是家婆第一个孩子。当初,她嫁到家公家三年都无所出,第四年托尽了关系,找到了一个老中医调理,这才怀上第一个孩子,可好景不长,怀孕期间因为过度劳作,让孩子在肚子里就已经死亡,临到生产就生下一团模糊的血肉,而这也是困扰家婆很多午夜的噩梦。
当时,村里陆陆续续传出一些闲话“孙芳肯定是上辈子做了恶,这辈子才报应没孩子”“老高家要绝后咯”“下不出蛋的母鸡要来干啥,炖来吃了撒”“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看她孙芳咋个跟老高家先人交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渐渐地,祖祖跟家婆婆媳之间就被这些闲言碎语离心了。
祖祖私下找到家公,要求家公跟家婆离了,再重新找一个好生养的,延绵高家的子嗣,让老高家有后。但是家公愤然拒绝了,他说:“当初娶是你们喊得,现在离也是你们吼得扎劲,啷个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想法,芳芳是个好婆娘,好媳妇,她没做过啥子对不起我们家的事情,即使是说她生不出娃娃,我也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她这个人!”
祖祖不愿放弃,多次劝诫家公,但家公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为所动,甚至对祖祖玩起了“冷暴力”。如此反复,祖祖见实在劝不动家公,就歇了这份心思,但对家婆也没之前好了。
这场小风波过后,家婆对待生育就看得愈发轻了,用她自己话说:“有没有都是一种缘,有又啷个,没有又啷个,顺其自然吧!”但这件事,对于家婆而言,却远远没有结束。
子嗣始终是祖祖心头的一根刺,一个执念,为了给老高家留后,她花费重金从庙里请了一尊菩萨回家,日日祈祷,到处寻医问药,每天一大碗一大碗的中药往家婆房里送。对此,家婆也不拒绝,顺从她的每一个安排。
不知道是药起作用,还是家婆心态的原因,没多久,家婆就怀上了我妈妈。这次,她成了全家的宝贝,骂也骂不得,吼也吼不得,连下田干活都不让她去做。甚至祖祖跟她之前的嫌隙也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烟消云散了,婆媳关系又和好如初了。
九个月后,我的妈妈顺利出生,看着眼前“嗷嗷”大哭的女儿,家婆既没有听懂她“吱呀吱呀”的意思,也没有看懂她粉拳乱舞的意思,只是满眼泪水地看着她傻笑。
从那以后,村里关于家婆的闲言碎语消失了,赞美她善良朴实大方顾家的话慢慢传播开来。
时光如梭,现在的我已嫁人成家,和家婆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这次回娘家,在路上我都拟好了一大串想吃的食物清单,当然第一道永远都会是家婆做的锅灰猪肝。本以为家婆年事已高,我回娘家她不会做,可当我进入堂屋,看见桌上那份静静放在那里的猪肝,眼泪顿时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
看到我哭,家婆佯装生气,“怎么,看见家婆我还活着不高兴吗?还有回娘家哭啥,不能哭,要笑!”
望着家婆那双早已深陷,略微浑浊的双眼,我用力地扯了一个笑容,家婆这才高兴起来,“诶!对!喜来屋,喜来屋!”
说着,家婆伸出枯柴似的双手,拉着我往桌边走,她满含爱意,颤颤巍巍拿起桌上的筷子,递给我,“囡囡,快尝尝,家婆我的手艺下降没得?”
我夹起一块,放入嘴中,缓缓地嚼,苦涩的焦味顿时布满整个口腔,猪肝也没有以前的绵密浓厚,家婆始终还是老了,我在心里默默感叹。可我还是转过头,笑着对家婆说,“好吃!和以前一样呢!”
听了我的话,家婆咧着嘴巴,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我的老公进来了,家婆从桌上拿起另一双筷子,递到他手中,“孙女婿,尝尝吧!看看我做的猪肝咋样?”也许是锅灰猪肝黑乎乎的颜色,老公面露难色,用身体轻轻推了推我,“家婆,我现在还不饿,还没开饭,等会儿一起吃。”
此前,我一直很尊重老公的饮食习惯,我不会强求他吃不喜欢的食物,可家婆做的猪肝怎么会是难吃的呢?这是我梦里都在想念的味道呀!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家的味道”!
“尝一尝吧!很好吃的!”我凑近他的耳边,小声地说,“家婆是好心希望你尝一尝,不要伤家婆的心。”
不知道老公是否明白了我的暗示,他夹起一片猪肝放进嘴里,边嚼边夸赞美味,家婆听了这句话,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眼角像淌着蜜。
妈妈走了进来,调侃道:“这么好吃,叫你家婆手把手教你撒!免得你去遂宁又天天在电话里面闹起想吃锅灰猪肝!”
“那为什么高女士你不教我呀!是不是你不会呀!”我偏过头,冲着妈妈狡黠一笑。
“哎哟,你这个小妮子!真拿你没得办法!”家婆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宠溺地说,“你妈结婚前都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能指望她教你吗?要我说呀,还得是我这个老婆子来教哦!”
家婆一边调侃着我,一边拉着我往厨房走去。
“囡囡,你看好哈!猪肝我们要先加盐和面粉,把它抓匀。”家婆用颤抖的双手,一点一点地将面粉抓到猪肝上,“等过一会儿,你看到猪肝外面的面粉颜色慢慢变浓,就可以冲洗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太浓的腥味了。”家婆拖着缓慢的脚步,把猪肝拿到井边的桶里清洗,这一小段路,以前她健步如飞,不停地在厨房和水井边跑,现在她步履蹒跚,每一步都走得沉重。不自觉,我的眼眶又湿润了。
猪肝洗净后,家婆又喊妈妈从屋檐后面的柠檬树上扯了几片叶子,走到后来新砌的水泥灶旁边,缓缓蹲下,用柠檬树叶一点一点把大铁锅上的灰抹上去,“现在我们把灰抹好了,就要放到灶里埋进去了。”家婆扶着腰,慢慢用火钳将猪肝放进去,接着盖上一层薄薄的草木灰,就用炭火盖住了猪肝,“接下来,就要用鼻子来等。”
小时候,我看家婆做了无数次锅灰猪肝,闭着眼睛都清楚每一个细节,可这次不知是怎么回事,家婆的背影与以前劳动的背影交织重叠,这一秒,我深刻地认识到:家婆,真的老了。而我的童年,也跟天边的云一起,被风吹走了。
“囡囡,你闻到香味没有?”家婆在旁边问。
“有,但不是那种焦香味,应该还没有熟。”我剥了一瓣沃柑,递了一牙给家婆,“家婆,今年家里的沃柑还是这么甜吼,你尝一尝。”
家婆摆了摆手,张大没有几颗牙齿的嘴巴,笑着说,“人老了,牙齿都掉光了,咬不动咯!囡囡,你喜欢吃,多吃!”
照小时候蛮横的性格,我肯定二话不说抓起沃柑果肉就往家婆嘴里送,可这次,我只是平和地笑着,调侃家婆,“吃不了香东西咯,那我就只好多吃点咯!”
家婆没有在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盯着我笑。
相聚的时光格外短暂,没过多久,我就回了遂宁。在家里,我第一次自己尝试做锅灰猪肝,老公皱着眉头,鼓足勇气又尝了一次,可这次他觉得意外的好吃,“口感很绵密,跟爆炒猪肝的嫩又不一样。”
我笑了笑,不置可否。
此刻夜已深,望着不远处的万家灯火 ,我又仿佛看到了佝偻着身子的家婆,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或许在有些人看来锅灰猪肝的制作方式不卫生,因为它的外表而拒绝这道食物,嫌弃和排斥。可我却觉得家婆就像这焦黑的锅灰猪肝,外表淳厚朴实,内里却柔软细腻,在我缺爱的幼年,是她用一颗细腻的心温暖着我,绵密的爱浓厚而又悠长,伴着我长大,在炭火与猪肝的碰撞中,我们将爱传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