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妈妈在北京郊区的村子里一起生活。

笔下的树叶、花、鸟都充满着想象。
突破以往的各种束缚与限制。
编辑:金 璐

在院子里和小狗玩音乐,他们会一起跳舞
在北京的深秋,金色树叶进入掉落前的倒计时,我们在郊区的村庄,拜访了胡格吉乐图和他母亲的家。
他们住在在燕山山脉南端的村子里,一间标准的四合院。我们敲响红色的大门,小狗嘟嘟率先迎接了我们,对来客逐一例行欢迎。
胡格在来到北京的第十年,从北京东二环搬来这里租住。妈妈则是在四年以后,从内蒙古被接来了北京。
院子里中着一棵杏树、一棵苹果树,胡格说这是入乡随俗,因为当地人说这代表着“平安幸福”,还必须成双,只种一棵也不行。树的中央,一株玫瑰伸得很长,躲在要仔细观察才能看见的地方。

胡格现在所在的Hug乐队演出现场
胡格刚来北京时,是杭盖乐队的早期成员之一。相比之前,胡格现在更多参与一些舞剧、诗歌节即兴配乐、学校音乐工作坊等工作
对他们来说,这里都是新的生活。胡格从一个19岁时离家来北京玩乐队、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转变成了放下对名利的追逐,观照内心的即兴音乐人,妈妈则从单调的家乡生活里脱离出来,开始和北京的艺术家朋友们一起画画。
但这也是一种旧的日子。他们的生活在一日三餐、锻炼、遛狗和弹琴画画中循环往复,复归了儿时在草原上生活时那种纯粹的、远离都市焦虑的心境。
院子里种的萝卜并不是为了吃,所以放肆地开出花来,吃完的柚子皮,可以成为植物的肥料。墙上到处贴着妈妈的画

妈妈画画时,会使用各种鲜艳的颜色
色彩占据了他们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墙上贴着妈妈的画,颜料盘里大胆的配色,自制乐器的喷漆落到地上形成像烟花一般的形状,红砖和黑瓦,黄色的嘟嘟和绿色的树,在这个空间里共存着。

胡格抱起小狗嘟嘟
音乐自然流动地发生。在我们拍摄的间隙,胡格会突然拿出一把不知名的乐器到院子里弹奏起来,和嘟嘟共舞,或是把和人身型差不多大的嘟嘟整个抱起来亲吻。
和母亲、嘟嘟走进树林深处,胡格吹起胡笳(蒙语:矛盾朝尔)——一种北方游牧民族的直管吹奏乐器,声音回荡在空旷的秋天里,丛林很大,他们三个的身影很小,却融合得像本就该在那里。



胡格会骑电动车带着妈妈和小狗的宠物车,一起去树林玩我以前住在北京市里,当时因为练琴不方便,在楼房里容易产生扰民的问题,很多练琴的计划就会被打断。我想着村子里空间大,也不会扰民,就慢慢在这附近找,最后2015年,就搬到村子里来。
我在这一个人住了4年以后,妈妈是2019年搬过来的。
我妈妈是特殊人群,她当年因为发育期营养不良,智力上有一些障碍,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内在是非常自卑的,整个社会对她有异样的眼光,她其实需要的是支持和肯定。在老家大家也是很爱戴她、照顾她,但是没有人可以很健康科学的角度去认识到她的状况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和关心。
当时正值疫情,不方便回内蒙古去看她了,我会很担心,就把她接到北京,到村子里一起住,一直到现在。

来了这儿以后我隔三差五会带她去看一些展,她慢慢地居然就喜欢上了画画。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我弹琴,她画画。早上起来先一起锻炼,喝个奶茶,然后各自去做自己的事,午睡一会儿,下午一起喝个茶,喝茶的时候一起玩会儿音乐。

把小狗装进宠物车

每天必须要出门遛狗,我和妈妈还有我的狗嘟嘟,我们三个每天必须要出去林子里走一圈。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进山去特别凉爽,爬到一个小山坡顶上看北京,北京城就像一个积木都摆在你面前。每个季节不同的花、树叶自然呈现出来的景色,其实都在给我们很多灵感。
下午回来,她继续画画,我也继续弹琴,吃完晚饭又睡,就这样周而复始。

妈妈的画

左:村子里的画家朋友来给妈妈上课
右:邻居给妈妈送的祝福
我妈妈的画颜色非常激情、热烈,非常地勇敢,每次我看到她的画,都觉得我可不敢这样画。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勇敢,但对她来说是本能的、自然的,她跟这个世界链接的方式完全是靠情绪的感应。
我之前见过很多格陵兰艺术家的画,他们是从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画得特别棒,和我妈妈的气质非常像,我就觉得把妈妈接过来以后,应该把她往这个方向引导。
正好我们周边的邻居有很多画家朋友、艺术家朋友,他们也愿意跟这种简单的老人一起玩。我和妈妈一般说蒙语交流,但他们交流往往不需要语言,一个笑一个肯定,然后一起画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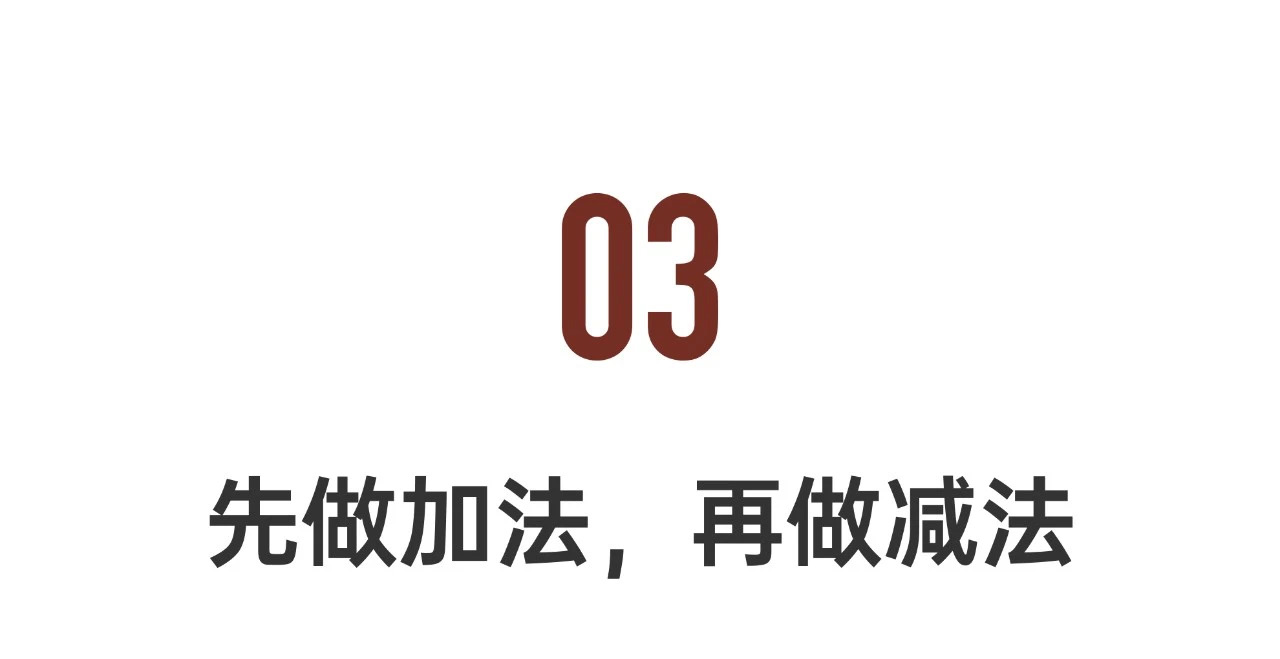
离开内蒙古是2005年,当时我19岁,刚刚从呼和浩特马头琴学校毕业。一个朋友说北京有个摇滚乐队要改成民族音乐,需要马头琴,我就过来了。当时我们是组成杭盖乐队的第一波成员。2006年,刚来北京一年时,父亲来看胡格演出
因为我父亲就是音乐家,我从小看到他非常受人爱戴,让我觉得这个职业是受尊重的,我就也很想做这个职业。当时离开家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想要实现梦想,走去全世界。
刚来北京的时候,都是往外探索的一个阶段,有一段时间是跟着欲望跑的,我们也确实到世界各地去巡演,舟车劳顿,行程特别满,我也很想要有好的乐器,追逐名利。而且跑着的时候,自己是察觉不到的,因为你会觉得大家不都是这样忙活吗。
那时候我心里面开始有很多的音乐鄙视链,什么是高级的,什么是俗的,另类的、黑暗的、先锋的、实验的,诸如此类。在音乐的设计、演奏上,我也会觉得编得越难越好,有时候会把一首歌变得非常复杂。但是却忽略了自己演奏的时候自己的心、自己的呼吸、自己的手是不是松弛的。
直到有一天我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我才意识到自己真正享受音乐的能力正在慢慢丧失。我的肩颈会突然卡到一个点,动不了了,我变得易怒、失眠,别说享受音乐了,生活都享受不了。胡格在家练习

家里的“排练室”,摆放着各种乐器,地上有着改造乐器时使用的各种喷漆留下的痕迹这五年我经历了整个生活上的一个变化,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做加法,然后再做减法的过程。之前都是在向外探索,但现在我更倾向于向内求了。
在这件事上,我妈妈其实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她没有受过教育,没上过学,对任何东西,音乐、绘画、时尚,我们这种受过教育的人、受过社会影响的人身上的鄙视链,她都没有,什么她都觉得是好的。

胡格在家和妈妈一起玩即兴音乐,妈妈可以以非常稳定的节奏拨动空弦我有的时候跟她一起玩音乐,她就在旁边在吉他上拨几个空弦,就可以非常享受、安定地在那里,没有那么多的障碍、技术上的思考。我极其佩服她这一点,所以后来我就学习她这个状态,每次演奏以前,我会刻意调一下呼吸,让自己思辨的系统不工作,然后才开始弹琴,思辨的系统在工作的时候我不弹琴,慢慢地我就发现很管用。
我不想成为让我的音乐变成一个满足我的欲望的技能。现在我去接一些演出,只要生活所需一定范围内够用就好,但有一些我要付出太多代价的演出,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我就会推掉。
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过去那些我自己给自己设的障碍,就好像这个酥肉绝对不能碰,那个甜食我不能碰,这些雷区我都不要了。音乐就是音乐,声音而已,震动而已,我觉得里面的要表达的情绪、情感更重要,没有雅和俗之分。左:胡格改造的马头琴,在上面挂了智齿和铃铛,它们造成的振动可以带来一种类似电音的感觉
右:胡格用饼干盒改造的三弦乐器,铁制琴箱的好处是可以不受天气风吹雨淋的影响,不易受潮,方便携带去户外这也反映在我自己做乐器这件事上,我不想要被乐器本身所限制了。
之前我有一个观念,乐器挺贵的,是人家标准生产的,就肯定是很好的,我应该好好弹,对得起它,但从来不会思考这个乐器的尺寸跟我的手的尺寸合不合。后来我就开始反思,因为物是可以改的,而我的身体就长成这样,是不能改的。
我开始有很多自己的计划和想法,比如把乐器调成我熟悉的调弦方式、舒服的尺寸,或者是利用一些生活中的物品去改造。
比如我觉得马头琴的头很大,很占地方,就换成了一个小小的马头。以前出门的时候总会被航空公司歧视,因为太长的乐器都不让上飞机,世界各地的标准就是34寸,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比较小的乐器,比如小的电马头琴,还有这个我买的旅行吉他,改成了我熟悉的5弦的特殊调弦方式。
这个过程中,不再是我去适应物,而是我有能力让物适应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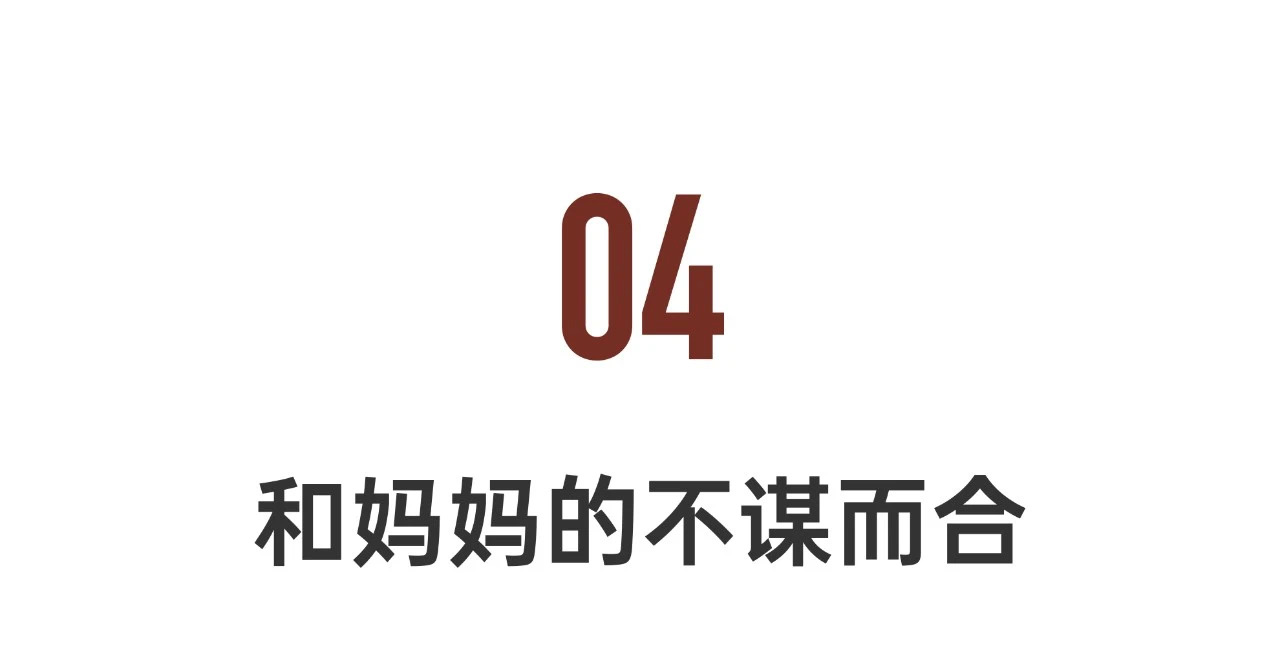
在树林里演奏

专辑里的插画用了妈妈平时画的画
大多数时间里,妈妈在屋里画画,我在这间房里弹琴,我们各做各的。但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是我发现她的那些绘画作品和我构思的音乐内容有呼应。
我的专辑《还童》里,用到了很多妈妈的插画,是因为我们发现我歌里想要表达的很多意象,比如鸟、大雁、宿草,歌里有写到的这些内容都能在她日常的画里找到。
可能是我们俩的内在世界更一致了。我们虽然各做各的,没有相互交流,但是几年下来,好像我们做出了一个整体的东西。


我还年轻,我还想跟更多的人分享我的音乐和艺术,所以有时候我需要去城里或者外地演出,我的生活是会被打断的。但是被打断以后,回到院子里,妈妈还是特别稳定地在这种节奏里生活着,所以我一回来马上跟上她的节奏,也很快就能安定下来。

这三年跟妈妈生活在村子里,我更开始探索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家庭关系,其实发现它是有一种冲突在里面的,尤其是在童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既有爱,又有恨,甚至有逃避。最典型的就是当开始有很多家人、朋友关注我学琴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都会用父亲的标准去期待我,这太恐怖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期待越大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越无力。我青春期的一些叛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每天早上我都会做冥想,坚持了几年以后,我梳理出了自己内在的一些情绪。专辑名字叫“还童”的原因,就是真正地从内心里去回归父母的孩子这样一个角色。这其实是意味着好好往后生活,你没有办法跟过去和解的时候,后面的生活也会是一塌糊涂的。现在的状态对我来说是特别好的,很滋养的。我记得童年小的时候在牧区,我们的心理状态跟现在也差不多,那时候还放羊,生活其实不怎么需要计划,生活自然就会有一个规律。在这种生活节奏里,我和妈妈都得到了很多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