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西郊,雒粒舟和杨宓的婚房
常被左邻右舍津津乐道。
150m²的家中没有空调、电视,
全是二手旧物,
有从拆迁的老村子里捡回来的,


夫妻俩亲自设计、装修、布置,
耗时1年打造完成:
奶奶的嫁妆桌改成洗手台,
酿酒器、脏衣篓、独木舟变身吊灯,
原始的洗手间,用200块老木板搭出一个阁楼……

夫妻俩把二手厢式货车内部改成小木屋,上路创作摄影作品
9月,一条到成都拜访雒粒舟和杨宓。
编辑:朱玉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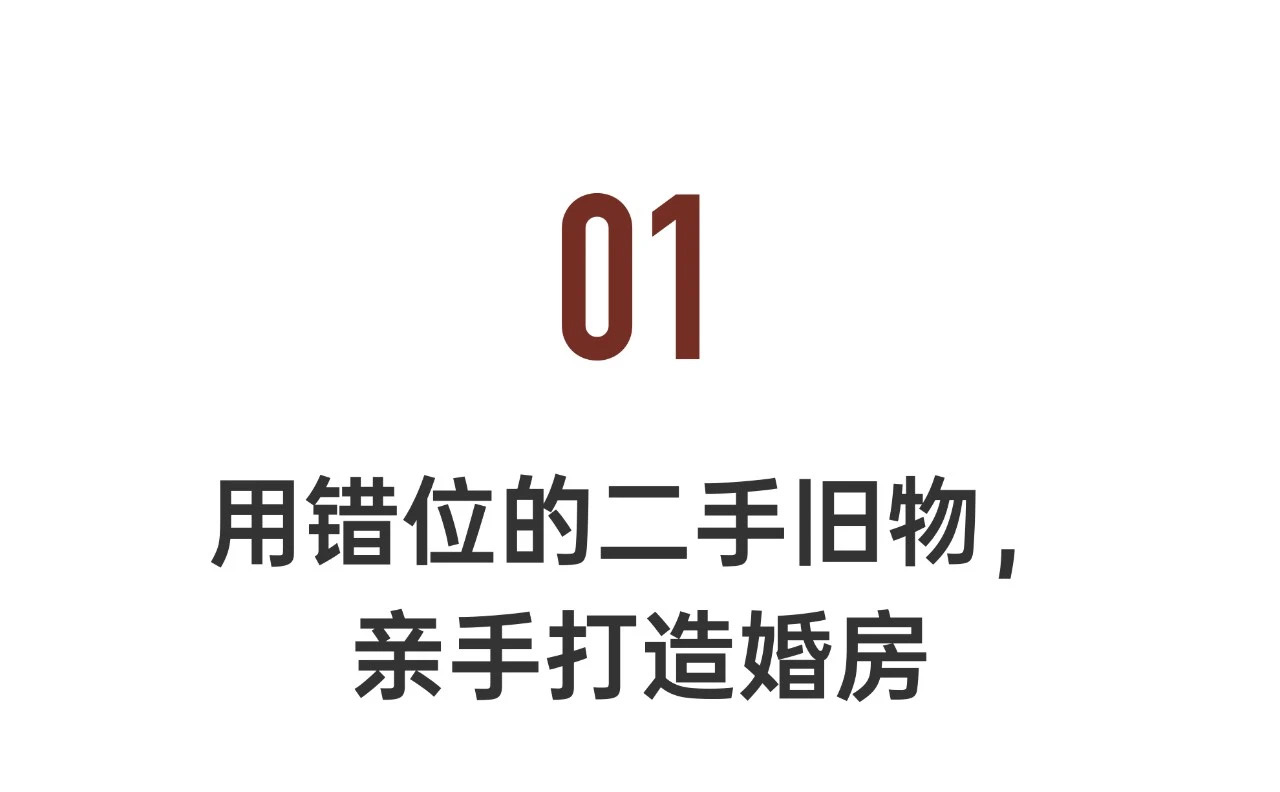

雒粒舟和杨宓在家
我是雒粒舟,84年生,我的妻子叫杨宓。2022年,我们结婚,在成都西郊买下了这套房子。它位置僻静,地界已经属于崇州了,有150m²,上下两层。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设计、改造,甚至水管、电线都是自己学着装的。尽可能保留原始的毛胚结构,主要用软装来搭配。
家里几乎所有物件,包括电器,全是二手的旧物。上面那些时间的痕迹、手工的痕迹,那种美我觉得是没办法替代的,每一件都独一无二。
有很多是过去3年里开车在各地做创作,碰见不少老的村子拆迁,他们不要的东西被我们捡回来。也有一些自己老家留下的,或是在废品站、二手市场淘到的物件……去动脑筋让它们产生一些错位,不再是原来的用途,变得更有趣一些。门口的鞋柜,是以前行政单位的文件柜,里面的隔层设计放鞋刚刚好
毛胚房里的展览,邀请中写道:“我们将每天住在水电不通的毛胚房中……我们一无所有,所以前来观展的你可自愿为我们携带一件物品,比如水、食物、蜡烛……一进门马上能看到一面毛胚墙,上面写满了字。这个房子交房时间晚了大半年,一度感觉要烂尾,与其干着急、焦虑,我们想,不如就做场展览。
2021年末,我俩当时就住在水电不通的毛胚房里,办了一场摄影展,每个来的朋友就在墙上留言。就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被一个铁链给拴起来,你无法去挣脱,只能带着它生活。这面墙就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代表了我们的一些思考和态度。

客厅的壁炉,是在废铁收购站找到的一个大货车后桥。旁边放碳的篓子,其实是米斗。东北地区炖大鹅的锅盖,大小正好可以盖上壁炉口。
我奶奶用过的木箱,自己手工加了四个角,做了个小茶几。农村夯土、做土墙用的工具,我给立起来,可以当一个书架。
家里的窗帘,都是用70年代的雨披缝在一起做的。遮光性很好,完全不怕水。咖啡角,用的以前工人做模具的桌子。淘到的时候两个把手就不一样,他们其实是一种纯实用主义,有什么东西合适马上就用,反而出来的效果特别有意思。
墙上,挂着我家祖上的一张地契,光绪25年,我爸特意给我带来的。

餐区的桌子,也是一个老的木工桌。在遂宁一个小村子找到的,以前被工厂用来堆柴油、煤油的大铁箱子,有400斤重,非常扎实。就200块钱,没人要他们就拿去烧柴了。
藏区黑陶的酿酒器,我用绳子捆起来做吊灯。旁边的两张长椅,是我以前在成都郊区租房子,睡的床就是这两个长椅中间搭了块板子。厨房,我父母那一代人给我的影响,觉得灶台一定要很结实,可以砍骨头,我就用钢筋混凝土做了一个。我跟我妈说,现在恐龙的骨头都可以砍得动。
旁边收纳厨具、调料的几根木条,是在云南金沙江边,有大量拆迁后废弃的木料被冲到岸边,我们俩大半夜就去捡,那基本就是我们最早开始收这些旧物。一楼的洗手间,奶奶的嫁妆,我给切了装了个台下盆,尺寸刚好合适。旧木材市场不要的边角料,拿回来拼了一个门,我就想要上面被斧头劈过的那种感觉。
旁边放毛巾的,其实是一个床架,我自己就在这张床上出生的。我把它拆成了两个放毛巾的,和一个长的梯子放在二楼木屋里。

楼梯下的空间用作工具间,墙上是杨宓为雒粒舟整理的工具清单
楼梯口,放着我2013、2014年最早进山的时候骑的摩托车。楼梯扶手都是自己买五金件装的,一个老的马鞍,扣在灯上。

二楼休息区的沙发,100块钱淘来的废品。上面很多破损,缝了有三天。后面是丹巴一个村子拆迁留下的窗框,我特意为它们作了两张画。
中间的吊灯其实是降落伞的引导伞,我当时在思考怎么让它很饱满地撑起来。突然有一天看到家里剩菜剩饭防苍蝇的罩子,不是刚好合适吗?另一边相当于我的工作室,桌面是自己用两块老门板拼起来的,两个老窗框当桌腿。云南采莲用的独木舟,做成一个吊灯,对应我的名字“粒舟”。
家里的风扇,还是从小老家用的。当时村子里大家要晒谷子、吹东西,全都用它。二楼的洗手间,借用原始的下沉区域,做了一个复式阁楼小木屋。当时淘了接近200块老木板,上面全是虫卵、老的灰、油渍,我们两口子刷了一星期。
冬天的时候里面搞点篝火,整个房间就非常暖和,我们就睡在上面。朋友来了在里面玩游戏打牌,就像回到以前老的绿皮火车。

主卧,我淘到老的木门,开关的时候还有那种老房子吱吱喳喳的声音。我们笑说如果有贼,他推门肯定会被吓死。
卧室里就非常简单,床就放在地上。床头灯是以前老的轮船上用的,脏衣篓,也给反过来做一个吊灯。


我们平时很少进城,喜欢往阿坝和甘孜走。把婚前贷款买的城里的房子置换到这里,也是觉得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空间更大,还更便宜,过了13年的贷款生活,我再也不想要房贷了。
房子里我们坚决不装空调,超过33度,就开车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换一种活法。一个月花两三千电费,还不如花在路上,对吧?
我们觉得人还是要多与自然去相处,过度把自己关在一个温室里面,就会越来越脆弱。

雒粒舟作品《自生塔2013-2014》
我最早是2013年,一个人带着600块钱,骑着摩托进山,到高原拍的第一套摄影作品。出发那一刻,感觉就像是一只鸟,笼子被打开飞出去了。
三年前我俩认识的时候,杨宓还在重庆做品牌、市场,和我的生活截然不同。当时她买错了车票,经一个共同的朋友提议,由我短暂接待一宿。我们在油菜花田里做了顿火锅,晚上她睡车里,我就在车顶搭了个帐篷。
后来她告诉我说,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像野生动物一样,生活非常极简,对所有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东西全都不感兴趣,只按着自己的想法活下去。她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活法,就不想从我的车上下来了。

我们把二手市场淘来的厢式货车内部改成小木屋的模样,后备箱就变成我们的厨房,开始频繁地上路,一起创作。
她以前也很喜欢买衣服、包包,进了山之后发现,其实人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一个睡袋就够了。见到好的风景,呼吸好的空气,你的幸福感,你开不开心,这些才是奢侈品。
她爸爸经常说,等到退休之后,我就买一辆吉普车,像你们一样上路,去旅行。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等到以后”。等到毕业以后,等到换工作以后……人生太无常了,没有那么多等。

爷爷病重时,雒粒舟最后一次去探望时拍下的照片

我记得很清楚,我爷爷病重的时候我回农村去看他,他说他很想去一个地方,其实离他也就十几公里。到了最后的时候,一个如此近的距离都变成一个遥远的距离。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爷爷应该看更多的地方,只不过他没有机会,我要帮他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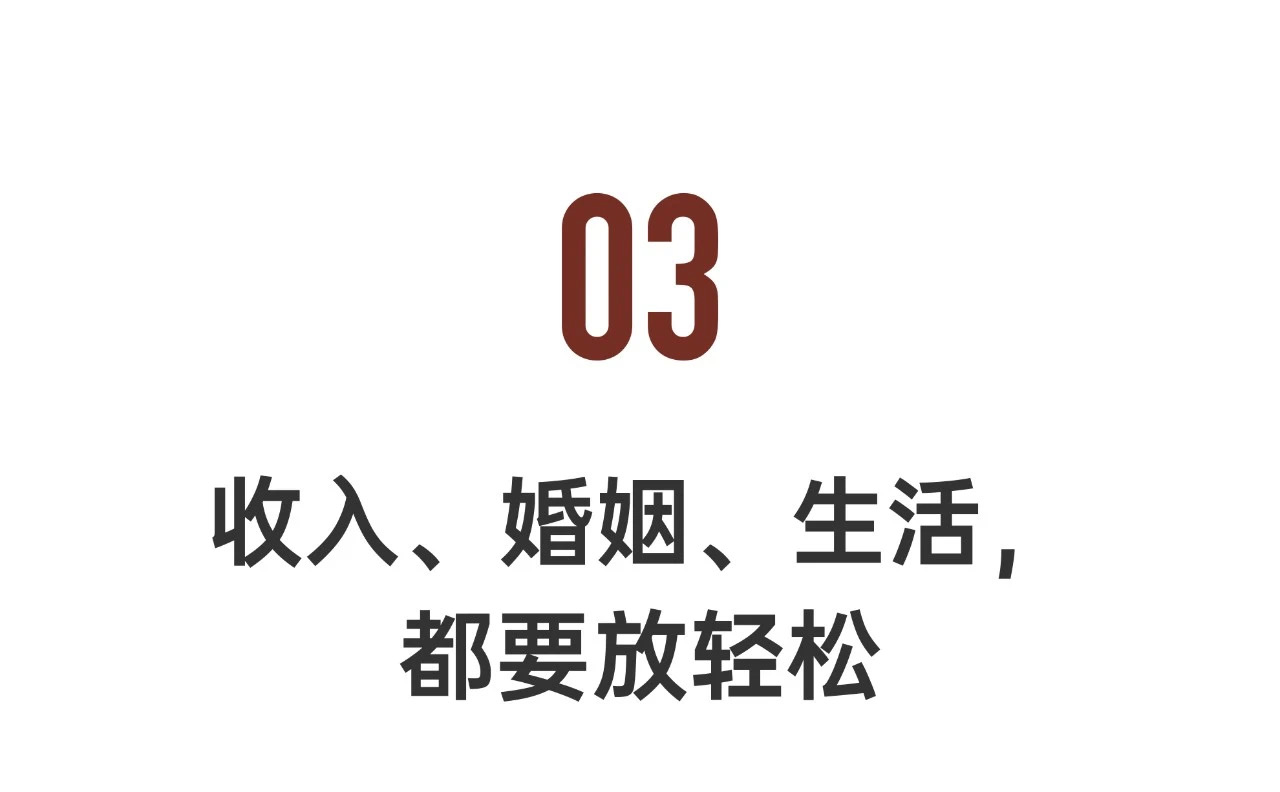
2007年毕业之后,其实我也上过班、创过业,也曾经非常渴望赚钱,收获名利。但是你发现很多东西是无法控制的,你很认真地做了事情,并得不到你认为应得的回报。
2013年辞职进山做创作,没有收入,每个月还有1500元的房贷要还,其实从任何理智的层面去思考,都觉得不该出去。但是现在回想,恰恰是你的焦虑,为了解决下个月眼前的事情怎么办,导致你很多思想被禁锢住。

雒粒舟的摄影作品在家中处处可见
当时出去拍东西,我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喜欢我的照片,收藏我的照片。才发现曾经你相当于只抓住了一个机会,而放弃了无数个潜在的机会。
我爸其实一直不太理解我的选择,直到后来我自导自演的短片入选戛纳,他第一次发了条朋友圈,说“你赢了”。
我就说,人生哪有什么输赢。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不用管别人跟你说的什么成功秘诀。

车是夫妻俩移动的家和工作室
现在其实我们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主要靠接摄影、设计等不同方面的项目为生,收入很不稳定,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焦虑。
我俩就是1+1大于2,这个能量是完全可以支撑我们,起码生活来说是没问题的。本身我们物欲也不高,只要我们两口子有饭吃,不去欠钱,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就完全足够。当自己心态放好了之后,反而有很多好的机会自己冒出来。

我俩之前其实都不算是对婚姻特别向往的人。甚至说如果0分是无所谓,100分是非常想结婚,我以前可能是-100分,因为我双眼能看到的婚姻走到后面都是一地鸡毛的感觉,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
去民政局登记前一天晚上,我们就把车停在门口,睡在车上,就讨论说婚姻到底是不是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人想进去。
当时杨宓就说,那如果这道墙本身就不存在呢?我们就约定以5年为期,每5年,就坐下来认真交谈一次:你有没有想过离婚?这个“合同”还要不要续约?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聊的。我觉得婚姻最主要的一个心理问题就是人要克服自己的占有欲。其实所有的矛盾都来自于占有欲——ta是不是每时每刻都被我掌控?有没有活成我想要的样子?其实你越这样做,对方越想逃。
相当于你创造了一个虚构的妻子,而虚构的一定会映射到具体的另一个人身上,第三者就一定会出现。而如果这个人没有占有欲,那个映射的影子也不会出现。像我们因为不同的项目经常要异地,我俩都不会说去查岗,有那些怀疑的东西。
我是觉得很多事情都要放轻松,你越放松,它越不会出现问题。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豁达的人,不断地去探索创造。部分照片由雒粒舟、杨宓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