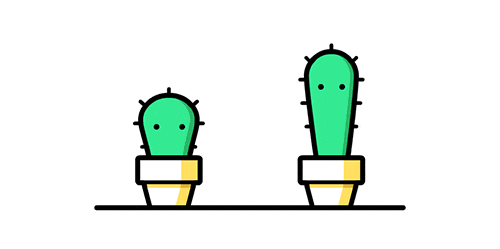诗人雷平阳回到故乡,在清明节跟随母亲去给父亲上坟。
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总想要扬眉吐气,结果活得什么都不合心愿。生命直到最后,还觉得整个世界都亏待了他。
母亲说他就像一个蜘蛛,被困在了一张网中,自己也不愿出来。能偷生于尘土表面,已是他的福分了。
本文原名《上坟记》,作者雷平阳。
01
荔枝河
清明节的早晨,空气里的清凉,不像特殊日子里夹着苍灰和悲戚的那种清凉。它有着一丝不经意的苦涩,舌头尖上的茶滋味,夏日中午出自地下河的微风,隐隐约约,去意彷徨。同时,它还有着刺芒穿越肌肤的功效,由神经的秘密线路,将最细小的感觉信息,传送给无所事事而又异常清醒的大脑。站在家门口的河堤上,我下意识地抬起左手,去摘杨树上的叶片,似乎想知道,杨树叶子是否与我有着相同的感受。我一连摘了三片,它们薄薄的身体,似乎也被什么东西袭击过了,处在常态中,但冰凉得未免过分。
母亲照例早早地就起床了,现在正坐在门前的石台阶上,认真地划着一刀刀纸钱。纸都出自深山的小作坊,工艺差,工人又粗糙,做得皮断肉不断、筋骨参差不齐,压在一起后,想一张张分开,若缺少耐心,乱用力气,那就休想得到一张完整的。母亲已经七十岁了,眼睛还不含糊,双手也还听使唤,只见她像在坎坷不平的锅底上揭鲜嫩而又热乎乎的面皮,“神三鬼四”,敬神的三张一叠,给鬼的四张一叠,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张纸揭起来,折叠成纸钱。
太阳每天都从同一个地方升起来,这种重复没有新意但又很神奇。它很快就把无处不在的蓝色、黑色和灰色一扫而光,给空气一一散发热能,甚至还将母亲折叠的纸钱涂抹得金光闪闪。母亲眼皮往上一翻,看见太阳,说:“这个鬼太阳,今天出来干什么嘛!”接着掉头往门洞里大声地喊我的哥嫂、弟媳以及他们的儿女:“还不出来帮我折纸钱?这个鬼太阳一升高,坟地上热得要命,到时我看你们钻到坟里面去躲阴凉!”
母亲也为自己的幽默感到很开心,一边笑,一边还喊着:“你们快点,快一点!”一伙人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出了门,个个拿上一捆纸,各自去折叠,大哥手上拿着纸,嘴巴上说着:“哟,整这么多干啥子,去年才给他们烧了几十亿,足够投资修一条从昆明到昭通的高速公路了,今年再烧这么多,我今天倒是要建议他们,把钱拿出一点点,把昭通城到欧家营这条破路适当修一下,你看人家三甲村,路通了,家家还住别墅……”大哥这么一说,大伙就笑。母亲也就来劲了:“修什么路嘛,如果纸钱要顶用,最好让人清理门前这条河,实在太臭了。”
我家门前这条河,名叫荔枝河。太阳没出来前,它黑黝黝的,像在暗处睡着了,扑哧扑哧地吹着梦呓的白泡。可当它迎着阳光醒来,变色龙似的,马上变成灰白色,继而又从灰白中泛起颗粒状的黑色。按道理,灰白色非常想死死地压住黑色,但黑色是沸腾的、向上的、压不住的。至于蔚蓝色,这水的本色,或说这清水与蓝天共同合成的色,多年没见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当腐烂的动物尸体和一座城市所有的污秽之物,汇聚到这儿,也许只有灰白色和黑色是协调的,是同一个话语谱系。
我也曾一次次从骨头上冒傻气,总觉得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故乡”仍然存在,一厢情愿、不管不顾地想把自己与之相依为命的那条荔枝河,重新找回来,什么碧波荡漾,鱼虾成群,天神的客厅,活命之水之类,忙乎了半天,只剩无语哽咽,有些词,阳寿已尽,没了。母亲说,在十年时间以前,有的妇女,因为种种原因绝望了,就投河自尽,现在,看见河流这种样子,绝望的人,改喝农药自尽了。让人捶着胸膛、大声质问,也问不出任何道理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十年时间,我们就彻底改变了河流?
烧一堆纸钱给爷爷奶奶和我的父亲,寄望他们的灵魂在实在无法忍受时,花钱来清理一下荔枝河。想法荒诞而且空洞,生者的无力感和对死亡者跨界的、无理的要求,也只能视为一种别样的、吊诡的、黑色幽默似的悲怆和控诉。至于控诉谁,该领谁来指认现场,该在天地间的法庭上审判谁,仿佛谁都可以,谁都又不可以。可以确认的是,犯罪嫌疑人,每个人都是,谁都逃不掉。于我而言,内心最为纠结的或许还不是这一条河流的非河流化,在很多诗篇和散文里,因为强调对盲目工业化的反对,我把本已面目全非的故乡、这一条河,当成了“纸上原野”的美好元素,并将其写成了乌有乡,这算不算犯罪?算不算遮人耳目、为虎作伥?
反之,每一次回老家,都会有老人、同辈和已经不认识的后辈来找我,给我递烟,邀我去喝酒,他们都以为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可以一言九鼎,希望我能找镇政府、区政府乃至市政府的领导反映一下,与其他乡村道路比,欧家营进昭通城的路根本就不是路,至于荔枝河,实在不像昭通人的母亲河,看能不能改善一下?也有初中同学某某,知道我卖文为生,多次鼓动我到有影响的报纸上去发文章,通过舆论监督,“逼”政府拨款修路。尤其是身边的三甲村一夜之间成为了“全国文明村”,阡陌交通,洋楼一排接一排,而欧家营仍然被遗弃、仍然作为垃圾堆,乡亲们内心的落差可想而知。人们说多了,我的心动了,也想有所贡献,但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背井离乡三十年,我应该去找谁?
02
“雷家坟山”
太阳渐渐升高,荔枝河浓烈的腥臭气,果然是河堤关不住的,洪水一样漫进了欧家营。母亲不耐烦了,找了几个尿素口袋,把折了的纸钱往里面一塞,吩咐弟弟一定把香火、鞭炮、酒肉和水果带上,然后对全家人说:“走,没折完的纸钱到坟地上去再折!”家已经不是折纸钱的地方了。于是,一家十多口人,跟着母亲,一只手提东西,一只手捂着鼻子,沿着荔枝河的河堤,朝父亲的坟地走去。
父亲的坟地离欧家营只有一公里左右,是父亲生前耕种过的土地中的一小块。按照风俗,父亲应该安葬到埋着更多祖先的“雷家坟山”上去的,但由于“雷家坟山”早已人满为患,再也插不进哪怕一根骨头,只好另找地方,而请来看穴的风水先生走到这儿,一口咬定父亲最熟悉的这块地,就是好地,我们一家人也就认了。这块地和它四周扩延出去的几千亩地,平展展的,是欧家营西面的一块高地。
小时候,我们曾在这儿割草、放牛,或者经过这儿,前往十公里之外的狮子山去拾柴火。很多时候,在路边上我们还会看到人们丢弃的死婴或尚会啼哭的病婴。见得多的还是人们“送鬼”时烧在这儿的纸钱,泼在这儿的水饭,丢下来的几分诱人将“鬼”领走的硬币。据说,送到这儿的“鬼”,谁第一个碰上,“鬼”就会跟着这人走。乡村是鬼魂游荡的地方,人们对“鬼”存在着无边的好奇和想象,“鬼”在人们心中,有时是亲人,更多的时候则是邪恶、恶灵和死亡的象征,而且,尸体总是与“鬼”连在一起,甚至就等于鬼。所以,当我们看见那些死婴和正在死去的病婴,以及送“鬼”的痕迹,仿佛就看见了“鬼”,身体就先是僵硬、脸色发白、呼吸急促,接下来就铆足了劲,没命地逃离现场。
电影《平原游击队》
有一年的秋天,我七岁左右,跟着村子里的人,穿过这片名叫“沙沟”的土地去邻村看露天电影。放电影的场地选择在一片坟场上,人山人海。电影是《平原游击队》和《龙江颂》,看过不下二十遍了,我先还跟着电影里的角色熟练地背台词,慢慢地,瞌睡来了,最后干脆倒在一座坟堆上就呼呼睡着了。滇东北的秋天,白天阳光灿烂,晚上则霜冷砭骨,等到我在冷霜里醒过来,曲终人散,身边全都是坟堆,鬼影幢幢。恐惧、孤单、被遗弃的失落感,另一种鬼,一齐扑了过来,我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叫了声:“妈呀!”脸上便全部是泪水,然后跌跌撞撞,高一脚低一脚地朝着欧家营的方向窜。摔了跤,连滚带爬地站起来,又跑。掉到尚未收割的稻田里,一身泥浆,鞋帮里灌满了泥水,一边叫着“妈呀,妈呀!”还在跑。腿摔伤了,手上出血了,还在跑。穿过沙沟那无边无际的玉米林时,夜风吹得叶片哗啦啦地响,就像鬼哭狼嚎。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空掉了,魂不在了,力气也快要用光了,喊“妈呀”的声音也卡在了喉咙里。再联想到看见的那些死婴,几次扑倒在地,用双手抓地时,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张皮,命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事后才知,撞开家门,我便倒在堂屋里,昏死过去了。第二天,我的母亲,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站在荔枝河的河堤上,疯了似的,用乡村最歹毒、最不堪入耳的话语,一边诅咒带我去看电影的人,一边涕泪横流。她骂得整个欧家营鸦雀无声,又人人都竖着耳朵听。她骂得快虚脱了,坐到地上,有人来劝她,她就披头散发,目光凶狠,死死地抓住劝她的人:“说,是不是你带我儿子去看的电影?说!”弄得谁也不敢去劝她。她就从早上骂到了黄昏。黄昏的时候,外婆来了,带着精疲力尽的母亲,沿着我失魂落魄的回家路,去给我喊魂。外婆喊魂的音调,我之后还听过,低沉、苍枯、急迫,有无奈,有恐慌,有哀求。
让母亲心有戚戚焉,又略感欣慰的是,外婆死后,也安葬在沙沟这儿,坟堆离我父亲的坟只有几百米。母亲的话是这么说的,欧氏坟山没空了,雷氏坟山也满了,两个没地方去的人,现在住在一块地里,也算有个走动,有个帮扶。所以,当我们在父亲的坟前,把纸钱折完,开始给父亲上祭,母亲拿一些祭品就往外婆的坟上去了。也不知什么原因、有何想法,每次去给父亲上坟,我们都想去外婆的坟上祭奠,母亲都坚决不允许。外公外婆一脉,同样子孙浩荡,不用我们跪谢?雷氏一族只有母亲是欧阳血脉,她足以代表我们?母亲希望我们在父亲的墓前多待一些时间?我每次都想破解母亲的谜底,一直没破解,问母亲,母亲总把话题一次次岔开。母亲到外婆坟上去所用的时间都不长,往往是她回来了,我们还在烧纸钱。等到我们磕头、放鞭炮、清理坟上荒草时,她就坐在一边看着,或自言自语地对父亲说:“又给你烧这么多钱了,看你怎么用!”
父亲的碑文、墓联都是我写的,对联有三幅,没追求格律,一点也不工整。其一:“生如五谷土生土长,归若八仙云卷云舒”;其二:“农耕一生尘中尘,极乐千载仙上仙”;其三:“望田畴犹在梦中,辞浮世已在天上”。三联的上联都是交代父亲的命运,下联写我对他的祈愿。不用说,尽管写对联的时候我心如刀绞,但它们还是写给人看的,是写在石头上以求不朽的。说父亲像五谷杂粮土生土长、一生躬耕是泥土中的泥土,这倒没什么夸张的成分,甚至根本没有说出父亲比五谷和泥土更卑贱的一面,问题出在语词中透出的豁达与超脱,仿佛父亲就是泥土和五谷之间的一个隐士。“望田畴犹在梦中”一句,更是留下了不小的误读空间,乍一看,别人还以为我父亲是多么地留恋令他屈辱万分的田地与劳作。

记得跪伏在石头上写这些对联和碑文时,手握毛笔,一心想着馆阁体,想着笔笔都是中锋,我是何等的严肃,就怕哪儿一旦出错,有辱了理想化的父亲。可越这么想,越往别处用力,手就抖得越荒唐,越不像我的手。旁边的錾碑人不看场合又不知玄机,一个劲下药:“张凤举和赵家璧先生给人写碑,总会提一壶酒来,写一个字,坐下,慢慢地喝上几口酒。一座墓碑,一般都要写三天。”听他一说,我没法写了,我能提壶酒来边喝边写父亲的碑文?我能在此为了求法度、得庄严慢慢耗上三天?我之所以没去拜请谢崇崐、陈孝宁、黄吉昌等昭通书法大家来写,无非是我想把对父亲的情义写到石头上去,如果请他们中的哪一位来,我会领受这份不安与无助?绝境中,大哥递来救命草,他在电话中说,请来操持葬礼的道士已经定下父亲的出殡日期,时间太紧了,要我抓紧点。我也就不再犹豫,提起笔就往石头上写去,太想写好,结果写出了自己至今败笔最多的一堆字。
不过,这倒也适合父亲,我的字处处败笔,他则是太想活得扬眉吐气,结果活得什么都不合心愿,活到最后,还觉得整个世界都亏待了他。但真要让他说出究竟是谁亏待了他,他又支支吾吾,不明不白。想想,父亲的一辈子,也的确活得不明不白。昭通解放时,他说枪声“像炒豆子”,豆子炒完,他八岁,没上学,当了合作社的放牛娃。长大成人了,被安排了当专职的赶牛车的人,遇到春耕大忙时,就牵着牛犁田耙地。农闲了,就赶着车拉煤或拉粪。如此,一直干到土地下放。土地到手,他却只会服侍牛,其他农活什么也不会做,或说总是做得难以达到母亲的要求标准。跟着母亲去栽秧,他把株距弄得比行距还宽,速度也比手脚边的蜗牛还慢,母亲让他拔掉重栽,顺便奚落了他几句,他用脚把栽错的秧苗一阵乱踩,把手中秧苗往水上一扔,走了。一个人坐在荔枝河埂上吸闷烟,有愤怒,也有内疚。
03
像只蜘蛛
1983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师专,从教育局领到录取通知书,一阵小跑,回家见了他,跟他说:“爸爸,我考上了!”他一脸不屑:“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说:“那打个赌?”他问:“赌什么?”我说:“一套军装。”他却想都不想就说好。我就把录取通知书拿了出来让他看,他不识字,但看到红彤彤的公章,就认输了,噔噔噔踩着木梯上楼,把母亲吊在屋梁上的,用来做种子的两袋小麦和蚕豆解下来,背篓一装,背进城变卖掉了。
结果,父亲递来的军装,我心花怒放,母亲却气得跺脚,赌气不吃晚饭。我能考上,母亲其实比父亲还高兴,她痛心的是种子卖掉,来年用什么下种?猪可以卖,鸡鸭可以卖,怎么能卖种子!夜深人静,我们都睡下了,他们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还动了手。之后的一个多月,两人形同陌路,母亲要下地,也不喊父亲,父亲则隔三岔五跑到乡供销社,与几个老哥们打了劣质散酒,坐在墙脚喝,醉了才回家。喝醉了酒,父亲总是头低垂着,双手的十指插在头发里,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去睡觉,一个姿势可以到天亮。快到我要去师专上学了,必须请左右邻居、世戚穷僚吃顿饭以示喜庆,父亲和母亲才勉强彼此搭理,父亲进城卖猪,母亲在家张罗,弄了一席家庭史上无比奢侈的“八大碗”大席。

我去学校报到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还很固执地要替我扛背包,我不干,他圆睁着双眼,头发直立,伸出一双大铁掌,从我手中就把背包抢了过去。背包其实也不重,进城的路也不远,对当时年富力强的父亲来说,这点活计算不了什么,可我总觉得这种活已经应该由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来做了,父亲只需跟着走路就足够了,而且他完全可以不用送我。
路上,父亲扛着背包走得很快,我一身崭新的军装,双臂好像变成了两只翅膀,身体想飞起来,却又行动迟缓,怎么也走不快。脚下的泥泞路,路两边的田野,田野里的禾苗、昆虫、阳光与阴影,在那时似乎都在讨好我,以卖命的方式向我呈现它们最单纯、最鲜活也最诱人的美。父亲走远了,见身后没人跟上,就大声地咳上一声以示提醒,而我也又才风一样地跟上。
途中,父亲碰上过几拨熟人,别人问他进城干什么,他少见地眉飞色舞,拿出烟,敬了人家,还要给人家点上,点上了还要缠着人家多说话。意思太简单了,无非就是想让这些人天一句地一句地猛夸我,别人一夸,他就咧着嘴巴笑,露出两排黑牙齿。到学校大门了,父亲却怎么也不进门,扶着大门处的水泥柱子往里面看,看够了,把背包塞给我,转身,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没有比母亲更了解父亲的人了,多年以后当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只会天天形影不离地跟着母亲,母亲曾跟我说:“你爹这个人,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患上了这种病,一直没好过,像只蜘蛛,结了个网,他不出来的话,谁都弄不出来。弄出来了,他还会再结一张网。”母亲说的这张网,父亲肯定是没有意识到的,而且我觉得父亲一直都想从这张网里钻出来,但又害怕被禽鸟叼走。与他同一个模子里塑出来的人何其多也,他能缩头、躬身、自认倒霉地偷生于尘土表面,已经是他的福分了。如此天命,他能做什么呢?那些所谓的庄稼能手、鸡鸣狗盗之徒、渴望美好生活而不惜离乡背井的人,又有几个得到了好下场?还不是一样的瞎折腾,谁也没见生活赏他们一个笑脸。
不过,母亲也羡慕父亲,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你爹倒是安逸了,到死还能喝酒,一喝醉,共产主义就来了。”也许很多没有乡村经验的人不知道,“共产主义”这个词条,因为它太普及又太诱人,集合了乡下人所有的理想和空想,甚至囊括了乡下人的太多的“想都不敢想”,所以乡下人就总是把它具象化、世俗化,力求能伸手就抓住。比如,一顿大酒可叫“共产主义”,逮住一条鳝鱼也可叫“共产主义”,偷了别人一只鸡没被发现,当然也可叫“共产主义”,甚至于见到了某个大人物、结婚了、高寿而逝、路上捡到一角钱、某人递过来一支烟等等,都可以叫“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在远方,就在手边上,如果在远方,人们就懒得去想了,一想就累。
就像现在,当我们在父亲墓前礼毕,坐在墓地旁的草丛中吃水果,吃了一个,母亲又会递来第二个:“吃,多吃点。”如果哪个人不吃,母亲就会接着说:“哼,你不吃?这苹果又不是纸扎的,吃,如果是纸扎的,你想吃也吃不着!”妹妹把剩下的几个水果放在了父亲的墓前,母亲不反对,但还是说了这么一句:“老辈人说,你爹那边有那边的水果,你放在这儿,他还能从坟里爬出来吃?”
从父亲的墓地上走开,已是中午了,太阳毒辣,荔枝河上的腥臭味开始变成恶臭。我们挤上弟弟的面包车,去几公里外的“雷家坟山”。车又得在荔枝河的河堤上颠簸好一阵子,车窗必须紧紧关上,但车是破车,怎么关都有裂隙,恶臭味都会进来。于是车子内,又挤,又热,又臭,人人都大汗淋漓,不敢喘气吸气,懒得说一句话。
04
铲除一切
“雷家坟山”位于昭通古城即“土城”遗址附近的一座丘陵上,在母亲的记忆中,大炼钢铁运动以前,这儿还是看不见天空的黑森林,现在一棵树都没有了,除了坟山,全都是耕种了多年的熟土,类似树木的,是一架又一架的高压线铁塔。高压线的下面,上坟的人络绎不绝,种植玉米和土豆的人则在春风掀起的灰尘中挖塘、下种、浇水,像地上冒出的泥巴人。其中几个是母亲认识的,他们与母亲打招呼,一笑,脸上皱纹里的尘土就往下掉,母亲不买账,虎着脸就咒骂:“你们这些绝人,种自己的地就行了,年年都要挖坟山地,多挖一锄,种得出几棵玉米,就不怕满地下的鬼跑到你们家里去闹腾?”那些人都是母亲的晚辈,不敢还嘴,赔着笑:“以后不敢了,不敢了!”母亲不依不饶:“啥子不敢了,挖吧,尽管挖,不就是一堆堆白骨,锤碎了,还可以做肥料,保证让你们的土豆长得比人的心还大!”
“雷家坟山”埋的大多数是雷家的亡魂,也有少数他姓人家的人,因为坟山满了没地方埋,又是雷氏的亲戚,便埋到了这儿。按照坟山上所埋之人的辈分和去世年庚推算,这片坟山形成的时间也就四十年左右,即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众所周知,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很多人肉体和灵魂都没有葬身之地。在我写的《祭父帖》这首长诗中,关于那个时候的父亲,也有这么一段:
围着他的棺木,我团团乱转,一圈又一圈
给长明灯加油时,请来的道士,喊我
一定要多给他烧些纸钱,寒露太重,路太远
我就想起,他用“文革体”,字斟句酌
讲述苦难。文盲,大舌头,万人大会上听来的文件
憋红了脸,讲出三句半,想停下,屋外一声咳嗽
吓得脸色大变。阶级说成级别,斗争说成打架
一副落水狗的样子,知道自己不够格,配不上
却找了一根结实的绳索,叫我们把他绑起来
爬上饭桌,接受历史的审判。他的妻儿觉得好笑
叫他下来,野菜熟了,土豆就要冰冷
他赖在上面,命令我们用污水泼他
朝他脸上吐痰。夜深了,欧家营一派寂静
他先是在家中游街,从火塘到灶台,从卧室
到猪厩。确信东方欲晓,人烟深眠
他喊我们跟着,一路呵欠,在村子里游了一圈
感谢时代,让他抓出了自己,让他知道
他的一生,就是自己和自己开战。他的家人
是他的审判员。多少年以后,母亲忆及此事
泪水涟涟:“一只田鼠,听见地面走动的风暴
从地下,主动跑了出来,谁都不把它当人,它却因此
受到伤害。”母亲言重,他其实没有向外跑
是厚土被深翻,他和他的洞穴,暴露于天眼
劈头又撞上了雷霆和闪电,他那细碎的肝脏和骨架
意外地受到了强力的震颤。保命高于一切
他便把干净的骨头,放入脏水,洗了一遍
我的父亲尚且如此,风头上、场面上的人物,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令我意外的是,同样是那个“铲除一切”的时期,原先的“雷家坟山”没空地了,国家竟然会在这距离昭通城只有三公里左右的地方,让出这么一块地来,供雷氏的亡人长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期,从合作社、大队、公社的手上让出来的土地绝不会只有这片“雷家坟山”,一定还有赵、钱、孙、李、周等等百家氏族的坟山。这一让,让出的是另一个世界,搭进去的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沃野千里。
就此,我曾经想过要去档案馆查询一下,看有没有相应的文件、政策和规定的资料,如果有,那“文革体”的字词语境中,说不定会找到令人热泪滚滚的,另一些有魂的字眼。“雷家坟山”的面积有多少亩,我没测算过,用它来种植,能养活多少人,我也没概念,但它确实安顿下了密密麻麻的难以数清的坟堆子。
在坟堆子里面,我奶奶的辈分是最高的,也差不多是最先入葬这儿的人(我爷爷比奶奶去世早,去世的时候原先的雷家坟山满员,这片坟山还不存在,借葬于一公里外的欧阳坟山)。在奶奶的坟墓四周,躺着的多数是我母亲那一辈的人,也有一些是我的同辈。也就是说,这儿的人们,全部都是母亲知根知底的人。与给父亲上坟一样,到了奶奶坟上,我们祭奠奶奶,母亲则点燃一大把香拿在手上,逐一地去给旁边的坟上香和烧一点纸钱。
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双腿变形了,走起路来总会左右摇晃,只见她到了任何一座坟头,上香和烧纸的过程中,都会跟坟里的人说说话。与她关系很好的,她会忆及美好的往事,说到动情处,就抬起手臂,用衣袖去擦眼泪;有些人生前与她关系一般甚至因鸡毛蒜皮的事儿交恶,她就会说:“×××,活着的时候,你倒是太可恶了……不过,今天我还是要给你烧点钱!”和我同辈而又长眠于此的人,死因不外乎两种:重病和喝农药。母亲到了这些人的坟前,边烧纸边说:“唉,老天怎么要这样对你啊,你留下的那两个儿子太可怜了。”或者说:“×××,我说你倒真的是个死脑筋,那么大一点屁事就想不通了,喝农药,不难受吗?”在奶奶的坟墓旁,有一座坟,死者只活了二十多岁,母亲从来不去上香烧纸,并且每年都是同一句话了之:“老子才不耐烦去理这个短命鬼,做什么事不可以,他要去吸毒!”……
去给爷爷上坟,步行,沿途都是坟墓群。地势忽高忽低,高处可以看见大兴土木的昭通城,在低处走,则感到明晃晃的人间不在了,自己只剩下了灵魂,走到了世界的终结处。爷爷死的时候,我只有四岁,他留给我的记忆只有一个:整天都坐在火塘边,敞着皱巴巴的胸膛取暖。即使是夏天,他也是冷的。听父亲说过,爷爷年轻时候所做的营生,就是以卖昭通酱养家,他挑着黄豆、辣子面等原料和荔枝河的水,从昭通步行十三天到昆明,在正义路的一家客马店里,现做现卖。那时候的荔枝河水,是做昭通酱的良好保证,爷爷挑着这水,走在莽莽苍苍的乌蒙山里,口干舌燥,却从来舍不得喝上一口。我有一首长诗,把荔枝河改名叫昭鲁大河,最后一段写的是1985年我师专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与家人和荔枝河告别时的感受,如下:
离开欧家营那年
他十八岁。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
一脸痤疮。身边的河水,清冽见底
几个捕鱼的人,看见他
撒下的渔网,忘记了拉
笑吟吟地跟他说话
他没有想到,那是昭鲁大河
最后一次清冽。人民的河流
神的宴会厅,十年之后,成了黑夜的家
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荔枝河已经不在了,我们记忆中的那条河,则像这一座座需要祭奠的坟墓,存在着,但已经远离了生活现场,是另一个世界,只有清明节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上香、烧纸、磕头。至于黑掉、臭掉的这一条真实之河,谁也说不好,它属于怎样的人们,从哪儿流来,又将流到哪儿去,它到底要流淌多长。

《我认出了风暴》
主编: 张莉
作者:雷平阳等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0
页数: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