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
出狱后,人到中年的广胜试图重拾生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拢回散落的家庭。可是儿子已经改姓、女儿早在多年前与爱侣私奔,而广胜的妻子,此时正在选秀节目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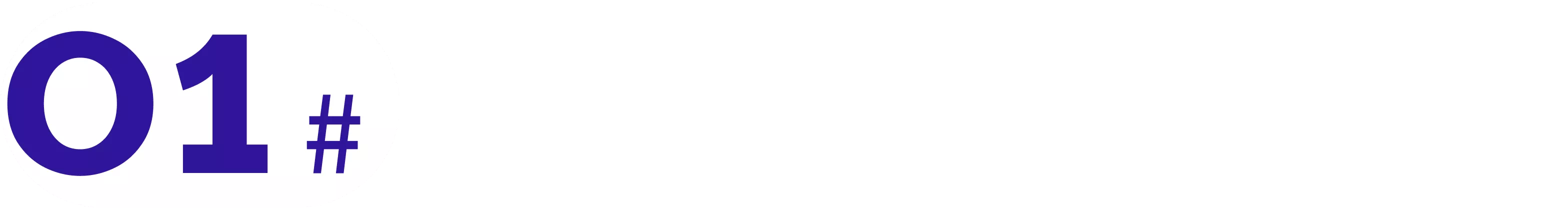
有些乐器天生就会哭,比如陶埙,原来是个酒罐,双手捧着喝,喝多了就想倾诉,于是多了几个窟窿,呜呜呜,就哭起来。你听声音,像极了带雪的北风在外面喊,一路从西伯利亚投奔而来,喊了多少家多少户,始终没有人收留它。
再比如二胡,上边锯着肉,下边借着蟒蛇的皮,就喊起了疼,一丝一丝的,低低地哭,忍着不敢喊,怕惹恼了“施暴者”。
这些“哭声”曾统治过我儿时的鼓膜,每当我从大街上撒欢归来,总有悲切的乐曲从隔壁的院子跨墙而过。那时我无法体会里面的情感,只是隐约觉着难受,它叫人想到葬礼,想到人埋进土里也会变成土。我听不惯这种悲凉,麻溜地爬到房顶窥视。演奏者闭着眼睛,眉头拧成死结,不是鼓着腮帮子在吹,就是拽着锯子样的东西来回扯动。我投一枚石子过去,他哀婉地“呀”一声,手随之一抖,整支曲子撕裂了。我妈看见我上房捣乱,大喝一声把扫帚扔过来。她不允许我打扰邻居的演奏。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些哼哼唧唧的声音,到底有什么意思,天天吹,天天拉,他自己听着不难受吗?没法子了,只得跟着他一再复习悲伤。这位邻居叫广胜,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7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天空刚下过雨,街上都是大大小小的水坑,上面浮着榆树叶子和破碎的云彩。我和弟弟正捡着被雨打落的知了,突然一个黑魆魆的影子倾斜过来。我们回头一看,是个瘦瘦高高的老头子,头发白而稀疏,面容憔悴。他先说话了:“小孩儿,你们是谁家的?”我弟弟傻乎乎地自报家门,我白了他一眼,叫他闭嘴。我妈这时正好出门,定定地看了几眼,突然睡醒了似地说:“你……你是广明他三哥吧?”老头子嘿嘿一笑。我和弟弟却撞鬼一样溜走了。传说里,广胜是劣迹斑斑的盗窃犯,早在我出生之前的1993年就住进了大牢。这次能提前出来,是因为得了肺病。他的肺已经像烂抹布一样了,指不定哪天就会憋死。这种病会传染,整条街的孩子都被大人警告过了,这会儿都躲在暗处老实躲着,亮着好奇的眸子。广胜徘徊了半天,才敲响广明家的大门。广胜的徘徊,让人想到溥仪回故宫老家的情景。这扇大门之内,承载了他所有的爱恨纠葛。他是娶过媳妇的,夫妻恩爱,育有一双儿女。媳妇兰荣是唱戏的角儿,听说有年庙会,村里请来一家有名的戏班子,十里八乡的人都赶过来看她,广胜自然也少不了要去看看这角儿。那时广胜的背不驼,一头乌黑的浓发,眉毛如剑,眼睛如星,颇有几分英武之气。据说兰荣当时正唱着《花木兰》,他见了兰荣的身段,听了她柔中带刚的唱腔,便挪不动步子了。直到落起大雨,台下的人七零八落了,他仍然不知避雨。兰荣对他有了印象。在歇工的一天中午,他们在集市上偶遇,她一眼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卸妆后的花木兰。
为了追兰荣,广胜跟着戏班子来回跑,日子久了,戏班子的人都认得他。琴师干脆教他学些丝竹乐器,为他搭个近水楼台。从此他们二人一拉一唱,日渐和谐,最终走在一起。兰荣是有名气的角儿,在爱情的滋养下,一开始还能过得惯苦日子。居家过光景,虽然显得笨拙,倒也能见到些心思在里面。家里的摆设都是细选的,吃喝也是农村人不多见的精致。夫妻俩跟着戏班子跑江湖,混口饭吃,日子久了便显出了穷底子。他不能为她买来华美的服装首饰,她的手在柴米油盐之间变得粗糙黢黑。也许想到了先前的纤纤玉手,他的心不落忍,一开始是在附近的电厂小偷小摸,偷些零碎的、没人在意的铁皮。
于是,兰荣用上名牌雪花膏,抹在脸上很香,抹在手上,温润如玉。
广胜被她的笑靥鼓舞着,慢慢地心野了。有一次,他想买一只银镯子给兰荣当生日礼物。趁着月黑风高,卸掉高压电线杆的螺栓,砸掉铁轨上的工字钢。后来的事,在传说里惊心动魄:
电线杆倒了,正好有放羊娃在下面,腿被砸断,邻近的几座村子停电……在县城的废品收购站,警察找到线索。广胜锒铛入狱,因为犯罪后果十分严重,被判20年有期徒刑。
这时候的兰荣仍不失光彩,在戏台上一开腔就能醉倒一片。她是心气儿很高的人,断没有在穷乡僻壤独自枯萎的道理。
很快,她就带着一岁的儿子离开,留下五岁的女儿茉莉。广胜在狱中收到老母的来信,大哭不止,几天不能下床。问他怎么了,他只幽幽地说:“家没有了!家没有了!”
从此,茉莉和奶奶相依为命。1998年,她10岁了,读四年级,因为家贫而早早辍学。每天在门前的菜地锄草,小手磨出水泡,呲牙咧嘴地哭,却没有人哄她。见到同学从门口经过,她倔强地背过脸去。
收玉米的时候最困难,她和奶奶一车一车往家推,道阻且长,不知流了多少汗,才将一季的粮食归仓入库。茉莉干起活来很卖力,奶奶说,玉米粜了以后就送她去上学。
可是就在粮食晒好之后,奶奶却被查出食道癌。奶奶看着新粮食煮的粥,怎么也喝不下,日渐消瘦,变成躺椅上的一根苦瓜。她看着茉莉,不停掉眼泪:
“唉,我走了你可怎么办?”
没多久奶奶就死了,死的时候没能闭上眼睛。
没有人肯收留茉莉。起初,她在几位叔伯家里轮流借宿,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为没有人哄她,她便忘掉了哭泣的本能,目光越发冷硬。
有次在大伯家里,堂哥的媳妇故意找茬儿,她觉得儿子的奶粉少了许多,便把矛头指向茉莉,非得说是茉莉偷吃了。茉莉和妈妈一样是心性很高的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受冤屈。她咬着牙回到奶奶家里,依靠自己种菜和奶奶留下的微薄遗产,过上果腹的生活。
广明见茉莉一个人生活,一直不忍心,想着法子给她提供帮助。当时,茉莉住在北屋,四叔广明住在南屋。广明的媳妇彩云不能生养,他们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
有次从外地名医那里归来,广明煮了黑乎乎的汤药给彩云喝,彩云叫苦不迭,呼啦啦把药汁全泼了,沮丧地说:
“算了吧,领养一个,骗自己说亲生的,一样养老送终。”
广明趁此机会,极力说服彩云收养茉莉。彩云抬眼看了看正在院中洗衣裳的茉莉,眼睛一亮,又往茉莉身后的北屋瞅瞅,眼珠子滴溜溜转了转,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她打起了北屋的主意,跟广明窃窃私语:“北屋在广胜名下,我们收留茉莉,那北屋……”没等彩云说完,广明瞪了她一眼,显得恕难从命的样子。彩云凶巴巴地说:“你不做恶人,我做!”
她走到北屋,盛开了一脸笑意,不提北屋,毕竟那是大人才能决定的事情。她跟茉莉套近乎:“妮子,婶子想跟你商量件事情,我们想认你当女儿,你看成不成?”
茉莉一直低头洗衣裳,对彩云说的话没有回应,手里的衣裳反复搓揉,搓得太狠,竟搓出几处窟窿。茉莉恨婶子,奶奶病重时婶子没有端汤送药;奶奶病逝后,婶子第一个表态不收留茉莉。现在却跑过来要收留她,实在让她费解。
彩云见茉莉不表态,暗中给狱里的广胜写了信:养活茉莉一直到出嫁,但是要用北屋的所有权做交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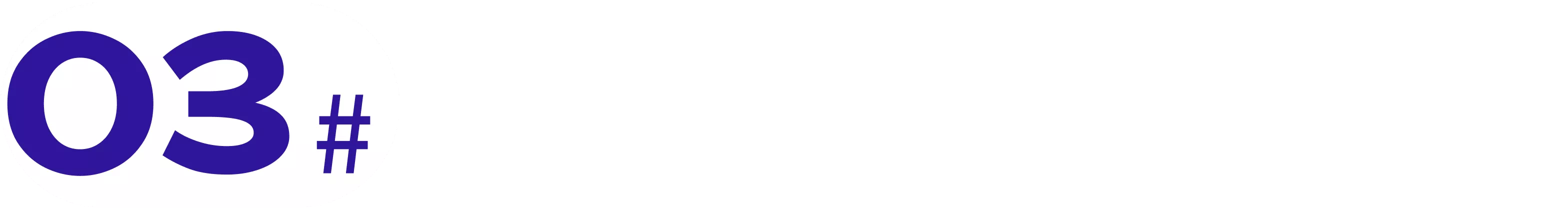
转眼来到2007年夏天,广胜因严重的肺病而获准保外就医。他灰突突地敲响广明的家门。彩云开了门,脸上一万个不乐意。
她勉强腾出一间小屋子,供广胜居住。那间屋子阴冷潮湿,显然不利于养病。但是作为一名寄居者,广胜没有底气为自己发声。
1999年,广胜在信纸上摁下一枚手印,拜托彩云照顾茉莉。那封信彩云一直收着,现在广胜回来了,它成了击退他的法宝。北屋朝阳,温暖敞亮,而且有他和兰荣的美好回忆,可惜这些都不再属于他。
就在他出狱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村又停电了,左邻右舍走出家门,摇着扇子,闲话家常。我们小孩子玩着捉迷藏的游戏,疯起来根本顾不得满世界的蚊子。
月亮明晃晃的,照得万物轮廓清明。突然传来一声撕布的声音,像试探似的,紧跟着就有河水潺潺缓缓流过耳膜。那声音好像一个寡妇在低泣,凉凉的,浸得人起了鸡皮疙瘩。
大人们说,这是多年不曾听的二胡曲子,早些年,逃荒的会在夜里演奏,第二天要挨家挨户讨粮食。乐曲越往后越凄怆,大人们听不惯了,都在问,这是谁吃饱了没事呀?彩云怏怏地没话说。
广胜尽量小心翼翼,演奏乐曲都是关门闭户。饶是如此,彩云还是给他脸色看。他每天都在咳嗽,吐的痰里面带有血丝。
彩云眼睛很尖,一旦发现地上有可疑的痕迹,就指桑骂槐,说他随地大小便。广胜被气得够呛,但没有办法,只能忍气吞声。
广明想给哥哥找点事情,免得他一个劲儿吹拉弹唱,突破彩云的底线。于是他给他哥哥装了一台电视机,只能收到两三个频道。
有了电视机,广胜确实不再演奏曲目。大家都在为耳根清净而暗自庆幸。世界上的苦难何其多,每个人都对他者的苦难缺乏想象力与同理心。各自忍着,把苦楚锁进胆囊才是正理。
这下好了,世界的口子被堵住了,每一只陶罐都完好无缺,再也不会有谁的苦水泄露出来。就连彩云都对广胜露出了笑脸。
电视上,一个戏曲争霸节目突然火了,那时候VCD刚开始流行,手机还是遥远的事物,很多老年邻居都还健在,戏曲的传唱度还是很高的。加上节目的幸运观众奖十分诱人,大家的热情自然水涨船高。
每周末,大家都聚在一起看比赛,紧张地等待评委们打分。到了挑战赛,突然上来一位出类拔萃的选手,整条街的人都被她震撼到了。
她的身段依然是年轻时灵动的样子,眼睛不改青春时闪耀迷人的光彩,声音圆润如珍藏多年、保存良好的唱片。
很多人一眼认出兰荣,这么多年过去,广胜已经萎颓不堪,兰荣却被时光的刻刀遗忘了。毫无悬念,兰荣获得了本场的第一名。
热闹过后,大家都想起广胜也有一台电视机。
彩云格外注意广胜的举动,不是担心他受不了,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广胜却没有什么异样,只是有天下午步行到镇上,但很快便回来了。大概没有看到这期节目吧。
直到秋明(我们这儿把七月十五叫作“秋明”,与清明类似,也是要上坟烧纸的)。广明喊广胜去给娘烧纸,他不去,拿着一封刚收到的信暗自落泪。后来听彩云说,那是兰荣回的信。
广胜寄出去的是他们的第一张合影,在那年的庙会上,照相还是一门很火热的生意。本来他以为兰荣不会回复,收到复信的时候,心剧烈地跳动。
他抖抖索索打开,里面不是一封倾诉衷肠的信,而是剪掉一半的照片,只剩下昔年靓仔广胜。
她的意思他懂,要把所有的故事一笔勾销。
陈家的祖坟树木林立,广胜下午带着陶埙去看母亲。他的肺已经很脆弱,可还是吹得没完没了,直到黑夜下垂,乌鸦都不敢回巢,绕树盘旋,叫声凄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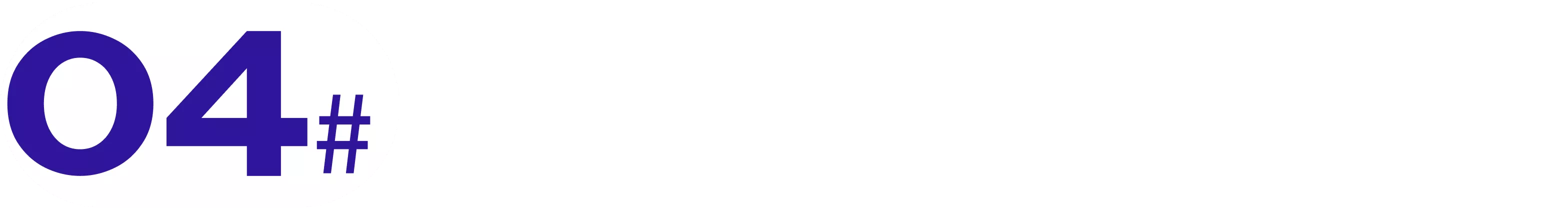
广胜一直被彩云视为眼中钉,他想找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比如看守仓库什么的,以免被当成混吃等死的废人。可是他这身体不行,没人敢用他。
为了让彼此都好受些,广胜主动提出要搬走。他在狱中做工,编藤椅,制假发,每天都有微薄收入,出狱时竟积攒了一小笔资金,正好可以用以租房子。
位于我们家与广明家中间的院子很久没人居住了,广胜给户主打了招呼,承诺给人家修葺一新,并按月缴纳租金。
院子荒草及腰,广胜费了好大力气才拾掇利索。看着空空如也的院落,又有些后悔,应该留些草木来填塞这巨大的荒芜。他把屋子用白灰抹了一遍,夜晚不需要开多大的灯,便可以光照出白亮亮的效果。
可是单调的颜色,将他的无望衬托得明明白白。一个人的时候不敢唱戏,空落落的,屋子里有回声。
他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搬进去,制造拥挤的假象。而镜子绝不敢往里放,有时候不经意地一抬头,他会被陌生的自己吓到。
好在有二胡陪着他。在别人手里,二胡有兴高采烈的时候,我在电视上就听过《赛马》之类的曲子;到了他那里却只剩下恸哭。
有次我正在写拼音,实在忍不住那份沉郁,一个翻身就上了房顶。我学猫叫学驴叫,想着法子干扰他。我妈毫不客气地扔扫帚过来,我做个鬼脸溜走了。
后来,我妈严肃地说:“别人能抽烟能喝酒,广胜只能用二胡解闷,你就不能行点好、积点德?”
我把妈妈的话当成耳旁风。等生出愧疚之心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知道他惯常拉的两首曲子分别是《江河水》和《二泉映月》,都是极尽悲凉的调子,孟姜女的悲苦恰似一江东流水,阿炳大半生的凄凉在月光下变得伸手可摸。
可是当时,我们小孩子都觉得广胜很怪,把他和村子里的其他几位失常之人列为一类,经常在他家门上涂鸦。他从来不恼,反而对我们抱有莫名的好感。
秋天到了,他帮广明砍玉米秸秆,顺手拣几根嫩绿的秸秆给我们当甘蔗吃。有时也带回一串蚂蚱,在院子里烧熟,让我们拿回去做鱼饵。我们却不为所动,仍然对这位病人敬而远之。
他与大人们的交往同样以失败告终。大人们一起干活,出一身汗,到了晚上抽烟、喝酒,打牌。这些他都做不来,自然会遭受冷遇。
我们看见他播下麦粒,每日操持,逗引绿色去覆盖苍老的黄土,他在院子里种上当季蔬菜,窃取植物的生机来抵对活着的苍白。
小白菜和萝卜缨子在秋日照耀下长势喜人,一畦畦,一垄垄,像写给生活的投名状。
可是呢,我们仍然时常听到乐器的哭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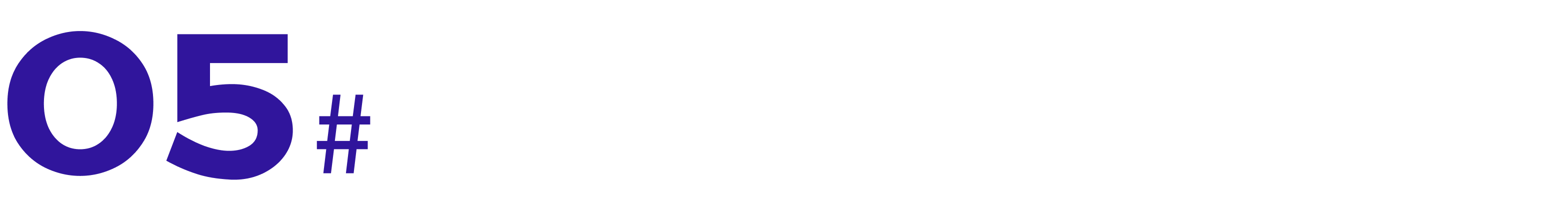
广胜出狱之后,最想见的人就是儿子。在向街坊的孩子示好的时候,他曾有好几次误喊了“冬冬”这个名字。我们学他的语气跟着喊,咯咯地发笑,不曾关心他落寞的表情。
据大人们说,冬冬已经十五岁了,在很远的地方读初中。广胜专门去那里找过他,兰荣不让他进门,这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不能接受的,是冬冬改了名字和姓氏。
他在冬冬放学的路上偷跟着,见他长得像小树苗似的,忍不住笑意。可是冬冬对他已经没有印象了。从1993年到2007年,他缺席十四年,时光如潮,将沙滩上的痕迹冲刷干净。
冬冬无意间发现身后的老男人,父子对视的一刹那间,他从儿子陌生而愠怒的眼神里确认了自己的无助。
他记得冬冬学会走路那天,院子里落满了鸽子。它们对着地上散落的粮食不停“作揖”,点头如捣蒜。一阵“咕咕”声,引得冬冬跟着叫喊。
冬冬想要靠近这群小精灵,于是世界跟着摇晃起来。落日抹红的大地上,一个小小的孩子抬着胳膊,趔趔趄趄地走向自己心仪的目标。
他偷跟着长大后的冬冬,一起来到了广场。偌大的广场也有无数只鸽子点缀其间。冬冬又一次抬起胳膊,一路飞跑。时光短暂地摇晃,广胜险些以为自己回到入狱之前。
他爱上了这样的跟踪,一连几天乐此不疲。可惜最终被兰荣发现,兰荣让现任丈夫出面阻止。在人家的地盘上,有无数种手段可供选择,最让广胜害怕的手段是冬冬亲口说出了一个“滚”字。
他不相信冬冬会如此绝情,一直幻想着能当面向儿子道歉,然后两人尽释前嫌,抱头痛哭。可惜一切都止步于幻想,儿子根本不相信他们是亲人。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村子,好几天都没有声响。二胡与陶埙已经不能解愁,最浓重的悲痛是没有声音的。后来,广胜制作了弹弓,每当屋脊上落有鸽子,他都发射石子。中弹的鸽子砸在地上,声音轻得比没有还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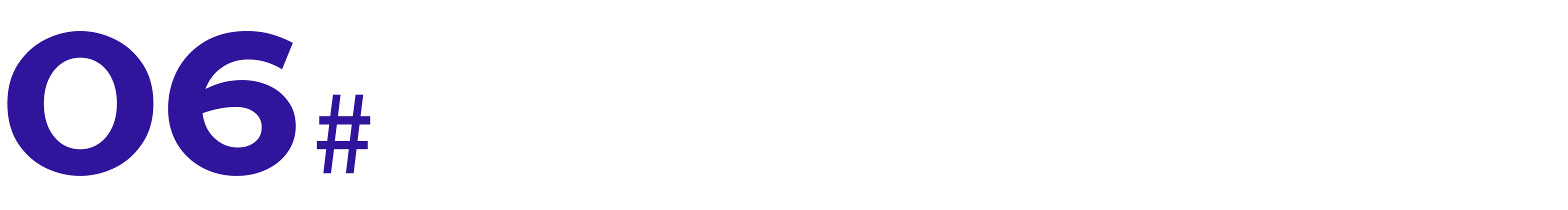
广胜放弃了对儿子的思念,好在还有茉莉供他挂念。可惜,他并不知道女儿对他怀恨在心。
1999年,彩云写信到狱中商量收养茉莉的事,广胜在回信中同意把北屋送给彩云。彩云马上把茉莉的东西搬到南屋,提供饭食。
茉莉不知道写信这回事,更不知道其中的协议。她对彩云的示好充满疑惑与排斥,又把东西搬回北屋。
彩云志在必得,用新衣服、好吃的零食,甚至上学的书本费去诱惑茉莉。当时茉莉11岁,极度渴望母爱,很快上钩了。
没过多久,彩云便对茉莉开始冷淡,并没有供她去读书。茉莉随着广明去山上敲石头,头天晚上爆破好的石头,在锤子的催逼之下进一步分裂,最终进到石灰窑接受烈火炙烤。
茉莉稚嫩的手伤痕累累,她受不了这份苦。后来又去贩卖蔬菜,半夜起来去市郊的批发市场,天亮前带着星光和露水归来,每次运输都会让体力透支。她永远忘不掉夜路上呼号的风,像鬼一样,一直哭一直哭。
到底是骨子里流着母亲的血,2004年,16岁的茉莉在庙会上认识了唱武生的浩峰,他生龙活虎的做派猎取了茉莉的芳心。
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浩峰一直是茉莉的精神依靠,她渴望浩峰带自己离开苦海。可是要彩礼的时候,彩云狮子大开口,浩峰根本无法满足,他们只能选择私奔。
2008年,茉莉要回来迁户口了,迁到浩峰的老家,然后去民政局领证,名正言顺地做夫妻。
广胜很激动,他有很多年没见过茉莉了,记忆中,她还是一个小女孩,不敢想,一眨眼就儿女成双了。他盼望茉莉能早点过来,想到外孙绕膝的情景,他忍不住笑出了声音。
在等待的日子里,他甚至学会用牛头埙吹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在他演奏过的所有曲目中,只有这一首是欢快的。
彩云的小算盘又噼里啪啦打起来。她极力邀请广胜搬回北屋,广胜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了让茉莉开心,他愿意表演家和万事兴的剧目。
茉莉终于回娘家了。一家四口齐齐整整地走过来,广胜快跑着迎上去,泪水模糊了双眼。他不知道自己正奔赴一场巨大的失落,当他满怀深情地迎过去的时候,茉莉赶紧把孩子往身后推。
广胜定在原地,张开的怀抱扑了一个空。
他忘了,他有传染病,笑容凝固在脸上。
茉莉并没有声泪俱下地倾诉思念,父女重逢,竟形如陌路,她甚至连一声“爸爸”都没喊。广胜准备的一箩筐贴心话,全部化作烟尘,一句也说不出来。巨大的陌生感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快窒息。
最高兴的是彩云,比见了亲女儿还要开心。她让出大床铺给茉莉一家睡,还准备了一大堆零食给孩子们吃。茉莉并不领情,她冷冷地回应着一切。她不可能忘记,过去的颠簸与辛酸都是彩云一手造成的。
彩云很快宣布了她的计划:趁着茉莉回来,替她补办一场婚礼。
她说,看着茉莉出嫁是她多年未了的心愿,希望茉莉能理解当婶婶的一片苦心。说着说着还抹起泪来。茉莉冷笑了几声,她明白彩云的心思,于是质问:“难道别人的份子钱,比我们的脸面还重要吗?”
这次回来迁户口,她顶着巨大的压力,怕别人提起私奔这一茬,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根深蒂固的乡村伦理。而彩云的计划,等于抓着她去游街示众。
彩云使出杀手锏:“我养活你五六年,你拿什么回报我?彩礼省掉了,份子钱还不让收?”
茉莉意识到,彩云还是那个彩云,一点都没有变。她说,北屋是奶奶留给她的,这么多年叔叔婶婶都霸占着,也该奉还了吧?
这时,彩云拿出那封摁有手印的信,那是茉莉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封信。多年以前,这座房子已经易主了。茉莉的气焰突然就熄灭了,她去找广胜质问:“你有什么资格摁手印?你问过我吗?”
广胜哑口无言,除了落泪什么也做不了。本该喜气洋洋的重逢,就此不欢而散。茉莉一家不告而别,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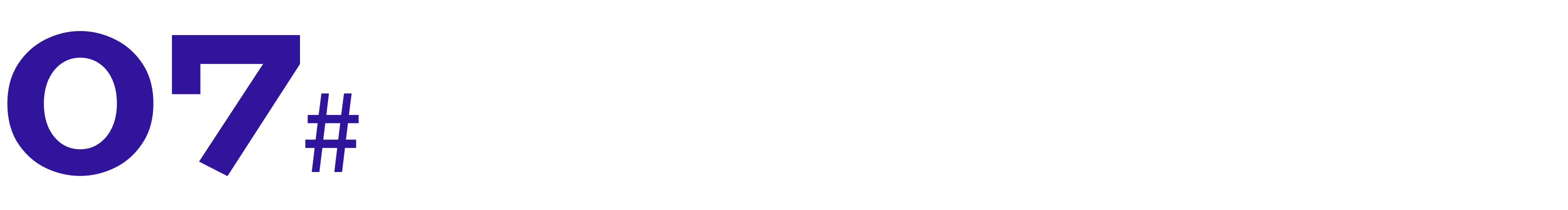
广胜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的次数明显多了。院子里的蔬菜已经没有心思去打理,天空中的鸽群忽然间恢复了原有的茂盛。二胡的嗓子喑哑不成调子,乐曲的碎片与咳嗽交替出现,已经很难辨识出真实的表情。
冬天来了,一场雪接着一场雪,万事万物都被覆盖住。一张白纸铺展开,等着人们用想象力在上面挥毫泼墨。幸福的人们想着开春的事情,他们知道雪下面涌动着无尽的地力和希望。
积雪蓬松,吸收噪音,天地间安静下来。很多人觉出了耳根的寂寞清冷,他们忽然想起很久没有听见广胜的乐曲了,便有人去院子里寻他。
他已经不能下床了。人们看见他两眼无神,茫然地看着屋顶。
屋子里很冷,每个人都像是落进了冰窟窿。人们受不了冰凉,说几句宽慰话就走了,都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面。雪化的时候,他的坟头爬上野草,白色的荠菜花,还有黄色的蒲公英花随风摇曳,像是一些坠落中的泪滴。
村子里彻底安静下来,再也没有二胡和陶埙的哭声。
多年以后我长大了,来到繁华的都市,每当夜深人静时,都会忆起广胜演奏过的乐曲。它们藏在灯火不及的角落,替失眠的人默默哭泣。
直到这时,我终于理解了广胜的孤独,它如此浩大,像夜色笼罩下的一切。
- END -
作者 | 杜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