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携程到红黄蓝,除了痛心,还是痛心,特别痛心。
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我的妈妈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我妈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耽误掉的一代。所以,当她拼死拼活考上了师范,拼死拼活进了幼儿园当老师,她特别珍惜这份工作,也很热爱。
我妈当年上班,每天下班都精疲力尽,我和她说话超过三个字以上,就会被回答:
“我们来玩个游戏,看看谁能够一直不说话好不好?”
但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就会特别喜欢我妈妈。一直到他们上小学,上中学,遇到我妈,都会特别兴奋地打招呼。
一直到退休,我妈都没评上什么一官半职,但是她挺开心的,因为她教过的那些小朋友们,都很爱她。
各种老师里,幼儿园老师一直是最被轻视的。工资低,待遇也不高,我妈做了一辈子幼儿园老师,听力受损,也没有人觉得这是工伤——包括她自己在内。
而幼师的社会地位也一直没有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那样高,幼儿园也没有专门的职称体系,只能遵从小学的体系,国家也没有出台面向学前教育的重要法律。
我妈曾经回忆,当年她们幼儿园来了好几个优秀的年轻老师,都觉得自己屈就,没过多久就转行,“觉得自己和高级保姆差不多”。
在幼儿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幼儿园的老师们,依然被认为“和高级保姆”差不多。
这个观点,其实贯穿了中国人的心理,整整一百年。
而在几十年前,有一个女生,站出来说:
“幼儿园老师,绝不等于高级保姆。学前教育,远远比你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这个女生,叫卢乐山。

* * *
卢乐山出生在一个教育家庭。
她的祖父卢木斋幼年家贫,只好每天到书店看书,书店老板有时见他可怜,就允他晚上把书借回家,他连夜抄写,为的是天明可以送回。这段经历,让卢木斋发愿,要广办图书馆,现在的天津图书馆前身,就是卢木斋创办的直隶图书馆。卢木斋后来当了官,被李鸿章看上,先调任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王士珍、段祺瑞等都是卢木斋那时的学生。后来,他又开始创办木斋系列学校。

▲卢木斋的曾孙卢元恺和木斋中学的同学们讲解
卢木斋的亲家叫严范孙,这个殿试二甲第十一名的进士,一辈子最反对科举,而崇尚教育救国,他办了一所学校,叫南开;在学校里,他设立了一个范孙奖学金,资助了许多学生,其中一位,叫周恩来。据说,当时周恩来远赴法国时,有人举报他是共产党,要求停止资助,严范孙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仍然继续资助奖学金。

祖父和外祖父盛名在外,对于卢乐山来说,印象却大不相同。
“外祖父喜欢跟孩子们玩耍,有时也教我们娃娃游戏,时不时还编个歌谣,弄个九九消寒图,讲些故事。”不过,祖父却是自己的童年梦魇,因为祖父喜欢训话,说到激动处,还要拿拐杖“咚咚咚”敲地板。每次被祖父叫去训话,卢乐山都要提前和保姆说,我去一会儿,你就来找我,说我妈找我啊。这个方法颇为奏效,可即使如此,卢乐山说,小时候,只要家里人说:“祖父来骂你了!”她立刻张嘴就哭。
卢乐山后来还把这段经历讲给学生们听:“我反思这段岁月,切身地体会到恐吓和吓唬对儿童教育是最要不得的。”
卢乐山这个名字,是她自己上小学的时候改的,她的原名是卢碧霞。“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卢乐山说自己太笨,做不了“智者”,但只有怀仁爱之心,做一个“仁者”,大约还有希望。
* * *
卢乐山和幼儿教育的缘分,在上一辈时就开始了——她自己所在的幼儿园,是外祖母开办的严氏幼儿园,老师是表姐严仁菊和严仁清,她们幼年时曾在严氏蒙养园学习,后又同进美国教会办的北平贝满女中附属幼稚师范,学习美式的幼儿教育。
1934年,17岁的卢乐山考入燕京大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卢乐山犹豫了。她找到了燕京大学心理卫生课教授美国人夏仁德,和他说起自己的困惑:她觉得自己依赖性很强,遇到事情容易退缩,恐怕不适合日后的教育工作。
夏仁德却认为,卢乐山非常适合选择学前教育专业,因为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不会有依赖心理,和幼儿相处可以锻炼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增加自信和勇气。
这番对话,让卢乐山决心,把自己这一生,都奉献给学前教育。
据说,卢乐山曾经在大四时搞了一个创新,她看到学校外的孩子整天闲游、打闹,身上很脏,还会说脏话、吐口水,更糟糕的是,“家长对这些小孩一般不管,有时见小孩闯祸了,就啪啪打两个耳光,轰开就是了”。卢乐山觉得,燕京校园内外,一墙之隔,却简直是两重天地,她和同学一起开办短期半日制幼儿园,劝说贫苦人家的孩子来上学,每天学习两个半小时,唱歌、折手工、做游戏、洗澡、吃点心……
来的孩子很少,来了几天,回去了好几个。
卢乐山反思说,自己当时心气儿高,对待孩子,都是用最高的要求,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跟不上。“孩子们其实很敏感,意识到自己没办法跟上,立刻就不想学了。”

▲燕京大学学生生活促进会合影,正中间为司徒雷登,三排左一为卢乐山。
卢乐山的一次实验没有成功。但这并没有阻碍她,大学毕业时,许多人问她,将来打算去做什么?她说,要去幼稚园工作。
朋友们都很吃惊:“当幼稚园教师?那是保姆干的事。你这大学生岂不是大材小用?”
卢乐山的回答是:
>> 幼儿教育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不仅仅游戏是教育,小孩吃饭、睡觉、洗手都是教育。
幼儿教育是一门科学。
而卢乐山打算用一生来实践这门科学,毕业后,她先后在家族的木斋幼儿园和协和幼儿园工作,并在1940年报考燕大研究生,研读幼儿教育。

* * *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的早晨,正在读研究生的卢乐山和同学们被聚集到大礼堂,她们得到了一条消息:
燕京大学暂时关闭。
卢乐山说,自己几乎都哭了出来,每个人都被命运裹挟着,陷入历史的洪流。当时,她只是以为自己就此失学,却不知道,校长司徒雷登等将被关进集中营,一直到1945年才获释。
三年后,当听到燕京在成都复课的消息时,卢乐山第一时间和同学约定南下,她们走了一个多月,“从北京坐火车到徐州,从徐州坐“架子车”到商丘,又坐马车到了洛阳”,好几个大家闺秀的身上已经开始长虱子。她们的食物是白薯,偶尔吃到一点花生米,就足够雀跃半天。进秦岭的时候,还曾经出了事故,有同学遇难。
终于过了剑阁,经过广元,入川了。
卢乐山到了成都,发现复校后的燕京没有教育系,所以特别请了四川大学教育系的蒲主任指导论文。

1945年6月,卢乐山完成了论文,获得硕士学位。也是在这一年,她结婚了。
>> 我和雷海鹏是在燕京大学本科阶段认识的。后来家里人知道我和雷海鹏好了,就创造机会让我俩多见面,也就算谈恋爱了。1945年夏,六月份我研究生毕业,八月中旬抗战胜利,八月下旬我们俩就结了婚,那是我人生中最热闹的一个夏天——卢乐山
因为环境有限,结婚的房子是借的,连床也是借的,卢乐山的好朋友茅爱立特别给她打电话,说“你帮我做一件衣服吧。”卢乐山不明所以,稀里糊涂照做,说要白色的,绣龙凤,做好了,茂爱立说:“这是我送你结婚穿的。”

结婚当天简单准备了茶点,不收礼,也不请客吃饭,临到仪式,忽然发现只有结婚裙子,没有婚纱,后来还是园长的加拿大朋友,找来一块白纱,然而大家都感叹:“好久没看到这么像样的婚礼了。”
当时抗战刚刚结束。

1947年,卢乐山和丈夫分别申请到了多伦多大学的奖学金,决心去加拿大深造,临别前,卢乐山最舍不得的是树基儿童学园的孩子们。据说,那天大家开了个欢送会,孩子们给卢乐山表演节目,最后让她上台讲话,她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还是丈夫雷海鹏代为致辞,孩子们一直送她到成都东门外:
>> 我上了车,透过窗户看着她们,汽车声音一响,她们就“哇”的一声,全哭了。我后来想,那真像人进棺材一样,棺材板一盖,大伙就“哇”地一下全哭了。
——卢乐山口述史
* * *
1950年,得到自己怀孕的消息,卢乐山的第一反应是——
我要回国。
为什么要回国?
后来无数人问她这个问题。
卢乐山说,你们不懂,那时候的中国人,总是觉得,我和我的孩子,都是中国人。我们拼了命,要回到故土,那是中国人的本质。
漂洋过海回到北京,正打算好好待产,却接到了来自北师大的电话,卢乐山后来回忆说:
>> 他们一下子就问我:你有没有收到我们寄给你的聘书?
我说,没有,我早就离开加拿大了。
他们说, 哦,我们聘请你做教育专业的教研组主任。
我说,这怎么行?我还大着肚子呢!
——卢乐山在纪录片《爱的教育》
这一年,她35岁。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新,赵珩先生回忆,当时北京比较先进的幼儿园,都是教会学校。当时大家的想法是,穷人家觉得“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所以不肯花那个钱去上幼儿园,觉得没有必要,在街上玩就可以了。而有钱人家也不愿意送孩子去幼儿园,只有新派家庭和父母都要工作的,才会送孩子去幼儿园。
赵珩先生差点也不能上幼儿园,“家里当时有好多佣人,也有空间玩,我母亲也不上班,完全可以自己带”,但他的母亲希望他能过一过集体生活。

▲卢乐山全家福
卢乐山面对的社会环境,对于幼儿园仍然是“高级保育所”的概念。所以,一回国,卢先生就开始制订一套针对新中国的学前幼儿教育教材。她得到了丈夫的无条件支持,他们一直住在师大,雷海鹏每天骑车去协和医学院上班,以至于后来过了很久,钟敬文先生一看见卢乐山,还总问:“你爱人还骑车上下班么?”
但是教材还没出版,问题来了。
苏联专家首先站出来指责,说卢乐山的东西太“资本主义”。
只好删删删,一边删,卢乐山心里想,这有什么资本主义呢?
苏联专家所说的资本主义幼儿教育,赵珩先生的回忆里也出现过,那是1955年圣诞节,老师让他们围着那棵大圣诞树大家一起走圈唱歌。“不论孩子家庭贫富,大家都要拿出一件礼物,有的孩子家可能花了很高的价钱买了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外面拿花纸包好了,或者是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小玩意儿,也要拿个盒子用花纸包好,到了幼儿园以后,都交给老师,老师放在一起,最后每个人抽签,由圣诞老人发给大家。孩子们对交换回来的礼物贵贱并不在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又抽回来的,这是我们圣诞节必做的一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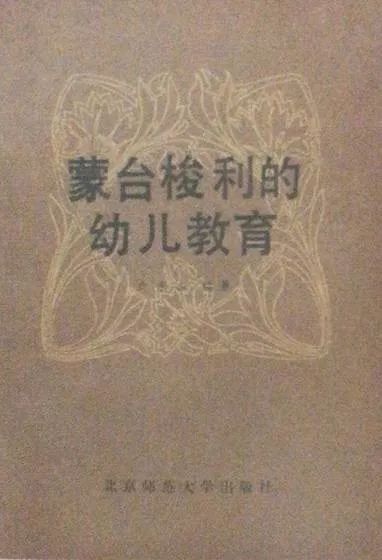
等到删改差不多,又出问题了。因为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成了苏联修正主义,又要删删删。
文革中,卢乐山的那一套被继续批判,她曾经回忆,自己当时做了一个小实验,研究怎样帮助小朋友有效地洗手。事先将洗手分为几个步骤,要求幼儿按一定的顺序完成已定的步骤,经过多次练习,按心理学的讲法“使之成为动力定型”。形成习惯后,孩子们会主动迅速地按步骤完成洗手的要求,而且洗得很干净——这个实验在“文革”中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卢乐山说,2003年非典,宣传卫生洗手的程序和方式,各处水龙头前都贴了洗手的步骤图。师大幼儿园的老师骄傲地说,他们不用推行,因为他们早有“卢先生留下的底子”。
卢乐山说,自己能够躲过一劫,是因为自己胆子小,在搜查之前,就把长辈们的字画瓷器统统“自我毁灭”,但她也目睹了一层楼,几个月就跳下去三对夫妇,“那时身边的人,今天看到这个跳了,明天看见那个死了,那种感觉真叫朝不保夕”。
* * *
1987年,卢乐山办理了退休,她的老同事启功给她写了“教永春长”,这四个字她非常喜欢,一直挂在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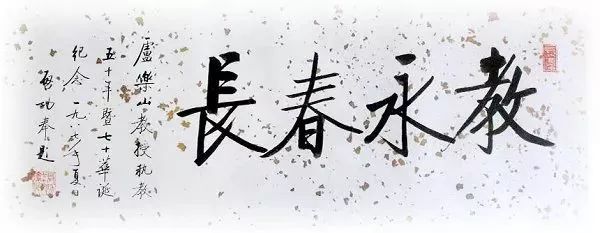
但她仍旧关注幼儿教育,并继续致力于幼儿教育的研究。
她坚决反对幼儿园的“小学化”。
“检验孩子能否升入小学的标准,应该重在考察孩子语言发展得怎么样,说话表达是否准确清楚,是否有想象力,而小学教师常常对小孩子考知识性问题,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卢乐山认为,如果让孩子提前学习了该学的内容,到了小学后反倒觉得学习没意思,老师教的都会了,这样容易让孩子养成不专注、不爱听讲的习惯,最后的结果只能事倍功半。
她坚持认为幼儿园老师应该少说教,多示范:“比如孩子吃饭,老师在周围站着,一边下指示‘你这样,你那样’,说教比较多。在美国幼儿园,老师们要对某个小孩说些什么,都走到他跟前轻声和小孩说。我们的老师总是在门口就大声地拍着手,高喊着‘注意啦注意啦’。”

她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按照“科学保育”的方法,什么时间吃、什么时间睡,到了什么时候应该自己睡,全部安排好:
>> 吃饭时我给他一个小桌子,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时间,我摆上他该吃的东西,碗、勺、喝水杯都摆上,东西他都得吃完,也没什么可挑。万一有时候没能吃完,我就让他留着下顿也要吃完。我们大人和保姆从来不吃他剩下的,也不许他有剩下饭粒。
睡觉之前,也要和幼儿园一样,脱了衣服,在床前摆一小凳子,把衣服叠好了摆好再睡觉。日常生活这些事都按照一定的规定办,他也照着做了,也没遇到什么抵触。
在生第二个孩子之前,我就给雷思晋做思想工作。我说:“既然你希望要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那你一定得照顾他。他刚生下来,什么都不会,就知道哭,你是大哥哥,比他大比他懂事,应该关心他照顾他。”我发现有些家庭第二个孩子来了,第一个孩子就嫉妒他,原来就他一个人,想怎么就怎么,现在来了另一个,分享了他的权益和母爱。我爱人雷海鹏说,他们兄弟俩差七岁,大的已经懂得照顾小的了。有一次弟弟思政要吃冰棍,我爱人给了两人份的钱,可是思晋就买回了一根冰棍,他给弟弟吃,自己不吃,我们觉得这种关爱和品质很难得。
卢乐山认为,对待孩子,要尊重,也要研究,但归根结底,当然要有爱:“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还是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子,而不是孩子本身可能成长的样子。”
大家都说,卢先生对待孩子,永远都是笑眯眯的,说话和颜悦色,慢条斯理,很少见到她会发火。
她喜欢一切新生事物,爱玩ipad,喜欢玩电脑的“蜘蛛纸牌”,还会用微信视频,和美国的孙子们通话。
2017年6月,卢先生100岁了。她微笑着说:
上次95岁时他们给我祝寿说我要活到100岁,
我现在真的活到了100岁。
很知足。
2017年11月9日,卢乐山先生去世。
参考资料:
赵珩,《民国时期的小学和幼稚园》,《南方都市报》2014年10月28日
卢乐山口述,罗荣海整理,《卢乐山口述历史——我与幼儿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