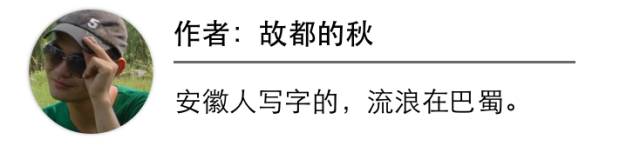图 | VCG
提起老水井的“出捻子”,方圆几十里一听就头皮麻。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说白了,其实是全村男丁上阵的集体械斗。通常,只有四种情况才会出捻子:抢女人、抢地、抢水、嫁出去的闺女在婆家被欺负死了。
前言
母亲看了翟欣欣骗婚的新闻,掰着手指头计算老邻居圣庭爷(安徽地方方言,泛指男性长辈,如父亲、叔叔)的死亡时间。也只有这样的新闻,才会让母亲记起这位老邻居。
20年来,我讨厌与酱油有关的食品。这是圣庭爷死给我留下的阴影。因为,我永远忘不掉那个画面:一个僵硬的男人,面部和胸前布满了红黑色的血迹,就像风干了的酱油。身边一个只有五岁的女孩,嚎哭着叫爸爸。
在圣庭爷身边嚎哭的女孩叫环环,是他的养女。她是谁家的孩子,没人知道。
23年前的腊月,在交了4000元的“彩礼”后,圣庭爷从蚌埠火车站领回来一个30来岁的女人和一个女婴。女婴刚满一岁,她的胳膊瘦得像秋后剥了皮的麻杆。这时候,圣庭爷已经快50岁了。
女婴是环环,女人是王赵氏。
这对母女来的那天,父亲咬着牙送去了50斤大白菜、半袋白面和一捆粉条。那本是准备用来过年的吃食,母亲心疼极了。
那时候,距离京沪铁路和两淮煤矿均只有20公里的老水井,是省里有名的“盲流”村。数百亩的盐碱地和几乎每年打照面的洪旱灾害,只给这里留下了讨饭用的花鼓灯和成打的光棍。
除开少数手艺人和吃公家饭的教师、村医,刚刚入冬,多数男人会裹着褡裢结队南下。或乞讨,或打短工。若是运气不好,来年春季,一家人便只能吃两顿糠了的红芋。留下的女人,多半要睡在粮囤边或者猪圈里守着——那是小偷们最爱的去处。
领回女人前,圣庭爷已经把青春挥洒在劳改农场。人贩子拿走的“彩礼”,差不多是他出狱后的所有积蓄。
听到母亲抱怨,父亲瞪着眼:建房子人家让了两尺地,他娶媳妇把粮食和猪圈卖空了,给这点东西能穷死你?
接下来几天,我每天都去圣庭爷家。新媳妇用粉条做的包子好吃极了。还有,她腌制的辣白菜,也比母亲做的水煮白菜强多了。
一个星期后,我再也不去了。
● ● ●
那天,新媳妇被捆在院子里的栎树上。圣庭爷的五弟圣唐爷,把一根赶羊鞭递给圣庭爷,说:“狠狠地打,打够!”
“你!”圣庭爷有点不情愿。
还是圣唐爷亲自出了手,不到半支烟的功夫,新媳妇的碎花袄露出了棉花,有点的地方,能看到青的紫的皮肤。
“好啦!”圣唐爷的小脚女人霞奶奶挤开围观的人,想保护自己的妯娌:“真牲口!她死了孩子谁喂养?”
见到有人解围,新媳妇开口大哭。
“她拿了卖羊的钱。”圣庭爷蹲在地上,痛苦地抱着头。
“你兄弟缺脑子,你也缺吗?这么冷的天要冻死人还是要打死人?”霞奶奶从屋里摸出一条凳子。她爬上去,要给新媳妇松绑。
“都走吧!”圣唐爷丢了鞭子,冲着围观的人吼开。觉得没戏可看,人群很快散了。
“去叫你爷(爸)来一趟,带上家伙事。这是我给他的。”圣唐爷冲我招招手,丢给我一包渡江烟。
我知道,父亲又要去帮人算账了。也难怪,圣唐爷和圣庭爷是“黑五类子弟”,连一天书都没念过。
那晚,老水井飘起了大雪。雪盖严实路面的时候,父亲才回家。
“这女人太讨厌,教训她也该。”父亲让母亲热了晚饭,嘟囔着嘴说,圣唐下手也太狠了,女人的胳膊都打麻了。
“也不怪别人,圣唐说她偷了卖羊的800块钱。圣庭又说他刚借的过年费没见了。”父亲顿了顿,又说,“霞婶子从来不碰钱的人,外人又没来过。这肯定是外地女人干的。”
母亲不可置否。父亲直摇头:“这女人嘴里没一句实话。你不知道,问她家在哪,她说了三个地址,有河北的、四川的,还有陕西的。问她孩子是谁的,她一会说自己跟着前夫生的,一会又说在火车上拾的。翻来覆去,就说自己姓赵。”
母亲不再言语。后半夜的雪夹杂着大风,屋外的枝条发出恐怖的嘶叫。
第二天,我还在被窝里睡懒觉。圣庭爷就在门外叫开了:晌午来喝酒!接着,圣庭爷又到其他人家门口喊了同样的话。
太阳偏西,父亲醉醺醺地回家,然后,打发我去买了蜡烛和电池。
待我回来时,他找出了手电、矿灯和马灯,还把门口的储藏室收拾了一番。我还注意到,圣庭爷的另一个邻居、老族长圣清爷的家门口,多了一处窝棚。
圣庭爷家门口挤满了抽烟的劳力,村长和圣清爷正在点名。父亲说,圣庭爷的新娘子想逃,村里人决定轮流站岗。每天四个汉子轮值,分别驻守我家的储藏室和圣清爷家的窝棚,每人守半夜。
圣唐爷和圣庭爷不住地给汉子们散烟,嘴里还念叨着些好话:爷们辛苦了,开了春,说啥也得买猪摆一场。
傍晚时分,霞奶奶和儿媳妇抱着孩子从圣庭爷家出来。随后,新娘子咆哮着冲出了院子,几个妇女和男人迅速把她拖走。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孩子一隔开,看你往哪去?”圣庭爷来了精神,冲着自家的院子又蹦又跳。
“别说了!这孩子她不一定当回事。”霞奶奶抿着嘴,恨恨地说,“你看瘦成啥样了。哪有这样当娘的,心太硬了。”
霞奶奶刚走,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女婴虽不是圣庭爷撒的种,但长在自家地里,没外人收走的道理。
在冬天,帮助霞奶奶下菜窖和红薯窖(下,方言,指钻进去取东西),是村里孩子们最在意的事情。这意味着可以在她家一顿免费吃喝,还能拿到零食。
每天日头偏西,值岗的男人们就带着自家的孩子来到圣庭爷家门口。霞奶奶会拿出炒好的南瓜子、花生或者瓜子。接着,便是霞奶奶拿手的红烧狮子头,一口咬下去,满嘴油汪汪。
至于圣庭爷的新娘子,几乎没出过门。
“透他娘,她是皇后娘娘呢,外面还有人站岗。”即便圣唐爷和圣庭爷兄弟竭尽所能地招待,寒风中守夜的人还是免不了牢骚。
但出了正月,男人们不再站岗了。
新媳妇似乎认命了,她开始和老水井的女人们打成一片,剪鞋样、挖荠菜,样样不落。
女婴也恢复了元气,在妇女们奶水的滋润下,她已经能站起来。看着蹒跚学步的女儿,圣庭爷乐滋滋卖了五口袋玉米,买了一头大白猪,兑现了冬日的诺言。
杀猪那天,喝红了脸的圣庭爷说,“新麦子下来前,一家三口只能吃棒子面啦。不过能留住女人,这猪杀得值。”
过了端午节,老水井的麦子黄了。各家各户磨快了镰刀,备好了干粮和晒场。
那一年午季(夏季),雨水特别足。村里仅有的几台拖拉机下不了田,男人们踏着没过脚面的雨水,把麦子一捆一捆地挑回晒场。
王赵氏——自从来到村里,人们都这么叫圣庭爷买来的媳妇——也跟在圣庭爷后面挽起了裤脚,挥舞着镰刀。
村里的男人见了,免不了抱怨自家的女人几句。从此,王赵氏又有了勤劳的名声。
收罢麦子,环环已经会开口叫爹了,圣庭爷专门给王赵氏买了身新衣服。
飘荡半生的圣庭爷,终于在人前人后能挺直了腰杆。“洗洗补补的有人管了,里里外外有人操持了。”不止一次,圣庭爷流露出对女人的满意。他还说,收了秋,就跟着女人回娘家。
老水井的秋天很快来了。
与午季不一样,秋收是漫长的——芝麻、大豆一发黄就得开镰,不然就得炸壳,黄澄澄的豆子、白花花的芝麻,万一掉进土里,就成了野兔、麻雀的口粮。然后是收红芋,老水井背靠澥河,只要一涨水,红芋就要遭浸渍,人畜都无法入口。最后是收玉米——棒子在秸秆上越久,玉米粒儿就越干。
收红芋的工序最复杂,最耗时。不只要刨出来,还要切片晒干。窖藏的只是小部分。往往这时,庄稼汉要在田头搭起窝棚,备上锅碗瓢盆。
王赵氏来到老水井的第一个秋天,她用红芋秧(喂牛羊的绝佳青储饲料)为代价,把环环托付给了霞奶奶。然后,跟着圣庭爷挤进了窝棚里。
圣庭爷家的那块红芋地,穿过机耕道便是军转农场。上世纪90年代,农场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干脆把田块承包给附近村庄的少田户。
与圣庭爷家相邻的那块地,承包人是东村的六毛子。六毛子有五个哥哥,兄长们早已成家另过,把田产分得精光。
红芋片快要晒干的那天,粮站的大卡车进了村。圣庭爷和王赵氏卖了大豆和芝麻,算账没有再麻烦我父亲,因为王赵氏的口算速度,直逼村里的数学老师。
后半夜,圣庭爷拎着铜锅叫醒了全村人:王赵氏丢了,后半夜没的。
圣唐爷和圣清爷打发了三路人,一路沿着澥河上几座桥向北,一路到附近的矿区,一路沿着官道往南,“要到车站里头翻,往细了找。”
午饭时分,三路人全部回来了。他们摇着头叹息,女人是走远了。
在圣庭爷杀猪一样的哭声中,众人知道,女人卷走了秋收的大部分成果。
“算了,就当花几千块买个闺女吧。”圣清爷安慰完,众人只好各自走开。女人找不到了,日子还得过下去。
● ● ●
天刚擦黑,圣庭爷的堂姐颠着小脚进了村。她嫁到东村已经近30年,进了村直奔圣清爷家。
晚饭时分,碗还没端起来。大喇叭里传来圣清爷的声音:男人们到我家集合,出捻子!
提起老水井的“出捻子”,方圆几十里一听就头皮麻。
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说白了,其实是全村男丁上阵的集体械斗。通常,只有四种情况才会出捻子:抢女人、抢地、抢水、嫁出去的闺女在婆家被欺负死了。
十六岁上下的劳力全挤在圣清爷家门口。他站在磨盘上说:圣庭的女人跟着六毛子跑了,咱们得按规矩办!大家听号令。圣庭,你狗日的不能熊。就是这,老婆田地不让人!
后半夜,六毛子被人抬着进了村,捆在了圣庭爷院子里的栎树上。听大人们说,六毛子家里除了他和爹娘,就没个活物。但邻居们都证实,他的确领了个女人回来。
“我跟你大(爸)说过,什么时候把人(王赵氏)送来,什么时候送你回去。三天人不送来,放了你的血!” 圣庭爷用杀猪刀的刀背敲打着六毛子的脚踝骨,后者的叫声已经没了人腔。
警察来了,是六毛子的父母引来的。王赵氏也来了。
圣庭爷拎了鞭炮,却被警察按在地上。圣唐爷和圣清爷拨开人群,说:都是我们干的。
那晚,村长家的电灯亮了通宵。天亮后,六毛子被接了回去,王赵氏留下了,但圣庭爷和圣清爷进了拘留所。
之后的一个月,隔着院墙,能清晰地听到女人的啜泣。圣庭爷没有打她,也没有谩骂。他的头发开始白了。
村里人骂他怂。毕竟,卷着家底养汉子,是老水井最忌讳的事情之一。放在本地姑娘身上,婆家人往死里打都没人敢伸手。
渐渐地,王赵氏不嚎了。除了上厕所和农忙,她再也不出门。
1997年初夏,王赵氏突然发福了,她怀了双胞胎。在玉米杆没过头顶的季节,她那圆鼓鼓的肚子,像是打磨好的石磙。走起路来,一摇一晃。
上了年纪的女人见了就是一阵“啧啧”声,背地里,都在骂:狗日的圣庭,老了老了还打双炮哩!
收完红芋,晒干玉米,王赵氏流产了。说是扛麻袋累的,但怎么扛的,没人看见。
孩子没保住,圣庭爷哭红了眼睛,把女人送到县城做手术。但谁也没想到,半个月后,满脸污垢、衣衫褴褛的圣庭爷,被县公安局的车送回老水井。
警察说,在县城,王赵氏第三天就逃了。这一次,她卷走了圣庭爷三年来的积蓄。警察又说,女人极有可能是有预谋的流产,“这女人,精得很,到徐州就换车了。”
带头警察说圣庭爷是个“憨X”。他们询问了,圣庭爷早就知道女人是“放鹰的”。只是,女人的丈夫没有按计划在三天内把她接走,所以她才待了三年。
“就这还替她求情呢,人都不跟你一个心。”
警察宣布了对圣庭爷的处理结果:因参与买卖人口,本应重罚。但案件没有完全侦破,又考虑其家庭贫困、女儿无人照料等实际情况,暂不移交起诉,交给村干部严加看管。
临时走,民警们丢给环环一把水果糖,并跟圣唐爷交代:给你哥弄点吃的吧!沿着铁路步行到了徐州,身上没一分钱。
第二天,圣庭爷带着环环来到澥河滩上。他们燃了一堆旧衣服,全是王赵氏留下来的。
在老水井,只有逝者的衣服才会被烧去,又被称之为“烧旧”。王赵氏虽然没有死,但已经跟死了的人差不多。烧完,圣庭爷又让环环对着灰烬磕了头——这是子女跟逝去长辈的告别仪式。
此后,除定期去派出所打听案件消息外,圣庭爷便闷在家里。杯中之物,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伴侣。
酒喝坏了他的胃,他死于醉酒后的胃出血,尸体被发现时“浑身酱油”。
给圣庭爷穿寿衣时 ,有人在他口袋里翻出了几张全家福和王赵氏的身份证。
看着照片,圣唐爷揩着鼻涕说:何必呢?早听我的,你就不会死。
编辑:朱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