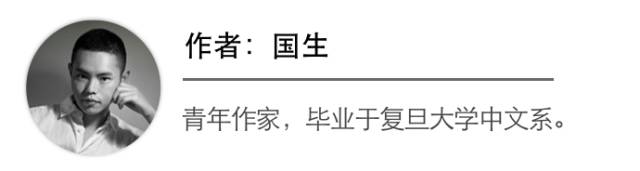图 | VCG
后来我想,我应该拉开车门下去,并且让爸爸也下车,然后就在这个山谷边,好好谈谈。我觉得我应该趁着火气上来,告诉他,你也该长大了吧?
那天傍晚,上海下了这个夏天最大的一场雨,我下班走路回家,到华山路淮海路口时,雨裹挟着热气浇了下来。我搂起装了电脑的书包,飞快跑回了家。
洗完澡,看到来自妈妈的未接来电。我坐到阳台上,回拨她的电话。
我有时会害怕她打来的电话,害怕那些突然降临的抱怨,害怕她要求我和爸爸、弟弟谈谈。有时我会想,我对于她来说,是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你什么时候回家?”她问。
“最迟九月中旬吧。”我说。大学毕业后,我得回家迁户口。这件事我从六月就开始说,一直拖到夏天快结束。
“能早点吗?”她问。
“我要出差。”我对她说过很多次出差,比如去年过年,我说要去北京。事实上,那会儿我连实习工作都没。我在空荡荡的上海待了整个春节。过年前,趁超市还有人,我买了一冰箱的食物。年三十那天,我与一个从台北回来、赶不及回家的女同学高高兴兴地做了一顿难吃的饭。
“你爸……病了。”妈妈说。“医生说他肾有问题。”
“哦。”我几乎有些漠然。“怎么回事呢?”
“他今天才告诉我的。”她的声音很平静,过了几秒钟,我却听到啜泣声。
妈妈在电话里讲得很不清楚,她说,你爸告诉我这些时,像交代后事。我问她有没有看过病历本。她说只有一本体检报告,但是她看不懂。我忍住责怪她的话,毕竟这种时刻,我首先需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既想立刻弄清楚,又希望自己根本没有打通这个电话。
我定了票,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出发。然后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半年里给他打的第一通。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不错,身体、生意。他似乎在睡觉,说话时重重地呼气,听上去很累、虚弱。我忽然想到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给我打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他通常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消息。比如某个人摔进了搅拌机,当场死亡;某个人得了癌症,第九天的凌晨走了,死的时候睁着眼睛。我认识那些人的儿女,与我同届,或者大一届。
而我自己选择报喜不报忧。我告诉他,我出了一本书,这是我头一回和他说起这个事情。他很高兴,说,我告诉别人我的儿子是个作家,别人都不信。我说,我用笔名写作。他没问我笔名是什么。他并不关心我到底在写什么。
第二天晚上八点多,火车到站。山里的小站,望出去一片黑茫茫。在上海时,我常常希望能有个机会看到山里的星空,在那条毯子般厚重的银河带下走路,可惜这几天都是阴天。在出站口,我看到他,似乎没变,又似乎老了一些。他好像喝了点酒,脸庞黑红。
我们一直没说话。车子上高速公路后,他说,星期六要去合肥,有个饭局。自从在合肥买房后,爸妈一直是镇上、合肥两头跑。我说我也去。他夸我终于懂事了。以前我从不参加他的任何饭局。
车子开进小镇,两边的路灯都关着。我印象里,镇上的路灯是天黑时亮,持续两个小时。我们到了。我拎着行李,看着他拉开卷闸门,熟悉的刺啦一声,在晚上格外刺耳。他就是做这个的,但从来没想过修一下。家里楼顶的窗户也是,这么多年,从没安上一块玻璃。以前过年回家,即使开着空调和电暖炉,也还是冷得发抖。
妈妈做了夜宵,我一口也吃不下,喝了半小碗稀饭。我说,我现在吃素,对身体好。其实我只是觉得晚上吃多了会变胖。爸爸吃了不少,一直在吧唧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这种声音特别敏感。妈妈热闹地说着话,嗓门大得让我耳鸣。
爸爸洗澡时,妈妈进了房间。我问她,体检报告在哪里。她说在车上。她让我今晚别提这事儿,明天再说。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你一直不信迷信。但有些事真的很准。”她说。“去年过年,对门小夏帮我问了她大嫂,说是你爸今年有大灾星。正月十六,我跟她跑到江苏泰州——她大嫂嫁过去的,她大嫂说,别说挣钱,你家当家的,今年只要不死,就是你的福气。”
她哭了。这让她看起来格外苍老。
“我求了一张符,塞进香包,挂在你爸车前面。”她说。
“你别怕。”我不知道能再说什么。我以前老有这种联想:很多年之后,他们彻底老了,五官皱在一起,只能坐在小矮凳上,靠着墙根晒太阳。我隔着家门口那条尘土飞扬的街道看他们,却无法在想象中穿过那条走过无数次的街道,到他们的身旁。
第二天,我们去山上大伯家吃饭。堂哥一家都去石家庄买了房子,临走前,把老屋扒了,给大伯和大婶盖了三间砖房。
吃饭时,大伯说,砖房住着真不习惯。他喝掉一小杯白酒,龇着嘴巴又说,他在石家庄批发蔬菜,每年能挣不少。我爸说,孩子们都长大了。大婶一直没说话,坐在一边默默看着我们。她一向这样,少言寡语,年轻时总挨大伯的打骂,孩子出门打工后才好了些。
父亲和大伯彼此也不相劝,一杯一杯地喝着白酒。下肚时,都是一副肝肠寸断的表情。
饭后,爸妈陪大伯大婶聊天,我独自走到车里坐着,翻了手套箱、挡光板,最后在副驾驶背后的袋子里找到体检报告,厚厚的一本册子。我翻开它,从第一页开始看起,血检、尿检……我发现其实我也看不懂。彩超那一页,写着各器官的描述,我找到肾脏那一行,“双肾轮廓清晰,形态大小正常,实质回声均匀,集合系统不分离,右肾皮骨髓质分界清楚,其未见异常回声。”
我轻轻地喘出一口气,然后将血检、尿检的结果拍照发给一位曾得过肾病的朋友。他告诉我一切正常,别担心。随即又说,就是血尿酸有点高。我问什么意思。他说,其实也没什么,中年人爱喝酒、爱吃大鱼大肉,都会这样。
我把妈妈叫出来,在山路边转告了她,她点点头,茫然又渴望地看着我。
“我是个没主见的人,我必须得依赖他。”末了,她说。
● ● ●
她进屋后,我沿着水泥路往山上走了一截,在一个开阔的坡上俯视山下,天阴着,远方的山都罩在雾气中,目力所及,都是一种黯淡的灰色。我点上一支烟,闻着山里的湿气。转头时,我看见了奶奶的墓碑在一个更高的坡上。
我没有走近,那条小道早已被齐人高的蒿草盖住,隔着二十米的距离,隐约能看见花岗岩上的痕迹。我知道上面写的是:“先妣某某之墓,孝子某某立。”
奶奶是三年前自杀的。
一点多,爸爸非要下山,有人找他打麻将。妈妈劝他睡一会儿,他没说话,硬是把车子从岔路上倒到大路上。妈妈坐在副驾驶,让他开慢点,劝了两次。我觉得他有些不高兴。
我望向窗外的景色,之前被云雾遮住的山峰逐一显现。我在这些山里长到五岁,但不知道其中任何一座的名字。许多向阳的山坡被开发成田地,这会儿稻子还是青色,我心不在焉地想,秋天都快来了。
突然,车被急刹住。我没有系安全带,身体随着惯性撞上副驾驶座位。跌向前方时,我脑海中出现的是“青黄不接”这个词语。立刻又想,那些究竟是麦子还是稻子?大概是在察觉到疼痛时,我才透过挡风玻璃往前看了看,前方视野开阔,竟没有雾气,一丝吊诡的阳光刚好投在对面的山壁上,下方是一片地势平坦的山谷。我们稳稳地停在一个大拐弯边,前轮已滑到水泥路之外。
我握住车门把手,想拉开车门下去。我听见妈妈嚷了几句,然后车子又倒回水泥路上。接下来谁都没谈这件事情,车子开得很慢,最终平安抵达镇上。
后来我想,我应该拉开车门下去,并且让他也下车,然后就在这个山谷边,好好谈谈。我觉得我应该趁着火气上来,告诉他,你也该长大了吧?
● ● ●
那晚我们谈了一会儿,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看了你的体检报告,也给懂这个的朋友看过,没事。他忽然就抹起了眼泪,什么也不说。我一项一项把我知道的全解释给他听,叮嘱他最要紧的是生活习惯问题,饮酒导致血尿酸指标偏高。
他仿佛没听到我说什么,固执地告诉我,他的身体不出五年就会垮掉。又说,这样也好,至少没死在外面。我无言以对。只好又絮叨地重复了一遍那些生活习惯的说法。
之后又有几个饭局,镇子上,以及去了合肥。席间他兴致都很高,在合肥时尤其。听到别人夸我有出息时,他几乎失态地咧着嘴点头。我知道,他又喝多了。但这次我非常配合,用饮料敬了几杯酒,说了一些好听的话。我知道他在乎这个。
饭局结束后,我们走路回家,他几乎走不直,啰嗦地重复着:儿子的光荣,就是他的光荣。只要这个家族有兴旺的希望,这一切都值得。我却不停地想起,高中有一次与他吵架,给他写了一封信,结尾是:不要对我有所期待,我只想潦草地成长。
离开合肥的那个早上,我陪他去中医院看了专家门诊,医生开了一点除湿去寒的中药,我抢着付了钱。回家的路上,他指着一家装修豪华的酒楼,说要带我吃饭,我说别乱花钱,快回去吧。其实我只是不知道和他面对面坐着时,可以说点什么。
下午,他送我去火车站,我过了安检,看见他在外面使劲地挥手,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他好像在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清楚。
我一上火车就睡着了,没有做梦。醒来时,我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我在脏兮兮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那张年轻的脸因为眼袋而显得格外疲惫。我忽然想到,这一切都是迟早的事情,有一天,他会搞砸一切。
我们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