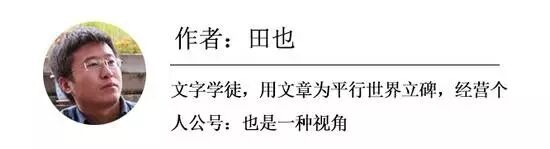电影《 一句顶一万句》剧照
“人长得越好活得越好,猪长得越好死得越早。”在杀了无数头猪,看了无数次临死前猪的双眼之后,三叔是懂猪的,尤其懂一头行将死去的猪。
三叔是个杀猪的,高鼻梁、大眼睛、双眼皮、深眼窝、串脸胡,身高一米七开外。
早在九十年代初,三叔就开始在村里穿西装、穿皮鞋了。不似影视剧里刻画的五大三粗形象,到了三叔这一代,几乎很少有张飞一般的糙汉,提着大刀,见猪就捅的杀猪人了。
虽然身上带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原始江湖气,但到底算不上武将,杀猪也不过就是个手艺。
三叔入行没有师傅。我爷爷不是杀猪的,爷爷的爷爷也不是,机缘巧合,自学成才,反倒还成了一位闻名乡野的杀猪人。
爷爷是个种田人,从小教给三叔也不过就是“麦子收了种玉米,玉米收了再种麦子。”
这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杨摩西完全不同。杨摩西延续了老一辈手艺人入行的各种规矩,是一个讲江湖道义的杀猪人——就像以前的藏族手艺人,老子是银匠,儿子才能是银匠;老子是行刑人,生下来的才有资格送别人上黄泉。
一开始,三叔就是个猪贩子,开着柴油三轮车四处奔走,收膘壮的猪,再转手卖给屠宰场。三叔很精明,也很爱他的事业,很快就开上了屁股冒烟的铁家伙,并且实现了五年换两辆的伟大壮举。
那时候我还小,立志长大了也要和三叔一样,当一个猪贩子,开着柴油三轮,扯着嗓子,走街串巷。
后来,三叔贩猪回来就不再去屠宰场了,有了杀猪的手艺,他开始将一车猪拉到后院,自己动起手来。
猪的“刑场”很简单。地上挖个坑,上面架起一口大锅,锅旁边撑一个比人高一头的木架子,架子上挂两根拇指粗的铁钩,下面摊一个两平米见方的水泥地。
“人长得越好活得越好,猪长得越好死得越早。”在三叔那里,这是我从小就学会的道理。
人有人命,猪有猪命,虽说都会死,但死法却完全不同。
虽然忘记了第一次看三叔杀猪的具体时间,但我却能清晰地记起整个过程。很奇怪,第一次看三叔杀猪,我没有害怕,等真正看到杀猪会害怕,则是在混迹江湖的多年之后。
三叔杀猪一般在冬天,腊月最多。那时候,杀猪在农村算是一件极具观赏性的娱乐活动,每次杀猪,村里人都会里三圈、外三圈的围着三叔。来的人有时也会帮三叔打打下手,完事后讨点猪下水,聊以丰富常年难觅荤腥的饭桌。
● ● ●
猪死后,三叔用铁钩子将猪倒挂在木架子上,猪头耷拉着,鼻孔朝下。这时,三妈将锅内的水烧开,倒到一个大桶里,三叔站在凳子上,从上往下将开水浇在死猪身上。
重复几遍后,三叔挥起一把弯刀,开始刮猪毛。刮猪毛是个费力气的细活,好在三叔动作熟练,十分钟后便落得一地雪白。刮完猪毛,换一把利刃,准备开肠破肚。
在猪脖根处一刀刺入,自上而下将猪肚子破成两半。这一刀的力道和深浅是有讲究的,全靠手劲控制,刺得太浅不能破开肚子,刺得太深会划破五脏。
这时候,三叔会在猪下面放一个干净的盆子,盛放流下来的猪血。三妈将这一盆新鲜的猪血做成血包(血旺),再切成薄片,放上香菜、蒜末、辣子油,拌成凉菜。等后来三叔不再杀猪,三妈的血包就成了令我回味一生的美味。
放完猪血,三叔小心翼翼地取出猪的内脏,拉出猪下水。猪下水原是可以卖钱的,但三叔每次都会把下水分给在场的村民。“这个给虎子、二牛,拿回去让你婆娘好好拾掇拾掇,喝酒吃美得很。”
在所有猪下水中,小孩子最喜欢的当属猪尿包了。三叔每次都会把猪尿包留给我和堂哥,用开水烫过后,洗干净,便成了一个天然的气球。猪尿包可以吹得很大,能一连把玩好几天。
发完猪下水,三叔将猪从架子上抱下来,放在案板上,切下猪头,从猪背上再划一刀,一头活猪便变成了两扇肉,赤条条摆在面前。
三叔凭借着职业杀猪人的专业素养,认真地送每一头猪上刑场,以艺术家的心态刮毛、开膛。三叔用刀子敬畏猪,我敬畏三叔。
一次,有一头猪在被三叔捅了一刀后,没死,翻起身子,拔腿就跑。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头神猪,是一头不能杀的猪。可三叔心里明白,在杀了无数头猪,看了无数次临死前猪的双眼之后,三叔是懂猪的,尤其懂一头行将死去的猪。
那头猪绕着村子跑了一圈,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拖着自己的身体,在所有人面前完成了一辈子也没有过的表演。三叔这时候才不缓不急的上前去,结束了他的生命。
看了三叔杀猪,我就用叉子叉青蛙,蹲在土墙角抓蛇,学着三叔的样子,把青蛙和蛇钉在树上,剁头、剥皮、开膛破肚,觉得这是成为一位杀猪人所必须的历练。以此引以为豪,乐此不疲。直吃到最后发现自己走路都能蹦蹦跳跳,趴在地上也可以像蛇一样蠕动时,才心有胆怯,金盆洗手。
如果细想起来,也有另一个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一个叫做“悲悯”的词走进我的意识之中时,我便不再吃青蛙和蛇了,甚至看到就会害怕,接连着能难受好几天。后来,机缘巧合在成都的文殊阁受了“八关斋戒”之后,连肉都很少吃了。
即便这样,我还是很怀念儿时目不转睛、一遍遍看着三叔杀猪的日子。
● ● ●
世纪之初,三叔不再杀猪,走南闯北做起了生意,经常到了年三十才回来。
那时候,我已经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几何了,最喜欢的还是听三叔讲故事,听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生。
三叔小时候学习好,本可以上大学,第一年高考差了四分,补习了一年还是差四分。后来由于家里孩子多,爷爷负担不起,三叔便放弃了,开始出来自己闯荡。
三叔高中时是住校,每个周末回来,奶奶都会给三叔做包谷面馍,返校时,三叔背着一兜子黄面馍馍,和城里那些有钱的孩子换白面馍馍吃。就这样,三叔做了三年的馍馍生意,吃了三年的白面馍馍,成了村子里最幸福的孩子。
辍学后,三叔通过杀猪结识了邻村的安庆和铁狗,三人常开着三轮出去,再拉着一车猪回来。
后来安庆不再杀猪,收起了粮食;铁狗还干着老本行,开了一家屠宰场,不光杀猪,牛、羊、狗,只要是喘气的、能挣钱的都杀,生意很好,很快就开上了小汽车。
不过,人活的长短和杀过畜生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三叔终究还是死在了前面。
老家人都说因果报应,可谁也没曾料到,三叔杀了无数猪,为儿读书却要了三叔的命。
那年堂哥高考失败后,决定再考一年,三叔听后,二话没说,托人给堂哥联系了个补习学校。学校在西安,在省内很有名,学费五位数。
“要不算了,还是回以前的学校吧,这儿学费太贵。”堂哥怯怯地对三叔说。
“别废话,钱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你的任务就是给我好好弄,明年考个名牌大学。”
三叔希望自己的儿子以后能靠着舞文弄墨养家糊口,走南闯北的日子实在是太难了。为了能常去看望堂哥,三叔卖了早已破烂不堪的三轮车,不再继续闯荡,安分地去市里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民工。
没多久,三叔就出事了。后来听三妈说,出事那天,三叔自己似乎已有预感,早上起来时左眼皮就莫名地狂跳,人也心神不定。果然,那天下午三点就收到了工友捎回的噩耗,一家人赶到医院时,三叔已经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了。
当天晚上,三叔就走了。
为了和施工方谈赔偿事宜,一直没有发丧,就这样三叔在医院里又躺了半个多月,最后在中间人的调和下,施工方赔了15万,三叔的尸体这才被推进了太平间。
出殡那天,村里人带着堂哥、堂弟、我去了医院。工作人员把三叔推出来时,雪白的布蒙在上面,严严实实。村里人抬起三叔,放进提前带来的棺材里,四处哭成一片。
三叔的眼窝、脸蛋、嘴唇已深深陷了进去,魁梧的身子也缩成了孩子般大小,不大的棺材漏出一大片空白,村里人用三叔生前的衣物塞满后,拉开了我们,盖上棺材盖。
回来的路上,没有人说话。我每每想回忆起三叔生前的样子,总会被泪水打断。三妈像被抽了魂一样,瘫坐在炕上,一面还不住地安慰我:“我娃不哭,我娃不哭。”
那天晚上,村里的戏班子免费在院子里给三叔唱了戏,《苏三起解》《苏武牧羊》《铡美案》《三滴血》……我第一次觉得老陕秦腔是那么的高亢、有力,又充满悲凉。
守灵的那天晚上,我陪三叔坐了一夜,没有害怕,也没有哭,只是按照父亲的嘱咐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拴在放棺材的椅子腿上的公鸡,看着画着神仙、猛兽、祥云、二十四孝图的灵堂装饰布。
老家有个风俗,孩子没成人的壮年人死后是不能立碑的,因此三叔的坟墓只有一堆黄土。把他的一生都压在了下面。
即便是在此时,我依旧敬畏他。
● ● ●
后记:
三叔死后,三妈带着堂哥、堂弟过得很好。
堂哥毕业后进了某省级事业单位,堂弟去山西做了工程监理,三妈也渐渐发了福。三叔的土堆在吸收了多年的雨水后,变得十分厚实,长满了青苔和蒿草,仓鼠也在上面打了洞,和三叔住在一起。
前年正月十五,我去看了三叔。拿着白纸折好的一个简易灯笼,中间点上蜡烛,插在三叔的坟头,烛火微弱,却很暖心。烧完手中的纸钱,扑灭残存的花火,转身离去。
编辑:任羽欣